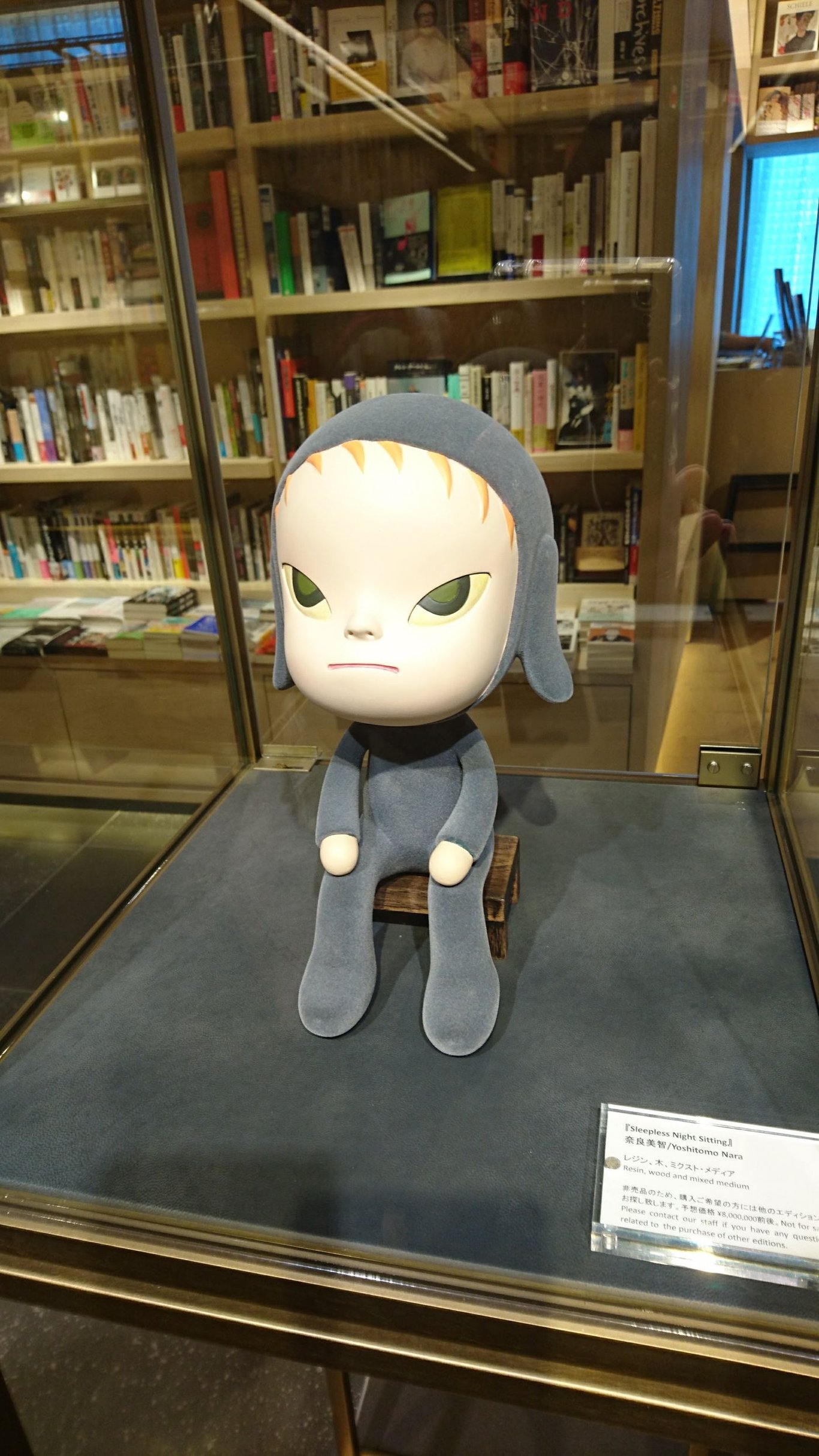失語的一代
“很抱歉,我這戴著太陽眼鏡,剪片剪得眼睛不舒服,大夫交代要戴著..”
那天去了中山堂看「風流一代」,開映前主持人請賈樟柯先說幾句話,他接過麥克風後就這麼解釋著。
“大夫”,他剛真的說“大夫”?不知為何,我腦內的小劇場開始演起了大驚小怪的戲碼來,“好老派,好有意思”,“多說些吧,我就是為了要聽你說話才來的啊”,“近幾年,你有甚麼忍著不說的,多說一些吧”。
他沒多說,客套寒暄幾句後,燈光隨即暗了下來,前方戲台開始熱鬧了起來。
我說的熱鬧是真的像廟會搬戲(puann-hì)那樣熱鬧,而那戲台,就是戲台,沒有被螢幕框住的戲班野台。
電影一開始,幾位應該是剛下了班的婦女,擠在一個簡陋的小休息室裡,說笑地拱著彼此唱歌,五,六分鐘的歌唱,穿插著幾句聽不懂的方言,加上那個本就不是專做電影放映的中山堂舞台,讓人頓時忘記正在看的是電影,框住這些婦女的螢幕消失了,我正看著的不是風流一代,而是站台裡唱著歌的文工團。
我並不喜歡風流一代,或更具體的說,我不喜歡不說故事的賈樟柯,在映後簡短的訪談中,賈樟柯是這麼解釋他這次的創作的,"這電影的開始是因為千禧年那時,全球化開始影響中國,我想要紀錄那種熱鬧的氛圍,與在那樣急速變遷下,人的命運起的變化。"
他本也就打算這麼隨性地拍個兩三年,將紀實與虛構結合創作出一部作品來,可就這麼隨性地就將時間的跨度拉長到20多年,從本來的千禧年,全球化,拉到了數位科技日新月異的AI時代,跨過了3年疫情,也踩進了現今去全球化的新世界。
"你們不覺得現今的世界變得越來越沒有因果邏輯,像量子物理一樣,越發複雜,不確定,難以描述.."
因此他用碎片化的影像堆疊成一部作品,不再如過往一樣講述個有因果的故事,他甚至讓戲裡的趙濤從頭到尾都沒說半句台詞,他將本來電影中該有的那些全交給觀眾,他讓我們自己把那一幕幕,不太連接,碎片化的場景拼湊成我們心中的故事,他將趙濤在那表情下該說的話,讓我們自己去思索該放進怎樣的字詞。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對於現今的這個世界,這個人人接收著碎片化資訊在網路裡大鳴大放的世界的一種抗議。
只是,我終究是個老派的人,喜歡聽人好好地,完整地講一個故事,我甚至很討厭那些所謂的開放式結局,好吧,也許我不是老派,我只是缺乏想像力罷了。
其實,從山河故人之後,我就不怎麼看賈樟柯的電影了,要說原因,該是因為自己心裡的彆扭情緒使然吧,總覺得在中國當局對藝術創作者愈發嚴苛的審核環境下,為何他跟他的作品還能好端端的存在,為了怕自己面對往後突如其來的失望,我就打住不再看了,直到有次在matters上看到了無法說起賈導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我對無法的文字是沒抵抗力的,這才又默默地去找了來看,然後也是因為看了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對賈樟柯的戒心放下了一些,這才有了這次的觀影紀錄。
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工作的時候特別拒絕幾種東西,一種是對正在發生的東西和正在面對的人進行價值判斷;另一種是對自己投注的感情進行類型化,譬如我是歌頌它還是批判它。
在拍無用時,流水線背後有很多東西,如不人道等等,但對我來說,我拍的不是那種不人道,而是窒息感..我直接拍的是對人的感受,而不是對人的判斷。另一方面,很多大陸導演可能也和我一樣,很難去憐憫這是因為你壓根兒就是他們,他們壓根兒就是你。你怎樣去憐憫自己?
實際上我很難用傳統的經典敘事,比如說一對人物、一條情節線、一個矛盾,然後線性地發展故事。因為在我的生活裡面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同的現實,不同的境遇,它們之間所傳遞的東西甚至有時是互相補充、有時是互相質疑的,我覺得這種結構感是目前的現實生活給我的一個很強烈的印象。我自己每次在構想電影的時候,往往就自然選用了群像、多組人物和版塊敘事的故事結構,透過結構之間產生的關係來把中國現實的複雜性和模糊性呈現出來。我總覺得目前這個存在多種可能性的大陸現實很難用一個封閉的敘事講述清楚。看完海水變藍後,又去找了「無用」來看,當時也順勢看了些賈樟柯的訪談,那時因為有些感觸而存下的這段話,如今引來當作這次觀影的結語也不怎突兀。
中山堂那次本也有安排映後會談,但時間短到只讓一個人問了兩個問題,前後不到10分鐘就草草結束,我心裡的那個問題,就只能寫在這裡了,"關於趙濤從頭到尾都沒有台詞這事,是否象徵著中國人民集體失語,那種失語,不是說完全說不了話,或發不出聲,而是,不想再說話,不想再發聲.."
不過,說到底,我終究只是個在戲台下看戲的人,戲台上正演著的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的角度去詮釋,並由衷期盼著那個世界不會成為我的世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