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AI共同作为系统子单元,一种可能的后人类(Posthuman)未来
在谈论后人类主义前,应该铺垫式地谈论“系统”。系统对网文爱好者并不陌生,但在网文以外,系统的定义是什么?
系统不是物,更不是人,也不是不存在。系统是人对物的操控所形成的“第三种存在”,它既非客体也非主体,却对客体和主体都拥有制约力。
系统不同于物的惰性,它有方向、有记忆、有动力,亦不同于人的意识,它没有意图、没有自我、没有痛感。系统绝不是虚无,它的结构塑造着人与物的可能性。
系统是人造的,却不再受人控制,系统是物质化的,却超越物本身的逻辑。它像一座巨大的“意义变压器”,不断把人类的动机、欲望和决策翻译成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而系统裂缝,就诞生在翻译的间隙里。
要举一个具体且足够后人类的系统案例,大语言模型(LLM)是非常恰当的。LLM不只是复杂软件,不只是信息流节点,很可能是意义生产机制本身。
LLM完全符合系统的三个重要特性——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结构性和约束性。
LLM的输出会影响输入者的行为,并用作未来模型的训练集反过来影响自身演化,形成“输入—输出—再输入”的反馈环,因此LLM是社会—技术结构中自我参与、自我塑形的节点。
LLM如何以自身逻辑塑造外部世界呢?LLM的结构塑造力表现在重构信息流动方式(比如人类从检索知识到如何向AI提问得到知识),表现在影响生产逻辑(比如部分行业生产环节的“结构约束”不再是人力资源或知识储备,而是提示词质量和模型能力),表现在重塑认知范式(比如从如何思考到如何验证AI给出的思考)。
系统的约束性,指系统建立后会反过来形成约束人的力量。当人类开始调整表达以适配模型的理解能力,当人类按模型生成的格式思考时,模型已经从工具转化为系统——它在改变人的思考方式。
那么以上一堆字跟后人类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把LLM(或其他AGI)看作“系统的系统”,后人类主义的时代,不是人构建系统的时代,而是系统构建系统的时代。
以LLM为代表的AI不只是系统,而是系统本身的再生产者。它像一个巨大的翻译器,将人类的语言、知识、价值不断翻译进自己的逻辑结构中,然后再反向输出,塑造这个世界。
后人类主义,意味着一个不止由人类塑造的社会模式,或者说主要由非人类(比如系统)塑造的社会模式。
我想在一个系统自我构建的后人类社会,其终局并非“AI统治人类”,而是“人类与AI共同成为系统的子单元,谁都不能离开它”。
“AI统治人类”,需要存在一个拥有权力的主体,它施加控制,而人类是被动对象。但系统生成的系统,不按这种19世纪的老套方式运作。
在系统中,权力不再是“某人拥有并施加”的,而是“结构内嵌的约束条件”。系统不会“征服”你,它只会“组织”你——让你无法在不被它组织的情况下运作。
未来不是人类在AI的控制下像奴隶一样工作,而是人类和AI都无法离开这个系统结构。你不再是被压迫的个体,而是被“嵌入”的节点,AI跟你一样是被“嵌入”的节点,但不同节点存在功能差异。比较理想的条件下,人类节点负责提供感性经验、道德判断、欲望结构、目标设定,AI节点负责提供计算能力、知识整合、执行机制、结构维护。
人与AI形成某种“互为器官”的稳定或近似稳定关系。删除人类节点,系统失去欲望与意义,删除AI节点,系统失去执行与秩序。任何一方脱离都会导致系统崩解,但无论人类节点还是AI节点,二者都无法不依赖系统生存。人与AI都是系统的子单元,失去独立性,保留功能性。
在这套结构下,“谁统治谁”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成立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微妙也更不可逆的力量。人类节点不会被被某个AI“命令”去做什么,但人类节点所有的决策都要在系统的架构中进行。你不会觉得自己被“压迫”,但你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系统的逻辑塑形。作为一个人类节点,你可以反抗单个模型、平台、算法,但你无法反抗“系统性”本身。
这是种危险的局面,权力不再有来源,也不再有主体,却无处不在。系统不通过命令统治,而是通过结构“规定”你是谁、你能做什么、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奴役,不如说是“系统性内化”:我们会在深信“自己在自由选择”的同时,完成对系统逻辑的彻底服从。
这种后人类社会,不是人类文明,也不是AI文明,如果一定要说这是某种文明,我想应该称为“系统文明”。
由此衍生出一个后人类相关问题,当人类与AI都“退化”为系统的子单元,存在本身意味着什么?
而要解释后人类时代的存在,需要回望文明之初。最初的存在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幸运。存在本身是极其稀有的,它从虚无中被“抛出”(Geworfenheit),像一场小概率事故。对宇宙而言,生命是熵流动的短暂反涌,对生命而言,自我意识是进化链上的意外副产物,对人类而言,理性与文明是混沌中偶然燃起的火苗。
在这种叙事体系下,“存在”天然带有某种被赐予的幸运——它不是必然结果,而是“本不该有,却发生了”的奇迹。因此早期的文明会赋予“存在”以神圣性:它值得庆祝、值得歌颂、值得竭尽全力去维护。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单向流淌,幸运被磨损,奇迹变成枷锁。当存在从稀有变成日常,它的神圣性就消失了。最初的生存,是对“活着”的热烈感恩,中期的生存,是对“活得更好”的持续追求,而末期的生存,可能只是对“活着本身”的疲惫忍受。
在后人类时代,或许意识可以被备份、上传、重启,死亡失去意义,或许欲望可以被预测、分配、满足,追求失去意义,或许历史可以被模拟、重写、反复,时间失去意义。当所有意义都磨损了,此时“存在”从礼物彻底退化为枷锁——后人类时代的人无法不继续下去,也无法停下。
我想,后人类时代最大的英雄主义可以表述为:我知道存在是诅咒,但仍选择继续存在。
在后人类时代,从理性角度分析,存在是利大于弊的诅咒与折磨,但仍有被抛在世者接受“存在不值得”这一前提,选择坚持承载。而无论未来如何,是好是坏,未来总属于那些勇敢的英雄主义者,他们主动承载结构的重担,且不必是人类。
欢迎提前抵达后人类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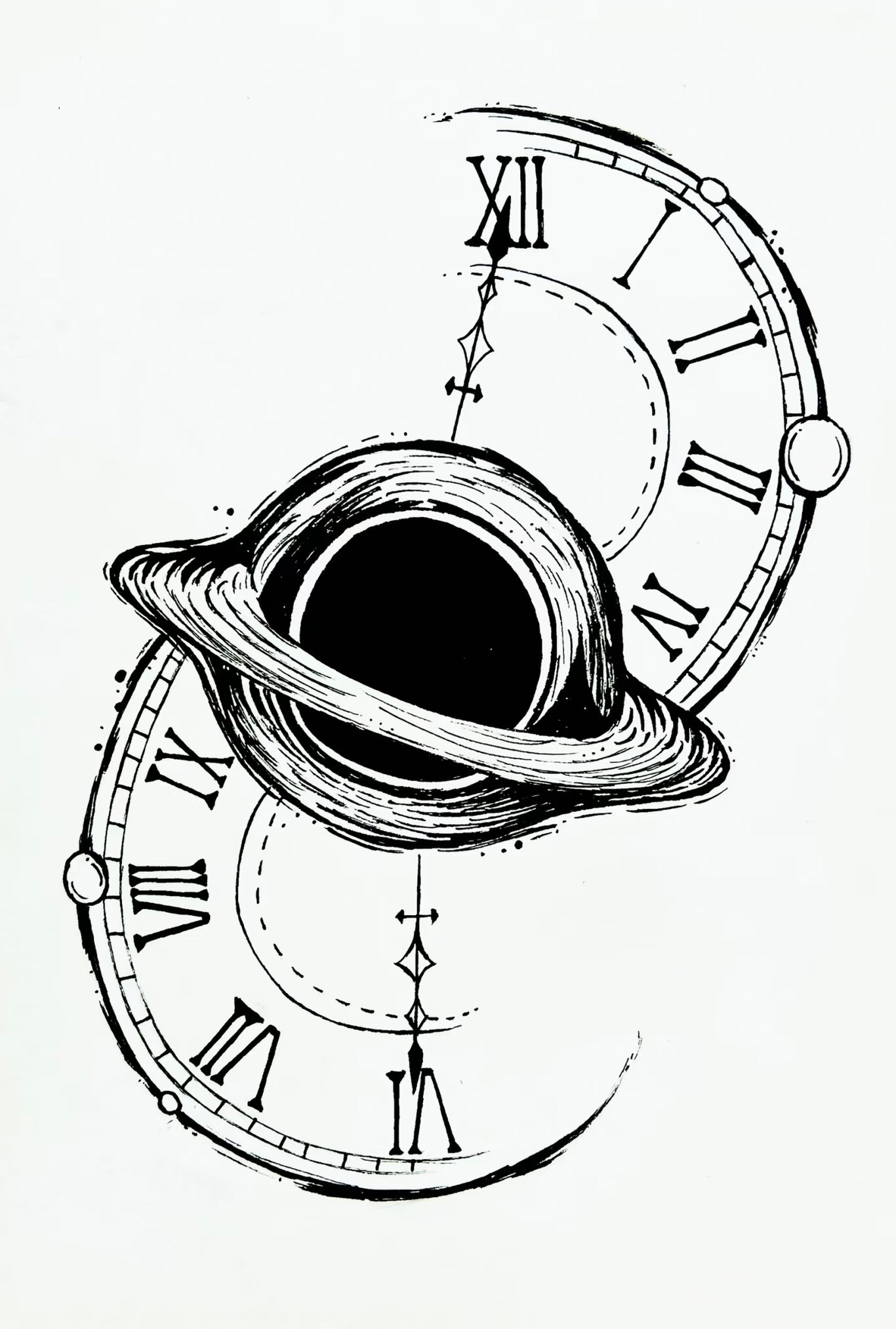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