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能爱他所不知道的,一个人不能知道他所不信的。

托馬斯·阿奎納—閃爍的中世紀理性與信仰之燈塔
趙建敏
提要:中世紀不是黑暗的,至少其理性思考不是黑暗的,而且非但其理性思考不是黑暗的,相反,卻是前所未有光芒四射的。中世紀是人類理性思考的巔峰和燈塔。人類理性由猶思定的艱難起步,到奧思定的蹣跚邁步,再到安瑟莫的自由漫步,之後達到托馬斯的閒庭信步時,理性逐步放射出她本有的光芒, 並達至巔峰。有了中世紀的理性光芒,才有了其後的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工業革命,乃至今日的信息革命和 AI。毫無疑問,它們無一不是理性的創造物。顯然,理性之燈恰恰是在中世紀的探求中不斷地被 擦拭,致使其放射出輝煌的光芒。確而言之,與信仰對立的不是理性,而是畏懼。反之亦然,與理性對立的不是信仰,而是傲慢。故此,剔除畏懼,遠離傲慢,才可以讓人得以安心而處,享受真正的生活。 當然,其關鍵在於如何才能剔除畏懼,遠離傲慢。
1. 中世紀之前的蒙昧與蒙蔽
中世紀不是黑暗的,至少其理性思考不是黑暗的,而且非但其理性思考不是黑暗的,相反,其理性思考卻是前所未有光芒四射的,是人類理性思考的巔峰和燈塔,以至於康德不得不對中世紀後期純粹理性主義走向給予三大批判。中世紀是人類理性之光的燈塔!這燈塔的光芒由聖托馬斯·阿奎納所代表 的經院哲學/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之理性思考折射出來,令人類的精神認知由蒙昧的迷信走向理性的虔誠,令人類心靈之眼目從遙遠的此岸世界就可看到近在咫尺的彼岸神聖之光。在此 fides qua creditur 與 fides quae creditur 之間,藉助經院哲學/士林哲學的縝密思考,經院哲學的哲學家或神學家們,用理性引領人類走出了遠古、中古、近古時代人類理性的蒙昧。這種蒙昧確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也許現在的 迷難,其咎不在事例而正在我們自己。好象蝙蝠的眼睛為日光所閃耀,我們靈性中的理智對於事物也是如此炫惑。」1 這炫惑也正是其蒙昧,詞二意一。故此,經院哲學,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或神學,毋寧說是 一種學習或研究的方法。這種學習或研究的方法就是由更多關注 fides qua(信之此)的歷史蒙昧或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炫惑,通過嚴格的概念分析與定義,利用縝密的邏輯理性之推理,把人類理性的認知推向 一個新的史無前例的高度。就此意義而言,中國傳統文化尚未歷經此「經院哲學」人類理性之洗禮,故此在許多層面仍然身處「人死為鬼,樹久有靈,頑石能言,風雨有主,越是蒙昧時代,越有無物不神無 鬼不靈的泛神信仰」的狀態中。「尤其是‘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的學說完成,上帝成為大封建主的私人宗教,不許臣民僭祀,無形中好像將天主教所崇拜全知全能的耶和華上帝予以有力的限制,中國人的信仰,遂由無中心的泛神發展到無神。」2 如此對比研究,就能更加凸顯出「經院哲學」對人類理性提升的重要意義了。在西方哲學發展中,無論是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氣」、畢達哥拉斯的 「數」、赫拉克利特的「火」,亦或是蘇格拉底的「靈機」(δαιμóνια)3、柏拉圖的「理念」(ιδεα, ειδος)4 或亞里士多德的「四因」5,他們都是對 fides qua 的研究居多,且處於蒙昧或炫惑狀態,6 而對fides quae(信之彼)的研究從未切實進入其中,依然處於蒙蔽狀態。7 對 fides quae 的真正研究要等到聖安瑟莫/聖安瑟倫的純粹本體論論證的出現。8 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應該是在那個時代,Logos並未卓然彰顯出來。在 Logos 成為人而卓然彰顯之後,面對著擁有全然真正人性的 Logos,人類不得不對 fides quae 的 Logos 進行認知與思考。在猶思定/查士丁、奧利振/奧利金/俄利根、卡帕多西亞三教父等教父哲學家或神學家們逐漸釐清了 Logos 的真實認知性之後,聖奧思定/聖奧古斯丁的一句 crede,ut intelligas,9 把 fides qua(信之此)指向了 fides quae(信之彼)的 Logos(言/道/理性)。可以說,這是中世紀經院哲學引領人類之理性蹣跚邁步的開始。之後,有了聖安瑟莫/安瑟倫的 credo ut intelligam,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10的更深入的對理性的探求。crede,ut intelligas(你信,就理解了)與 credo ut intelligam(我信,以求理解)之間的巨大區別,恰如人蹣跚邁步與漫步前行之區別。就此而論,早期經院哲學家或神學家們在 Logos(言/道/理性)的光輝照耀引領下,開始由 fides qua 更多關注於 fides quae 及其兩者之關 系。毫無疑問,真正給予人理性的是 fides quae 的 Logos。對 fides quae 的認識、理解及闡釋隨即成為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主要目標。聖托馬斯·阿奎納成為在此領域閒庭信步的泰斗和燈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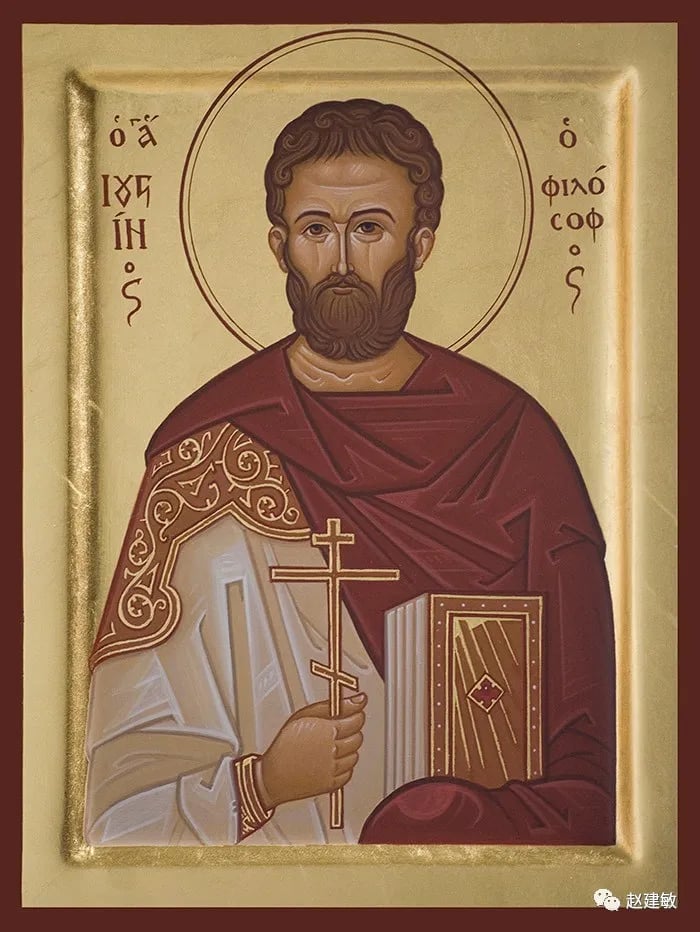
2. 聖猶思定(+公元 165 年):人類理性的艱難起步
早期中世紀經院哲學以聖奧思定為代表。這些哲學家或神學家蹣跚起步,開始了對人類理性的思考之旅。為他們奠定基礎的先聖前賢,即那些早期的教父們,其中以猶思定為代表。彼時的基督徒們, 因為他們對降生成人的 Logos 的信仰,被上至朝廷皇帝、中至哲學家賢者、下至普通百姓等心靈處於蒙昧或炫惑狀態的人視為無神論者。猶如哲學家殉道者猶思定一樣,11 這些基督徒備受極刑的罪名不是對 至上神的信仰,而是以無神論者及褻瀆神明者的罪名被處以極刑的。眾所周知,此時的羅馬皇帝也被視為神明且建有祠廟。猶思定為基督徒辯護說:「蘇格拉底運用健全理性,謹慎考察,竭盡全力祛魅啓蒙,意欲救民於邪魔,然邪魔豈所心甘,借助彼等喜聞樂享罪孽者,將其判罰處死。其罪名即為無神論 者及褻瀆神靈者。彼等冠以蘇格拉底之罪名即‘他宣揚新奇的神明’。 我等基督徒亦被此等人冠以類似之罪名。」12 就此意義而言,他們堅信卓然彰顯之Logos言/道/理性,豈非正是因為彰顯理性祛除蒙 昧,從而如同蘇格拉底一樣而身受極刑嗎?猶思定明確聲稱:「蓋理性之功能實由天賦,乃天主親賜以期勸服導引我人皈依信仰者也。我等以為理性裨益人類,故而不可禁阻其愛智並研習此等知識,甚或理應驅策鼓勵之。借助邪惡之人及諸傾向為惡之人,邪魔惡神意欲禁阻人之理性。然而,人為之法對此無以禁阻設限,蓋 Logos 基督/言/道/理性/乃神聖者也。」13 在猶思定的辯護中,他不僅是在為基督徒所信仰之基督辯護,而且也是甚至更是為人類之理性辯護,因為在猶思定的著作中,他就是在為 Logos 辯護。當然,這起步是艱難的,甚至讓猶思定等眾多基督徒為此付出了現世生命的代價。這幾年學界常常在紀念奧思定、托馬斯、康德等人,事實上推動人類理性艱難起步並為此而付出生命的猶思定更值得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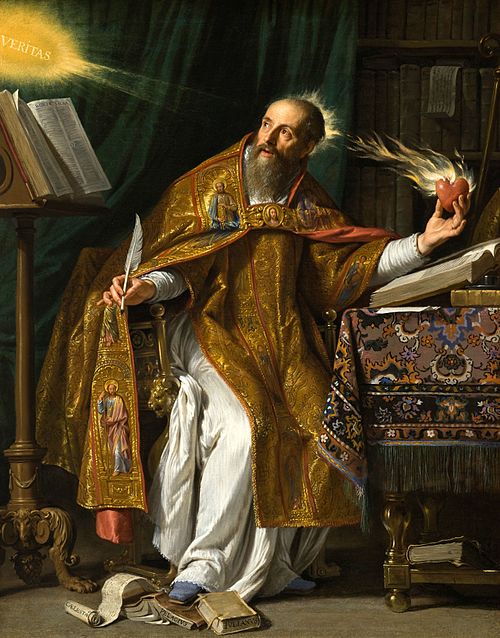
3. 聖奧思定(+公元 430 年):人類理性的蹣跚邁步
聖奧思定的 crede, ut intelligas 引領人類的理性開始蹣跚起步。奧思定的這句話,是在回應人的提問:我一旦理解了,就會相信。這個「理解」顯然是對 fides quae 的理解。事實上,人類對 fides quae 的理解一直處於蒙蔽狀態。這種蒙蔽狀態所彰顯出來的形式就是神話。屈原固有「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的 天問,但卻沒有人追問而解釋之。「盤古板斧開天地」,人們也沒有追問,板斧從何而來(鐵制板斧的 神話必源自鐵器時代之後)。顯而易見,fides quae 仍然處於蒙蔽狀態。對 fides quae,人類仍然處於無知、恐懼(「我在樂園中聽到了你的聲音,就害怕起來。」[創 3:10])、死亡(「人看見了我,就不能再活了。」[出 33:20])、復仇者(希臘復仇三女神)的認知中。究其根本,在於 fides quae 並未完全顯示出來,人類理性尚無法知其究竟。fides quae 究竟是什麼?這要等到 Logos 言/道/理性成為人的時候,才 徹底揭示出來。當然,這個「理解」也涉及到對 fides qua 的理解。因著 fides qua 的蒙昧,人類要麼自高自傲,視己如上帝(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身體我做主),要麼令人自卑自賤,視己如糞土(人命如草 芥,生命如「物流」)。在這種 fides qua 的蒙昧中,無論 fides quae 是蒙蔽的亦或清晰的,人都是無法真正理解的。之所以說,聖奧思定的 crede, ut intelligas 是人類理性的蹣跚起步,在於他並未像聖安瑟倫那樣直接且僅僅在 fides quae 中行走。聖奧思定仍然致力於在 fides qua 中來理解 fides quae,而且這種理解只能是類比的、模糊的、無法達至 fides quae 的本體。14 故此,奧思定認為,把天主/上帝理解為,「善而無質,大而無量,創而無需,在而無所,擁有而不佔有,無所在而處處在,無時間而存永恆,自身無改易而改變所有且毫無匱乏」就足矣。15 無論如何,聖奧思定的 crede ut intelligas 讓人開始邁向理性本身對fides quae 的理解,開始走出 fides qua 的蒙昧狀態,而去嘗試著揭示 fides quae 的蒙蔽狀態。在聖奧思定看來,聖安瑟倫/安瑟莫或許就是他所指稱的「頭重腳輕」的那一類人,「他們努力想爬到勢有改變的受 造宇宙的上面,將他們的思想升高到不變的實體即上帝那裡。不過,他們因受必死性之累而頭重腳輕。」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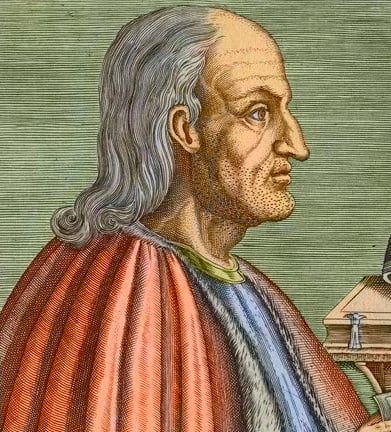
4. 聖安瑟倫/安瑟莫(+公元 1109 年):人類理性的自由漫步
在此,我們先選引一段安瑟倫/安瑟莫理性的縝密邏輯思考:「假若某事物是借虛無存在的,那麼或者是借助自身,或者是借助它物,或者是借助虛無而從虛無中存在。顯然,從虛無中絕不會有任何東西產生。假若有某物是從虛無中產生的,那麼或者是借助其自身,或者借助它物,或者是借助虛無而產生的。但是顯然,從虛無中不可能有什麼產生。然而假若某物是從虛無中產生出來的,那該物或者是借助自身,或者是借助它物而從虛無中來的。但借助自身從虛無中不可能產生什麼;如果真能有這種情況,那麼該物事先就應存在。但該物本身事先絕不存在,因而它決不可能借助自身從虛無中產生。」17 我想,一般人在讀安瑟倫這段邏輯思考時,能跟上安瑟倫此時的理性思考已經很不錯了。18 無論安瑟倫 是「頭重腳輕」亦或是「自由漫步」,他的這種本體論上的極為縝密的邏輯思考,無疑是人類理性的極 大光芒!
無論如何,聖安瑟莫並沒有不顧及 fides qua。他明確聲稱:「我理解也並非為了信仰,而信仰卻是為了理解。我也相信這一點:除非我相信,我就不能理解。」19 聖安瑟莫的 credo, ut intelligam 或者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引領人步入到理性的自由漫步中。安瑟莫被稱為「最後一名教父和第一個經院哲學家」。以安瑟倫為代表的教父和經院哲學家基本終結了人類的蒙昧狀態,並開始揭示人類的蒙蔽狀 態。安瑟倫的本體論論證貌似虛幻縹緲,卻是理性的自由漫步,是揭示蒙蔽狀態的方法。這也是古希臘 三賢從未企及的一種理性思考,是以理性思考理性的一種方式。「一個人本身,當他懷疑或否認這個具 有可設想的偉大的無與倫比的存在者時,這個存在者已存在於他的心中;因為當他聽到別人說這個存在的時候,他就理解了別人所說的對象是什麼;再者,從他所理解的對象來看,這一對象必定是不僅存在於心中,也存在於現實中。從這事實,還證明瞭凡是存在于思想中,又存在於現實中的對象,比僅僅存在于思想中的更偉大。因為,如果把上述的存在者只算是存在於心中,那末,由於任何既存在於心中又存在於現實中的東西,一定比它更為偉大,這樣一來,那個在心中比一切事物更為偉大的東西,總會不如某一事物,同時也不能算作比一切事物更偉大。顯然,這是矛盾的,所以,必然的結論是:那個已經存在於心中的無與倫比的偉大的存在者,一定不僅存在於心中,而且也存在於現實中,否則,它就不會是比一切事物更偉大的了。」 「所以,說這個至高無上的存在者不能被設想為不存在,也許還不如說: 它不能被理解為不存在或有不存在的可能性。因為,嚴格講來,不真實的事物,是不能被理解的,雖然它們卻是可以想愚人設想上帝決不存在一樣而被人設想到。」20 顯而易見,在理性中這種游刃有餘的自由漫步中,理性的步步為營,層層環扣,縝密邏輯,逐步揭開了 fides quae 被蒙蔽的面紗,讓人類一睹其芳容真貌。安瑟倫的本體論論證所彰顯出來的,就是人類理性所追求的近在咫尺的彼岸 fides quae 的自由漫步。換言之,如果人從未進入到安瑟倫的理性自由漫步中,人的理性就僅僅是在遙遠的此岸世界流浪徘徊,不是《流浪地球》,而是流浪理性。然而,安瑟倫並非理性主義者,甚至距離理性主義者非常遙遠。他明確聲稱:「我希望我所說一切,都要在此條件下來理解:就是我所認定的任何事,如果上一級 權威未予以證實,即使在我看來已獲理性之證明,但在天主以某種方式進一步啓示我之前,仍然不能視為具有確切可靠性,僅是在我看來暫時如此而已。」21 在安瑟倫看來,於fidesquae中的理性徜徉漫步,「並非為了藉著理性來獲得信仰,而是為了從信仰、理解及默觀中獲得愉悅。」22 的確,安瑟倫用前所 未有的方式在理性中自由漫步,但他並未切斷 fides quae 與 fides qua 之間已然存在著的密不可分的聯繫。甚至可以說,fides quae 仍然以 fides qua 為鵠的。由此,我們亦可理解《Cur Deus Homo》(天主何以成人)確是安瑟倫將《Proslogium》(對話篇)與《Monologium》(獨白篇)關聯起來的重要著作。
至此,在綜括教父哲學/神學的基礎上,「最後一位教父」聖安瑟莫引領人類走出了古代理性的蒙昧狀態。可以說,教父時期就是引領人類走出遠古理性蒙昧狀態的時期。
由此,「第一位經院哲學家」安瑟倫開啓了揭開人類理性蒙蔽狀態的經院哲學/神學的路程,成為了中世紀人類理性達至巔峰的開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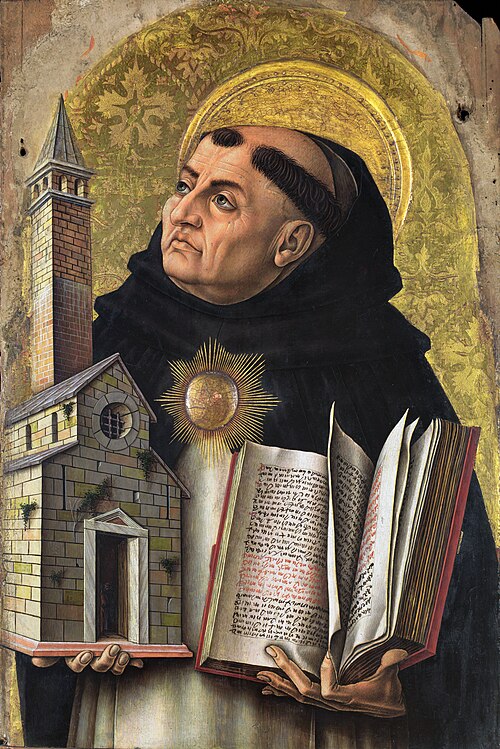
5. 聖托馬斯(+公元 1274 年):人類理性的閒庭信步
顯然,理性不僅是邏輯縝密,這還遠遠不夠,它還應該能夠自我質疑。自我質疑彰顯出人類理性的本質。我們或許可以用類比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理性的這種本質。如果說蜜蜂築巢好似嚴密遵循「邏輯」的話,蜜蜂決不會質疑自我築巢的「邏輯」就是其沒有邏輯的最佳確證。故此,理性的不能或不敢自我質疑,就談不上理性的閒庭信步,就不是理性的信步而游。聖托馬斯·阿奎納採用亞里士多德的哲 學思考進路,通過「質疑」、「反之」、「正解」和「釋疑」的方法把人類理性思考推向了一個嶄新的巔峰。聖托馬斯將亞里士多德並未解決的 fides quae 的問題,以邏輯理性進行了幾乎無懈可擊的闡釋。在論及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原理或根源時,托馬斯解釋道:「所以,必須考慮到,一物之被稱為是無限的,就是因為它不是有限的或不受限制的。但是各依某種方式,質料受形式的限制,形式受質料的限制。質料之受形式的限制,因為質料在接受形式之前,對於很多形式都是處於潛能的狀態,但接受了一個形式之後,就被限定於此一形式。至於形式之受質料的限制,是因為形式以本身來說,是很多東西所能共有的;可是,一旦為質料所接受,便因此而成為這一固定或個別之物的形式。質料因自己受其限制的形式而獲得完美或成全;......。形式卻不因質料而獲得完美或成全,形式的範圍反而受到質料的縮減;因此,沒有受到質料限定的形式方面的無限,是有完美者的性質。萬物之最普遍和徹底的形式根源,就是有或存在本身。......。所以,很明顯地,天主是無限的,及完美的。」23
恰如聖奧思定所言,我們的信仰是「藉對真實之物的信仰,最終轉變為所信仰之物本身。」 24 聖奧思定對 fides qua 與 fides quae的這種闡釋,也為聖托馬斯所吸納並加之以進一步的發展。托馬斯將學問 scientia 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 naturale intellectus 獲得的,一類是通過 superiori scientia 獲得的。學問不是依據對象來判定的,而是依據由對象(物質)而來的理性形式 rationem formalem 來判定的。換言之,對 象(物質)在通過感官及理性形成理性的形式前,不是學問,因為它並不具備普遍性。托馬斯以人、驢和石頭來舉例說,它們普遍共有的「是有顏色」這一理性形式才是學問。顯然,它們此時已經在感覺之上。故此,托馬斯才說,「神聖的知識或學問,既是唯一的,又是單純而包羅萬象的。」25 然而,在托馬斯看來,無論神聖的知識或學問還是其它世俗的知識或學問,它們都需要 fides。Fides 本身就是 fides qua creditur 與 fides quae creditur 的中介與樞紐。托馬斯明確解釋說:「在 fides 里,只看它對象的形式之理這一方面,它就是第一真理。因為我們的 fides 之所以相信某對象,只是因為由天主所啓示;所以,信 仰天主的真理有如媒介。可是,從質料方面來看 fides 所相信的一切,它們就不僅包括天主,也包括許多其它的事物了。因為這些事物之所以能成為被相信的對象,是因為它們與天主有著某種關係。」 26 顯 然,聖托馬斯這裡的 fides qua 與 feides quae 是完全統一的,而且 fides 就是此統一的中介與樞紐。由此而言,在聖托馬斯那裡,人類理性的閒庭信步,雖然達至人類理性的巔峰時刻,但卻沒有走向極端的理性主義。燈塔依然是燈塔,他既有溫度又有亮度。

6. 中世紀哲學:依然閃爍的理性燈塔
中世紀是人類理性之光的燈塔。因著 Logos 的降生成人,聖史若望宗徒石破天驚地闡釋說:「太初有 Logos」。隨後,起步於聖猶思定,邁步於聖奧思定,漫步於聖安瑟莫,信步於聖托馬斯,人類理性在 Logos 內開始大放異彩。縱觀人類理性的成長史,聖安瑟倫是真正的理性自由漫步者。當人類理性走向純粹理性主義時,還是要回過頭來看看這位理性自由漫步者的足跡。在他那裡,fides qua 與 fides quae 是緊密相連的,用他自己的話說:理性的徜徉漫步,「並非為了藉著理性來獲得信仰,而是為了從信仰、 理解及默觀中獲得愉悅。」 用較為通俗及類比的話說:科技是為了人的肉體生命,理性是為了人的精神生命,但是純粹的科技主義與極端的理性主義殊途同歸,都會毀滅人類。換言之,假如極端的理性主義走向否定 fides quae 的極端,那麼 fides qua 也將遭遇毀滅,這就是人類心智的毀滅,那也將是人類的毀滅。沒有 fides quae,也就不會有 fides qua,而 fides 正是此 quae 與 qua 的中介與樞紐。故此,中世紀理性思考的先聖賢哲們,他們從未忘記,Logos 不僅僅是 logos, 而且是成了血肉的 Logos,成了人的 Logos。人,既有理性,又有肉體。
中世紀的確是人類理性大方光芒的時代。經院哲學則是人類理性走向巔峰的發動機。可以說,沒有中世紀的理性光芒,也就沒有稍後的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的興起(Siècle des Lumières,The Enlightenment,中文翻譯為「啓蒙」並不確切,似乎翻譯為「光啓」更佳),更沒有後來人類的幾次工業革命,畢竟這些工業革命的成果都是理性的創造物。在此,我們或許可以引用距今 2500 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話,來感荷距今 1000 多年前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們的理性光芒。亞里士多德的話一點兒也不過時: 「我們受益於前人,不但應該感荷那些與我們觀點相合的人,對於那些較輕浮的思想家,也不要忘記他們的好處;因為他們的片言臢語確正是人們思緒的先啓,這於後世已有所貢獻了。」 27 更何況,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們的理性光芒決非「片言臢語」!中世紀的理性光芒愈演愈烈,以至於逐步走向純粹或極端 的理性主義。對此可能性的極端理性主義,聖奧思定在《論三位一體》的開篇中已然告訴時人及後人: 「我執筆是為了反對那些不屑於從信仰出發,反因不合理地、被誤導了地溺愛理性而深陷虛幻的人的詭辯。」28 當然,走向虛幻的理性詭辯與發揮理性的偉大光芒,兩者迥異。由此而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事實上關閉了極端理性主義的大門,阻斷了極端理性主義的走向(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理性成為認識真理的唯一淵源),將理性重新拉回到 fides qua 的領域。當然此時對 fides qua 的認知已然遠非遠古的蒙昧狀態。如果說康德意欲完成的是知情意的合一,29 那麼,它也是 fides qua、fides quae 及其之間的關聯的合一。如果說康德的「先驗唯心論」與主觀唯心論大有區別,30 那麼,它所謂的先驗也應該是一種對 fides qua、fides quae 及其之間關聯的一種先驗。
我們需要確認:無論 fides qua 還是 fides quae,fides 既是根本的,又是先驗的或可稱為超驗的。 沒有 fides,哪裡會有 qua 或 quae?即便有,人也無法認識和理解 qua 或 quae! 換言之,一個人不能知道他所不信的。這或許就是先聖賢哲們所一直強調的「相信,你就會理解」或「信仰尋求理解」的真意。 的確,連接 fides qua 和 fides quae 的就是 fides。然而,fides 並非僅僅存在於 qua 或存在於 quae。我們應當謹記,依照聖托馬斯的分類,fides qua 中的 fides 是灌輸之德(ex infusione divina)。那麼,誰是此灌 輸之德的始作俑者?顯然只有 fides quae 中的 fides 上帝/天主。這裡所體現出來的,恰恰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主動的總是先於被動的。」31 在這裡,我們或許已然看到康德意欲完成的知情意合一的倩影 了?無論我們對康德的知情意合一的努力有多麼崇敬,亞里士多德的話似乎更不應忘記:「這於真理也一樣;我們從若干思想家承襲了某些觀念,而這些觀念的出現卻又得依靠前一輩思想家。」32 的確,人類理性,沒有猶思定的艱難起步,哪兒有奧思定的蹣跚邁步;沒有奧思定的蹣跚邁步,哪兒有安瑟倫的 自由漫步;沒有安瑟倫的自由漫步,哪兒有托馬斯的閒庭信步;沒有托馬斯的閒庭信步,哪兒有康德的知情意的合一。歸根結底,沒有 Logos 的成為血肉,降生成人,哪裡會有後來的猶思定、奧思定、安瑟 倫、托馬斯等等!
最後,需要總結性的一點兒說明。由神學思考層面來說,中世紀也是人類理性璀璨光輝的時代。 藉助思考 fides quae,人類開始反省 fides qua 的信仰。這種反省也啓發人類開始走出蒙昧的迷信。這種蒙昧的迷信,既處於 fides qua 的自我迷信,又指向對 fides quae 的向他迷信。用宗教的詞彙來說,前者的自我迷信,就是源自亙古的那種驕傲自我:「你們將如同天主一樣」(eritis sicut dii。創 3:5)的極端理性主 義,包括休謨的極端經驗主義,正是這種亙古驕傲自我的一個翻版。對極端理性主義者而言,Logos 僅僅 就是 logos 而已,而非降生成人的 Logos,具有血肉的 Logos。故此,它令人否定人格的天主/上帝,亦即否定 fides quae,從而也否定 fides qua,最終會否定 fides 自身,否定人類自身。後者的向他迷信,就是源 自亙古的亞當與厄娃的那種畏懼而非愛德:「我在樂園中聽到你的聲音,就害怕起來。」 (vocem tuam audivi in paradiso et timui eo。創3:10) 「為什麼你們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谷4:40) 這種畏懼將否定 fides 自身,否定人類自身,從而令人遠離天主/上帝,無法接近天主。宣認「太初有 Logos」的同一位若望宗徒,也同時宣認「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若一 4:16)。若望宗徒的三大 弟子之一,殉道教父聖依納爵(St Ignatius, +107)闡釋道:「信德與愛德是生命的開始與完成。信德是開始,愛德是完成。」33 此後,聖托馬斯解釋說:「按生長等次,必然信德是先於望德和愛德」,「但在成就的等次上,愛德先於信德與望德;因為無論信德或望德,皆受愛德之鼓勵,並因愛德而成為完美的德性。」 34 恰如奧思定所言:「一個人不能愛他所不知道的」,35 當然,這是就其成就層面而言的,與之後的托馬斯一脈相承。就托馬斯所說的生長等次而言,一個人不能知道他所不信的。換言之,信在先,認識在後,愛亦在後。這並不難理解。一個人無論如何聰明,他必須先信由外在於自己的訊息源所給出的出生日期,沒有這個信,他根本無從知道或認識自己的生日,更談不上愛或慶祝自己的生日。談及相信、希望及愛時,我們需要謹記托馬斯的提醒:「雖然愛德是愛,但愛不常是愛德。」36 或許,我們同樣可以說:雖然信德是信,但信不常是信德。換言之,當信具有超越性而成為灌輸之德時,它才是信德。
概而言之,與信仰對立的不是理性,而是畏懼。畏懼讓人喪失信,丟失信德。反之亦然,與理性對立的不是信仰,而是傲慢。傲慢讓人墜入迷信,陷入迷茫。故此,剔除畏懼,遠離傲慢,從而讓人得以安心而處,享受真正生活的就是 fides。「為這個緣故,我強烈並懇切地呼籲——我相信並非不合時宜 ——讓信仰與哲學恢復深度的合一,使二者能保持各自的獨立,又能合乎各自的本質。應該以理性的膽量,響應信仰的坦率。」37 的確,中世紀的理性與信仰的燈塔依然在閃爍!
(第六屆全國中世紀哲學論壇暨中世紀哲學專業委員會 2025 年會)

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2頁。
2 丁山 遺著,《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龍門聯合書局,上海,1961 年 2 月,第 567,568 頁。
3 「你們曾經聽我在各種各樣的時候,在各種各樣的地點說過,有一種神物或靈機來到我身上,這就是梅雷多訴狀中譏笑 的那個神。這是一種聲音,我自幼就感到它的來臨。」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 館,1987 年,第 70 頁。
4 「當一個人想到自己不久要死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害怕纏住他。關於地獄的種種傳說,以及在陽世作 惡,死了到陰間要受報應的故事,以前聽了當作無稽之談,現在想起來開始感到不安了—說不定這些都是真的呢!」[古希 臘] 柏拉圖 著 郭斌和 張竹明 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5 頁。
亦請參閱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著 吳壽彭 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16 頁,腳注3。
5 「人們似乎都在尋求我們在‘物學’中所指明的諸原因,我們再沒有找到過其它原因。但他們的研究是模糊的;他們有 些象是說到了,又象全沒說到。因為古代哲學正當青年,知識方開,尚在發言囁嚅的初學時期。」[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著 吳壽彭 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31 頁。
6 這裡所言蒙昧狀態,亦即吳壽彭先生所評判的:「若說畢達哥拉斯是迷信與智慧的混合,亞里士多德該是理知的化身。 但在他建立這宇宙‘最高實是’時,他又顯露了柏拉圖純意式的氣息。」請注意,吳先生這裡用的是理知(νους 心、思 想),而非理性(λογος 言、道)。此外,吳先生所譯的「意式」(ιδεα)即柏拉圖的理念。[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 彭 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378 頁。
7 「有那麼一種善,我們樂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後果。比方象歡樂和無害的娛樂,它們並沒有什麼後 果,不過快樂而已。」「另外還有一種善,我們之所以愛它既為了它本身,又為了它的後果。比如明白事理,視力好,身 體健康。」「你見到第三種善沒有?例如體育鍛鍊啦,害了病要求醫,因此就有醫術啦,總的說,就是賺錢之術,都屬這一 類。」[古希臘] 柏拉圖 著 郭斌和 張竹明 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44 頁。 請對比托馬斯·阿奎納的《神學大全》第一集第六題 論天主之善或善性。
「假定有神,神又確實關心我們,那我們所知道的關於神的一切,也都是從故事和詩人們描述的神譜里來的。那裡也同時 告訴我們,祭祀、禱告、奉獻祭品,就可以把諸神收買過來。」「如果我們是正義的,諸神當然不會懲罰我們,不過我們 得拒絕不正義的利益。如果我們是不正義的,我們保住既得利益,犯罪以後向諸神禱告求情,最後還是安然無恙。」[古希 臘] 柏拉圖 著 郭斌和 張竹明 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54 頁。 請對比托馬斯·阿奎納的《神學大全》第一集第二十一題 論天主的正義和仁慈。
8 「當人的這三個部分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慾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這樣的人不是有節制的 人嗎?」[古希臘] 柏拉圖 著 郭斌和 張竹明 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70 頁。顯而易見,柏拉圖 並未進入到純粹本體論之中。
9 「Someone says to me, ‘let me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I answer,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t. Augustin, Sermons 43,Edmund Hill,O.P.(Trans.),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art III, Sermons, Volume II:Sermons 20-50, New City Press, New York, 1990, p.240.
10 「et sequens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diceretur."「Neque enim quaero intelligere ut credam, sed credo ut intelligam.」 St. Anselm, Proslogium,Prooemium 1.
11 克萊森(Crescens)與猶思定是同時代的一個哲學家,控告基督徒為極端無神論者,並導致猶思定被處死而殉道。其生平 未知,僅從教父著作中知道其名字及哲學家身份。
12 猶思定,《第一護教書》,致安東尼凱撒書,第 5 章。中文為筆者自譯。
13 同上,第10章。
14 參閱:[古羅馬]奧古斯丁著周偉馳譯,《論三位一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11頁。
15 「ut sic intellegamus deum si possumus, quantum possumus, sine qualitate bonum, sine quantitate magnum, sine indigentia creatorem, sine situ praesentem, sine habitu omnia continentem, sine loco ubique totum, sine tempore sempiternum, sine ulla sui mutatione mutabilia facientem nihilque patientem.」Augustine, De Trinitate,Liber V,2.
16 [古羅馬]奧古斯丁著周偉馳譯,《論三位一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27頁。
17 安瑟倫著塗世華譯,《安瑟倫著作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38頁。
18 亞里士多德類似邏輯公式:「同時,這是明顯的,若當 A 是真實時,B 亦必真實,則當 A 是可能的,B 亦必可能;因為 B 雖不必要成為可能,這裡卻沒什麼事物可來阻止它成為可能。現在試使 A 為可能。於是,如果 A 已是真實的,這就並無
不可能因素在內,而 B 也必需為真實。但,B 曾假定為不可能。就讓 B 算是不可能。於是,如果 B 是不可能的,A 亦必 如此。但 A 先已擬定為可能,所以 B 亦必如此。於是假如 A 是可能的,B 亦將是可能的;如果它們原有這樣的關係:假如 A 是真實的,B 亦必真實。那麼,承認了 A 與 B 的上述關係後,若說 A 是可能而 B 是不可能,則 A 與 B 的關係就不符合於 原來的假定。假如 A 是可能的,B 亦必可能,這裡相關的定義是這樣,A 若在某時候與某方式上為真實,B 亦必在某時候 某方式上為真實。」[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著 吳壽彭 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172-173 頁。
19 安瑟倫 著 塗世華 譯,《安瑟倫著作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第 266 頁。
20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 244,250 頁。
21 「sed eo pacto,quo omnia, quae dico, accipi volo:videlicet, ut si quid dixero, quod major non confirmet auctoritas, quamvis illud ratione probare videar,non alia certitudine accipiatur, nisi quia interim mihi ita videtur, donec mihi Deus melius aliquo modo revelet。」Anselm,Cur Deus Homo,chap.II.
22 「Quod petunt, non ut per rationem ad fidem accedant,sed ut eorum,quae credunt, intellectu et contemplatione delectentur.」 同上,chat.I.
23 聖多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第一冊:論天主一體三位;第七題論天主的無限性;第一節天主是不是無限的。
24 「Optabiliter autem rerum verarum in easdem res fides transit.」Augustine, De Trinitate,Liber XIII,3.
25 「ut sic sacra doctrina sit velut quaedam impressio divinae scientiae, quae est una et simplex omnium.」St. Thomae de Aquino,Summa Theologiae, Prima Pars, Q.1,A.3.
26 Sic igitur in fide si consideremus formalem rationem objecti, nihil est aliud quam veritas prima. Non enim fides de qua loquimur, assentit alicui, nisi quia est a Deo revelatum. Unde ipsi veritati divinae fides innititur tanquam medio. Si vero consideremus materialiter ea quibus fides assentit, non solum est ipse Deus,sed etiam multa alia;quae tamen sub assensu fidei non cadunt, nisi secundum quod habent aliquem ordinem ad Deum, prout scilicet per aliquos Divinitatis effectus homo adjuvatur ad tendendum in divinam fruitionem.」 St. Thomae de Aquino,Summa Theologiae, Second Pars, Q.1,A.3.
27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2頁。
28 [古羅馬]奧古斯丁著周偉馳譯,《論三位一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27頁。
29 趙敦華,「康德哲學的革命意義」,見:https://mp.weixin.qq.com/s/IcpXc7FcTPQSpWugnddGsQ
30 李秋零,「走進康德,重新理解’人是什麼’」,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動態》・人物專訪,2024年 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