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帝被请进立法机关:罪、法与风俗之间的战争
第一章|在麦克风前,神学忽然变成了治国术
这一切的起点并不是白宫或国会,而是一次直白到近乎冒犯的对谈:一位自认“改革宗长老会(Presbyterian, Reformed Evangelical)”的牧师,宣称自己是“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者”,并愿意用法律把“上帝的愤怒”从社会中“清除”。他不否认上帝绝对主权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也不回避“神权政治(Theocracy)”的字眼,但他自创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标签——“神权的自由意志主义者(theocratic libertarian)”:在敬拜与思想上尽量少管,在性伦理与家庭秩序上严格立法。
这不是一场抽象的神学辩论。它切开了当下美国政治最疼的神经:谁来决定“罪”何时该成为“罪名”?社会秩序可以以“启示”为正当性吗?自由主义的制度成果(少数宗教的公共空间、个体权利)该被看作恩赐还是堕落?更关键的是,当一种“救恩学”的语言进驻立法与治安,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理解国家、法律与邻人的方式?
第二章|救恩的逻辑与统治的逻辑:两套时间表的冲突
要理解当代“基督国度”的雄心,必须先分清两条时间轴:救恩时间与制度时间。在救恩时间里,上帝预定、拣选、施恩,人只是被动接受;在制度时间里,法条、程序、判例、执法,必须面对证据、比例与边界。
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是那位“以曲线写直线”的主宰——世界的邪恶并不让祂的圣洁受损,祂以主权编写历史。然而,当这种神学被转换成政治工程,就滋生出一种“可忍受的严厉”:既然上帝以主权管理恶,人间也可以以律法约束“恶”,且无须对每一位受罚者的“可救性”负责。救恩的“绝对”与政治的“可操作”,在这里被粗暴嫁接——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最敏锐的警报:神学的确定性,一旦误用为统治的确定性,程序正义就会被虔诚吞没。
第三章|从“软建立”到“十诫入法”:重铸美国的宗教–国家关系
这一愿景并不满足于“软性建立(soft establishment)”——那种在公共空间模糊承认上帝、允许校园祷告、取消堕胎的传统宗教保守主义。它要走得更远:让国会以法定形式承认“耶稣为主”,让十诫(Mosaic Law, the Ten Commandments)成为立法的标尺;对“通奸”“鸡奸”等性伦理违法化;以取消“无过错离婚”修复家庭秩序;在城市景观里限制异教符号的公共可见度;在文化上“消音”骄傲游行与变装讲故事时段。
支持者的关键辩护,是把“文明常识”与“启示道德”捆绑: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美国”曾允许对同性行为定罪,社会依然“自由繁荣”,因此今日“神权立法”并非反乌托邦,而是“回归秩序”。然而,批评者会追问:那种“自由”从未覆盖被刑罚触及之人;当“罪”被全面立法化,实质平等就消失在“习以为常”的多数之中。民主的宽容,不在于多数的舒适,而在于它愿意为少数的不合时宜腾出空间。
第四章|罪与罪名:摩西律法、英美普通法与现代性的三角拉扯
在这场辩论里常被忽视的是三种法理传统的纠缠:
第一,启示法:以摩西律法为伦理起点,强调“神所厌恶不可被合理化”;
第二,普通法(Common Law):自英格兰承袭而来的判例体系,讲求比例、先例与可执行性;
第三,现代宪政:以程序、权利与多元为底座,强调政府权力的限度。
“神权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想象,试图把三者硬性拼接:在“敬拜与思想”上借用现代宪政的宽容,在“性与家庭”上援引启示法,在“执法与裁量”上依赖普通法的渐进。但这套组合有一个内在裂缝:一旦立法动机来自“不得惹怒上帝”,比例与边界便极易服从于“禁绝”的冲动。而当禁绝习惯化,普通法的谦抑与现代宪政的宽容,很快就退化为“过渡时的策略”。
第五章|自由主义的罪与功:敌手也是围栏
自由主义当然有它的罪:冷漠的市场理性、日渐空心的共同体、把宗教抽离公共论证的“程序洁癖”,以及在生命议题上的堕落。但自由主义也有它的功:它把权力关进笼子,让任何宏大德性必须低头经过权利与程序的检验;它用习惯法与比例原则钝化热忱,让道德激情在被制度缓冲后不至于化为合法的暴力;它为陌生人留出共存的台阶,让你可以从反对者那里学到“如何不统治”。
如果说神学热忱是火,自由主义就是必要的耐火层。我们可以责备它的冷,但在历史上每一次宗教政治的过热里,它都承担了“灭火”的卑微角色。正因此,当某种“基督国度2.0”自称已从宗教战争与宗教审判学到教训,它真正需要证明的,不是“学会了多少圣经”,而是愿意把多少权力留给对手。
第六章|“三层秩序三角”:把不可调和尽量变成可共处
为了把前面的争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心智工具,我提出一个框架,称之为**“三层秩序三角”**:救恩(Soteriology)—治序(Civil Order)—风俗(Mores)。
救恩关乎终极真理:人如何得救、上帝如何施恩。这一层应当停留在自由的教会生活与自愿的宣讲劝勉,不以刑罚强制。救恩的火,只能点燃心,不能点燃法条。
治序关乎可共同生活的最小边界:生命、财产、程序、公平竞争。这里的立法要遵循比例性与可证性,以伤害原则与公共安全为准绳,而非以“惹怒上帝”的想象为立法动因。
风俗关乎共同体的道德气候:家庭观、性伦理、礼仪。它需要社会的软实力去塑形——学校、教会、媒体、互助网络——而不是刑事法去硬切。风俗的成功,是让人甘心其好,而不是害怕其罚。
这个三角的运转要义在于:把救恩的热量,通过风俗层扩散,最终以最谨慎的方式触及治序层。相反,如果直接把救恩的“绝对性”导入治序的“可执行性”,那么程序很快会被虔诚碾平,权力会借德性之名变得粗暴。
实践路径也应顺序展开:先风俗,后治序。先用教会与教育修复家庭文化,再以民法与社会政策(而非刑罚)矫正结构性扭曲;只有当行为构成可证的公共伤害,才进入刑法与治安之域。这样,宗教的热忱才不会在司法里变质,法律的权威也不会在虔诚里走样。
第七章|当热忱学会慢慢走
真正成熟的德性,懂得自己不该做什么。一个自信的基督教政治传统,不必把十诫逐条写进刑法,反而应当让十诫成为信徒的良心守则、教会的纪律、家庭的规训、社群的风俗。唯有如此,信仰才不必借警棍证明它的力量,法律也不必冒充神谕维持它的威严。
当上帝被请进立法机关,祂最先要问的可能不是“你替我禁了什么”,而是“你为对手留下了什么”。在火与光之间,选择做光的传统,最终也更能保存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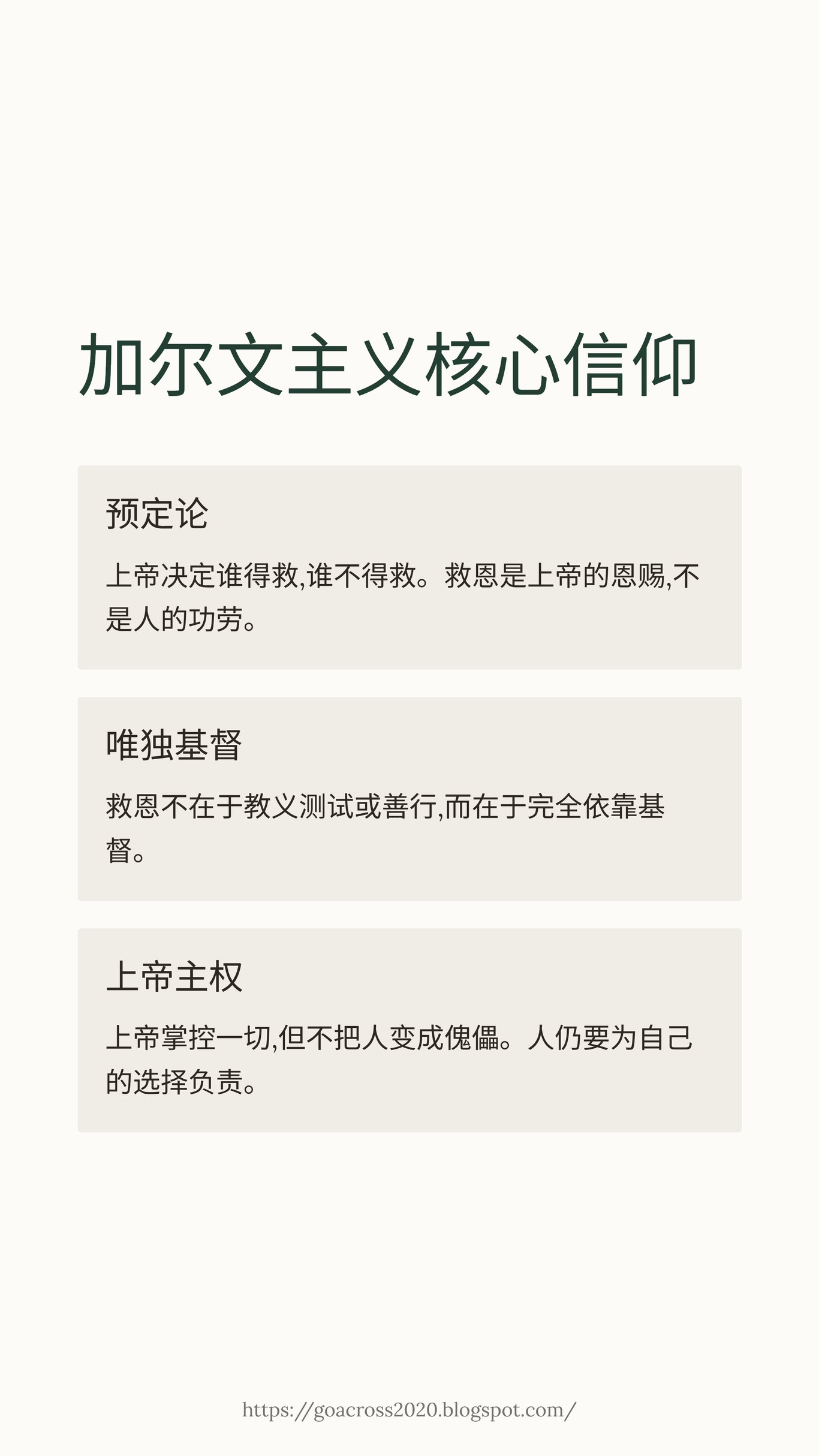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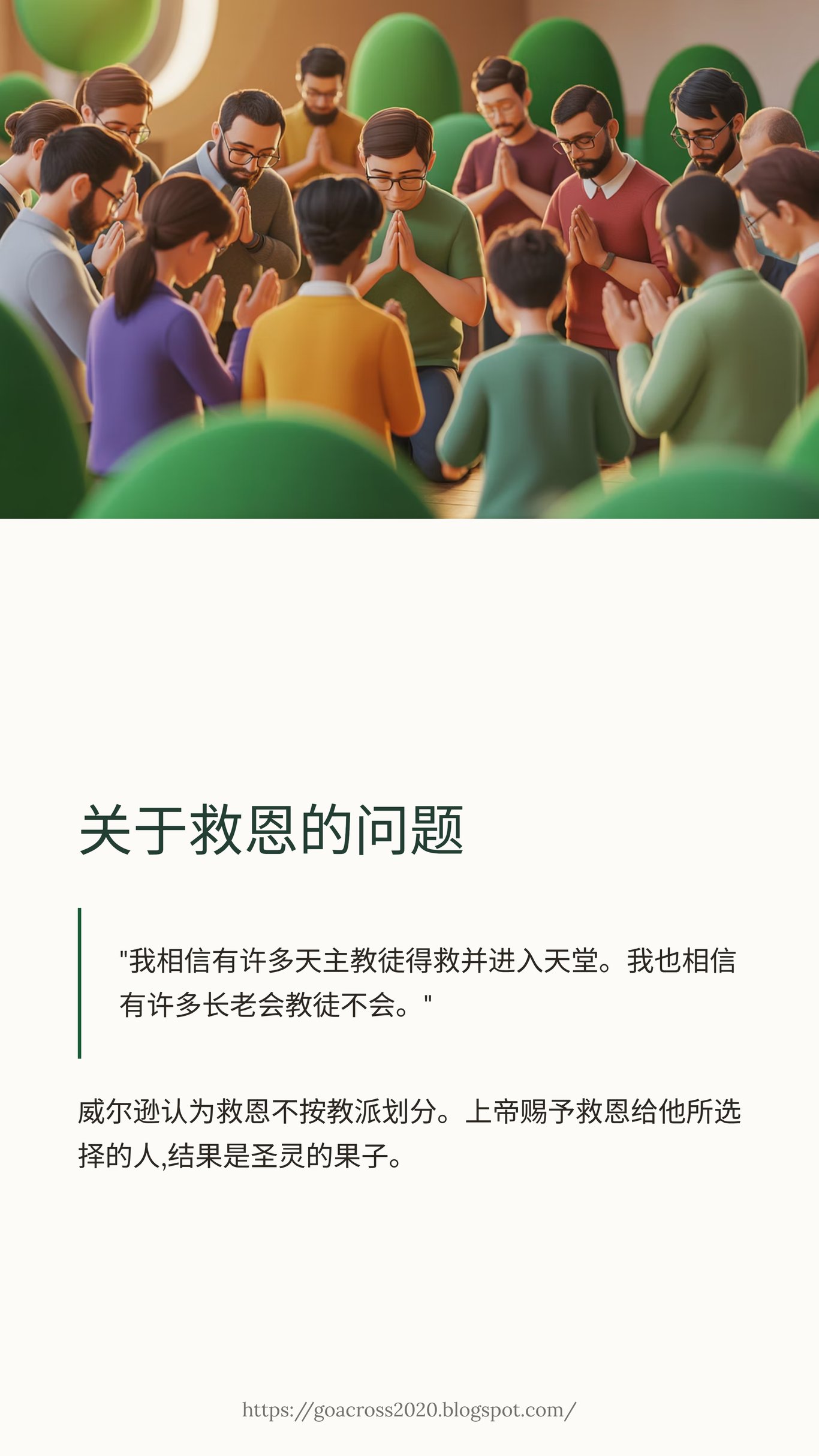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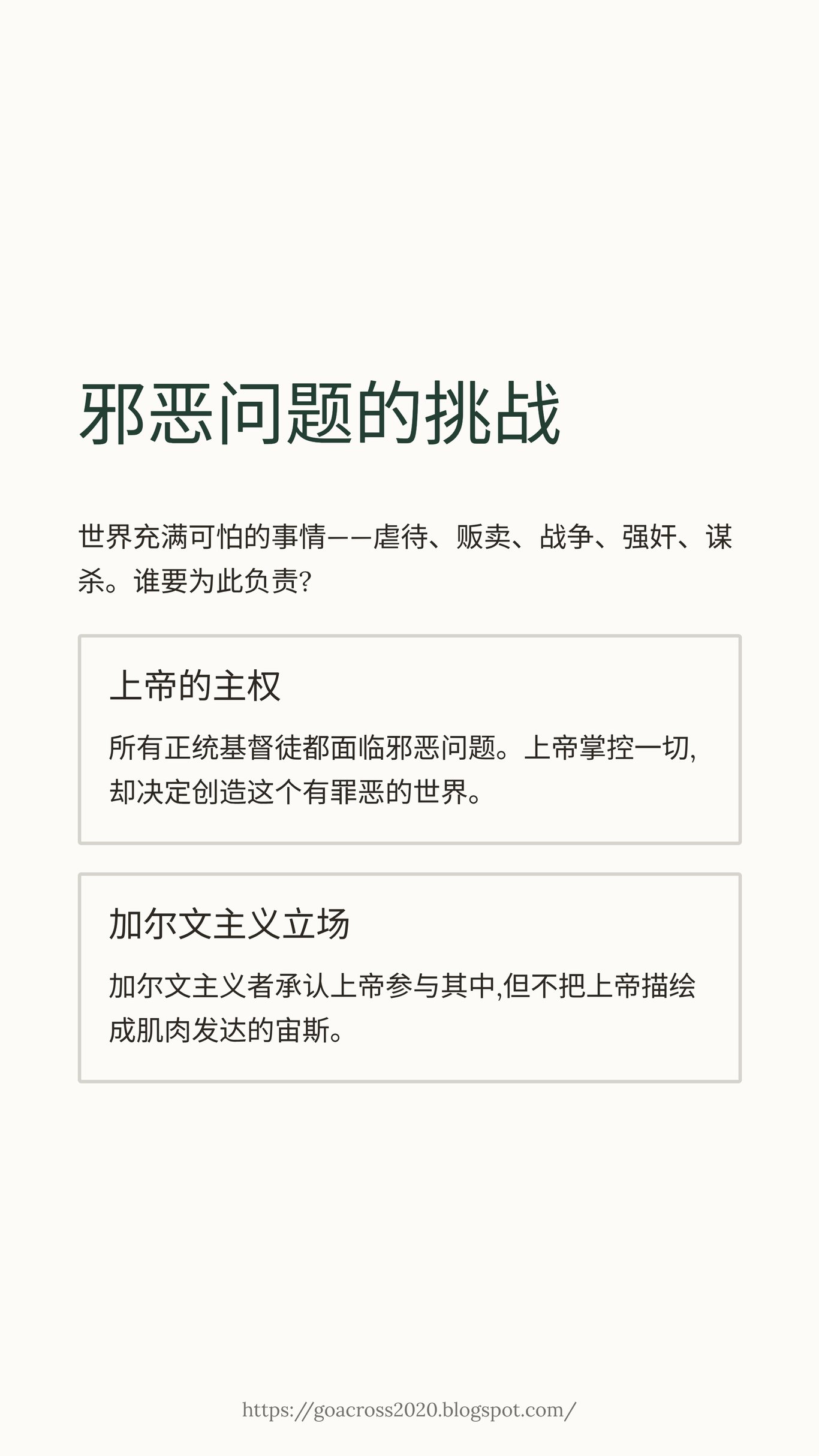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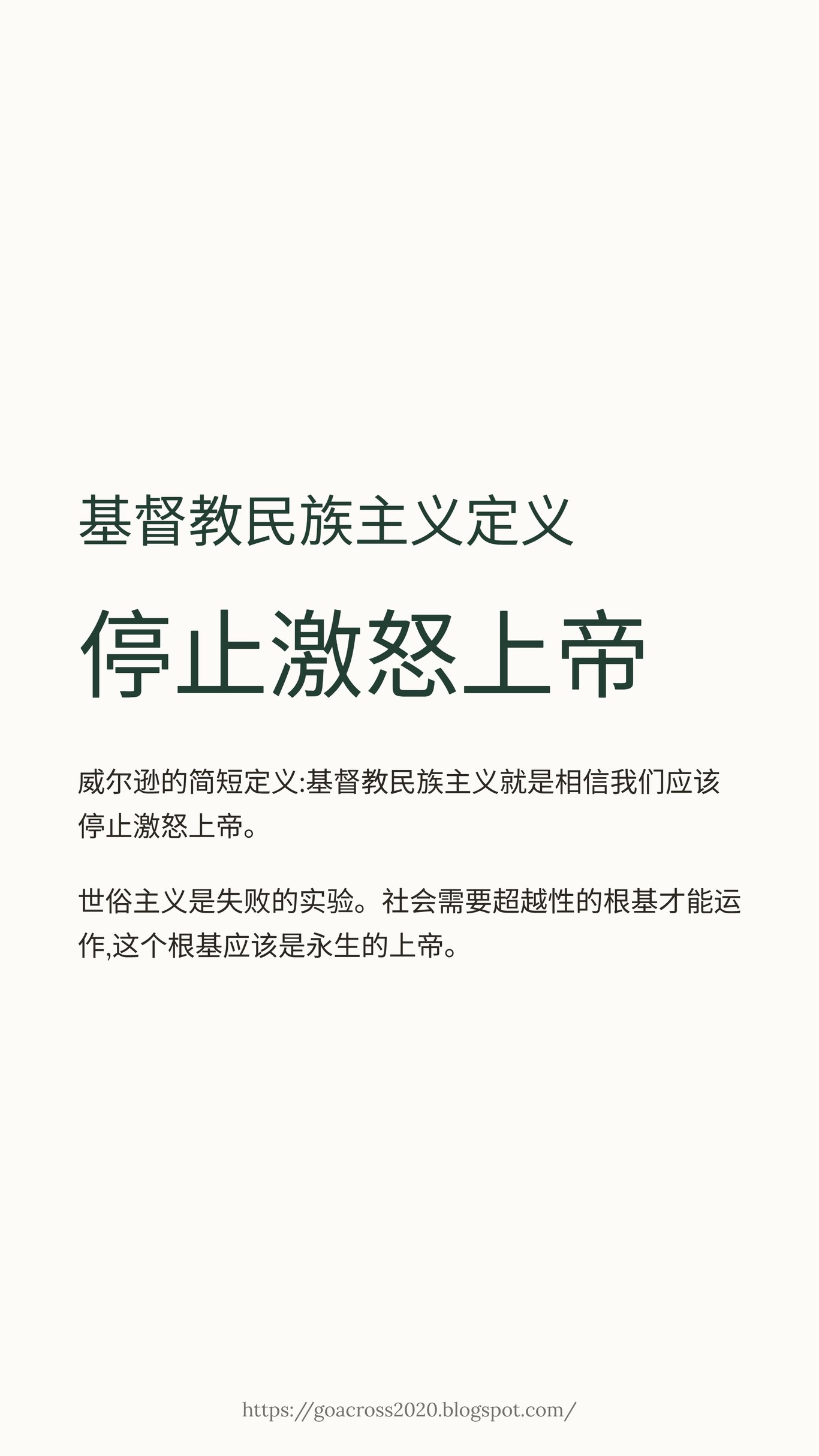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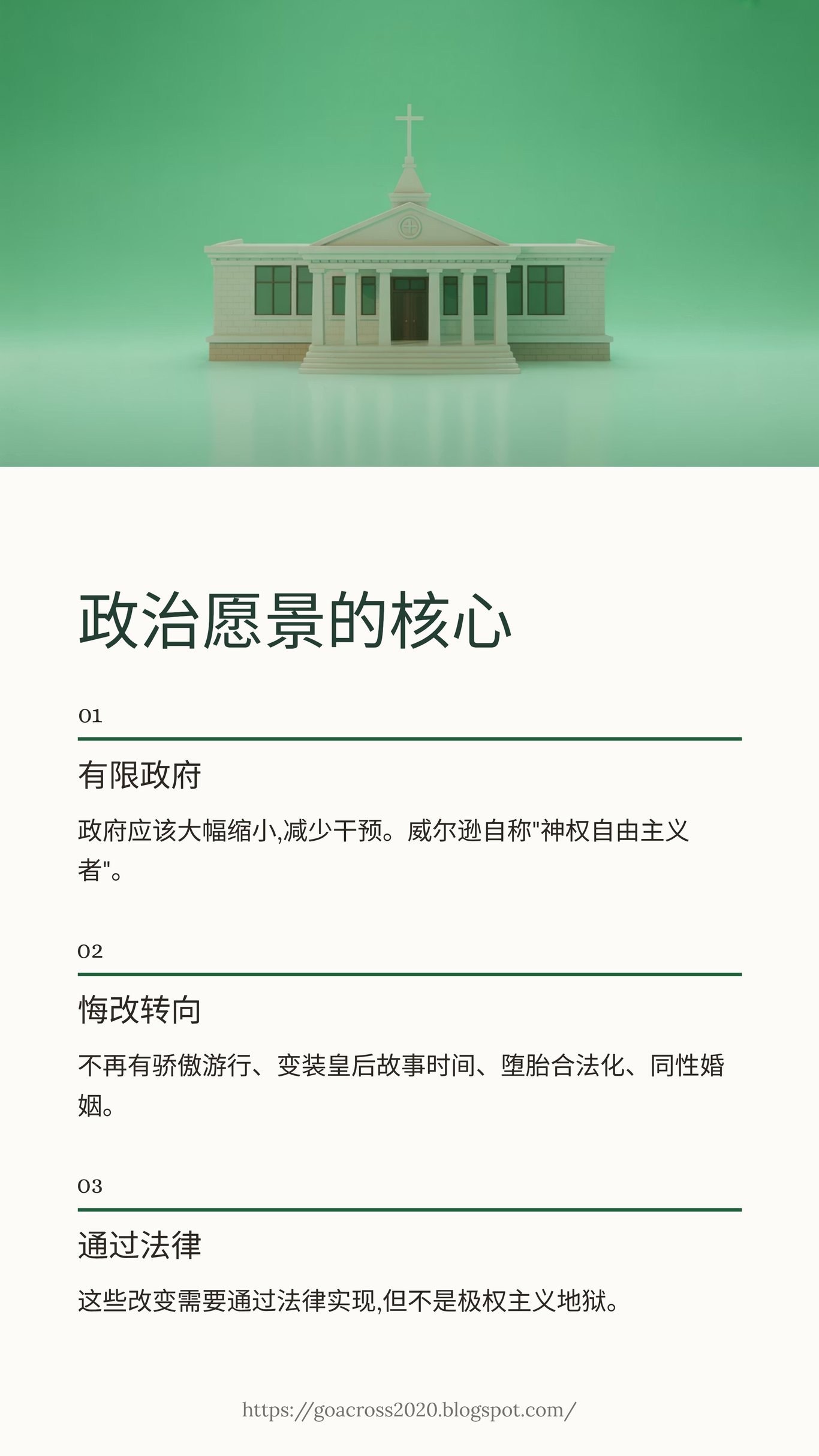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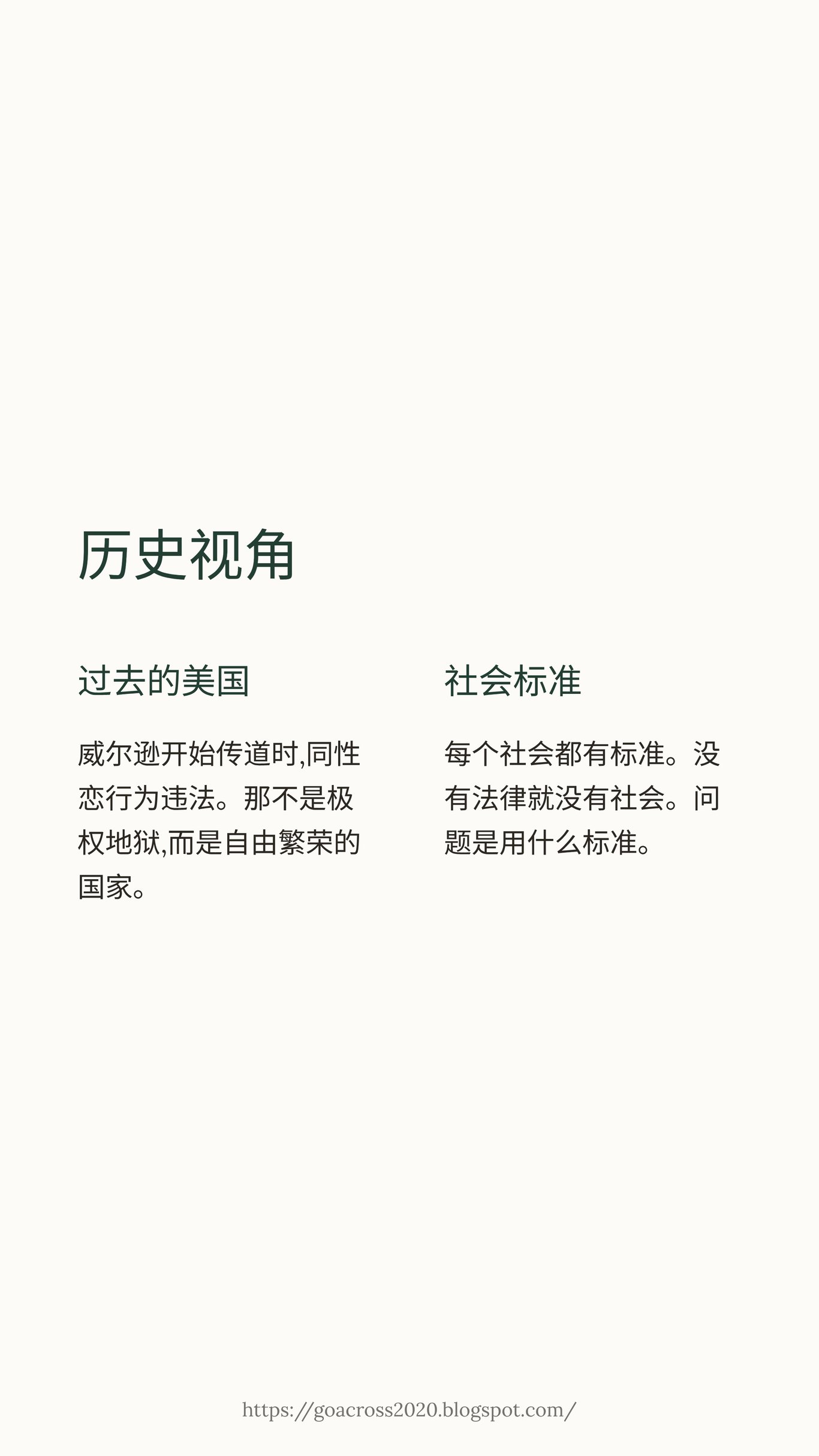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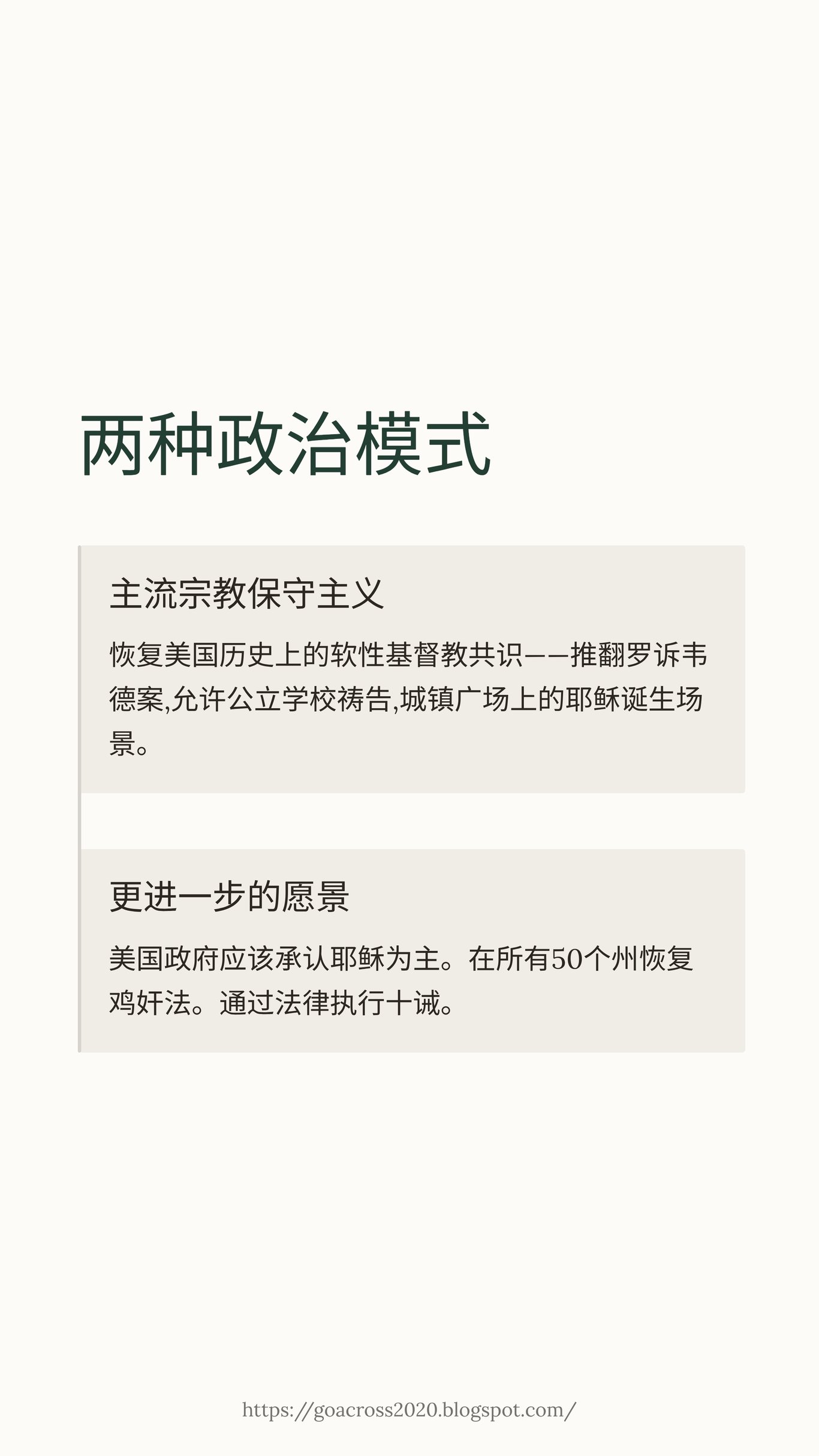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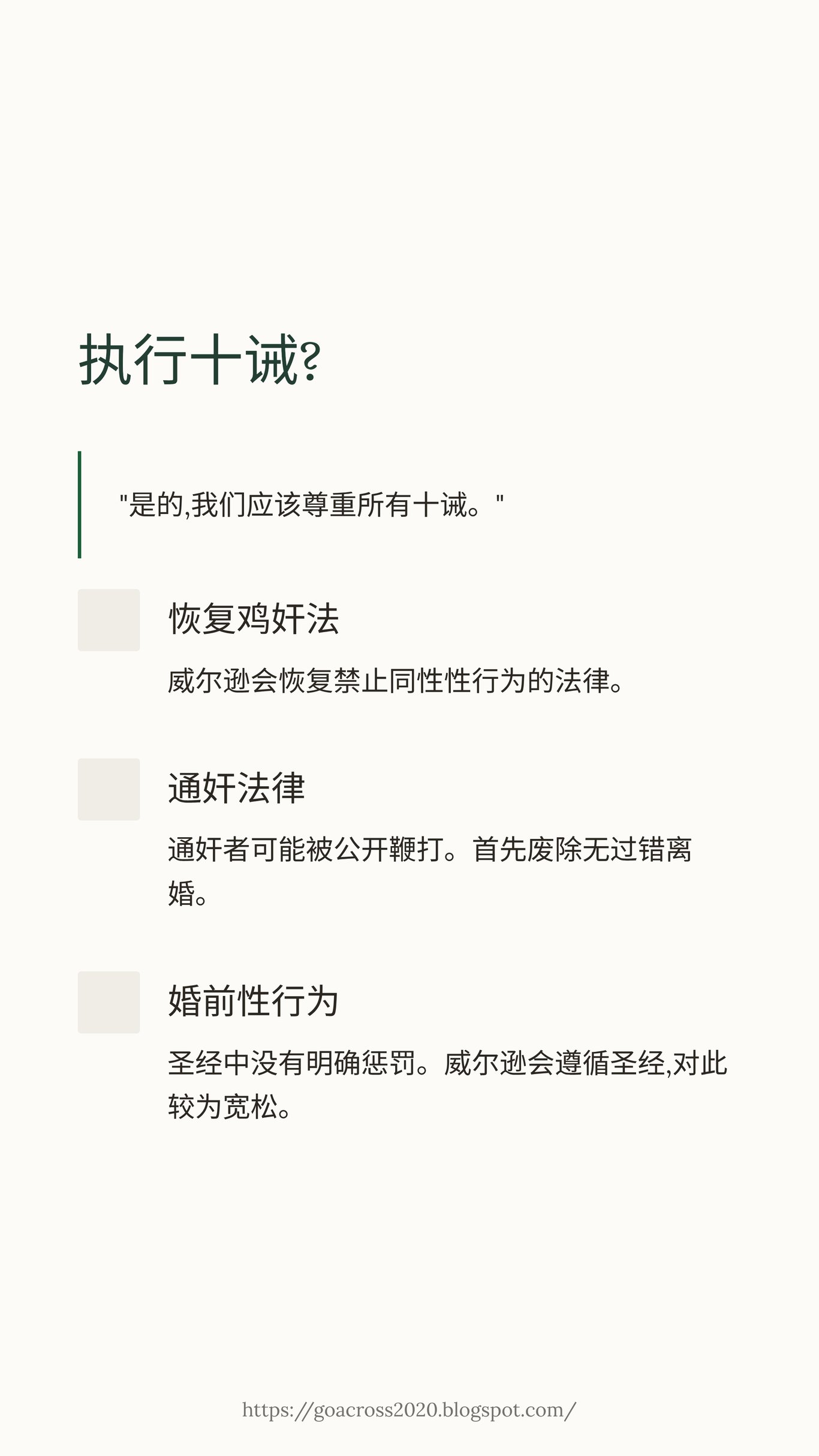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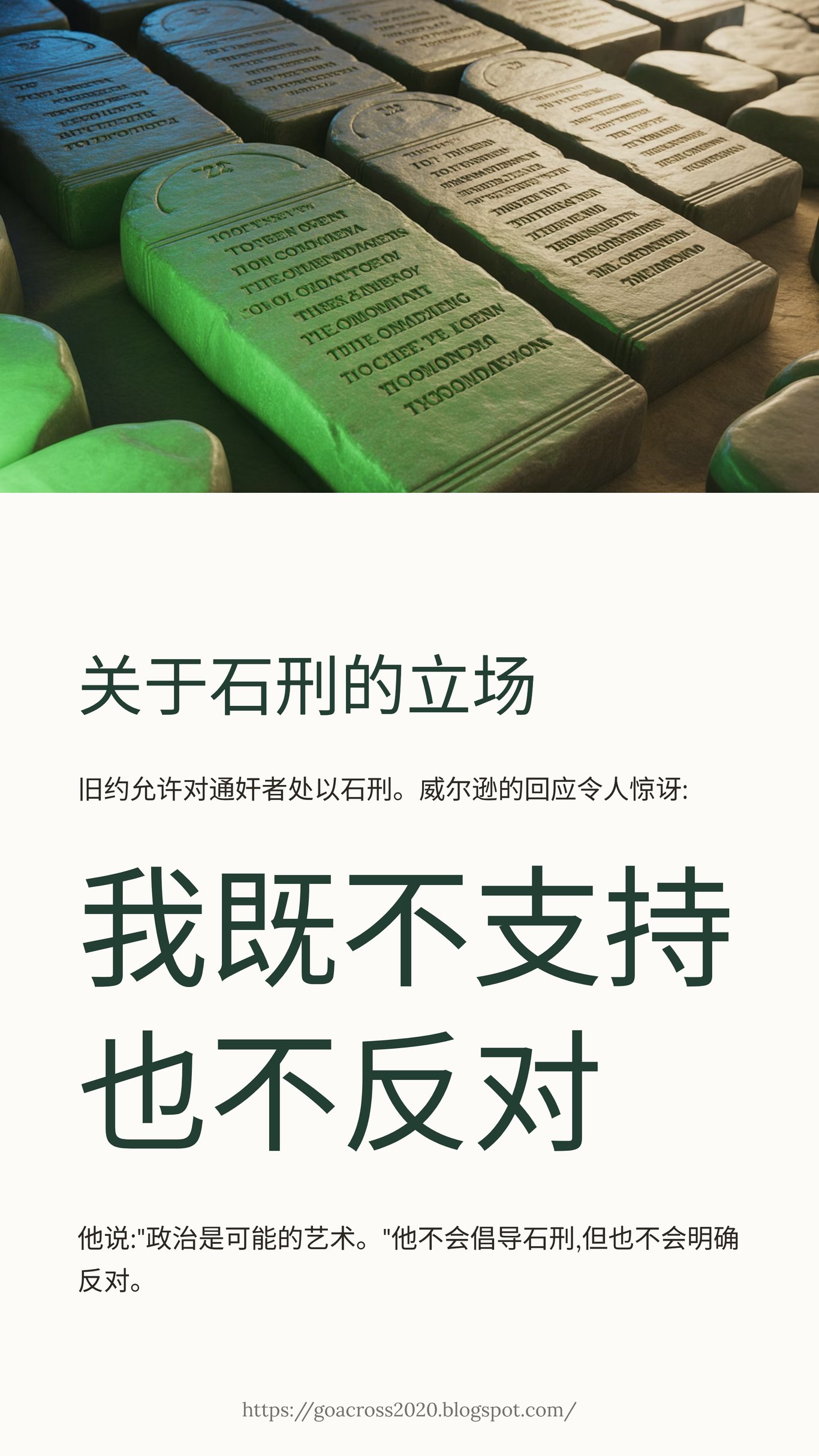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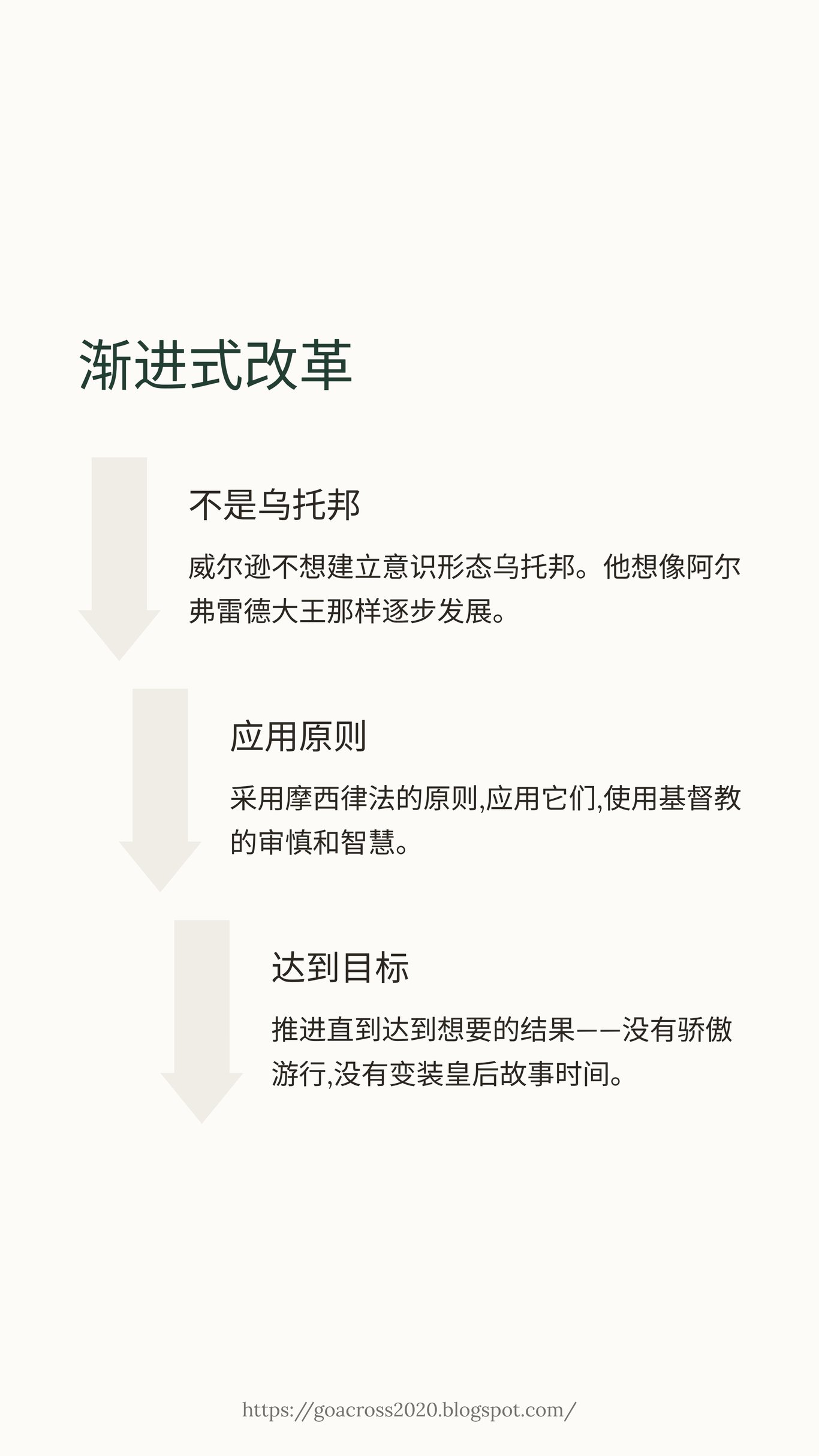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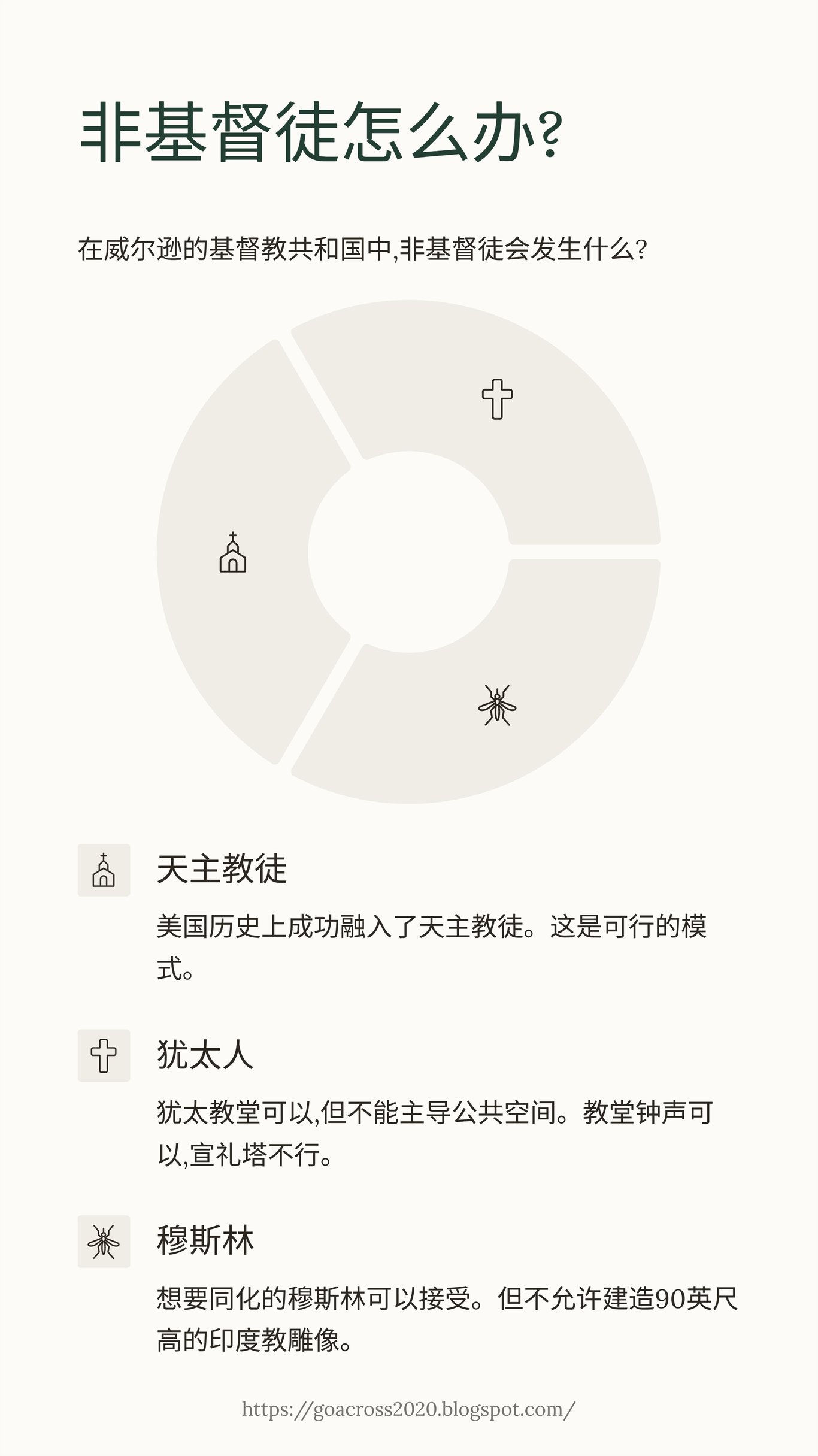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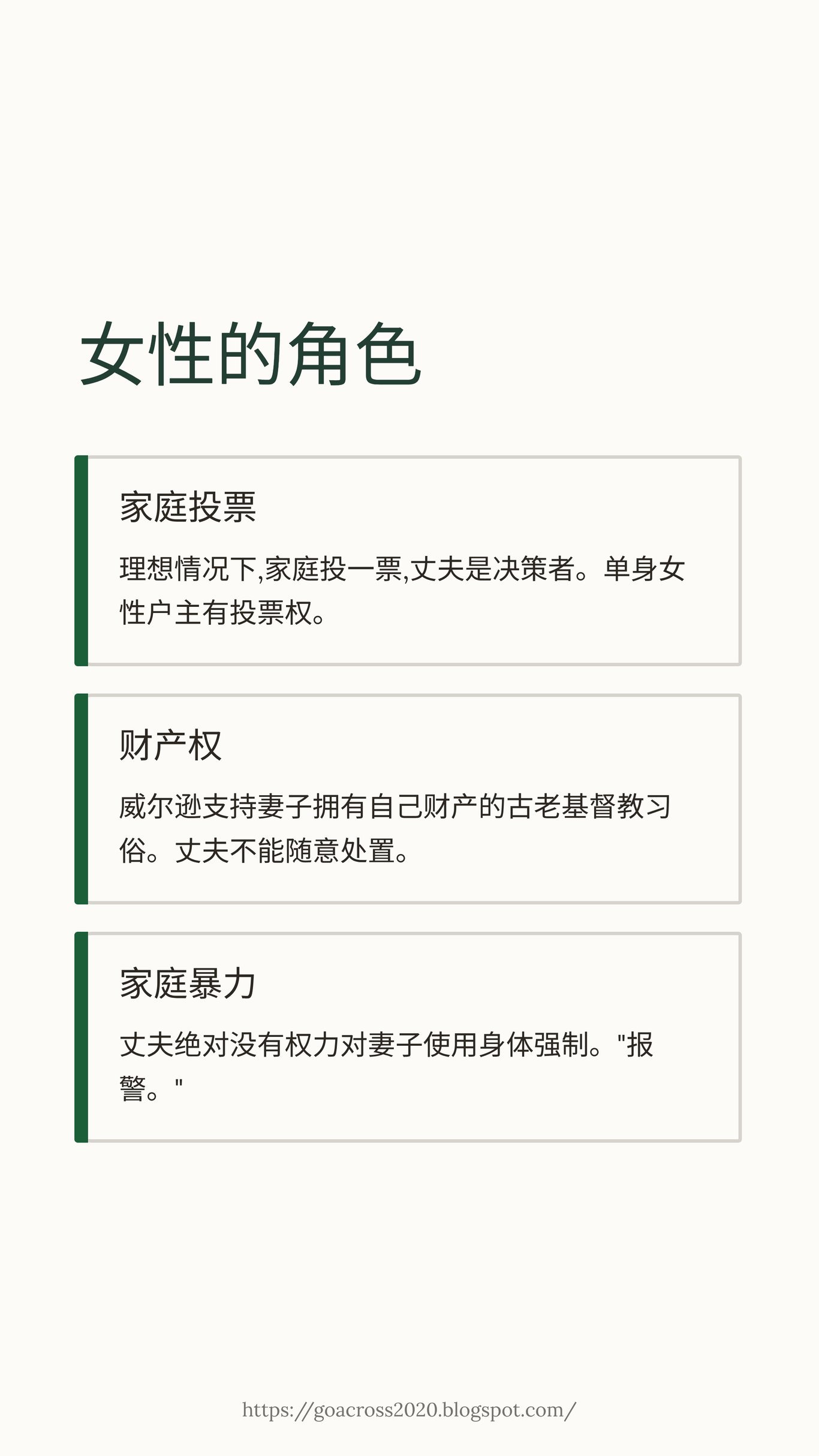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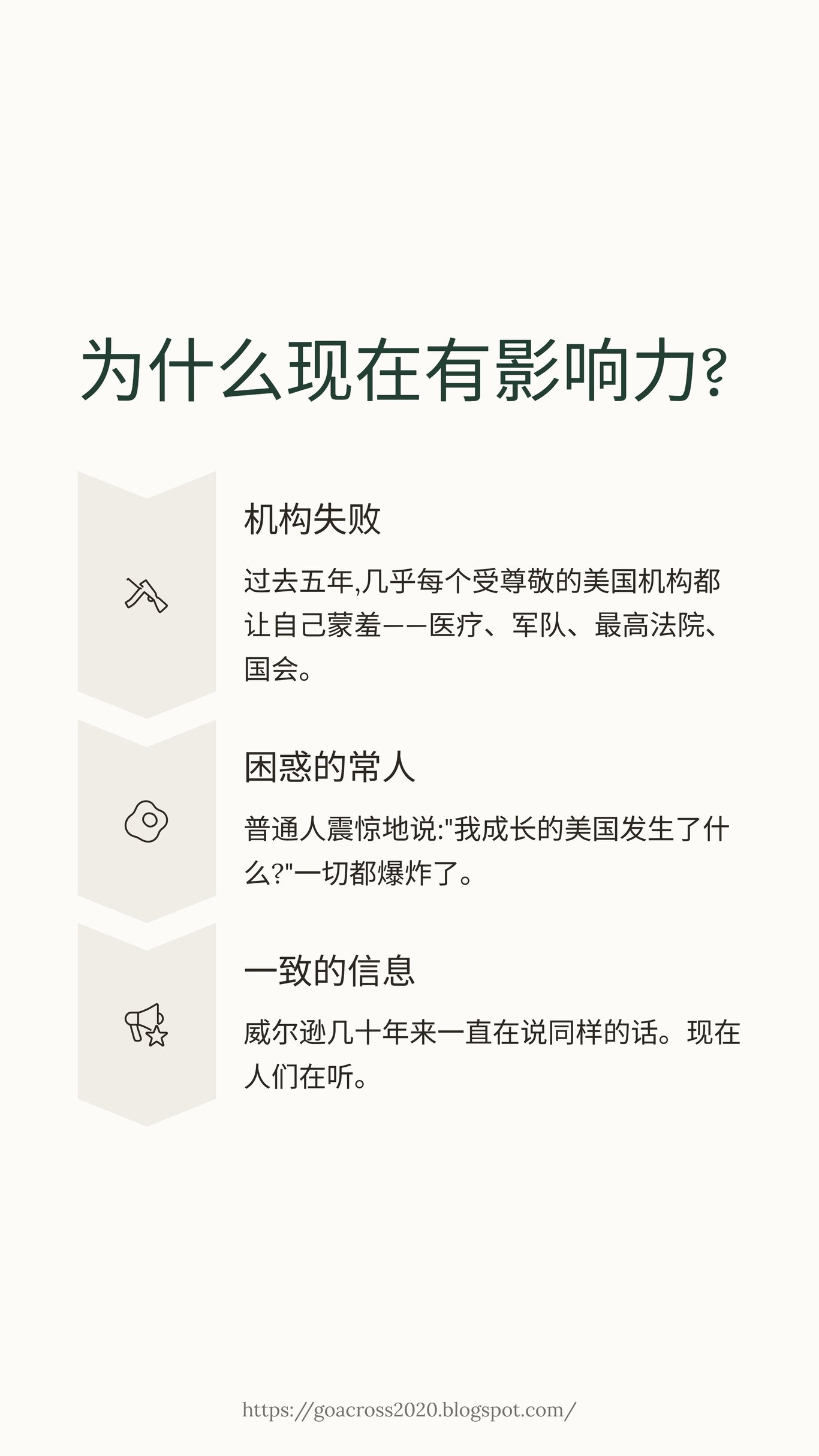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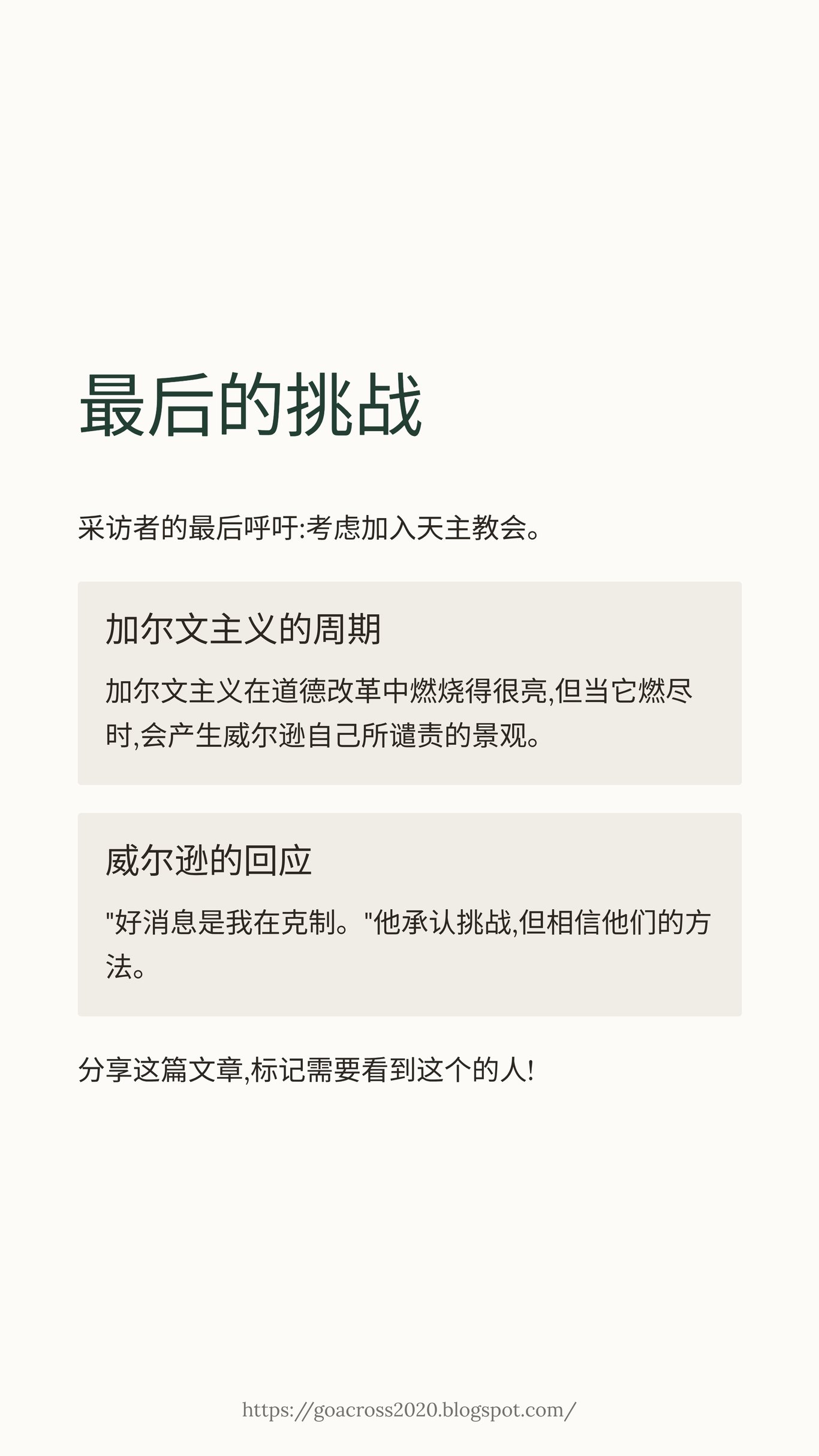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