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中國網路圈套》「只要地球有人的地方……」
「只要地球有人的地方……」
位於美國蒙大拿州格拉斯哥鎮的「尼蒙電話合作社」(Nemont Telephone Cooperative)辦公室地下室,有數百台小風扇不停運轉。我行經上方蜿蜒著大綑電線的整排金屬塔時,注意到一個老舊的棕色金屬箱,上面有個熟悉的名稱:Nortel。垮台前的北電是尼蒙的首要供應商,尼蒙為散布於約三萬六千兩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顧客提供電信服務,這遼闊的面積相當於紐澤西州和康乃狄克州加起來那麼大。
華為的花形標誌到處可見,印在這主庫房裡、那些最新棕色金屬箱上面。這些金屬箱裡頭是最新的基地台設備,當資料流經時,它們的綠燈閃爍著。主庫房旁邊有一間零件庫房,裡頭堆滿零件與工具,牆上鑲著一塊紅棕色的塑膠方框。在華為的標誌上,一名技術員開玩笑地用黑色麥克筆寫上「Nortel」這個字。
前來格拉斯哥鎮可說是舟車勞頓,很不容易。在美國具有至少一千位居民的全部小鎮中,格拉斯哥鎮是離任何大城市最遠的。這裡的居民以此獨特性為榮,在當地的運動用品店,你可以用十美元買到一件上頭印了「Middle of Nowhere」(荒無人煙之地)的T恤。小鎮上的旅館很少,我挑選的這間旅館,用一句可愛的謙遜詞為自己打廣告:「荒無人煙之地的某處」。
尼蒙和十幾個美國州的鄉村地區電信服務業者都投靠華為,這顯示了美國政策的重要失敗。由於這小鎮人口只有幾千人,不是幾萬人,規模較大的美國電信公司不感興趣投資。儘管有美國政府的補助,尼蒙發現易利信、諾基亞或三星(Samsung)的設備太貴了。
任正非擁抱毛澤東主張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下令華為聚焦於被西方電信公司所忽視的市場,「到農村去,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華為早年的宣傳冊子上,這麼指示員工。華為在中國農村地區建立了市場占有率,再擴張至其他開發中國家,以及美國的鄉村,把網路連結帶到被遺忘的市場。
格拉斯哥鎮的經驗並非那麼不同於全球各地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經驗。在行動電話基地台、高速網際網路交換機及光纖電纜等珍貴資源稀少的情況下,從美國鄉村地區到非洲的較小市場都沒有多少選擇。它們也知道,不能加入全球網路就是死路一條。華為並不是它們的首選,但往往是它們能負擔得起的唯一選擇。
在世界各地,中國企業靠著西方公司留下的數位落差而繁榮起來。很多人把這些工程僅僅視為散亂的機會主義,但中國的冠軍企業進軍海外,取得重要經驗,做好宰制未來快速成長市場的準備。
********
「為了我們的生存」
來到格拉斯哥之前的十年間,華為已經在世界其他最偏遠及最危險的地方建設網路。一九九○年代中期,任正非認知到公司必須開始在國際上競爭,他認為,若華為在國際市場上失敗,就必須競逐愈來愈縮減的中國國內市場。「為了生存,我們被迫走進國際市場。」他後來解釋。
在離本國最近的香港,推行了第一個海外計畫後,華為瞄準風險更大、更被忽視的海外市場。乍看之下,它的時機點再糟糕不過了,但時機點往往出現於危機浮現之時或翻騰過後。這也意味著華為面對較少的競爭,因為西方公司通常會離開,或是等到商業環境更安全時才會現身。為了在新興市場立足,華為聚焦於地區定錨,例如,在俄羅斯獲得成功可以使它更易於進入前蘇聯國家。
華為在這些風險較高的環境中,磨練自己的推銷技巧,它的人員也變得更有經驗和外國人共事。它發展出一種強而有力的處方——結合低成本、快速完工,以及關注顧客,「華為的產品也許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麼樣呢?什麼是核心競爭力?」他問自己的團隊:「選擇我而沒有選擇你,就是核心競爭力!」
華為以急迫、堅持及耐心來追求國際市場。一九九七年,它藉由和俄羅斯的一家電訊公司共同成立合資企業「貝托華為」(Beto-Huawei),進軍俄羅斯市場,製造銷售交換機。翌年,俄羅斯政府的主權債券及貨幣違約,暫停商業銀行還款給外國債權人。
但華為有耐心,「緊接著的一場金融危機更像是一場大雪,將整個大地都冰封了」,最早被派去俄羅斯的一名華為員工回憶:「於是,我不得不等待,由一匹狼變成了一頭冬眠的北極熊。」兩年後,他見到任正非時,唯一能夠呈交的勝利是一筆三十八美元的電池合約,但任正非認為,當時離開俄羅斯仍嫌太早,「如果有一天,俄羅斯市場復甦了,而華為卻被擋在門外,你就從這個樓上跳下去吧!」他開了個黑色玩笑。
中國政府為華為早年進軍海外開啟了大門,例如,在俄羅斯,中國大使出手干預,幫助華為的合資企業通過審核。一名前華為員工承認,「政治考量是突破僵局的唯一力量」,他還撰寫了一本書讚美華為的成就。二○○一年迎來了重大突破,俄羅斯政府的考察團造訪華為總部,簽了一筆一千萬美元的合約。到了二○○三年,俄羅斯成為華為的最大市場之一,年營收超過一億美元。任正非的堅持獲得了回報,他利用中國政府的能力也得到了成果。
華為一直掙扎、困頓於建立品牌,海外顧客無法正確唸對它的名稱發音,並且把中國和低科技、低品質產品聯想在一起。一家俄羅斯當地營運商在得知貝托華為是中國公司時,該公司主管問道:「中國的高科技公司?你們不是賣電水壺的吧?」
華為的員工還在學習,但他們願意前往西方公司不願意去的地方。一名勇敢的華為員工,在俄羅斯待了十三個月後,同意前往葉門幫助建設該國的國家網路,「葉門國家窮困,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艱苦,高溫、高海拔,衛生、交通、安全都很差,」他回憶:「烈日當頭,停電,酷熱難熬,睡在地窖。」33回憶自己的工作時,他解釋:「其實,比較自己小時候在貧窮的湖南農村長大,光著腳丫子在田埂上跑的日子,我覺得不苦。在華為,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華為的彈性使它能夠在大不相同的市場上成功。一九九九年,該公司在非洲的第一項工程是,在肯亞安裝行動通訊網路。一名華為員工抵達肯亞首都奈洛比的西北方、約九十六公里處的大城鎮「奈瓦夏」(Naivasha)時發現:「旅館房間裡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洗澡設施。」接下來九個月,他設立系統,解決種種問題。某天深夜,因為用戶使用的華為設備飄出異味,華為人員去更換零件,緊急進行測試,忙到凌晨三點多。翌年,他轉調至衣索比亞,建立相同的行動通訊網路,那裡的高山地勢挑戰性更大,為了保證支架的穩固,耐得住強風,系統的天線支架需要經過特殊加工處理。他在《華為人》這份企業內部刊物中,回憶自己在非洲時遭遇流鼻血、飲食不適、孤獨、折磨等等困難。
更顯著的是,華為成功應付不同類型的顧客。肯亞和衣索比亞是鄰國,但它們的電信業生態大不相同。在肯亞競爭時,必須競標開口合約,並和其他私人公司(例如伏德風)合作;反觀衣索比亞,政府壟斷電信業,阻絕大多數西方公司。華為在這兩種不同環境下都成功贏得合約,靠的是向當地政府官員獻殷勤,提供最低價格,快速完成工程。儘管被控行賄並且受審定罪,也無法減緩華為的推進速度,到了二○一九年,據估計,非洲的4G網路有七○%是華為建設的。
華為的公司文化推崇犧牲自我,任正非把吃苦耐勞視為對員工的期望,而非例外。「很多國家很貧窮,有些國家還有瘧疾。」他在二○○○年告訴員工:「海外員工沒有太多補償,與國內工資相差不大,主要是華為員工的奮鬥精神。」二○○六年的一次內部談話中,喜歡誇大的任正非估計,在非洲工作的華為員工有超過七○%感染了瘧疾。
華為員工敘述他們的海外經驗,讀起來就像往昔的新世界移民和未來科幻探險者的混合版,十七世紀移民北美洲的清教徒遇上科幻電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我們生活在一個名叫『夢境』的小區裡。」一位在蘇丹工作了五年的華為員工寫道:「矮矮黑黑的小屋子裡,上下鋪七、八個人擠在一間……我們房間前面的一間破屋就是客戶的營業大廳。」蒙大拿州格拉斯哥鎮雖然地處偏遠,但相較之下,算是奢華了。
華為公司很快就遺忘個別員工的悲劇。當任正非開玩笑地告訴那個去俄羅斯開疆闢土的員工,若華為在俄羅斯的創業不成功,他可以去跳樓時,那名員工聽了可以莞爾一笑;但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二○○六年至二○○八年間,華為有六名員工非自然死亡,包括三名自殺。
批評者說,任正非首要關心的不是員工的安全,而是公司的獲利。二○○七年,華為付錢解雇七千名年資較長的員工,再和他們簽新的短期合約,這行動被廣為批評是為了逃避新的中國勞動法規——容許服務年資達十年或以上的員工,可以與公司簽立開放合約。華為還在二○一三年舉行董事會「自律」宣言宣誓大會上,做出種種宣誓承諾,其中包括:「我們熱愛華為,正如熱愛自己的生命。」
就連談到員工的安全時,任正非也忍不住提到費用與獲利。他在二○一五年時,向員工解釋:「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確保他們安全,避免做出更危險的事。」他指出,華為在葉門的辦事處:「可以在室內安裝鋼板,用膠合玻璃取代窗戶玻璃,使用機械式通風系統……葉門辦事處只需支付安裝成本。」他又說:「當我們在面臨戰爭或暴亂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去供應產品或服務時,我們的產品價格就應該調升……我們不是想敲詐誰,但必須讓那些營運商了解我們的情況,這樣,我們在小國家的生意才不會虧錢。」
華為這種我行我素的態度與行徑,有時也會引發逆火。到了二○○○年,該公司已在古巴、緬甸及伊拉克設有營運據點,這些全都是遭美國制裁的國家。二○○二年,華為被譴責違反聯合國對伊朗的禁運制裁,供應可用於空中防禦系統的高科技玻璃纖維零組件給伊朗。根據向《華盛頓郵報》洩露的文件內容指出,華為也幫助北韓政府興建及維修無線網路。二○一八年,美國指控華為違反對伊朗的制裁,加拿大當局逮捕任正非的女兒、華為財務長孟晚舟。
華為進軍外國市場時,美國大都漠視,有時甚至幫助它。二○○三年初,當情勢看來美國愈來愈有可能入侵伊拉克時,華為開始偵察機會。二月,美國入侵的一個月前,一名華為員工前往伊拉克的庫德族半自治區,洽談擴展行動通訊網。「一天天,伊拉克的形勢日益緊張,美國大兵日漸完成攻擊的部署,戰火真的很快就要燃起了。」這名華為員工回憶。但戰事的展開似乎只是暫時性阻礙,「伊拉克市場重新拓展的決策擺上公司高層的議題」,該員工解釋。到了五月,他返回伊拉克北部,繼續原先的計畫。
美國入侵伊拉克,對華為而言是個禮物,是一大幫助。為了破壞敵人的通訊,美國軍隊在攻擊行動中,破壞伊拉克的電信基礎設施,戰後,華為樂得幫伊拉克重建。二○○七年,當絕大多數西方公司在考量安全環境而迴避機會時,華為贏得了一筆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合約,幫助伊拉克建設起無線網路。二○一三年,一名華為員工回憶他在伊拉克工作的五年:「底格里斯河畔升起煙霧,空中響起迫擊砲聲」;「發出低沉聲的美軍悍馬及坦克在街道上巡邏」;「為了慶祝成功推出新網路及獲得新合約,而舉行宴會」。
華為也在阿富汗找到機會。二○○三年,阿富汗政府和華為及中興通訊簽下行動通訊網路的合約。翌年,阿富汗最大的行動通訊服務供應商「羅山電信公司」(Roshan Telecom),跟美國與日本位居最大股東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取得申貸。羅山原本預計向阿爾卡特及西門子購買電信設備,但進一步檢視後,亞洲開發銀行同意以華為設備取代,它說華為的設備:「壽命週期成本較低,架構彈性較高。」美國及盟軍為華為的工程提供安全保護,正如同當中興通訊在阿富汗興建寬頻網路時,他們也同樣守衛他們。
華為員工在阿富汗工作,忍受艱辛環境與條件。美國在二○○九年宣布增派阿富汗駐軍後,華為立刻增加派往阿富汗的人員數目,擴大在阿富汗的營運。一名華為員工撰文回憶:「我們的本地員工曾被挾持……在辦公室裡,我們一直放著幾件防彈衣,辦事處有兩個同事感染了傷寒。」在外國資金湧入,安全環境改善之下,華為在阿富汗的辦事處員工人數,從二○○九年初的一名常駐人員,提升到翌年的二十名;很快地,華為便和阿富汗的所有四家電信服務供應商簽約合作。阿富汗的第二大行動通訊服務供應商「阿富汗無線」(Afghan Wireless),是美國公司和阿富汗政府所共同持股的公司。在二○一七年五月推出阿富汗的第一個4G LTE網路,使用的就是華為的設備。
華為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擴張,引發不少人對美國戰略或美國究竟有無戰略的不安與質疑,一位亞洲國家的外交部長告訴美國知名的中東專家學者強‧奧特曼(Jon B. Alterman):「美國在中東奮戰了二十年,但什麼也沒贏得;中國沒奮戰二十年,卻一直在贏。」美國耗費龐大的財務及人員成本,提供保安;中國的企業則利用這些,取得了新的商業機會。在美國終於清醒,看出華為造成國安威脅之前,美國軍隊在海外的行動實際上是倚賴華為設備的。
到了尼蒙電話合作社,在格拉斯哥鎮及其他鄉村地區,為其3G網路尋找供應商時,華為早已具備在偏僻、困難地區建設網路的長足經驗。縱使在歐洲城市擴張業務及贏得合約之際,華為仍然把鄉村地區和開發中市場視為攸關成功的重要因素。華為建設的網路為派駐伊拉克的美國政府人員、攀登聖母峰的登山者,以及愈來愈多的人類提供連結服務。「我們從事的是為社會提供網絡……無論在缺氧的高原、赤日炎炎的沙漠、天寒地凍的北冰洋、布滿地雷的危險地區、森林、河流、海洋……只要在地球有人的地方,都會覆蓋。」任正非在二○一一年這麼告訴華為員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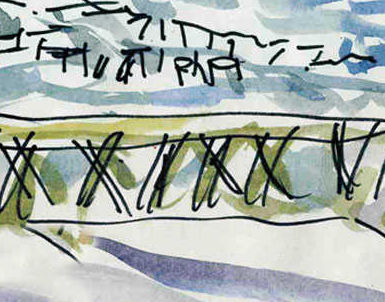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