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穿越錄:行過兩界千山,皆有佳人回盼,第十二章,看的見題目的人

窗外的新埔市夜色仍在流動,遠處偶爾傳來車聲,像是與這間房間毫不相干的世界。
沈硯仍被定在床上,連呼吸都不敢太用力。因為整個人還沒從方才的混亂中回過神來。
顧宛心跪坐在床邊,一動不動。她的目光,落在沈硯腰際。
那裡——
方才高張的「患部」,此刻已明顯平復下來。
不再躁動,也不再緊繃,只餘下一種剛歷過風浪後的疲倦與沉靜。
顧宛心靜靜看了好一會兒。
像是在確認症狀是否真正消退,又像是在回想方才的每一個細節。
終於,她輕輕鬆了一口氣。那聲氣息極輕,卻帶著如釋重負的意味。
「……原來如此。」
她低聲自語,像是在心中記下一筆醫案。
隨後,她抬起手。
纖細的指尖在空中輕輕一點,原本纏繞在沈硯四肢上的陰冷束縛,無聲地散開。
沈硯只覺得身上一輕,血液重新流回四肢,整個人幾乎是本能地長長吐出一口氣。
「……終於。」
他的聲音沙啞得不像話。
顧宛心卻沒看他,只是微微點頭,語氣認真而平靜:
「患部已消腫,氣息亦歸於平順。」
「看來……施術是有效的。」
她語氣篤定,像完成了一件該做的事。
而沈硯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只覺得——
這句話,無論怎麼聽,都讓人心情複雜得要命。
房間,再度陷入靜默。一人,一鬼。就這樣,在夜色裡,呆坐了一會兒。
方才沾染在顧宛心身上的黏膩與濕潤,無聲逸散,彷彿從未存在過。
空氣重新歸於清冷。
顧宛心低頭,將那件破碎的白色喪服重新披回身上。
衣料殘舊、邊角破損,卻被她整理得一絲不苟,像是在為自己收尾,也像是在為方才的一切畫下句點。
她神情平靜,甚至帶著一點完成任務後的安心。
沈硯躺在床上,眼神放空。那是一種靈魂被抽乾後的「死目」,連吐槽的力氣都懶得擠出來。
過了好一會兒,他轉過頭來看著顧宛心,輕輕開口:
「……謝了。」
說完這句,他自己都忍不住在心裡苦笑。
顧宛心聞言,微微頷首。她站在床側,語氣溫和、篤定說道
「如此一來……小女子便明白了。」
沈硯眼皮一跳。
她抬起眼,語調依舊輕柔,甚至帶著一絲安心地微笑:
「日後若公子再有相同症狀,該如何施術……宛心已記住了。」
沈硯:「…………」
這丫頭到底在說啥阿……
沈硯的靈魂,徹底沉默了。他望著天花板,眼神死得不能再死。
這一整晚,
他的人生觀、世界觀、還有對「醫療行為」的理解——
全部被重新格式化了一次。
疲憊的他換下了穿越時穿的古裝,換上了他那身不算特別乾淨的居家服
牙也沒刷,澡也沒洗,往床上一倒便緩緩睡去
…
……
………
——隔天早上。
沈硯走在街上。
一身普通便服,沒有任何多餘裝飾,
背上背著一個看起來再尋常不過的背包。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背包裡,用毛巾層層包裹著的,
是一顆足以讓各界震驚不已的玉石。
他是從家裡「逃」出來的。
原因很單純。
那個知識結構嚴重歪掉的女鬼,
在天色微亮、陰氣尚存之際,
竟然又用一種極其認真、極其專業的眼神,
對他清晨的某些自然生理現象——
產生了「需要立即處理」的誤判。
甚至還非常體貼地補了一句:
「公子不必擔心,這次宛心已熟悉流程。」
沈硯當場魂飛天外。
幸好清晨陽氣初升,
她凝實的力量遠不如夜裡,
他才得以掙脫那份過於「貼心」的醫療關懷,
其實說起來,他也不是什麼初出茅廬的童子雞。
混保險這行的,哪個沒陪過幾個大老闆應酬?
酒局、夜店、招待所,該見的不該見的,多少也都見過。
逢場作戲的笑、按著價碼來的溫柔、
燈光一暗就能複製貼上的親暱——
他從來不陌生。
只是那些東西,說到底都很「清楚」。
清楚得像帳單一樣,明碼標價,來去分明。
可顧宛心不一樣。
沈硯很清楚,
那不是經驗、不是技巧、也不是刻意取悅。
那是一種他此生未曾在任何女子身上見過的存在感。
不是風月裡的艷,
也不是人間的媚,
而是像誤入塵世的一段清光,
只要靠近,就會讓人忘記比較。
老實說——
若要他在記憶中列出所見過的女子,
顧宛心,毫無疑問,是最美的那一個。
完爆他這輩子在風俗場所見過的任何一個女人。
這也是他為什麼會——
連一句完整的拒絕都說不出口。
……
不過,直到此刻站在街頭,被晨風吹了一臉清醒,
雖然人是逃出來了。
但問題,並沒有跟著消失。
沈硯站在人行道邊,背包沉甸甸地壓在肩上,他低頭看了一眼背包拉鍊。
——裡面那顆東西,
不是普通石頭。
不是紀念品。
而是一顆足以改寫他人生的玉石。
「……可是,現在要怎麼辦?」
他在心裡喃喃。
賣掉?肯定是要賣掉的
問題是——要賣給誰?
他腦中浮現第一個畫面,是自己把背包打開,蹲在路邊,對著路人喊:
「來喔來喔,古代穿越回來的頂級翡翠,一顆五億不二價——」
下一秒畫面就變成警察把他押上警車,旁邊還有精神科醫師搖頭嘆氣。
「不行……絕對不行……」
這種東西,
不是菜市場能處理的。
也不是網拍能上架的。
更不可能拿去銀樓說一句「老闆幫我估個價」。
他一個連玉跟玻璃都分不太清楚的市井小民,
突然手裡多了一顆能買下一整條街的璞玉——
唯一的下場只有一個:
被坑到連骨頭渣都不剩。
沈硯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腦子裡一片空白。想著想著,他抬起頭。
前方街口的路標上,幾個字映入眼簾——
「新埔古玩市場」
沈硯腳步一頓。
那地方他聽過。不算太乾淨,
也不算太光明正大,
他深吸一口氣,握緊背包的背帶。
「但至少……總比在路邊亂賣強吧。」
於是,沈硯轉了個彎,
順著街道的陰影,
朝著古玩市場的方向走去。
…
……
………
古玩市場的入口,比他想像中熱鬧得多。
還沒踏進去,聲音就先撲了上來——
吆喝聲、討價還價聲、金屬碰撞聲混在一起,
像一鍋煮過頭的雜湯,濃得發燙。
一排排臨時攤位沿著老街鋪開,
紅布一掀,玉石、瓷片、銅錢、佛牌、殘卷亂七八糟地堆著。
有的老闆一臉篤定,指著一塊發白的石頭說是「唐礦原皮」;
有的則半躺在藤椅上,嘴裡叼著菸,
一句「喜歡就拿,真假隨緣」說得漫不經心。
不遠處,還圍著好幾群人。
有人蹲在地上抽盲礦,
一塊一塊石頭被敲開,
人群隨著每一次裂響發出低呼或嘆息,
像是在賭命,又像在拜神。
也有情緒更激動的——
開出一線綠光就歡呼,
什麼都沒有的則當場黑臉,
嘴裡罵罵咧咧,卻還是不肯離開。
再往裡走,風格卻突然變了。
市聲漸低,地面換成了拋光石板。
一間間高檔古玩店整齊排開,
玻璃櫥窗裡燈光柔和,
玉佩、翡翠、古玉一件件躺得端正。
門口站著穿旗袍的迎賓小姐,
高叉貼腿,步伐輕巧,
笑容拿捏得剛剛好,
像是訓練過的風景。
沈硯下意識地移開目光。
不是不想看,
而是——不敢。
背包裡那顆籃球大的玉石,
此刻像有重量般壓在他背上。
他總覺得,只要多看一眼、慢一步,
就會被人看穿。
於是他低著頭,加快腳步。
就這樣,
他在市場裡繞了一圈,又一圈。
從熱鬧的攤販走到安靜的內街,
從喧囂的盲礦區走到冷氣充足的精品店,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腳步卻越來越沉。
兩個多小時後,
他終於把整個古玩市場走完了一圈。
卻什麼都沒做。
他停在街口,
站在人來人往的縫隙裡,
背包還好好地背在肩上。
其實一路上,
他不是沒看到專門收玉、收原礦的店。
招牌都寫得很清楚。
「現金收購」、「高價回收」、「專業鑑定」。
只要推門進去,
事情或許就能開始。
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不敢。
不是怕被騙。
也不是怕被壓價。
而是一種說不上來的直覺。
因為那顆玉,太大了——
大到不是「隨便找一家店就能處理掉」的東西。
整個市場逛下來,他幾乎把能看到的玉石都看過了一遍。
無論是攤販上擺著的原礦、
還是櫥窗裡打著柔光的成品玉件——
沒有一塊,
能和他背包裡那顆相比。
甚至就連那間看起來最氣派、
玻璃櫃後站著旗袍迎賓、
標榜「鎮店珍藏」的精品古玩店裡——
陳列在展間中央、
被稱作鎮店之寶的那塊頂級玉石,
體積也不過是他背包裡那顆的一半。
沈硯站在街口,
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
錢,
並不是只要值錢,
就能輕易換成現實的。
正想著算了,乾脆先回家,
再慢慢想該怎麼處理時——
他的腳步卻不由自主地慢了下來。
街角陰影裡,
有個不起眼的小攤。
不是賣玉的、不是收礦的,
甚至連算命都不像。
一張舊木桌,一把竹椅,
桌後坐著個乾瘦老頭,眼皮半垂,像是隨時會睡著。
真正讓沈硯停下來的,是桌前立著的一塊手寫木牌。
上面只寫了八個字。
「若可解謎,贈金十萬。」
十萬新幣。
不算小錢,卻也不至於讓人瘋狂。
真正詭異的是——
桌上攤開的紙張,一片空白。
沒有題目,沒有字,沒有圖。
乾乾淨淨,就是一張白紙。
沈硯站在那裡看了兩秒,忍不住在心裡嗤了一聲。
「……搞什麼。」
他很快得出結論。
大概又是哪種博人眼球的把戲,等人上鉤再臨時編題目,
或者乾脆只是這老人家想找人聊天解悶。
正當他轉身、準備離開的那一刻——
胸口,微微一燙。
不是痛。
不是炸裂。
而是那熟悉……被輕輕碰了一下的感覺。
沈硯的腳步,瞬間停住。他愣了一下,下意識地按住胸口。
「……?」
那塊印章碎片。自從昨晚之後,一直像死了一樣安靜。
偏偏在這裡——
在這張什麼都沒有的桌子前,
居然有了反應。
沈硯皺起眉,慢慢轉回頭。
他再次看向老頭。
老頭依舊低著頭,像是睡著了。
他又看向桌面。就在他的視線落下的瞬間——
那張原本空白的紙,
像是被什麼看不見的手輕輕劃過。
一行字,
極慢、極慢地浮現出來。
彷彿不是被寫上去的,
而是從紙裡滲出來的。
——
「一加一等於?」
沈硯:「……」
他盯著那行字,整個人僵了兩秒。
然後,一臉無語。
「……這啥問題?」
一加一等於二。
小學生都知道。
十萬新幣?
就為了這?
沈硯盯著紙張看了兩秒,終於忍不住抬頭,看向那個老頭。
「只要解謎,就給十萬對吧?」
他的語氣已經有點不耐煩了,「不反悔?」
老頭這才慢吞吞地抬起頭,像是剛睡醒似的,伸手抹了抹嘴角掛著的一點口水。
「喔……喔喔,對。」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眯著眼看向桌面。
「那……答案是什麼?」
沈硯:「……」
他沉默了半秒,實在懶得再陪這種怪人繞圈子。
因為他不相信對方會真的付錢。
「一加一等於二。」
他語速很快,語氣敷衍到不行。
「一加一=二,十萬給我,趕快,我要回家了。」
話音剛落。
老頭的眼睛,猛地睜大。
那不是誇張。
而是一種——像是聽見什麼不該被聽見的東西。
「你……」
老頭的喉嚨動了一下,聲音突然變得有些乾澀。
「你……你看得到題目?」
沈硯眉頭一皺。
「你這不是廢話嗎?」
他語氣更不耐煩了,「就在紙上啊,我又不是瞎子。」
老頭的視線,卻沒有再落回紙上。
而是——
緩緩移到了沈硯的臉上。
那一眼,看得沈硯莫名有點不舒服。
「……對,看得到。」
沈硯乾脆直接承認,「怎樣?」
下一秒。
老頭忽然轉過頭。
不是轉向沈硯。
而是——轉向桌子旁那片空無一物的空氣。
他張開嘴,低聲說了幾句話。
聲音壓得極低,
像是在念什麼,又像是在詢問什麼。
沈硯完全聽不清。
只覺得那畫面——說不出的怪。
就在那一瞬間——
一股涼意,忽然從他身側掠過。
不是風。
更像是什麼無形的東西,貼著他的肩、他的背,
輕輕滑了過去。
沈硯下意識地打了個寒顫。
「……?」
那感覺很快就消失了。
快到讓人懷疑是不是錯覺。
老頭沉默了一會兒。
接著,他才慢慢轉回頭,
臉上的神情,和剛才已經完全不同。
不再渙散。
不再漫不經心。
而是一種——終於確認了什麼的神色。
他低低地吐出一口氣,像是在對誰下結論。
「……原來如此。」
老頭忽然哈哈笑了兩聲。
那笑聲不大,卻低啞得很,像是憋了很久,終於能吐出來似的。
他伸手,把桌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一樣一樣收起來——
舊紙、破布、那張方才還浮著題目的白紙,全都被他隨手疊好,塞進桌下的木箱裡。
動作輕快得不像個剛才還流口水的怪老頭。
「唉……」
他一邊收,一邊搖頭感嘆,語氣竟帶著點釋然。
「在這兒擺攤擺了大半年了。」
他抬頭看了沈硯一眼,眼神清亮得不像剛才那個人。
「今天啊,總算能收攤了。」
沈硯眉心一跳。
還沒來得及接話,老頭已經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像是終於等到正主般,語氣一下子直截了當起來。
「小子。」
「那十萬新幣,我給你。」
沈硯一愣,下意識張嘴:「喔……那——」
話還沒說完。
老頭的視線,已經落在了他背後。
準確地說——
落在他背著的那個、用毛巾裹得嚴嚴實實的背包上。
老頭眯起眼,嘴角勾起一個意味深長的笑。
「然後。」
他慢條斯理地補上一句。
「你背上那個東西——」
沈硯心臟猛地一縮。
老頭語氣平靜得像在談一件再普通不過的買賣。
「我出十億新幣。」
「跟你買。」
空氣,瞬間靜了一下。
「怎麼樣?」
沈硯心臟猛地一沉。
「……你怎麼會知道?」
這個念頭幾乎是本能地炸開。
十億。
不是試探,是篤定。
那一瞬間,危機感像冷水兜頭澆下來——
他根本來不及細想,身體已經先一步做出反應。
跑。
他猛地轉身,背包一沉,腳才剛踏出去半步——
下一秒。
「——!」
他的手臂,被死死拉住。
力道之大,甚至讓他整個人踉蹌了一下,差點失去平衡。
「放——」
話卡在喉嚨裡。
沈硯轉頭。
拉住他的,不是老頭。
而是一隻手。
纖細、修長、指節勻稱,肌膚白得近乎冷色。
看起來柔弱得不該有任何威脅性——
可那隻手扣在他手臂上的力道,卻穩得驚人。
像鋼索。
像鉗制。
他用力一掙。
——完全掙不開。
沈硯呼吸一滯,順著那隻手往上看。
站在他身旁的,是一名女子。
一身合身的秘書裝,剪裁俐落,線條乾淨,裙襬筆直貼合,沒有多餘裝飾。
姿態端正,像是隨時準備記錄、執行、完成任務。
她戴著一副細框眼鏡。
鏡片後的眼神冷靜、理性,幾乎沒有情緒。
容貌極美,卻不是柔媚的那種。
而是那種——
讓人下意識挺直背脊、不敢輕佻對視的美。
可真正讓沈硯背脊發涼的,不是她的長相。
而是——
她的存在感。
明明就站在那裡,
輪廓清楚、觸感真實、手臂的力量壓得他生疼。
可不知為何——
她的身影,卻像隔著一層薄霧。
不是人群中那種扎實的「在場」。
而是一種……
介於「有」與「不在」之間的狀態。
那種感覺——
沈硯太熟了。
熟到胃部一緊。
昨晚。
顧宛心。
夜深陰盛、魂體凝實時——
一模一樣。
他喉嚨發乾,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妳是……?」
女子沒有回答。
只是推了推眼鏡,視線冷淡地掃了他一眼,
那目光像是在確認一件物品是否安全到位。
然後,她的手——
依舊沒有鬆開。
這時,老頭才慢悠悠地開口。
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起身,雙手背在身後,臉上掛著那種「事情終於對上了」的笑。
「年輕人,別害怕。」
他的語氣,和剛才談十億時一樣平靜。
「她沒惡意。」
「只是習慣先抓住人。」
老頭眯起眼,看著沈硯,語氣意味深長地補上一句:
「你也——看得到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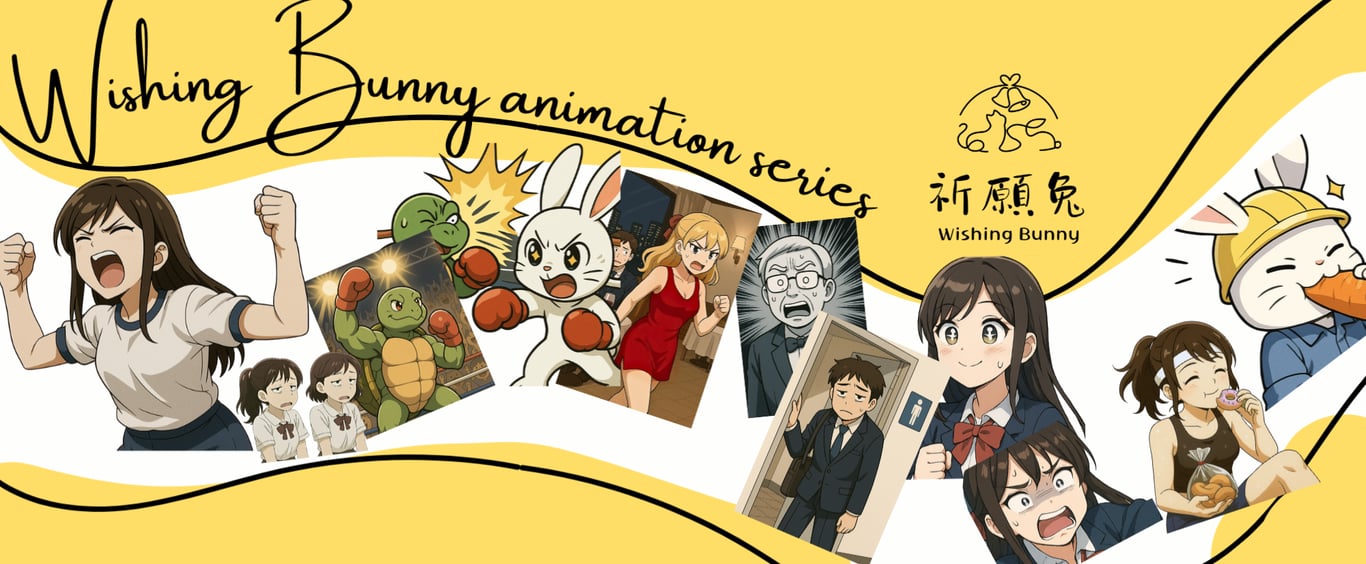
祈願兔商場:shopee.tw/ayasuzu827
祈願兔YT:www.youtube.com/@wis...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