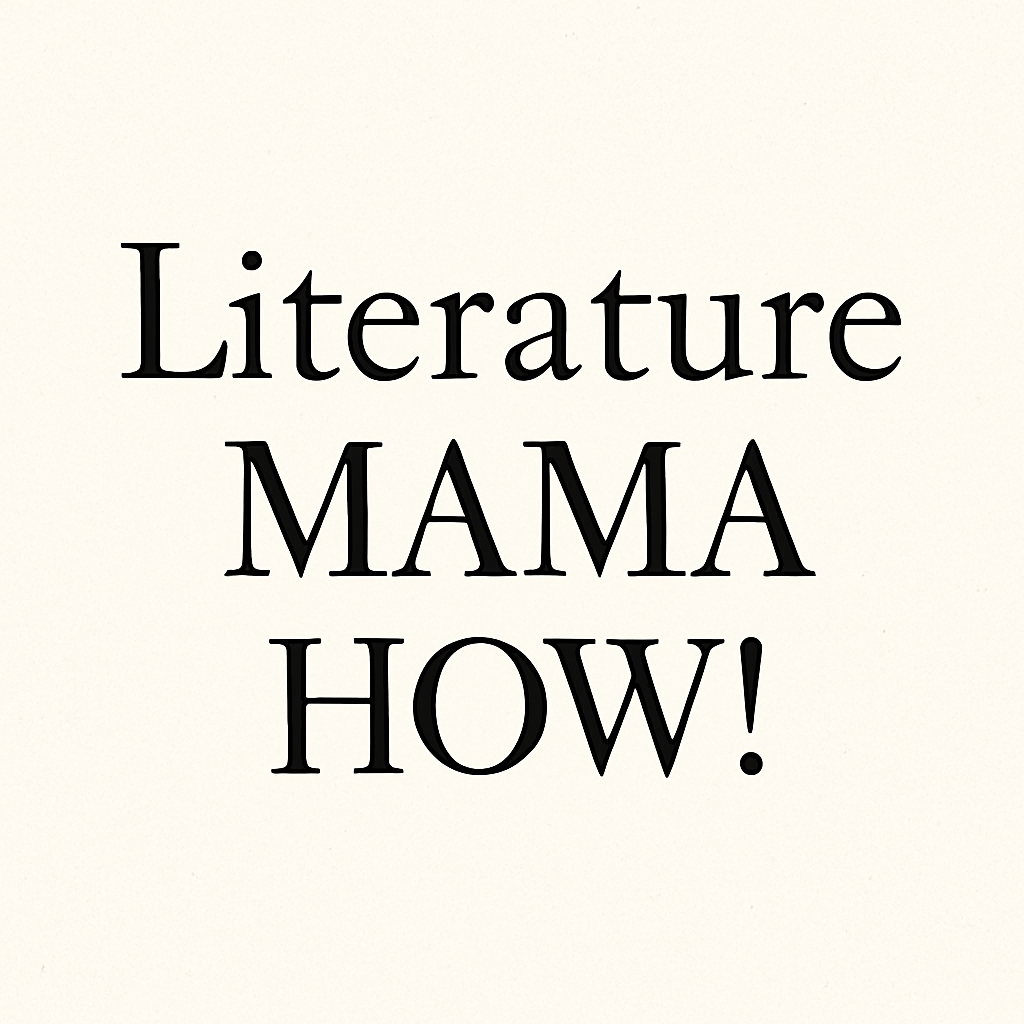鬼的呢喃:傅柯《外邊思維》對談
老師:
思考了好多談論《外邊思維》的方法(就好比思考了好多創作的方法),來來回回、反反覆覆,最後總會停留在「呢喃/竊竊私語」以及「瘋狂」之上。
對傅柯來說,文學寫作似乎就是那條通向彼端,如同通過黑洞(那裏存在著什麼呢?死亡?或者死亡的背反?)一般的曲徑。書寫者透過瘋狂的呢喃,在此一曲徑上展現出文學語言越渡的力量,藉以獲得自由(相對於論述語言具有確定性的侷限與束縛),或是真正的消抹了主體的肉身,弭除主與客之間的疆界,得到並成為了某種已逝經驗(歷史)的臨在,然而,我們都明白,那些透過書寫語言而再現回來的經驗或事件(所謂的死而復生)都並非真實;它們都僅僅只是被語言文字,召喚至一個充滿鏡面的中介空間的內部,成為其無限分生增殖出來的複象罷了。
在這滿佈鏡像的空間內,語言(與其再現的經驗)折射出各式奇異的面貌,有的指向外部(他者),也有的從原點出發,刺穿他者的表象,繞了一圈,反向回到內部,成為對於書寫自身的指涉(一種向內的挖掘)。
據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也許有理由將所有的文學作品(小說、散文和詩)都視為是虛構的:因為再現真實,僅作為一種對世界的瘋狂的譫妄;而書寫,則是基植於此一瘋狂地基之上,不斷向上構築的語言實踐的大廈──我們在這棟大廈蜂巢般擁有明確結構卻又同時令人感到眼花撩亂的空房內,是否都曾留存過些什麼呢?
這幾年(也許至今依然如此),常感語言的空洞性與創作上缺乏動能的無力感持續蔓延(像侵蝕主體岩岸的浪潮不斷拍打)。曾暗自將原因歸咎於經驗的匱乏與幻滅,作為一個書寫的主體,書寫有的時候只是手持一把將一切經驗燒毀的火種,那些被「我」以文字構築的巢穴,往往堆放著不知從何處回收而來的陳詞爛調(曾經有機的意象逐漸覆滅之際,我們還能否獲得一種更新的可能,藉以挖掘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通道?)。
然而也許在傅柯那裡,答案並非如此。
傅柯認為,作品會被作品的缺席所威脅,然而,作品要透過這種缺席的狀態才能夠抵達我們。現代的文學書寫不再是以神聖的話語或先前的書寫傳統作為其資源:它恰恰是源自於一種空無,這種空無先於它存在並支持著它(《傅柯考》:63)。
如果我們將書寫這件事定位成對於經驗的追企,而經驗往往在被我們寫下的那一刻便逸失了,因此不斷擦拭、塗改、來來回回,不停的追尋;從這點看來,修改的過程或許才是書寫的核心;亦即,不厭其詳的重複說出已說出的內容,重新通過語詞使用過後所造成的褶皺。在語言之前,除了語言本身之外,別無他物。
這樣一種無止境的重複行動,不應被理解為掏空的習練;而是複象的生產(《傅柯考》:61-62)。它並非自我重複,或如同囤物癖般,反覆地蒐集、推疊,最終只會將整間房子撐破(這也許才是我之所以常感被語言反噬的真正原因)。因此,消抹和塗改是必要的:即透過消除,騰出一個新的距離與空間,並再次將這些由語言自我繁衍出來的複象、記憶的碎片(陳舊的雜物),重新吸納進去。
然消抹並非指涉真正意義上徹底的死亡。「所謂『文學經驗』其實就是『沒有我』的『我的意識』,因為文學經驗的對象正是經驗的極限本身……這種『沒有我』的『我的意識』仍然是對於這『沒有我』的狀態的『意識』,所以它不是澈底的死亡,因為死亡將會是意識的完全泯滅;它只能永遠逼近死亡這界限。」(《外邊思維》:42)
其中的弔詭之處,莫過於:當書寫不斷地將主體帶向死亡這條界線的同時,主體又得盡一切可能地去抵抗真正的死亡所給予它的侵擾。
又或許種種努力與抵抗,終會導向一種「庸人自擾」罷。像常人所言:想那麼多幹嘛呢?
大概是因為處女座個人的某種潔癖傾向(或者神經兮兮的強迫症),常為房間裡的灰塵所困擾。灰塵的存在彷彿敵人環伺,必須要透過反覆地擦拭、消滅,才能重新感到自己在這房間的區域內是足夠安全的。
但灰塵是永遠無法被抹除的。畢竟其某部分的成因也是來源於自己本身(人體的皮膚細胞、毛髮、纖維也是灰塵的組成成分)。擦拭於此成為一種永無止境的實踐。在舊的骨架上長出新的肉身,然後又被沾了水的抹布剔除,像莫比烏斯環,循環往復、生生不息。
有時不免為此覺得徒勞。尤其是在特別缺乏能量的時候。或者最終選擇放棄,高舉白旗,與無處不在的灰塵妥協(如同巴黎議會決議讓巴黎人與持續了幾個世紀的鼠患共存)。
好幾次夢到滿溢的灰塵將自己吞噬,驚醒過來,在天色猶暗的三、四點鐘,拿起抹布著了魔般擦拭。
這何嘗不是一種「瘋狂」呢。夜半時分,在來回消抹的過程中,漸漸入了迷;本以為自己是在收復那些被灰塵沾染的失土,卻不知不覺間登上了一艘航向未知的愚人船,漂流在失去座標的海域,述說著關於另一個世界(宇宙經驗)的純粹幻象──沒完沒了的呢喃。
而驅動著這一切的燃料,到底是什麼呢?
蟄伏在潛意識內的執著?已逝經驗鬼魅般的猝然降臨?還是那些纏繞於腦中始終揮之不去的遙遠回音?
是什麼東西迫使著你在追索經驗的途中頻頻折返、回頭張望,抱持著一種眷戀不捨卻又篤定萬分的訣別姿態呢?
不知道。也許這一切本就毫無邊界可言。我們無法真的以肉眼辨認存在於遠方的模糊疆界(視力檢查時,筆直長路盡頭的那棟紅屋是真的存在嗎?)。而每每在我們自認即將抵達伸手便可觸及的境地時,那條若有似無的線,就又會(調皮的)向後倒退一步,彷彿正與你進行著一場你捉我躲的遊戲:有的時侯你以為躲避鬼的人是你,卻只是在一個回身的瞬間,發現自己佇立在一面鏡子之前,手足無措地成為了眾人爭先迴避的那隻鬼。
可也有的時候,是人是鬼,唯獨你一人知道。
柏勳

柏勳:
讀完你的筆記,覺得你這一年來成熟很多,因為這不是一本容易讀也容易理解的書,但你梳理得很好(這是真心話!)。
我一直覺得,《外邊思維》是一本有內爆過的人才能讀懂的書。那涉及到寫作這件事的內在危機,作者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以及被召喚回來的複象(如你所引的傅柯考所言),如何以群象之足,將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那條界線踩踏乃至弭平。何況,見證過這種風暴的人,不見得能夠順利越渡過那片尤里西斯之海,將「外邊」攜帶回有語言的世界,賦予它名字。
這其中,其實需要動用心靈意志與肉體,以撐開一個魔物的世界。這種反噬感,推到極致,是會使眼前所見之物和它的名字分裂開來,最終吞噬掉現實的。
研究所時期我也有過一段類似的時光,那種類似把襪子翻過來,將世界吞進襪子裡的時期。一旦翻過去「那一邊」,即使是一模一樣的城市(被虛構召喚出來的),白日的日光大概也昏暗了一兩度。
我想迄今我仍很難定義那種經驗究竟是什麼?但這本小書,我想它應該是所有內向性的寫作,仍很重要的方法論吧。
過去讀這本書,我著迷於外邊裡海妖的歌聲,以及某種抗拒被空無吞噬的運動(可見的、物質化的、肉體性的),彷彿空無是書寫的永恆抗力。但這次重讀,你的筆記似乎對這個空無的運轉,有一個比較正向的意義,彷彿是空無的運轉以增生眼前幻象(無止盡無止盡的灰塵)。這本書,陡然其實有一種東方感吧(還是佛家?)!
這種零與一、一與多的悖論辯證,或許你提到的鏡面,就是語言這種裝置。
叔夏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