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治癒」到「生活品質」
從「治癒」到「生活品質」
過去,我們對醫療的期待幾乎一致:生病了,就要設法治癒。即使病人進入生命末期,社會與醫療體系也常本能地選擇「做所有能做的」,希望多爭取一點時間。這種思維深植在我們對疾病的想像裡:治癒等於勝利,放棄治癒等於失敗。
然而,隨著醫學的發展與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們漸漸意識到:並非所有疾病都能被治癒。生命末期可能來自癌症,也可能是心臟衰竭、肺部疾病、腎臟病,或是腦中風、失智症等長期神經退化疾病。在這些情況下,無止境的治療往往換來的不是更長的生命,而是更多的痛苦。
因此,一個新的醫療觀念開始被重視:與其執著於治癒,不如專注於生活品質。
一個真實的故事
2019年,一位懷孕末期的女性因腦幹中風突然昏倒,被送往醫院急救。雖然先生當下簽署了「不急救、不用藥物」的意願書,但醫療團隊依然插管、打針,因為在臨床上「救命」仍被視為天職。
她撿回一命,但從此全身癱瘓,只能用眼睛與外界交流。在後續六年的日子裡,家屬在醫院、復健與照顧兩個孩子之間奔波。
這位太太早已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與《病人自主法》的《預立醫療決定書》,明白表達過「拒絕延長治療」的選擇。但因為醫師普遍不認為腦幹中風屬於「末期」,因此她始終被餵養與維持生命,無法依照意願善終。
直到六年後,家人根據憲法保障的「拒絕醫療權利」堅持撤管,太太才得以在家中陪伴孩子和先生,度過生命最後的 17 天,平靜離世。
先生在最後一封寫給太太的信裡說:
「雖然只有短短 17 天,但我知道這是你六年來最快樂的日子。」
這是一段令人心碎的歷程,也讓我們清楚看見:即使簽了文件,如果缺乏家屬的理解與堅持,醫療現場未必會照著病人的意願走。
決策與責任:為什麼我們依賴專業者
人最怕的不是「做錯決定」,而是 承擔決定後的責任。責任太沉重,使我們傾向把重大決策交給手握權力的專業者:
醫師手握生死權,我們相信他們有知識與權力,所以可以替我們承擔後果。
位居高位的人做決定時,社會文化自動給予合法性,而普通人往往被默認「不應該表達意見」。
即便表達意見,也因缺乏專業身份而被忽視。
在生命末期的醫療決策中,這種心理結構非常明顯:家屬怕承擔責任 → 把生死交給醫師 → 醫師怕法律與道德責任 → 結果病人被延命而非依意願善終。
理解這一點,可以幫助家屬認識:勇於表達、參與討論,是尊重病人意願的前提。
家屬可以怎麼做?
在現行制度與文化下,光靠簽署文件是不夠的。家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託在專業者身上,因為:
醫師的任務是救命,他們對「末期」的定義往往嚴苛,傾向「不放棄任何機會」。
醫療法規雖保障病人有拒絕醫療的權利,但臨床上執行困難,醫師也常出於責任感而選擇繼續治療。
最了解病人想法的,往往不是醫師,而是家屬。
因此,家屬需要更積極地參與討論。這不是把專業推翻,而是把病人的價值觀帶進來,讓醫療不只是「延命」,而是「照著病人希望的方式活下去」。
與醫師討論時,可以從以下幾個問題切入:
這次治療的主要目標是什麼?
——是治癒、延長生命,還是緩解症狀、提升生活品質?能改善哪些症狀?效果持續多久?
——例如,是否能減輕疼痛、改善呼吸、恢復進食或行動?治療或手術的風險與代價是什麼?
——會不會讓病人短期內更痛苦?這樣的代價是否符合病人的價值?如果不做這項治療,還有什麼替代方案?
——藥物、支持性照護或緩和醫療,能否達到類似效果?
每個人都是「利益相關人」
在生命的盡頭,醫師、病人與家屬都不是旁觀者,而是共同決策的參與者。
不要期待醫師能替病人做完所有決定,也不要把醫療視為單向的專業指令。病人的價值觀、家屬的理解與支持、醫師的專業判斷,必須放在同一張桌子上,討論後才會有真正符合病人意願的選擇。
因為醫療的任務,不只是延長生命,而是讓人能活得有品質,並在最後走得有尊嚴。
行動建議清單
及早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AD):不要等到病危時才倉促決定。
定期與家人溝通:讓家屬清楚知道你的價值觀與選擇。
就醫時勇於提問:不要只聽醫師的建議,也要表達病人和家屬的想法。
尋找緩和醫療資源:在醫院或社區了解相關團隊,他們能提供更符合病人需求的照護。
建立「共同討論」習慣:把醫師、病人與家屬放在同一個討論平台,而不是誰替誰決定。
結尾思考
生命的盡頭,不只是生與死的問題,更是價值與選擇的呈現。每一次決定,都承載著責任與勇氣;每一次討論,都讓病人、家屬與醫療團隊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當我們敢於面對決策的重量,生命的最後時光,不再只是延續時間的長短,而是活出尊嚴與愛的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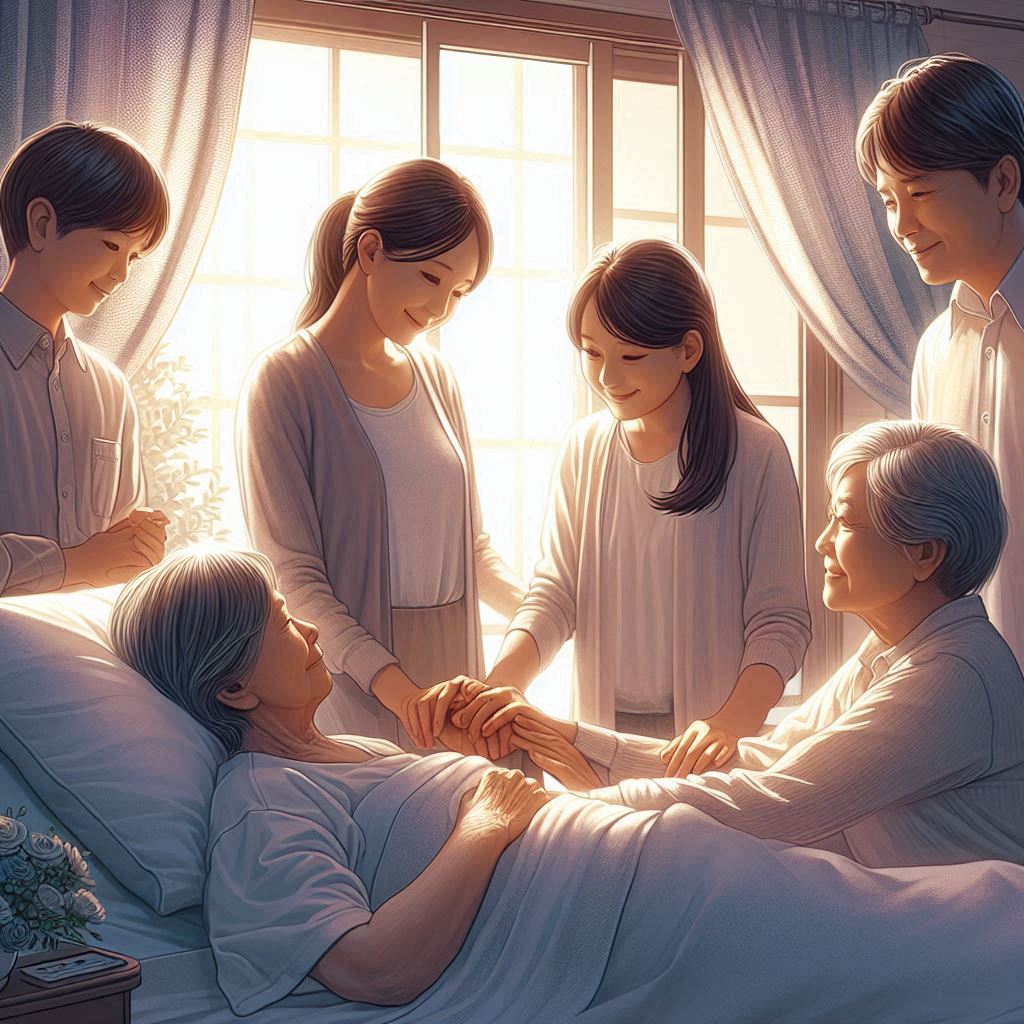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