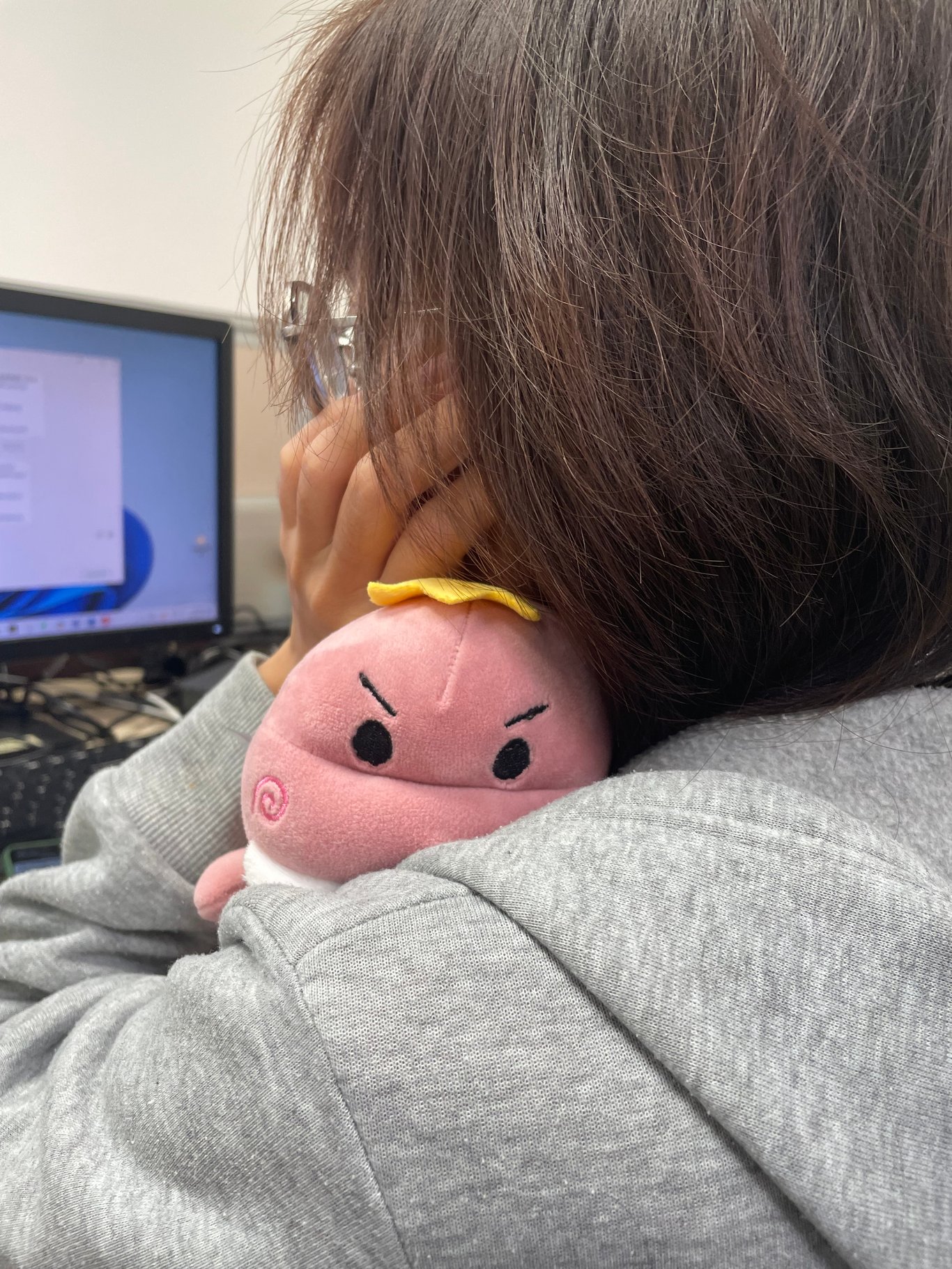见了王安忆
因为同是新加坡城市阅读节的活动,所以见到王安忆是在见到龙应台之后不久。活动地址也是capital theatre,一个两层的剧院。
在我卡点冲去剧院,担心这次又会排不上号被发配到二楼的时候,看到现场的人数远低于我的想象。前排没有多少被reserved的席位,我竟然也成功坐到了第三排。直到活动开始,一楼也才将将坐满。
讲实话,我当时有点担心王安忆会不会因此尴尬,特别是如果她知道前几天龙应台的盛况的话。
开场前王安忆就坐在我前两排不远处。我只读过她的书,并不曾了解过她的长相。是看她一遍遍从座位上站起来同好多来与她搭话的人握手,才知道,哦原来这就是王安忆,堪称腼腆和随波逐流的亲和。
讲座开始,主持人简单介绍完王安忆,邀请她上台。穿着深色针织外套,白色半身裙,围着白底黑色波点围巾的她,挎着随身携带的大包,扶着栏杆慢慢走上台了。
特神奇的画面,仿佛这不是她的主场,是去哪个商场的大门,而她是熙攘人群里的普通一人罢了,随时可能径直走远去。
还好她没走掉,她走到舞台中央,扭头放下包,慢慢坐了下来。
“今天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这个,这个场面太大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写小说是很个人的事情,我们写小说的人都是有点社恐的。”
(脑海里即时浮现余华邪魅一笑)(从这句话就开始喜欢她了)
“这次的主题是‘历史和我’,这其实是费兰特的题目,这是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
埃莱纳·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在这次讲座中,王安忆多次提及她对费兰特的喜爱与赞许。
王安忆说,我们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这种关系“紧密”,却又很“微弱”和“脆弱”。有的时候“历史大环境”和“个体”,很难在一体中表达。
她一旦开始说话,就把目光看向右侧虚空。主持人低头在小本子上哗哗做着笔记,所以王安忆可以看向主持人的方向,却无需和他四目相接,她也不扫视观众。我想象她应该是上课不喜欢提问,也不喜欢点到的教授。
主持人笔记做得真用功,但他不知道,王安忆压根没有需要互动的意识,也无需他引导谈话,她就这样望着虚空讲到了一个多小时。
我从没见过这么社恐的公众人物。但她一点笔记和slides也没有,又能非常有逻辑地,一刻不停地完成整场演讲。我听得津津有味。
她说自己在动荡,容易感到压力的环境中长大。生活就像是一面墙壁,她面对自己生活的这面墙壁生存,只处在局部的环境中。而写作不能放弃大时代。有的时候人无法立刻意识到自己是活在怎样的历史中。
她特别喜欢《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卷中工人运动的描写。在一个工人罢工、工会抗争,学生运动频繁的时期,作者用多个人物局部的故事,描写出了一个时期的动荡。
她说在中国,她生活的时期,文学是被时间划分概念的。有知青文学、然后寻根文学等等。
但是这些概念并不能网罗所有的个体命运。
她总在脑海中想起那些,游离在命运都被安排的分类之外的“漏网之鱼”。
“这些在命运安排之外的人,就像时代的泡沫一样。”她说。
如果没有人描述,没有人记录,他们就会像制作叶脉时被刮去的细胞。可能叶片形状不变,但历史会少了生命和鲜活。这大概是她写这本书的初心。
她开始述说她自己的故事,用充满自嘲的口吻:“我是上海人。上海市民其实是井底之蛙,以为看见了全世界,其实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上海人觉得上海以外都是乡下。(她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在叙述。台下观众超多上海人,但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我的邻居的小孩考到了北京的学校,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他的妈妈都希望他赶紧回来,回来找个一般般的工作都比在北京好。”
(崩溃,写到这里发现坐车坐过了7站)
“当年我被安排插队,我什么也不会,是很不受待见的。我们去了还要占他们很多名额,却给不了多少帮助。当时如果要考大学,是需要村里领导提交申请。但是我,是吧,我又很懒惰,和农民关系也不好,上不了大学的。”
她讲述她怎么凭着青涩的技艺进了文工团。她讲当时所有人的迷茫。
“写作的都是很懦弱,很不堪大用的人,你不要指望我们在历史上承担什么重大责任。”(大概意思是这样,都不是逐字逐句记录的)(她说的太诚恳,又很难不笑)
“当时我们村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我后来就一直想起这个人,我老是想起这个人。他不是被安排来的,他就是自己来的,他好像什么都懂。我们问什么他都知道,和我们滔滔不绝地聊天。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消失了。我就又想起这个人,想到这个命运没有被安排的人。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来。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的这个书叫《儿女风云录》,但它不是武侠那种掀起了很大的风浪,而且落在个人身上的。”(妈呀,这句话真记不太清了,差不多是这样吧)
然后王安忆哗啦哗啦讲了一下她写这本书的思路,说起人物的人生轨迹,几次命运转折。可能别人说同一个故事我不会有太多情绪,可是王安忆讲话就透出书中人物的一种执拗,听她讲话总是觉得有趣,明明挺正经挺有深度一讲座的,我偏偏使出了听奶头乐的劲儿,大脑啧儿啧儿地品。
但令我有些惊讶的地方是,王安忆说,她写作的时候会刻意地规划角色命运。而且这种刻意不是出于人物动机,而是出于她(作者)的价值观:“写作需要有人物,人物体现价值。人需要有蜕变,变得比原来好一点点。所以你要想,要给他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生活。比如我的角色,我让他‘好好谈了场恋爱。’”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一直以为角色意志是会高于作者意志的。
不过讲座的意义也不是在于“接纳”,而是“看见”吧。我看到王安忆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思维模式,对我来说已是受益匪浅。
提问环节也有非常有趣的地方(王安忆怎么这么有趣哈哈)。
问:信不信神
答: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很难说相信,但也不敢说肯定没有。如果真的有神,那他一定在莫言身上待过。就,就我们写作都是要很辛苦打磨的,但是莫言他不是,他就凭着感觉写下来了。虽然他不是都写的很好,有的时候写的也不好,但有些写的特别好。如果有神,那他就是神。(太绝了这个回答,太搞笑了)
问:你最喜欢的莫言的一个作品?
答:《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莫言短篇写得是比长篇要好的。
问:你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对文学发展影响大吗?
答:其实我感觉,有时候好像也需要有些抵抗的力量。在这种时候,想写还是能够写出来的。原来我参与过给俄罗斯编小说集。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完全解开了所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写了,就很多人投稿。然后我们就很惊讶地发现,那些稿件质量并没有说得到显著提升。不要等待时代变化,要写就要立刻写,千万不要等现在变成历史。
问:您最喜欢的科幻?
答:《别让我走》(好像还有一个,有点忘了,好像在别的帖子有看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