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字造海洋:香港.文學.海洋讀本》——前言:在香港讀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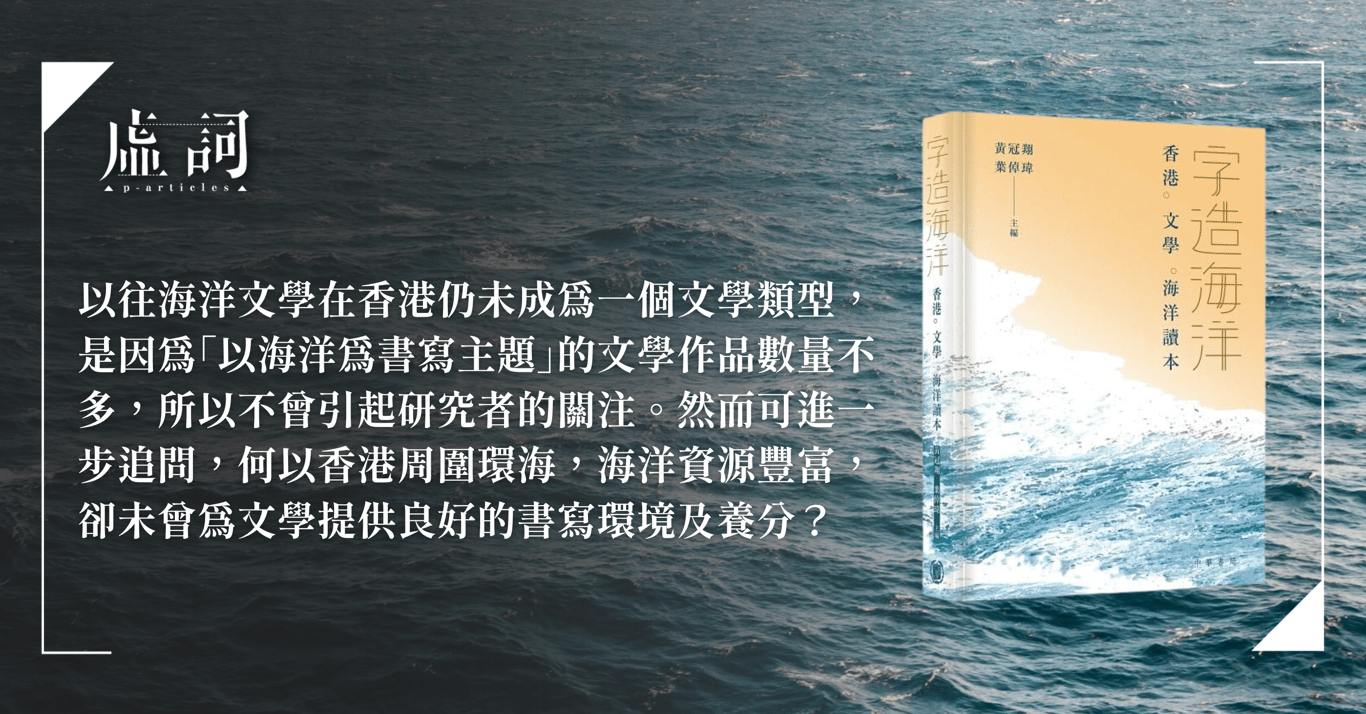
文|黃冠翔
一
海洋的廣大無垠、波濤洶湧,自古以來是人類敬畏且欲征服的對象。習慣「腳踏實地」的人們不甘受制於陸地有限的空間,於是踏上畏途,登上輕舟揚帆航向滾滾海濤,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未知、交給大自然。野心與冒險精神乃一體兩面。海的神祕感和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變幻無常、難以預測,颶風、海盜、水怪加上豐富的想像力,凶險更帶來征服的刺激與快感。東西歷史浪濤中多少千古文人對海洋的書寫融合着想像、慾望和經驗,形成人類精神文明與文化的珍貴資產。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歷史上不同時期大量移民或為躲避戰亂、或為政治理念、或為攢錢餬口,前仆後繼湧入香港,無論這些人出於主動或被動,面對未知的前途離鄉背井,或多或少都具有冒險性格,至少在競爭激烈的香港地要能掙一口飯吃,需有過人的堅忍毅力。香港環海,居住於此的人們即使不為搵食,生活範圍和視線所及皆離不開海,況且來往香港島與九龍半島必須過海,可以說海是此城的一部分,照理說市民對海洋應有豐沛的感情與想像,香港應能孕育出傑出的海洋書寫及批評體系。在香港談海洋書寫或海洋文學(Sea Literature, Ocean Literature 或Maritime Literature),首先需面對一個基本問題:香港是否有「海洋文學」?如果有,應如何定義?如果沒有,又該如何談起?事實上,香港目前未有系統性討論海洋文學的研究,遑論相關定義和發展脈絡的爬梳。以往海洋文學在香港仍未成為一個文學類型,是因為「以海洋為書寫主題」的文學作品數量不多,所以不曾引起研究者的關注。然而可進一步追問,何以香港周圍環海,海洋資源豐富,卻未曾為文學提供良好的書寫環境及養分?
帶着這個疑問,我們開啟了對香港文學作品的搜索、閱讀與研究,發現文學作品裏出現海洋的比例偏低,遠不及描繪城市其他面向的主題。在為數不多的作品中,海洋大致以兩種形式出現,一種是以主體的形式現身,另一種則是字裏行間的偶然閃現,換句話說,海洋只是陪襯、並非主角。而後者的數量可能更多。這個現象延伸幾個問題:一、香港的「海洋文學」如何界定;二、海洋作為陪襯或是作為主體的整體文學表現,涉及歷史的變化,隱然有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三、海洋作品各有不同側重的主題與關懷。第一點牽涉到本書如何取捨作品的尺度問題,後兩者則是選輯主題的拿捏問題。在回答上述問題前,筆者認為需先了解周圍地區相關研究的概況,並以筆者較熟悉的台灣文學研究情況為借鏡。
二
綜觀現當代華文文學創作,歷來雖不乏海洋相關作品,但海洋書寫長期未被視為獨立的文學類型而加以重視。直到一九九○年代,隨着海峽兩岸文學研究的系統化和細緻化,海洋文學才作為獨立的文學類型受到較具規模的注意與研究。
於中國文學發展長河,早在《山海經》裏已出現「海上仙山」和「人魚」的想像,(1)成為中國文學裏兩個重要的海洋元素。到《史記.封禪書》和《列子.渤海五山》後,「瀛洲」、「蓬萊」等島嶼名稱更成為神仙島的代名詞,流傳至今;魏晉南北朝張華《博物志》、任舫《述異記》和明代馮夢龍《情史》等作品都對「鮫人」(人魚)有「他者」(the Other)的奇想與演繹。(2)此外,有一種海洋書寫類型以觀海、望海為題,如曹操〈觀滄海〉、劉峻〈登郁洲山望海〉和吳筠〈登北固山望海〉等作,也大多是立足高山遙眺海洋,並非真的親身進入、體驗海洋,仍舊帶着極高的想像成分。於是,海洋在古典文學裏,大抵出自中原對於「夷」(邊疆異族)與「異」(未知領域)帶有幻想色彩的凝視。一九九一年九月在福建舉辦了首次以「海洋文學」為題的學術研討會,儘管會議上對於「海洋文學」的定義及中國海洋文學的特徵為何,仍缺乏嚴格的學術定義,(3)但已開啟中國學界對海洋書寫的關注,發展至今累積數百篇學位及期刊論文成果,亦時常舉辦海洋文學或海洋文化相關的研討會,研究議題橫跨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和區域研究等。
一九七五年朱學恕等人在台灣創立大海洋詩社,發行《大海洋》詩刊,致力發展海洋文學。但有研究者指出,一九八○年之前「海洋」在台灣文學作品中較少作為關注的焦點,只是故事情節發展的空間場景或意象,要到東年的小說《失蹤的太平洋三號》發表後,台灣的海洋文學才算邁入新的里程碑。(4)一九九○年代,由於作家廖鴻基和夏曼•藍波安的有心投入,將台灣的海洋文學創作推向高峰。(5)廖鴻基和夏曼•藍波安都是長期於海上征討奔波又筆耕不輟的作家,豐富的海洋勞動經驗與海洋生態知識作為他們書寫的底蘊,標誌着海洋文學的一種經典類型,卻也因此衍生爭議──海上經驗與岸上想像的對壘。亦即,作為海洋文學作品,作家的實際經驗是否為必然?「經驗」與「虛構」的比例是否成為篩選作品的標準?有論者從「自然書寫」的角度出發,將海洋文學視為「自然書寫的一股支流」,重視生態經驗的客觀描寫,而排拒過多的虛構與想像。(6)亦有論者對此持質疑觀點,認為將具體海上經驗之有無作為區別是否屬海洋文學作品的標準,無疑是限制海洋文學發展的阻礙,畢竟從事航海、漁撈或以海維生又從事寫作的人實在少之又少,在「非虛構性」的客觀描寫之外,更應該深化海洋的想像性,使海洋文學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和發展性。(7)除了作家身份與經驗的爭議外,歷來台灣學界在談海洋文學時,主要仍以「海洋性」的有無作為判別標準。所謂「海洋性」可大略分為兩種,一是具體的海洋元素,如書寫海洋或其相關題材;二是抽象的海洋精神,如冒險犯難、不畏艱難的堅毅心理等等。狹義的定義需要兩者兼具,廣義的定義則二者備一即可,然而,姑且不論抽象的海洋精神如何定義,即便是具體的海洋元素,是否包含海洋之外的港口、海濱、漁村等等空間,也都頗具爭議、暫無共識。(8)採取狹義界定者如姜龍昭,他在〈論海洋文學〉一文中指出「海洋文學作品的背景,必須在海上,人物必須是生活、工作,戰鬥在海上的那些水手、漁民、和海軍」。(9)但這個定義顯然已經過時,且如前述,過於狹隘的界定反而限制了海洋文學的發展。採取寬廣的定義者,如東年在〈山、海與平原台灣的對話〉一文提到:
海洋文學,就是描寫海洋以及相關海洋的現象、精神、文化以及人在其中生活的意義。
海洋文學的寫作就像我們一般所談的文學寫作一樣,能夠表現作者自己對生命、生活的感情、感受和思想,也能夠反映外在世界的歷史變遷、社會現實和文化;不同的只是以海洋和相關海洋的領域為背景。(10)東年擴大海洋文學的定義與範圍,只要是藉海洋題材表現作家對生命、社會、歷史、文化等的感受與思想,皆可以納入海洋文學討論的範疇。廖鴻基進一步指出,海洋文學及藝術的產生乃根植於海洋文化、海洋環境,具有獨特的意義。(11)
三
值得注意的是,依現有對華文寫作的海洋文學研究成果可知,「海洋文學」一詞最早見於一九五三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楊鴻烈《海洋文學》一書,只不過雖然此書正式提出「海洋文學」名詞,作者卻未進一步定義及解釋,而是將海洋文學與山嶽文學、平原文學、天象文學、動植物文學、人倫文學等文類並置,並在此框架下將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做比較。(12)換句話說,海洋文學在當時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次文類(sub-genre)概念被提出。雖然「海洋文學」一詞早在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出現,卻一直未引起香港作家及學者的注意,反倒是此書一九七七年由台北經氏出版社再版,對後來台灣海洋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與影響。(13)此外,七十年代吳其敏主編的左翼藝文刊物《海洋文藝》,以及二○○七年十月香港浸會大學曾舉辦名為「海洋與水岸寫作」的國際作家工作坊,(14)顯示海洋書寫在香港曾出現零星的水花。可惜一直未激起相關研究的浪潮。
根據政府資料,香港全域(包括新界、九龍、香港島和鄰近島嶼)的陸地面積為1114.35平方公里,而海洋面積為1640.62平方公里,(15)海洋面積遠大於陸地。香港有豐饒的海洋環境,也產生相應的海洋文化和性格,如蜑家人的生活習俗、盧亭人魚的身份想像、生猛海鮮的飲食文化、天后媽祖及洪聖的崇拜信仰、海盜張保仔的鄉野傳說、英國與日本入侵的抵抗歷史和作為世界金融貿易中心的驕傲自信等,都是發展海洋書寫的豐沛資源。可惜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長期填海造地的城市發展策略,使海洋不斷讓位給陸地,加上人口結構主要來自內陸移民,陸地觀點與生活習慣逐漸成為主流,都不利海洋文化的延續及想像。
香港島及諸離島星懸海上,與九龍半島對望,九龍則背靠新界諸山,可說整個香港地勢是背山面海,但從文學、文化角度看,香港長期都是背海之城。在城市發展歷史中,尚未出現如西方《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Sea )和《白鯨記》(Moby Dick)一類磅礡的海洋文學名著,甚至在早期,海洋鮮少成為作家投射、想像、稱頌的對象,海洋隱身於陸地之下,被城界排拒於外,海洋在文學作品中佔比偏低。然而,這個現象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有了變化,受到本土意識興起的影響,作家們開始看到本地的海洋,一九九〇年代甚至到了千禧年代之後有更顯著的轉變,許多作家開始挖掘香港海洋文化的價值,以海洋意象及想像作為創作主體,「文學海洋」在香港開始受到創作者重視。本書的編輯初衷,便是想喚起讀者和研究者的興趣,去探尋香港文學中「海洋」的面貌,藉此找回這座城市的海洋文化及其意義。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遺留的問題。首先是有關香港「海洋文學」的定義問題,本書書名的「香港.文學.海洋」或可作為回應。選擇用「香港.文學.海洋」這三個詞組為題而不以「香港海洋文學」命名,乃因相關的研究現在才處於起步階段,我們認為應該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才能辯證出適合香港本地的「海洋文學」定義與內涵。「香港.文學.海洋」是三個中性客觀的名詞,也分別代表三個主體概念,能最大範圍容納有關的文學作品,只要作品裏寫到海洋且能反映香港特色的,無論是體驗海洋生活(外在景致的描繪)、感知海洋意境、凸顯海洋元素、關注海洋生態、轉化海洋精神或者擁抱海洋文化,只要具備其一,都是我們考慮的對象,其中收錄範圍不限於香港本地作家。即使海洋在該作品所佔篇幅比例低,都有它背後的意義值得推敲。現階段若以狹義的海洋文學定義框限,在香港文學範疇中可稱為「海洋文學」者,恐怕不多。甚至,什麼是香港的「海洋文學」也是一個暫時存疑的概念,這部分有賴文學同好們激盪討論的浪濤,並交由時間淘洗、沉澱創作及研究的金沙。書名中的「字造海洋」即在凸顯此意,當城市發展朝「填海造陸」方向前進,文學能否以文字造回海洋?這個龐大工程有賴作家、讀者和學者們共同參與。
本書的選輯,不拘文類與年代,收錄具文學性和香港性(香港特色)的現代詩、散文和小說,唯部分文本篇幅較長,僅能以節選方式收錄重要片段。全書將五十一篇作品分為五個單元:「島、渡、灣、港、魚」,各單元有兩位編者撰寫的導言,單元主題選擇與香港海洋環境有關的五個關鍵詞,希望展現香港特色的同時,降低編者主觀情感對讀者閱讀的影響,期望把文本的豐富性最大程度留給讀者細細品味。「島」的敘述空間為香港島和諸多離島,包括對於海島起源的想像和各種生活、情感的描繪。「渡」穿梭於港、九之間,或是往來更遠處,碼頭與渡輪總是承載旅者此刻的足跡與思索。「灣」隨着綿延的海岸線不斷變遷,城市的形貌也隨時改變,海灣與填海的虛浮,訴說着被覆蓋的昨日故事,以及新生的明天。「港」是早期住民聚居和地方發展的中心,維港和漁港是城市的兩種面貌及雙重性格。「魚」的海洋動物書寫,有對現實環境的關懷,也有對虛幻意象的營造。需特別說明,五個主題並非相斥的概念,在文學海洋裏,可能彼此交集、共享意義。
四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須感謝各方的支持。首先感謝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自二〇二一年起的支持,當時的系主任CLAPP Jeffrey Michael 博士希望我們主持一個知識轉移型研究計劃,激發葉倬瑋博士與我產出「從海洋視野看香港文學」的思索,從而建置了「香港.文學.海洋」閱讀主題平台,作為該計劃第一期研究成果的具體展現。在閱讀平台上,初步收錄了與海洋有關的八十篇香港文學作品,時間橫跨一九三〇年代至今,海洋在香港文學中的面貌及其所佔篇幅的多寡,反映這個城市裏的人(無論是定居者或過客)如何看待與想像海洋,並可從歷史縱深裏窺探人與海洋關係的變化。
感謝各位作家和授權人的慷慨成全,使本書的編選成為可能。感謝陳國球教授、須文蔚教授慷慨賜序,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看到了此議題的發展潛力,主動聯繫、催生本書的出版事宜,期望透過紙質媒介的傳播,觸及更多人加入相關文學作品的閱讀與討論,董事長趙東曉先生、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和責任編輯葉秋弦小姐勞苦功高。感謝參與本書設計、排版、校稿等編輯工作的所有夥伴。感謝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的經費支援,以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的支持,使前述研究計劃的第二期工作得以持續進行。相信在葉倬瑋博士與我的互相砥礪之下,加上恒生大學鄒芷茵博士的投入,第二期研究計劃成果更值得拭目以待。
本書容量有限,仍有許多滄海遺珠未能盡錄,或許留待續集。邀請各位讀者從現在起閱讀海洋、認識香港。
(1)如《山海經.海內北經》寫到「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射姑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大鯾居海中。明組邑居海中。逢萊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對海洋充滿異國、異族的想像。
(2)如張華《博物志》寫到「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或如任舫《述異記》亦有敘述「南海出絞紗,泉室潛織,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又如馮夢龍《情史》則有:「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於水面,戲囑曰:『汝能為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的描述。
(3)倪濃水:《中國海洋文學十六講》(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頁1。
(4)吳旻旻:〈「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海洋文化學刊》第1 期(2005年12月),頁118-119。《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作者東年曾在1974 至1976 年間以發報員身份在遠洋漁船上工作,此小說可說是據自身經驗創作的作品,於1980 年《民眾日報》連載,1985 年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5)廖鴻基在35 歲時開始成為「討海人」,於海上曾從事漁撈作業、執行鯨豚生態調查等工作,並據其自身經歷創作散文作品《討海人》(1996)、《鯨生鯨世》(1997)、《後山鯨書》(2008)、《黑潮漂流》(2018)、《23.97 的海洋哲思課》(2020)等二十餘種及小說《最後的海上獵人》(2022)等。夏曼.藍波安身為蘭嶼達悟族人,以與生俱來的海洋文化和原住民視野為基底,創作小說《八代灣的神話》(1992)、《黑色的翅膀》(1999)、《大海浮夢》(2014)與散文集《冷海情深》(1997)、《海浪的記憶》(2002)、《大海之眼》(2018)和《沒有信箱的男人》(2022)等十餘種。
(6)如黃騰德:〈從廖鴻基《鯨生鯨世》看台灣的海洋文學〉,《台灣人文》第4號(2000 年6 月),頁47-61。
(7)吳旻旻:〈「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頁125-127。
(8)有關台灣「海洋文學」定義的歸納整理,詳可參李友煌:《主體浮現:台灣現代海洋文學的發展》(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2011),頁11-14。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英語文學中雖然有許多以海洋為題材的作品,卻也缺乏明確的「海洋文學」的定義。參張陟:〈「海洋文學」與類型學研究〉,收入段漢武、范誼主編:《海洋文學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頁55-59。正因為「海洋文學」難以用一個統一的、可全面概括的定義去規範,恰恰說明了它的複雜性、多元性與因地制宜。如何借助其他地方的研究經驗以探索香港海洋文學的內涵及發展的可能性,值得探究與深思。
(9)姜龍昭:〈論海洋文學〉,《海洋生活》第1卷第4期(1955年4月),頁26-28。
(10)東年:〈山、海與平原台灣的對話〉,《給福爾摩莎寫信》(台北:聯合文學,2005),頁191、201。
(11)廖鴻基:〈海洋文學及藝術〉,收入邱文彥編:《海洋永續經營》(台北:胡氏圖書,2003),頁118、129。
(12)楊鴻烈言《海洋文學》為其「世界文學的比較研究」的第一編,其他各編為山嶽文學、平原文學、天象文學、動植物文學和人倫文學。楊鴻烈:〈楔子〉,《海洋文學》(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53),頁1。
(13)許多研究海洋文學的學位論文皆提及此書,如葉連鵬《台灣當代海洋文學之研究》(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王韶君《台灣海洋文學的發展與文化建構(1975~2004)》(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6)、林怡君《戰後台灣海洋文學研究》(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7)等十餘篇,詳可查閱「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4)林幸謙:〈海洋文學與海的精神美學──2007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專輯〉,《作家月刊》第65 期(2007年11月),頁5-10。
(15)此為截至2023年1月的資訊,詳細數據參考香港地政總署網站(https://www.landsd.gov.hk)「資料庫>地圖資訊>香港地理資料」(最後瀏覽日期:2023年8月27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