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的守關人,從大理到沙溪到馬坪關
雲南大理劍川縣的沙溪古鎮,因茶馬古道唯一幸存的古集市而聞名。而在沙溪鎮深處,藏著一個更為古老、也更顯寧靜的村落——馬坪關。它曾是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關卡,卻因時代變遷而沈寂。
近二十年來,在建築師黃印武及其團隊的陪伴與努力下,馬坪關正悄然煥發新的生機。
馬坪關自然村隸屬於雲南省大理州劍川縣沙溪鎮鰲鳳村,是 “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沙溪古鎮的唯一留存至今的古鹽關 。當地不僅保留著豐富的古建築和完整的鹽馬古道,還傳承著每年春節身著明代戲服唱戲的文化傳統。
由於地處深山,馬坪關村2009年才通電,2015年才通路,40多戶人家,發展因此遠遠落後於其他村莊。傳統的農耕和閉塞的環境使得村民紛紛外出務工謀生。直至2015年,入村道路打通前,從沙溪鎮到馬坪關需沿著羊腸小路步行4個小時;如今乘車輾轉也需一個多小時。

沙溪復興工程與馬坪關陪伴式鄉村發展項目
從建築師到鄉村建設者、鄉創英雄,黃印武老師及其「卡卡果果志願者團隊」是駐紮沙溪和馬坪關的長期主義者。
「卡卡果果」在雲南話的意思是「角角落落」,除了通電、通路,也想把希望帶到深山鄉村的角角落落。
“走出馬坪關”項目的負責人邊莉君回憶2015年首次進村時說:“大多數村民不會說漢語,村里沒一條像樣的路,太窮了!山坡、溪澗到處可以是廁所。”身為江蘇無錫人,邊莉君感覺這里恍如隔世。
外界的關注目光,主要是黃印武引來的。作為國內知名建築設計師,從2003年起,黃印武已在沙溪紮根14年,曾經主持中國—瑞士合作項目“沙溪古鎮修復工程”。後來,他又將目光轉向了偏遠閉塞的馬坪關。“想通過激發村民內在的活力、能力和自組織水平,讓馬坪關人過上從容、自信、有尊嚴的生活”,這是黃印武和同學吳楠等一群“走出馬坪關”項目發起者的初衷。
我在沙溪十三年:鄉村建設必須回到當事人這個主體
兩岸語彙:地方創生=鄉村建設或振興
黃印武,東南大學建築學學士、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建築學碩士、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碩士。從2003年起擔任沙溪復興工程瑞士方負責人,具體實施國際慈善資金項目,負責建築保護設計、資金管理和維修施工。十三年的鄉建在黃印武看來是真正了解和理解鄉村的過程。通過長期的接觸和在地生活,他更堅定了鄉建必須回歸到當地人這個主體,關注鄉建過程對他們的影響。

有方:現在“鄉建”熱潮中,討論熱門問題之一就是鄉村發展與旅遊之間的關系。你怎麽看這個問題?
黃印武:我認為鄉建和旅遊沒有必然的聯系,我並不認為村子遊客的增多就意味著鄉建的成功。現階段,旅遊只是快速改變鄉村狀態的一種手段,但在長期的鄉建工作中絕不能過度依賴旅遊。試想一下,全國所有的鄉村都依靠旅遊來發展,這根本不現實。
同時,歷史已經證明,只依托單一的發展方向,會極大阻礙鄉村的良性發展。沙溪就是一個例子,它的興衰都是因為茶馬古道:古道興,沙溪興;古道衰,沙溪衰。同時,沙溪周邊的雙廊和麗江新老兩個例子也佐證了過度發展旅遊的危害。不過,鄉建可以借助適度的旅遊來帶動當地手工業、生態農業、加工業等其他產業的發展,形成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所以,旅遊只是推動鄉村發展的一個工具和手段,而不是鄉建的救命稻草。
有方:你的文章和講座中常常強調鄉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建設和沈澱。請問你所認為鄉建的理想發展方向是什麽?
黃印武: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讓大量農村資源集聚到城市,以幫助城市的發展,這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這樣一個幾十年堆積起來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也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真正了解和理解鄉村也需要長時間的接觸和在地生活,不是幾次調研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我們現在不乏了解西方哲學和西方理論的建築師,但是真正明白中國傳統文化的建築師卻是少之又少,對鄉村的研究也很匱乏,想要深入的、全面地了解和理解鄉村因此變得十分困難,然而,這卻是鄉建的第一步。鄉建的根本目的應該是改善當地人的生產、生活條件,恢覆產業活力,重建文化自信心。所以,鄉建必須回歸到當地人這個主體,必須關注鄉建過程對本地人的影響,不能越俎代庖。
(摘錄有方2016年4月采訪)
關注鄉村本地人主體性的黃老師將羅伯特議事規則和自組織的運用帶入村里,先改變人的思想;只要人成長起來了,村子會跟著成長。
相關播客:起朱樓宴賓客▷女俠段四合和她的家鄉馬坪關
羅伯特議事規則如何在中國邊遠鄉村落地生根?
自組織如何幫助馬坪關解決大小紛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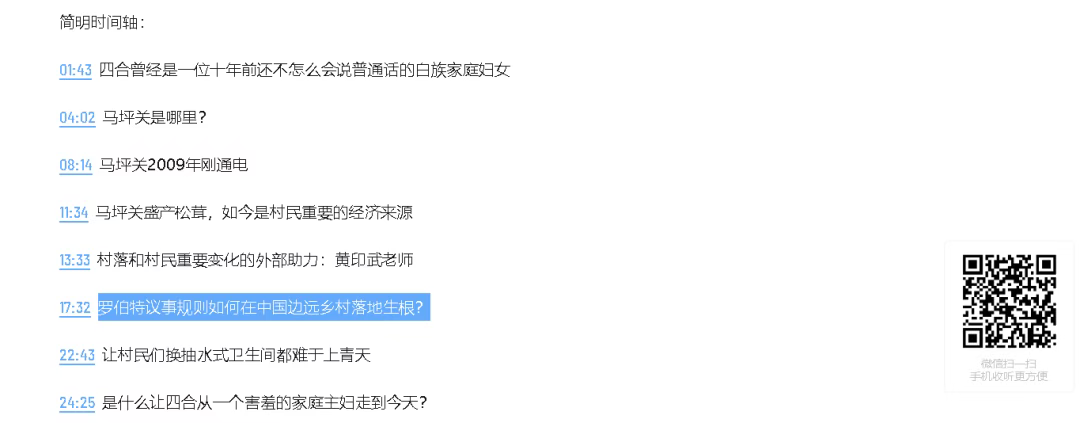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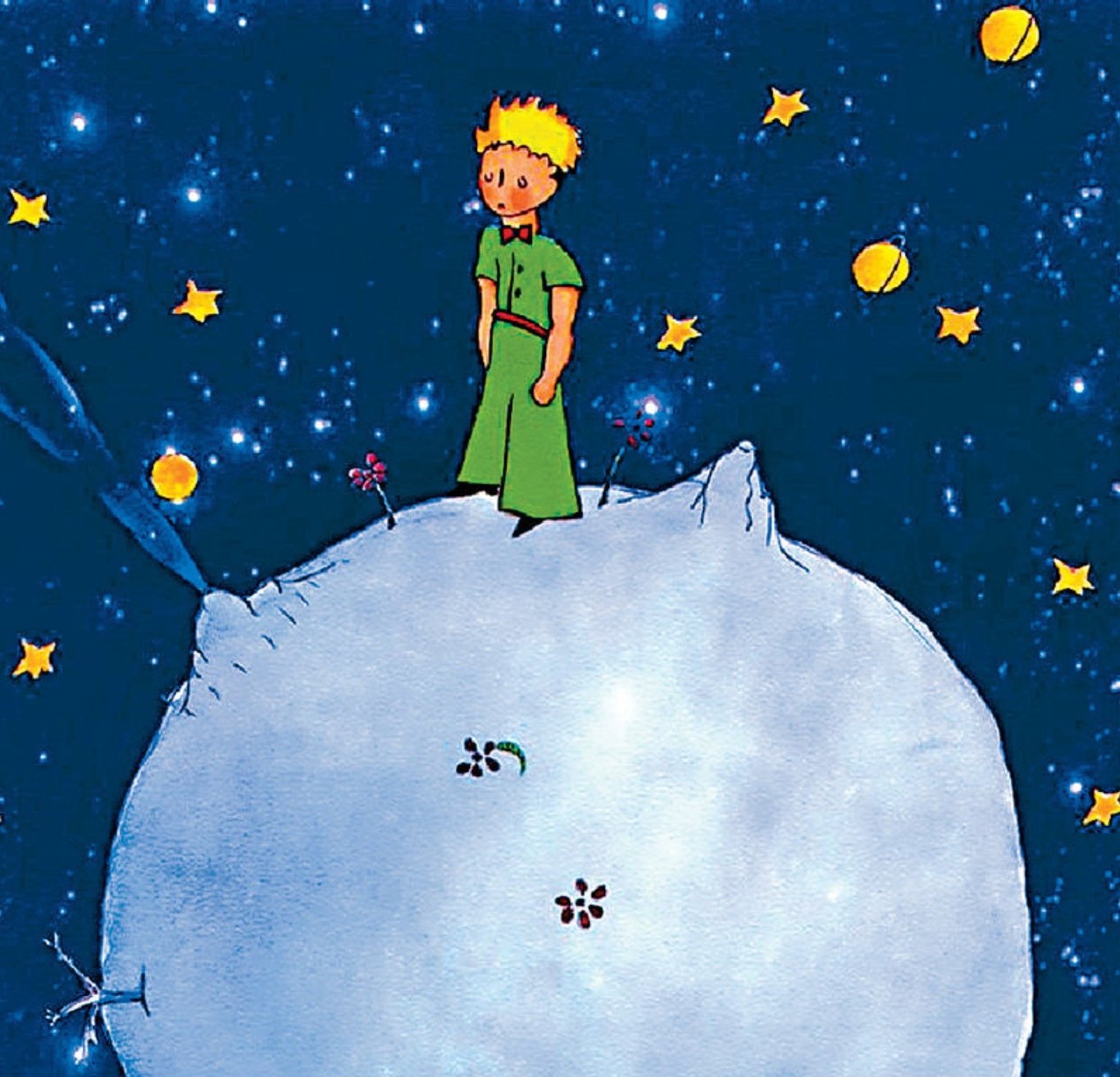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