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台眺望月台的節目
自從我發現從某棟建築高樓望出去,可以看到捷運站月台候,我就不斷地眺望別人的人生,像是不停放映、自動輪播的不同但相似的節目。每隔幾分鐘就有人抵達、有人離開,時序不斷更替,演員卻永遠穿著差不多的服裝,擠著一樣的車廂,表演相同的上下班、趕場、奔波與等待。
出發和抵達,其實都是令人值得興奮與期待的事吧。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填上了工作或是其他的義務在終點,我們都不再對這些感到新奇,即便是你知道那會換來月底的輕快步伐,但在戶頭數字或是考卷數量仍然沒有動靜的時候,無法往前推移的月台,塞滿沈重的嘆息。好像生活的軌道一旦劃定,就注定是筆直、無聲、甚至無望的。那些人和我一樣,也都是出門又回家,可是看著他們的背影,我竟生出一種無從詢問的困惑,我們明明選擇了自己的路,怎麼走著走著,就像是跌進了某種萬劫不復的副本?
我就這樣呆呆地望著,看著那樣的畫面,月台一瞬間滿了,又迅速空了,像是被設定好會自動清空的舞台。人潮一退,地面冷掉,時間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那一刻,無論是我站在高樓的凝視,還是他們在月台的步伐,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月台不過是一個載體,是把我們從一個段落送往下一段落的臨時中繼站。我從最初只是想逃避,看著別人來替代自己思考,到後來開始反思自己的路徑──我也會在時間到的時候,日復一日的加入隊伍,那些不確定、被動、又故作堅定的選擇,也不過就是另一種走法罷了。
所以,我們都沒有不同。
我來到天台的時間並不固定,但都能看到同一個男人站在月台的第五節車廂位置。白襯衫、深色長褲,永遠站得筆直,手裡提著一個透明塑膠袋,裡頭裝著什麼,我看不清楚。有時候袋子鼓鼓的,有時瘪瘪的。他不看手機,也不與人交談,只是靜靜地站著,看著軌道的方向,就像等一班始終不會到的車。
男人固定得像是城市自動系統的一部分,像一根應該存在於月台邊緣的安全柱。精準幾乎讓我都相信了,他是不是為了讓我看而出現的。甚至有一兩次我故意早十分鐘去窗邊,他已經站在那裡了;我晚一點看,他還沒走。他的存在彷彿在證明什麼,但又什麼都沒說。
他真的是為了搭車而站在那裡嗎,還是為了讓自己在那裡被時間拉直。我想到自己曾經也有那樣的姿態──站著,不說話,等某個意義慢慢靠近自己。
然後他突然不見了。連著兩天、三天都沒出現,我開始不自覺地望向那個位置,像是在找遺失物,我沒有想探究背後的原因,單純就是意識到什麼存在感變那樣。車還是照常來,門一樣開開關關,但我很清楚那個固定的身影消失了。一個陌生人不見了,我竟覺得自己像是被遺棄了一樣。
那個第五節車廂的位置成為我對時間最脆弱的測試點。不是因為他特別重要,而是我不自覺地在他身上寄放了某種溫和的依賴。我沒有參與他的生活,但我默默讓他成為我日常裡一種確認「世界如常」的標記。就像日曆上的圈選、茶水的蒸氣、臉上的痣。他不在了,我才發現原來凝視也能夠看得如此深。
我也曾站在某個月台上,握著兩張票,一張給自己,一張是留給沒來的人。那是個灰灰的下午,月台上風很大,我的外套拉鍊拉到最上面,但風還是從衣襟灌進來。那天我比預定的時間早到很多,因為我不確定那個人會從哪個出口走出來。我不停看表,不停左右張望,像是某種被施了定咒的動物,只能在原地繞圈。
列車進站又離開,人潮推擠又散開,世界一切如常,只有我處在一種奇怪的凝固狀態裡。我記得我有好幾次想撥電話,但又收起手機。那不是矜持,是不想破壞那一點點還可能發生的奇蹟。我寧願相信對方正奔跑著,也不願面對可能對方根本沒出門的事實。
站了三班車的時間,我終於鬆開手裡那張票,把它順著月台邊的縫隙塞進下層的鐵軌裡。不是氣憤,也不是決絕,只是身體突然就動了起來,像是放下一塊無法再握緊的石頭。
我那時只是慢慢走到另一端的電扶梯,像是一個被通知演出取消卻還是來到現場的演員,知道自己無戲可演,但又不能直接離開。我想我在那裡等的不是那個人,而是等一個版本的自己出現,來告訴我:你做得對,這個空等是值得的。但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車來車往,和我自己的背影。
後來我還是照常吃飯。像每一個普通日子那樣,洗米、煮飯、燙青菜,把冰箱裡的剩湯重新加熱。那一天我用的不是新的碗筷,刻意選了早就微微缺角的那一只碗,像是在提醒自己:有些東西沒壞透之前,是不會捨得丟的。
一個約定,讓我看清了一個人,也看清了自己還有多不甘心。我以為我只是等待一個回應,後來才明白,那場等待裡真正焦灼的,是我心底那點還不肯退場的期待。不是期待他出現,而是期待自己可以不在乎。結果我還是在乎了。
吃飯的時候我沒看手機,電視也沒開,我只聽到湯匙敲到碗底的聲音,一下一下像在證明:你還在這裡,你沒有事。你受了傷,但你還是吞得下這頓飯。
這不是什麼堅強,是一種太習慣生活如常的體質。即使有什麼崩塌了,你還是會在七點準時開飯、在十點關燈。日常這件事,有時不是撫慰,而是一種徹底的擺爛。你知道明天還會有地鐵、還會有月台、還會有人準時站在第五節車廂前,而你也還會不小心看過去──那就是日常。
也許我只是好奇,男人最後不再需要等待那班車來臨的原因,是否跟我一樣也接受事實,改變了念頭。即使列車還是總是來。
大部分的時間,我也在其中,在那條鐵軌的延伸線裡,一個車廂與另一個交錯的時刻裡,與那些人貼得極近。
我記得有一次,我睡著了,有個女人坐下時,粗心的壓到我腿上,我嚇得驚醒。她像是沒事一樣,坐得自然,甚至沒有回頭看我一眼,像是我本來就應該是那個位置的椅子。我的腿動了一下,她沒有動。我沒有說話,也沒有推開她。不是因為寬容,而是我還沒能理解這件事,就已經過去了。
車廂裡,大部分時間是安靜的,但是有人開著快轉播放的劇集,手機聲音不大,但讓整節車廂都聽得到節奏破碎的配樂。也有的時候,在喉嚨特別乾癢的,不是故意,是下意識的不段咳嗽,肺炸裂的轟鳴,像是在車廂裡像是不停歇的鞭炮,但只得靠著這樣的運輸抵達我承諾之地。這些聲響不會停歇,到站時,啟動時,列車進站,或是到終點站時,只要列車的燈還亮著,就還有人。人們轉頭看向聲音的來源,可是投射的眼神們飄過我,像掃描障礙物那樣。我看了一下自己的位置,確實卡在聲音和出口之間。
我看著看書的人,也感覺到別人看著我。尤其當我在車廂裡打字的時候,視線像釘子一樣落在我手背上,彷彿他們正猜測我要寫的是什麼,是誰,是不是寫著他們。有人甚至慢慢地移近我這個位置,好像那張座位底下藏著什麼祕密。
那些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衝突,只是城市裡不斷重複的微小摩擦。不需要說話,也會成為別人路徑裡的一顆沙子;不需要表態,也可能一不小心進入了別人生命的盲點。而曾經以為自己只是個觀察者,後來才知道:一旦在場,就不只是觀看。存在,就佔據空間,就會在別人的記憶裡留下痕跡,即使從未說話。
誰去哪了,沒有再出現。他的缺席沒有引起什麼風波,甚至沒有人察覺,像一小段被剪掉的錄影檔,輕輕滑出了日常的播放序列。但對我來說,他的消失,像是有人靜靜將一個習慣撤下來,卻不告訴你為什麼。像忘了早期某一班沒搭上的車。但沒有。卻仍然會在某個瞬間——地鐵進站、燈光反射、遠處人影交錯的時候——想到什麼,但差那也就忘了。
我現在仍然會在高樓遠遠的看月台。不是因為期待誰出現,也不是因為那裡有什麼非看不可的畫面,而是我發現,這個舉動本身讓我安定。就像某些人需要在睡前關一次瓦斯,有些人習慣洗碗的聲音,而我需要的是這個固定距離的觀看。
這個距離讓我不被捲入,但也不至於徹底抽離。它讓我得以站在一個不主動參與的位置,卻不等於毫無感覺。我看著他們奔跑、遲疑、揹著包包、低頭滑手機,也看著他們拖著疲倦的身體歸來或出發,我看著,是因為我明白那種疲倦,那種奔跑,那種錯過。
我不會再說自己是缺席的。我曾在月台上等待過,曾經在車廂裡睡過,也曾用一個咳嗽回應過不合時宜的聲音。我在。我一直都在。只是不總是說話,不總是衝刺。
有些人選擇上車,有些人選擇等待。而我,學會了承認自己的觀看。不是因為害怕參與,而是我終於相信,觀看也可以是一種參與,一種不打擾、卻誠實存在的方式。
我仍會照常吃飯,照常看月台。仍會在一個人離開之後,把他的身影記得比自己還清楚。但我已經不再逃避了。那個站在高樓上的我,也是在走一條自己的路。只是比較慢,比較靜,比較不張揚而已。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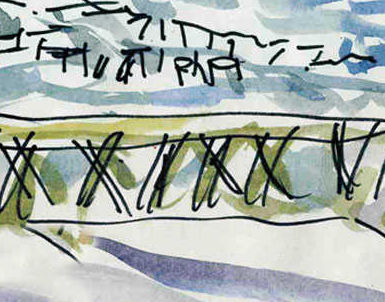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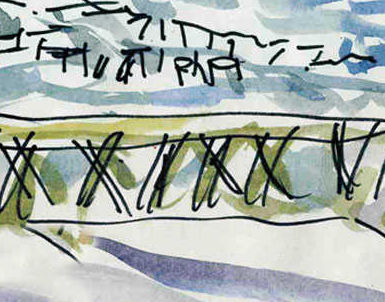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