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偽《過伯簋》《旅鼎》《疐鼎》偽銘文
證偽《過伯簋》《旅鼎》《疐鼎》偽銘文
《過伯簋》原為清末民初羅振玉舊藏,《旅鼎》亦清代梁章钜舊藏,而《疐鼎》亦為清代己見。但可惜,此三青銅器的銘文全是後人加上的,非西周舊物,何以知之。按,其內容全可不看,即,全無任何史料價值可言,因為一見《過伯簋》的銘文內有『反荊』,《旅鼎》的銘文內有『反夷』,《疐鼎》的銘文亦內有『反夷』,即知此三具青銅器的銘文,全是後人所偽的。何以見得?
按,先列出後人在《過伯簋》《旅鼎》《疐鼎》青銅器上所撰此三段銘文如下:
《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反荊,孚金,用作京室寶尊彝。』
《旅鼎》:『唯公大保來,代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自,公賜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
《疐鼎》:『王令遣栽東反夷,疐肇從遣征,攻(目目+廾廾)無啻,省於人身,孚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按,“疐”之上方“十”改“士”;“ 遣”改”辵”為“走”)
按,先秦無所謂什麼『反荊』『反夷』的用法,如果是先秦用法,則所謂的『反』是動詞,而主詞是要反的人,所以荊人要反,則先秦用法,則是『荊反』,若是夷人要反,則依先秦用法,則是『夷反』。如果用『反荊』『反夷』,則意謂有人要反荊,有人要反夷。如《呂氏春秋·古樂》講『成王立,殷民反』,而不是『反殷民』,義即已明白了,不可以用『反荊』『反夷』,而要用而『夷反』『荊反』一如『殷民反』。另一個可用的動詞,則是“叛”字,如『荊叛』『夷叛』。
因為,“反”這個字的出現,依字義上的源頭,是反轉返回歸返、重複、違反相反、相背、自反省的意思,“反荊” “反夷”在先秦不成語義,因為,是指荊的背面。荊的反面,及夷的背面,夷的反面。即反面的荊,反面的夷,或反對了荊人,反對了夷人,或違背了荊人,違背了夷人,或反叛了荊,反叛了夷。
因“反賊”之類所連想到寫出了『反荊』『反夷』等,此係後世的人在文法變遷之下始發生的用法,不在先秦出現,即使漢朝,《史記·田儋列傳》載田儋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史記》也載辯士蒯通往見範陽令,講『今諸侯畔秦矣』。又《史記·彭越列傳》載少年謂彭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可見『反秦』『畔秦』於秦楚之際所使用。而『反秦』不是指秦是個反賊,相反地,一如先秦之“反”字的用法,指反對,反叛秦朝。
因此『反秦』的意思一如先秦,不是秦是反賊,而是說反叛秦,而也用到叛秦(畔秦),義亦同。也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漢朝,所謂『反秦』不是秦朝是個反賊,而是指反叛了秦朝,再看一看所謂此三青銅器上的『反荊』『反夷』,比照『反秦』即知不會是反叛的荊人,或反叛了的夷人,而反而依先秦語義應是成了反叛荊人,反叛夷人。而用了比漢朝還要晚的後世講誰是“反賊”的用法,來用到青銅器的銘文上,寫出了『反荊』『反夷』的《過伯簋》《旅鼎》《疐鼎》青銅器上的銘文,不正就是明白自招就是後世人的文筆。(劉有恒,2025.10.27)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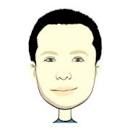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