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内在性制造的差异
德勒兹与上帝的命名:后世俗与内在性的未来 Deleuze and the Naming of God: Post-Secularism and the Future of Immanence
丹尼尔·科卢切洛·巴伯 Daniel Colucciello Barber
译文是《德勒兹与上帝的命名:后世俗与内在性的未来》的第二章,本书第一章已经有可读的译本,由豆友发在豆瓣长评区,建议佐以导论一起阅读。在英语写作的背景之下,作者不可谓不强,上述三个篇章连在一起,甚至可以对德勒兹早中期思想产生一个异常清晰的界定。注意:目前的译文存在很多粗糙、拗口的部分,为了赶时间我还没有修到最佳状态,所以仅供参阅,尤其概念的译法不应作为学术参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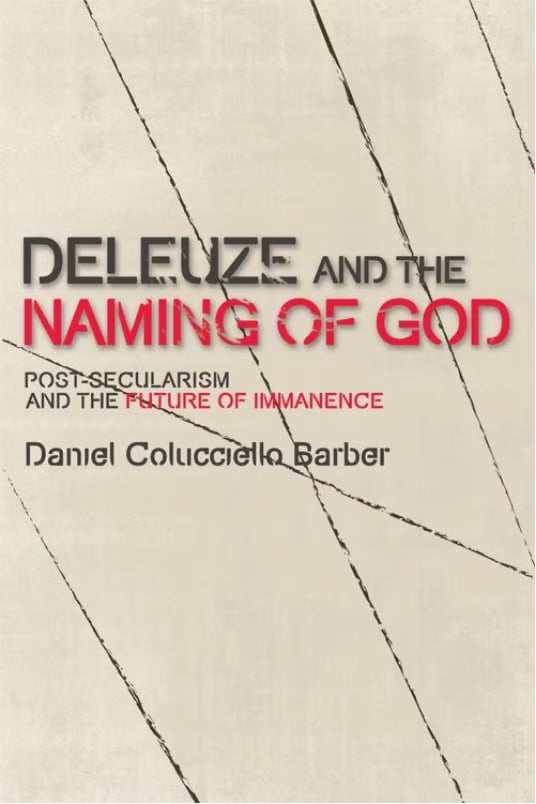
第二章 · 德勒兹:内在性制造的差异 Deleuze: The Difference Immanence Makes
内在性的架构(The Architecture of Immanence)
德勒兹对内在性的论述始于他对斯宾诺莎(Spinoza)——他称之为“哲学家之王”——的解读。¹具体而言,源自他对斯宾诺莎三元组(Spinozian triad)的讨论,即:实体(substance),或者说上帝,即存在的一性(oneness of being);属性(attribute)或诸形式(forms)以及样态(mode)或诸个体(individuals)。这些提供了实在的架构的术语彼此以内在性相关联,因而既不可分离(separately) 开来思想,也不可置于等级秩序(hierarchically)中去思想。相反,它们是互相构成的(mutually constitutive),因此我们谈实体、属性或样态,必然就是在谈实体—属性、实体—样态、属性—样态三种关系。为了梳理出德勒兹内在性的架构,让我们逐一考察这三种关系。
居于实体—属性关系中心的乃是实体的同一(unity)与属性的区分(distinction)的联姻(wedding)。思维与广延这两种属性同时谓说唯一的实体,这意味着差异(属性之间的区分)与同一(唯一的实体)并非互相排斥,反而是共生(symbiotic)的。这一创见正处在内在性的核心——回想海德格尔也曾沿着相似的路径将差异与同一并思——把它与更具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主张同一先于差异。事实上,正是在坚持同一先于差异这一点上,超越性(transcendence)被引入了:凡是先于(precede),就意味着超越(transcend),于是同一的先行于差异,就等同于同一的一者对分化的多者的超越(the precedence of unity over difference amounts to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unified) one over the (differentiated) many)。[译注:文中将不会把differentiated/differential翻译成微分、差异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反对这两种翻译]
这种超越性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对存在的类比性(analogical)阐释(关于此论更充分和复杂的阐述见下一章)。就类比性而论,真、善、美(形式或属性)在一个单纯的神圣存在(simple, divine being)(即实体[substance])中可以互相化约(convertible),以至于这个简单的存在无区分地具有它们。个体也具有真善美,但它们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且是以一种分散的、不可互换的方式拥有这些形式。换言之,使个体与上帝分离的原因在于:上帝以本质的、同一的方式拥有这些形式,而个体仅以部分的、分化的方式拥有之;上帝超越个体,正因同一超越了差异。与此相反,德勒兹使形式区分(formal distinction)(即属性(attributes)之间的区分)(译注:《差异与重复》第78页,本篇部分段落参照中译本进行再译,可能会有关键术语和表述上的差别,关于本处另见Peter King, Duns Scotus on Metaphysics: Identity and Distinctness)对于实体(或上帝)而言成为本质性的,这意味着差异乃是上帝(实体)本身的内在。其间的差别即在:德勒兹并非在一个同一的一者超越多样的多者的框架内分配差异,反而,他使差异内在于、并构成着实体-属性的内在关系。
在实体-属性的关系里,我们已经瞥见实体-样态关系的端倪:一旦属性的差异对于实体而言成为本质性的,那么一个同一的上帝或实体与分化的个体或样态之间的分离(separation)便消失了。此前,维持实体-样态之隔离的,是同一与差异的分离;当同一与差异变为内在相关时,实体与样态也能够变得内在相关。德勒兹以“实体的繁复性”来表述这种实体-样态的内在性。
实体固然是同一,但因其被分化,所以它同样也必然是多。术语“多样的”(multiple),作为实体的谓词,正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但与此同时,它也开启了实体之为一(substance-as-one)与实体之为多样(substance-as-multiple)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实体是存在于两个平面上的吗,一个同一的平面和一个多样的平面?如果我们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引入了超越性(transcendence)。然而,如果我们回答“否”,则会生出同一是否只是掩蔽差异的实在性的幻象的疑问——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差异是否只是掩蔽同一之实在性的幻象。正是为了摆脱一与多之间的这种循环——一个由多样性(the multiple)这一概念所维持的循环——德勒兹转而谈论繁复性(multiplicity)。
为了反对将个体间的差异转译为一种存在于一个被给予的(且仅为表象的,或较不真实的)多样性(multiple)与一个支撑于其下的(且为真,或最终是真实的)本体论的同一性(ontological unity)之间的区分的这种诱惑,德勒兹坚持上帝与个体,或实体与样式的内在性。这种内在关系正是繁复性(multiplicity)所帮助阐明的。具体来说,它所阐明的是一种实体的繁复性(substantive multiplicity),这意味着实体同时是同一的与分化的,是一与多样的,任何一方都不优先于另一方。这怎么可能呢?其所以可能,正如在实体-属性关系中已经展示的那样,在同一与差异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不同于多样性(the multiple)与一(the one)的对立,繁复性(multiplicity)则同时是由多构成的一以及由一构成的多。
因此,繁复性刻画了一与多的内在性,并使多者的差异(样态差异 [modal difference])与实体的同一不可分。于是我们可以说,实体的同一在两个方面与差异互为内在:先前我们看到了实体的同一与属性的差异的内在性;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实体同一与样态差异的内在性。在每一种情况中,差异对于构成那个被命名为实体的同一性而言都是本质性的;差异构成了神圣本质(divine essence)。尽管如此,为了补完三元组,并为了显示样态差异与属性差异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属性-样态的关系。
德勒兹主张,属性,或者说形式(form)具有内在的样态(intrinsic modes),借此,他反对了形式是恒定不变的(invariable)这一观念。根据后一种观念,单个形式的不同诸模态(modalities)必须诉诸形式与某种外在样态(extrinsic mode)的组合来解释,其创造了一种不变的形式模塑(moulds)多种多样的质料的情景。之所以必须引入外在于形式的东西,恰恰是因为形式是在一致性(identity)的层面上被理解的。如果形式是不变的,那么解释此形式的变异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形式与某种外在于它的东西(如物质性的个体)相结合。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超越性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实体超越形式,也不是实体超越个体,而是形式超越了个体。就形式-个体(或属性-样态)的关系这一情况而言,正如在其他关系的情况中一样,之所以引入超越性,是因为同一被设想为先于分化(differentiated)之物。并且,正如他在前述情况中所做的那样,德勒兹在此也通过呼吁对那个被设想为超越性的同一体进行一种内部的或内在的的分化(internal or intrinsic differentiation),来反对超越性。就属性-样态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样态之差异将被理解为内在于形式的同一性(formal unity)。
具体而言,德勒兹断言“自然从不以模塑(molding)的方式运作”。² 形式并不是去模塑别物——那别物最初外在于形式,或可能对之潜服不屈。个体(或样态)之差异的原因并不能在形式的外部找到。恰恰相反,同一形式(或属性)之所以有不同样态,乃因在形式之中——或形式之为自身——存在着形式的度数之差异。此处,德勒兹有一例(借自司各脱)尤为有助于理解:一面始终是白的墙,但仍能呈现不同的白性之强度(various intensities of whiteness)。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何以区分白的各种色度(shades)?不是靠某个被施加在(外在于形式的)不同材料上的不变的白的形式,而是靠白性的度数之区分——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形式(属性)自身内在的差异。德勒兹将一个变易的、差异性的形式的度数称作“内在样态”(intrinsic modes)。于是,内在样态就是属性的一个强度度数(degree of intensity)。在白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某一白之样态是通过其“发白”的强度度数而被分化的,而不同度数的白共同构成了白的形式。正如德勒兹所言:“强度度数是内在的规定,是白的内在样态;无论在哪种模态(modality)下被考量,这种白都保持着单义的同一性(univocally the same)。³ 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将同一形式内的差异置于分化的外在质料中来说明这些差异;内在样态的差异足以说明属性的分化,并在此过程中构成了该属性。⁴
现在——在把握了德氏对斯宾诺莎三元组的三种关系的阐释之后——我们便可看到:对德勒兹而言,实在(reality)如何无非就是内在性: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内在性,或上帝、形式和个体的内在性。如同海德格尔关于思与在的同一性的叙述,这三者没有谁先谁后。而且,德勒兹的叙述与海德格尔相似之处还在于:这种内在性围绕差异的支点而转动,并且除非作为差异,否则便不可被思(unthinkable)——这里的差异既指实体、属性和样式之间的差异,也指构成这些术语之间所浮现的三种关系的差异。不过,德勒兹超出海德格尔之处,在于他有能力使内在性包含个体。这一点在实体的繁复性(substantive multiplicity)这一概念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该概念,个体或样态以其本质性的差异性构成着那独一无二的实体。确然,德勒兹把他借用斯宾诺莎来建构自身内在性理论的尝试描述为“使实体围绕有限样态转动的希望”。换言之,并非实体为一场运动奠定基础,而这场运动在生成之后,再被样式所承接或在样式中展开。⁶ 恰恰相反,样态的多样化就是实体自身的多样化。实体是一,但其同一并不独立于样态之多样或分配;样态的差异就是那独一无二的实体。正如德勒兹所坚持的:“实体必须被谓说而且只被谓说于样态。”⁷(译注:《差异与重复》第80页)
这种对内在性之个体化(individuation of immanence)的强调,对于转化(transformation)问题有何后果?实体的繁复性——让现实围绕样态之多样化、围绕其变状(modification)而转动——如何能为回应超越性所带来的挑战提供思路?换言之,样态对实体的差异化变状如何使我们得以把内在性想象为新颖之物(the novel)的生产者?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内在性的架构转向内在性的力量。
再-表现与内在性的无条件力量(Re-expression and the Unconditioned Power of Immanence)
上帝生产,因为上帝是;上帝的实存就是生产。按照德勒兹的说法,“上帝是凭其实存所凭借的同一个力量,生产出无限的事物。”⁸ 这些事物就其自身而言,是诸样态。但就诸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而论,它们并非真正独立的实体,而是实体性的变状(substantive modifications)。因此,实体的繁复性再次得到肯认,因为样态的产物(modal product),通过其变状的力量,并不外在于其所生产的实体。样态性的产物是对其所表现的实体的一个变状,以至于该实体并不脱离(事实上恰恰因)此变状而存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注意到,变状的力量与那使我们得以言说实体是无条件的力量正是同一的:变状所施展的力量,正是实体的无条件的力量。于是我们得到一种既是实体性的、又是变状性的无条件力量——一种实体性变状的力量。
当我谈论“无条件者”(the unconditioned)时,我并非从否定性的意义上,即将其理解为缺乏恰当的制约(conditioning)或规定性(determinacy)。后一种意义上的无条件者,将不过是不确定的(indefinite)而非无限的。然而,上帝的存在与生产之所以是无条件的,乃是因其自身的力量,也就是那种能够生产出其唯一的制约条件便是该原因之自身力量的效果(effects)的能力。 这种致因力(causal power)是无限的,而所生产的无限之物(那些实体性的变状)也必须安置于它的无限力量之中。但若这些属于上帝所生产之无限之物的是实体性的变状,那么它们如何既是具有规定性的(determinate),又依然内在于(inhere in)一种无条件的力量之中呢?毕竟,无限的事物,即实体性的变更,显然是原因的效应(effects)。那么,一个结果如何能对产生它的那个原因的无条件力量有所主张?德勒兹的回答是:上帝“‘在同样意义上’是万物的原因,正如[上帝]是其自身的原因一样。”⁹ 样态不同于上帝之处在于它们是效果,即它们不是自因——但这并不使它们置身或屈居于因果力量之外或之下。一个样态的本质(modal essence)是一个力量的度数(degree of power),但这力量并不是其他的,而就是上帝的力量,因为样态的力量与神性的力量是内在相关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内在性与流溢(emanation)比较,以作某种阐发。流溢是一种与内在性相近而又明显不同的因果范式。所谓流溢,指向一种建立起赠予者相对于受予者之至高地位(eminence)的给予。结果,虽然由原因所生,但在其被产生出来的过程中便和原因相分离。因此,连结结果与原因的流溢,创造出一种原因高于结果的等级制(hierarchy),因为结果并未充分留驻于原因之中。此种情形下,一个结果仅仅通过出离与复归(exitus and reditus)的中介才从属于原因。诚然,这种流溢并非二元论的(dualist),因因为结果之生产的理由是在原因之中被发现的,并使我们返回原因。尽管如此,结果的生产不能与原因的自我生产(或自我存在)在同样的意义上被谓说。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留驻于原因之中,但并非在原因停留于自身之中的那种相同意义上留驻。另一方面,内在生成/虹吸(Immanation)则以原因与结果的内在性为标志。结果固然是某种可与原因相区分的东西,然而它留驻在原因之中,“其程度不亚于原因留驻于自身之中”。¹⁰ 因此,结果的生产确可与原因自身的生产(或存在)在同样的意义上被谓说。那么,正是在这种方式中,样态的力量(结果)与神圣的力量(原因)是内在相关的。
原因与结果的内在性把变状(affection)引入了内在性的核心。在流溢中,结果不能触动(affect)原因,因为结果并未留驻于原因。同时,结果的生产也不能涉及结果之所引发的变状(affection)的生产;被生产者不能触动(affect)生产者。在流溢中,原因拥有生成结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代价是拒绝被自身所生成的结果所触动(affect)。这与内在性截然不同,在内在性中,上帝“生产无限的事物,而这些事物以无限的方式触动(affect)着他”。¹¹ 上帝的生产性力量并不因变状(affection)而受损——恰恰相反,它被增强了,因为力量不仅包括生成结果的能力,还包括接受被由结果所生产者触动(affect)的能力。我们此前已经看到:存在的力量与生产的力量是同一的;变状的力量与上帝的力量是同一的;现在还应该补充:受触动(affected)的力量也是这同一种力量。于是,无限者的无条件力量可以表述为:原因 → 结果 → 对“原因 ”的变状(cause → effect → affection of cause)。正如上帝生产无限事物这一行动实际上构成了实体自身之生产——因为实体除非作为其(自身的)变状就不会存在——同样,由无限之物带来的变状(affection)也是实体自身的生产。这种影响和变状(effection and affection)的双重构成(double constitution),是因果内在性的一个结果,在此,上帝的无条件力量既是因果性的(causal)又是情动性的(affective)。(译注:本段进行了一些灵活翻译,但请注意这里对affect(affectus)/affection(affectio)的使用背后有着严格的斯宾诺莎-德勒兹语境)
有规定的生产(作为结果的样态[modes-as-effects])与无条件的生产力量(作为原因的实体[substance-as-cause])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德勒兹对内在性的表现性加倍(expressive doubling of immanence)的断言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宣告。样态的结果(modal effects)直接地表现原因,以至于变状立即就是实体自身的变状。因此,内在性不同于至高(eminence),在后者中,结果是在一个次于原因的层面上表现原因。对于内在性而言,结果毫无分离地表现原因——并且,再说一次,正是因为这种表现是无分离的,结果才能够被理解为环绕回来(looping back)以触动(affect)它们所表现的原因。总之,样态的表现(modal expression)内在于(inheres in)无条件的生产力量,但又同时对后者具有规定性;样态是赋予所表现的力量以规定的那一表现。这意味着存在一种“‘表现之于表现自身的内在性,以及被表现者之于其表现的内在性’的双重内在性”。¹² 表现与被表现者的双重内在性确实承认规定活动(determination)与被规定者(what is determined)之间的差异,但它同时将规定活动(结果,或样态的表现)与被规定者(原因,或实体)置于内在性中,以至于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赋予优先性。因此,原因与结果之间没有同一性(identity),但它们确实是内在相关的,所以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分离。其结果是,上帝的表现性结果(expressive effects)并不位于上帝的无条件力量(即被表现者)之下,因为原因正是被这些表现性结果所规定的。
内在性的双重化(doubling)——即表现与被表现者、样态与实体、规定活动与无条件者之间的内在性——还可用外展(explication)和内蕴(implication)来分析。结果是原因的外展:它们表现性地铺展(unfold),或赋予无条件者以规定性。与此同时,这外展从不与原因分离;它留驻于原因,正如原因自留于自身。因此,结果不仅仅是原因的外展,它们也依然内含于——被卷回(folded back into)——原因之中。我们据此得到一个开褶与合褶(unfolding and enfolding)的过程:一个在多样的开褶与合褶的整个过程中,无条件的力量从未被削弱或耗尽。表现的力量、或上帝,从不缺席于任何其表现或结果;它总是每一表现活动的“被表现者”(what is expressed)。这意味着,虽然每一个表现都是有规定的,但它从未与无-条件者相分离。
表现的双重内在性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每一个表现都在其自身之内,包含着其被再-表现(re-expression)的理由。¹³ 这是因为表现的外展总是可以与其内蕴互相转换。让我们设想,例如,一个给定的表现(E1)。如上所述,E1是无条件原因的展开,并且作为此种外展,它赋予原因以规定性。然而,表现的力量,或无条件的原因,并不超越这个给定的表现。这毕竟正是内在性之双重性(doubleness of immanence)的要点所在:表现内在于被表现者,而被表现者亦内在于表现。那么,回到我们的例子,我们看到E1不仅展开无条件者,它也依然内含于无条件者之中。这意味着,即便在E1赋予无条件者以某种规定性的同时,这种规定性也绝不会损害或妨碍无条件者的力量。
如果E1不仅外展而且也内蕴着无条件者——也就是说,它不仅被无条件者所致成(effected by),而且也环绕回来并触动(affects)了无条件者——那么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初始的表现。必定会有一个后续的表现(E2)。如果E1这个结果,是原因的一个内在的双重体(immanent double),那么它就会加倍地返回到原因之上。当它这样做时,必定会发生某种变更(alteration)——也就是说,当E1双重地返回到原因之上时,原因便以生产出一个新的表现,即E2,作为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E1,由于其在原因中的内含,而要求着E2。换言之,正是因为E1依然被卷回到原因之中,所以在其自身的开褶与合褶的动态“之后”,E2 必然出现。当然,E2 与 E1 具同一地位:关于 E1 与无条件的关系所说过的一切,同样适用于 E2。因此,重点不在于E2在某种程度上是对E1的一种必然改进(a necessary improvement),而仅仅在于一个E2必须涌现。并且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以至于E2要求E3,E3要求E4,如此等等。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我所说的“再-表现”。
因此,被再-表现,并非要抹除其展开,而是要将此展开折回到那驱动它的力量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带来一个新的表现的生产。这种再-表现的逻辑极为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解释内在性如何促成新颖之物(the novel)的创造。通过再-表现的逻辑,超越性的挑战开始得到回应。这是因为再-表现阐明了在内在性之中,新的事态(new states of affairs)——即实在(reality)的新表现——涌现的必然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挑战具体来说是:如果我们不接受存在某种超越实在之既定坐标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够解释我们何以能与这些坐标决裂?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超越如其所是地被给予的实在,那么我们能以何为据,去想象某种能够逃离实在之主导性坐标(regnant coordinates)的东西呢?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超越既定之物,又如何能与既定决裂呢?
于是,再-表现提供的,是一种阐明内在要求(immanent demand)的方式,这种要求指向某种不局限于所予的东西。它阐明了所予如何超越其自身,当前的表现——因为它依然内在于它所表现的无条件力量——如何必须引出另一个表现:E1 作为无条件的内在双重(immanent double),必然引出另一个无规定的双重,即 E2。重要的是,这一另一个表现的生产是必然的。样态的表现是以与上帝或实体的存在所凭借的同一必然性被生产出来的,因为样态的表现生产着上帝的存在;既然样态的表现必然被再-表现,则样态的再-表现同样是必然的。然而,即便另一个表现的涌现是必然的,这个另一表现的本性却是偶然的。表现必须被再-表现,但再-表现究竟与最初表现相似还是与之偏离,则依然悬而未决(up for grabs)。因此,再-表现因此是必然地偶然的(necessarily contingent)。埃里克·阿利耶(Éric Alliez)贴切地指出:德勒兹受斯宾诺莎启发的内在性总是遵循“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 =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一等式。¹⁴ 还可补充:表现之所以直接就是建构,是因为表现必然地必须被“再-表现”。建构与表现因而按同一必然性推进:一旦有 E1,就必然会有 E2。虽然 E1 是必然的,E2 的涌现也是必然的,但 E2 的具体特征是偶然的——它必须被建构。
于是,我们便可看到,再-表现的逻辑有力地阐明了涌现(emergence)的必然性,并且它这样做时并未离开内在性的架构。此外,应当看到:上述逻辑并未立刻回答那涌现地被建构出来的表现,是否会与给定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甚或是否会更好。再-表现确能迫使另一个表现出现,但究竟是什么使得新的表现能够成为真正新颖的(truly novel),成为对新的东西、对与当前表现决裂的东西的创造,而不是仅仅对既定之物进行重新排列呢?
赋予实存样态以强度(Giving Intensity to the Mode of Existence)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差异在德勒兹的内在性中的角色。正如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已经注意到的:那种产生出与当前事态之差异、或与之决裂的能力,取决于差异在当前运作的方式。以德勒兹语,可以说:正是因为差异以内在的方式存留于给定的表现之中,才会有再-表现,即一个新的表现从一个既有的表现之中涌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仅从无条件的表现的力量角度看再-表现,还要从差异内在于表现的角度考察。我们具体需要看到:无规定的表现的力量正是作为差异而发挥作用。无规定的表现的力量在根本上是分化性的(differential),它无非就是它自身内在的差异。因此,本节我将考察表现的内在的分化特征。
在对样态的解读中,德勒兹区分了内在样态(intrinsic modes)与外在样态(extrinsic modes)。相应地,我们或许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样态的位置(position)内在于属性,另一种是样态的位置外在于属性。这似乎较为玄奥,但它之所以切题,恰恰因为它使我们能够阐明内在性的双重性(doubleness of immanence)。如果,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内在性既是无条件的又是被表现的,或说既是内含的(implicated)又是被展开的(explicated),那么这种双重性就需要在个体(或样态)的层面上得到刻画。那么,样态的内在位置与外在位置之间的区分究竟是什么?以及这种区分如何在个体的层面上与内含和展开相关联?
样态的内强(intensive)位置指称的是其在属性之中的内蕴。让我们回想一下,样态就是它内在(intrinsic)地规定着属性的强度的度数(degrees of intensity),而这正是样态的内强位置的含义。然而,即便样态以内强方式规定属性,它们也同时展开着属性——即广延地(extensively)发展其内强规定。这就是样态的广延位置。重要的是要理解,内强与广延是同一样态规定的两个侧面。 样态的强度是其在属性中的内蕴,而样态的广度(extensity)即其对属性的外展。进一步地,我们可以观察到,是内在(intrinsic)样态生成了外在(extrinsic)样态:外在(extrinsic)样态是内在(intrinsic)样态的结果或展开,是其内蕴之外展。样态的规定性之所以拥有一张广延的、阐释性(explicative)的无限,恰恰是因为样态早已经内含于——既是内在于亦是构成着——属性。正如德勒兹所言:“量并非因其部分之多而为无限,而恰恰是因为它是无限的,所以才分化为超出任何数目的众多部分。”¹⁵
德勒兹坚持个体必须从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性角度来理解,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把握内在性为何不可被还原为给予之物。用我们当前正在建立的术语来说,内在性的既定表现将被等同于外在样态的集合。内在性的无条件力量并未被所给之物所穷尽这一事实,正由这些外在样态在属性之中的内蕴所表明。正是因为样态从不仅仅是外在地被定位,而总是同时内在地被定位,再-表现才必须发生。样态的广延位置从不是终点,但样态的内强位置也并非就是超越性的——毕竟,广延与内强指向的是同一样态,其区别仅仅在于言说样态的不同位置。但外在与内在是如何相关的?既然它们是在不同方面指向同一样态,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趋近同一事物的不同路径呢?
对于斯宾诺莎而言,内强样态与广延样态之间的这种关系,包含着一种一一对应(one-to-one correspondence)(我将称之为“关联/相关”[correlation])。¹⁶ 在这种关联存在之处,很难想象一个非常动态(dynamic)的过程——事实上,这样一个外展与内蕴的过程、再-表现的过程,如何能由这种关联所生产,是不清楚的。因为如果内强与广延是相关的,如果它们彼此相似,那么于它们之间就不会存在张力——没有不均衡(disequilibrium)。而如果没有不均衡,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催化运动。因此,德勒兹将内在性的个体论发展到了这一关联性框架(correlational framework)之外就显得格外重要。具体而言,他通过将内强样态表现阐明为一个由诸奇异点(singularities)构成的场域(field),从而回避了关联,这些奇异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强的无限(intense infinity)。德勒兹通过将斯宾诺莎关于内强样态和广延样态的概念推进为虚拟(virtual)与现实(actual)的概念,而取得了这一进展。
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保留下来的,是属性由差异所构成的或属性是内在分化的(intrinsically differential)这一观念。我们已经看到,个体差异是如何被想象为一种内在于属性的差异的:个体或样态之间的差异已经在属性自身之中;样态差异无非就是同一属性内部不同度数的差异。事实上,正是这种样态差异,被内在样态所指称。但问题再次浮现:如果外在样态是这种内在样态差异的关联性外展,那么为何要预设在内在与外在之间甚至会有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求内在与外在之间的不均衡,而关联无法提供这一点。然而,所需要提供的东西的种子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是属性是内在分化的这一观念。
属性之内的差异——即内在样态之间的差异——成为驱动展开的动力(motivating force)。内在差异之所以能够充当动力,恰恰是因为差异,就其自身而言,是内强的(intensive)。要看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将内在差异从任何与外在差异的关系中剥离出来。我们必须独立地思考内在差异,而不带任何由外在差异所呈现的图像。只要外在之物还被纳入视野,内在之物就会被构想为与外在之物(关联地)相关,因此被忽略的,正是内在差异在其自身中运作的方式。那么,差异是如何在内在的层面上,脱离任何与外在差异的关联模型而运作的呢?差异是如何将自身从关联中解放出来,或施展其力量以对抗关联的呢?德勒兹强调的是其纯粹内强(sheer intensity)。一旦内在差异不再与另一组(外在的)差异相关联,这些内在差异就只剩下与自身发生关系了。差异不再与另一组差异一一对应,它们与自身相关——并且既然是差异与差异相关,我们便得到一种相当强烈的混沌(chaos),一种充满着差异引出更多差异的混沌。差异就其自身而言,变成了纯粹内强性的,因为在根本上彼此相异的项之间,所谓“在其间者”恰恰就是内强。差异自身就是内强,而内强则具有一种纯粹分化的特征;差异居于诸内强之间,但内强恰恰就是差异自身。正如德勒兹所言:“‘强度的差异’这个表述是同义反复。强度就是差异的形式。”¹⁷(译注:根据《差异与重复》第375页修改。中译本为:强度是作为感性物之理由的差异形式)
德勒兹将这种分化(differential)的内强叫做虚拟(the virtual)。相应地,样态差异的度数则叫做奇异点(singularities),于是我们可以把虚拟界定为一个由诸奇异点构成的分化的(differential)内强场。引入虚拟作为分化的(differential)强度,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外在(extrinsic)差异(这将被称为现实 [the actual])有着重要的意味。具体而言,正是虚拟的纯粹差异使我们能够以非关联的方式谈论外展。现实之物作为被外展者,并不类似于虚拟的内强分化(intensive differential)。相反,对现实的外展起到了对虚拟之纯粹差异的一种解析(resolution)的作用。于是,变状(modification)不是内在与外在的的相对应(correspondence),毋宁说是把内强之差异或差异之内强广延性地予以解决的过程。内在性的给定表现(现实)被内蕴于一个内强的差异(虚拟)之中,而这个内强差异不仅是该给定表现的条件,也是其他表现之必然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虚拟,正是现实之所以再-表现所凭借的东西。18

虚拟之新(Virtually New)
因此,虚拟是任何现实的规定(actual determination)的条件。然而,因为虚拟是由诸奇异点所规定,所以当它制约现实时,它并不是某种无分化并超越了世界的现实性的一性(oneness)。19 理解德勒兹的虚拟概念,要点在于要强调虚拟的分化规定特征(differentially determinate character)以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交集(intersection)或者交换(interchange)。20
如果保留此前术语,广延样态是诸奇异点的现实化(actualisations)或个体化(individuations)——更精确地说,是诸奇异点之间分化(differential)关系的现实化。这些虚拟奇异点是前个体的(preindividual)——就它们规定了现实的个体化的意义而言——但它们并不是未分化的一,因为它们既是被规定的,也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即便其关系纯粹是分化(differential)的,因而指称一种“非关系”[nonrelation])。德勒兹的个体化理论在此处承债于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而没有人比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更好地阐发了这一联系,他将西蒙东的前个体关系性描述如下:
“尚未个体化之时,前个体的存在已可被看作被关系性所触动。这种前个体关系性,发生在异质性的维度、力量或能量趋向之间,然而又是一种非关系:异质性作为存在的无源始限定(anoriginary qualification)。正因其所有潜能无法同时被现实化,存在由此被说成是多于一的。”21 (译注:关于德勒兹与西蒙东“个体化”的承继,以及Toscano解释的新颖性的说明,另见路易斯·莫雷尔与许煜的论文《强度的政治:论德勒兹与西蒙东思想中的加速概念》,可线上查阅:https://philosophyandtechnology.network/1239/politics-of-intensity-cn/)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虚拟的或奇异的规定方式/序列——其自身是关系性的——与一种现实的规定秩序,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与关系。
虚拟既不与现实同一(关联性的),也不超越现实;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既非类比的(analogical),也非分殊的(equivocal)。诸奇异点规定着虚拟,从而提供一个前个体的场域,这个场域并不类似于它所制约之物,然而这种不类似也并未引入两个层面或两个平面。这个个体化过程必须被理解为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一种通过虚拟的现实化(E1)以及通过其新近涌现的现实化对虚拟的潜在的再-表现(E2)而涌现的关系(the potential re-expression of the virtual by its newly emergent actualisation)。若以关联或超越的方式去想象虚拟-现实关系,便会阻塞个体化的动态过程。
为反对这种将虚拟与现实视为两个平面的误解,德勒兹坚持认为,现实规定的过度(excess)恰因虚拟的奇异的规定。一个由诸奇异点构成的先验(transcendental)场域,设定了一个差异场域,一个客观且被规定的分化场域。德勒兹以此方式评论道,“虚拟的概念不再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这意味着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可以被构想为问题(problem)与解决(solution)的关系:由诸奇点构成的虚拟场域是问题,它制约着由现实所提供的解决。德勒兹在此的巨大进展,是将客观规定性(objective determinacy)与开放性或偶然性(contingency)结合在了一起。诸奇点的客观规定性,或说由诸奇点构成的虚拟场域,必然引出问题式的关系(problematic rel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纯粹内强的差异场域中,将会生产出何种偶然关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虚拟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或说既是客观规定的,也是问题式开放的。诸奇异点使差异变得客观,但它们如此做的差异化方式又使客观性成为问题式。客观性,作为诸奇异点的内强差异,将实在性(reality)赋予了一个超越了既有解答的疑难。²³ 相应地,我们的任务便是将给定的解决问题化(problematise),并凭借这一问题式地平(problematic horizon),去生产新的解答。
因此,探讨虚拟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就是调用一种问题化的实践——也就是说,将已个体化之物,或已经给予之物,置于一个或许可以被以别样的方式解决,或许可以促成其他的解答的虚拟的、问题式的场域中。这种问题与解答的动态——即再-表现的过程——必须被设置在虚拟与现实的共在(coexistence)中。再-表现,当其被当作一个生成的通道(passage of becoming)时,有能力生产除更新、更强的解答,但这一能力的施展有赖于问题的生产。换言之,它取决于使诸奇异点构成的问题式差异化场域,转变为一个思想的问题。思想必须变得与虚拟相称(adequate to),但这种相称并非相对应(correspondence),它毋宁说是一种对问题式客观性的栖居(inhabitation)与主体化(subjectivation)。“理念(Ideas)是思想的差异化”,而“差异化则表达了问题式的客观一致性’”。²⁴ 于是我们既可说“问题就是理念本身”,也可说“一个先验问题的不确定地平”是理念的对象。²⁵ 通往虚拟的通道,或者说问题化的任务,把我们带向我们所卷入的理念的“客观一致性”。这是相称的第一要素,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要与这一问题式理念相称,还必须再-表现其差异化中所内含的内强,要非同一性地或生产性地重复差异。因此,对虚拟的差异的相称,只能经由创造(creation)的方式才可能。
至此,在经历了一段相当密集的抽象论证之后,我们现在正触及差异与新颖之物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the new)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内在性能够想象超出实在的已给定表现的新实在的表现的生产,其所以可能,正因为任何表现都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本性(intrinsically differential nature)。内在性得以超出所给,乃由于所给之物本身的虚拟本性。无论如何,这就是从差异角度而言的再-表现的逻辑。在从差异角度阐明了这一逻辑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从无条件力量的角度来阐明它,以使差异与力量能够被结合在一起。
再-表现中运作的无条件力量,与在再-表现中运作的差异,并非相互分离。相反,无条件力量就是差异。内在性的力量并不超越其差异化架构(differential architecture),它将自身表现为差异,并且从不脱离差异性的表现而实存。“虚拟从不独立于那些在内在性平面上将其切分和划分的诸奇异点。”²⁶ 只要虚拟的诸奇异点给予内在性以规定,就以此制约(condition)着它;而内在性则赋予虚拟一种无条件的力量。德勒兹对差异与力量的交换有一个表述:“事件或奇异点赋予平面以全部的虚拟性(virtuality),正如内在性平面赋予虚拟事件以充分的现实性(reality)。”²⁷ 虚拟使内在性免于崩塌为现实的既定之物:它要求一种从无条件力量的角度对内在性进行的思考,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将此无条件力量与诸奇异点的差异化场域联结起来。因此,我们既可以从无条件力量的角度审视再-表现,也可以从差异的角度审视它。确有一种再-表现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被流溢(emanated)给个体,毋宁说是作为差异而内在于个体。具体而言,虚拟,作为差异化的内强,是现实化背后的动力。它就是再-表现的差异化力量。
再-表现——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模糊地被祈请的力量,而更确切地作为一种确定的、差异化的力量——所昭示的,是这样一种与既定之物的激进决裂是可能的。它展示了想象新可能性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追问,这将如何运作?必须满足什么样的判准,才能确保再-表现的差异化力量被导向新颖之物的创造,而非对既定之物的维系?
对此,我们已隐约得到一个答案:问题化的要求,即变得与任何既定表现中所内含的差异化内强相称的要求。如果新颖之物的创造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必须被问题式(the problematic)所触动,被差异自身的内强所触动。这是一种内在性伦理学(ethics of immanence):被差异所触动,与问题式相称,并从这一点出发去建构新颖之物。然而请注意此种伦理的目标:它以新的实存可能性(new possibilities of existence)为名而被施行。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内在性的伦理学最终而言是政治的,因为它关乎实在的造就(making of reality)。于是,与既定之物激进决裂的政治问题,对于内在性而言,同样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此,伦理学被理解为被问题式所触动并建构新颖之物。因此,进一步阐明内在性之伦理-政治(ethico-political)面向的本性,便是切题的。我们最终将转向这个方向,但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时间的问题。
为铺陈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忆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异议:对差异的肯定,不能脱离对时间的肯定而发生;差异必须被思,但它不能先于时间而被思,它只能作为时间被思——一个不可预先预期的时间。我们在德勒兹的内在性叙述中,已经看到由再-表现的差异化力量引发的新的实存可能性的想象;然而,我们尚未看到时间在这种再-表现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缺漏是严重的,因为再-表现是一个过程,它与时间性(temporal)有明确的关联。没有时间,就没有再-表现。那么,德勒兹的思想是如何将对差异性力量的肯定与对时间的肯定混合在一起的呢?只有当这一点被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推进到伦理-政治之创造的问题。
时间是块儿晶体吗?(Is Time a Crystal?)
通过更仔细地审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探讨时间与再-表现过程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指出,虚拟凭借其由奇异点所规定的内强力量(差异本身)引出一个新的现实化过程。然而,这不应被想象为一个两步过程,因为二者谁也不先于谁:“内在性平面同时包含虚拟及其现实化,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可指认的界限。”²⁸ 然而,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区分虚拟与现实又有何意义?以及这种区分的本性又是什么——如果说在被区分之物间不可能指认任何界限,那么一种区分又何以可能?为此,我们须把现实划分为两个侧面:现实化(actualisation)与已现实化之物(the actualized)。
现实化的疲尽(exhaustion)或终点,是作为“现实”而可见的,于是,“现实是……现实化的产物,是对象,其主体无非是虚拟(the virtual)”。²⁹ 但即便现实是现实化的对象,即便现实是现实化所生产之物,现实也不应与其生产过程相分离。现实是现实化的产物,但它也是环绕回来至那开启了现实化过程的虚拟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化过程会引出一个并不使其自身与此过程之原因(虚拟)相分离的结果(现实)。至少,这便是在现实与虚拟的内在关系中,恰当地谈论现实所意味着的。反之,误解现实,就是将现实看作已从现实化过程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与虚拟及现实化过程相关的现实;毋宁说是已现实化之物。“现实如一颗果子般从平面上坠落,而现实化则将它关联回那个平面,就仿佛是要将一个客体(object)重新转回成一个主体(subject)。”³⁰ 因此,只是把现实看作已现实化之物,是错误的,因为它错失并否定了现实化与虚拟的内在性。当我们感知到现实对象已“坠落于”平面“之外”时,我们只看到了过程的一部分;我们错失了现实对象同时环绕回来以触动(affect)虚拟的方式。³¹
既然现实化能将现实对象关联回虚拟,甚至使得(现实的)对象成为(虚拟的)主体,那么一种虚拟对现实的直接优先性便被拒绝了。这种环绕回来(从现实到虚拟)的过程加倍了现实化(从虚拟到现实)的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谈论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永恒交换(perpetual exchange)。德勒兹说,内在性平面不仅包含现实化,即“虚拟与其他虚拟项的关系”——先验场域的诸奇异点,或差异自身——而且也包含着现实,即“虚拟所与之交换的’项’”。³² (译注:《对话》第223页)这避免了一种困境,即当给定一个现实对象时,似乎唯有先克服现实来回到虚拟,再从虚拟坠回现实,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并不需要克服现实才能抵达虚拟。现实可以直接阐明其自身与虚拟的特定交换。
循着这些思路,德勒兹将坚持谈论“影像与它自身的虚拟”。³³(译注:《对话》第223页)在一个产物与它自身的虚拟的这种永恒交换中,虚拟与现实把它们之间的邻近性(proximity)不断强化(译注:采用田延在《德勒兹:关键概念》中的译法),直至几乎难以分辨彼此:“虚拟愈靠近现实,二者愈不分明。你得到一个仅仅把现实对象及其虚拟影像连接起来的内在环线:一个现实的粒子具有一个与其几乎不分的虚拟的二重。”³⁴ (译注:《对话》第220页)这个“内在环线”就是“虚拟与现实的结晶(crystallization)”(译注:《对话》第221页)。
“虚拟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这种永恒交换界定了一个晶体(crystal)。正是在内在性平面上,才出现了这些晶体。现实的东西与虚拟的东西共存着,并进入一条狭窄回路,持续把我们从一者带回另一者。……纯粹的虚拟性不再需要实现其自身,因为它与现实的东西是紧密相关的,并与现实的东西一起形成了最短的回路。不再有现实的东西与虚拟的东西的不可指定性,而是在两个互换的项之间有不可分辨性。”³⁵(译注:参考网络译本)
因此,晶体指明了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虚拟与现实的内在性达到了一种纯粹性,在这一点上,现实化的过程(虚拟导致现实)与环绕回来的过程(现实触动虚拟)变得不可分辨。这使我们得以看到虚拟与现实的激进内在性,以及再-表现的不可避免。然而,这样做的时候也引出了时间的问题,因为正是虚拟与现实的相对区分,以及现实化与环绕回来的过程的相对区分,帮助我们想象再-表现的时间性。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区分,实则代表着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之间(译注:现实化与环绕回来)的区分,它们似乎是彼此滋养、相互推进,就像一场双人跳山羊游戏。但结晶使这种区分归于无效,因为它指向一种虚拟与现实不可分辨的情境。这是否意味着内在性的目标——如果结晶确是其目标的话——是取消甚至悖谬地超越时间?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内在性,尽管肯定了差异,却未能肯定时间。而情况并非如此,但为了理解其中缘由,我们必须明确地审视时间究竟是如何在虚拟-现实关系中涌现的。
分割时间(Dividing Time)
在虚拟与现实的不可分的中间,仍有一种由时间——即“其流逝(passage)被分划成两股喷流(jets):‘当前的逝去’与‘过去的保存’”——所决定的“裂分”。³⁶ (译注:《对话》第222页)在此,虚拟的时间性由“过去的保存”所标示,而现实的时间性由“当前的逝去”所标示。固然,人们很容易把当前理解为“在连续时间里被度量的一个可变的给定”、一种“假想的单向运动,在其中当前不断流逝直至时间被耗尽”;³⁷ (译注:《对话》第222页)但这将是以一种纯粹现实的方式来诉说时间。这样就未能看到,任何从一个当前到另一个当前的(现实的)流逝,不可没有一股不遵循此单向运动的“同时的时流”:一股“面向过去之保存的(虚拟的) 喷流”。这股“喷流”发生在“比标志着单一方向之最小运动的时间跨度(space of time)还更小的时间跨度”之中。³⁸ (译注:根据《对话》第222页修改)因而“虚拟”保存着过去,以至于这个“小于最小(当前间)间隔”的时间跨度,包含着一个跨越或贯穿每一个当前,甚至跨越可想象的最长时段的长度。“小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单向连续时间中)最小单位的时间段,也正是最长的,长于我们所能想象的(全向连续时间中的)最长单位。”³⁹ (译注:根据《对话》第222页修改)因此,一方面,这股虚拟的时间喷流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被计量,它指称着一个真实的、却又不断消失于一时刻与另一时刻之间的时间;另一方面,它又可被视为比所有这些时刻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长,因为它正是那贯穿并因此环绕着所有这些时刻的东西。
晶体如何与现实的及虚拟的时间喷流间的这种不对称性相连接?并非晶体会以某种方式取消这些时间喷流,更确切地说,是晶体使它们无分离地相互沟通。事实上,晶体无法取消时间,因为时间是不对称的——所以即便当现实的与虚拟的时间喷流被结晶(crystallised)时,它们依然保持着彼此间的张力。因此,结晶所做的,是将我们带入“时间之间”(between-times)或“时刻之间”(between-moments)。⁴⁰ 换言之,它将注意力不聚焦于已耗尽的、已现实化的(actualised)时刻,而是聚焦于那些时刻之间的间隙,在那里,时间一方面正离开一个时刻走向下一个,另一方面又在保存着过去。因此,在结晶中发生的,并非时间的取消,而是对两股不对称时流的同时肯定。晶体因此使我们得以离开一种由诸前后相继的当前构成的时间性,而进入另一种时间性。德勒兹说:“我们在晶体中看见时间。”⁴¹ 晶体得以与虚拟和现实的不对称性相称,因为它把我们推进到时间自身之中,即那个分裂为不对称之喷流的时间。
因此,结晶归属于看见时间自身(seeing time itself)的任务范畴。迄今为止,我们已在概念上探讨了这一任务,尽管概念层面的分析仍将继续,但现在我们必须开始抽绎这一任务的伦理赌注(ethical stakes)。换言之,我们需要将对时间的理解与实存的可能性关联起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将时间的观念当作一种实践来谈论:既是与时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也正因此成为想象时间性实存(temporal existence)或 “栖居于时间之中” (inhabiting time)的方式。具体而言,我们转向德勒兹提出的构想时间的两种实践:艾翁(Aion)与克洛诺斯(Chronos)。⁴² 二者在概念上的差异,意味着它们在时间可能性的层面也有一种差异;而当处于危急关头的(at stake)是关于对未来的想象时,这一点就表现得尤为显著。
虽然应该注意到:当我们开始追踪这个差异时,艾翁使得克洛诺斯无法赎回的可能性得以开启,但是不能因此说艾翁是无限的,而克洛诺斯不是。因为克洛诺斯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在它[克洛诺斯]包容每一个当前、重新开始,并在先前的一个周期之后丈量出另一个宇宙周期,而后者可能与前一个周期同一的意义上,它可以形成环形”。⁴³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6页修改)换言之,克洛诺斯可以在当前的无限继起意义上是无限的。的确,它的诱惑正在于它能把过去的规定维持下去或再生产到未来中去。它以对当前的规制、以将时间化为当前的限缩(delimitation)的方式达成这一点。因此,即便克洛诺斯可以是无限的,它却不能不受限制。但把时间限缩为当前是什么意思,又是——因为正如我们都能发现的那样,当前必然逝去——如何可能的呢?
对克洛诺斯而言,“唯有当前实存于时间之中。过去、当前和未来并非时间的三个维度;只有当前填满时间,而过去与未来是相对于时间中的当前的两个维度。”⁴⁴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5页修改)显然,这里说的并非某个吸收了一切过去与未来的单纯的当前。这会与克洛诺斯式的再生产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 Chronic reproduction)相矛盾。过去与未来对当前有一种不可抹除的扰动,而一个单纯的当前时刻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尚不足以强大到吞噬这种扰动。对克洛诺斯而言,重要的并非将时间吸收进一个特定的当前时刻,而是——更确切地来讲——无限地叙述从一个被限缩的当前到另一个被限缩的当前之间的通道。它是仅仅根据当前把时间理解为不受扰动的诸当前的连续。由过去与未来所引入的扰动,并未被克洛诺斯所否认;它也不护卫一给定的当前免于扰动。毋宁确切讲,克洛诺斯响应并接纳这些扰动,并让它们在许多当前之间被循环(circulated)并吸收。这个“许多”(many)不仅包括继起的诸当前,也包括更广阔的当前(vaster presents),后者把扰动吸纳其中。根据德勒兹关于克洛诺斯的叙述,“任何相较于某个当前(某种广延与绵延(duration))而言是未来或过去的东西,都属于一个拥有着更大广延或绵延的、更广阔的当前。总有一个更广阔的当前在吸收着过去与未来。”⁴⁵(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5页修改)
于是,继起的诸当前通过这些更大的包摄(greater encompassments)而相互关联。尽管必然存在着“一种诸当前本身互相的相对性”(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5页修改),但克洛诺斯根据一种极其广阔(formidably expansive)的流转来组织这种相关性,这是一个可变但永不止息的过程,尽管它不断增生、波动,但只会再生产出一个巨大的、被限缩的总体(totality)——一个并非因其有限性本身,而是以无限地吸纳扰动来作为限缩方式的总体。⁴⁶ 由此涌现的是每一当前时刻对于所有其他当前的不断增益的相互包纳,以此而生成一个无所不包(all-encompassing)的在场的持续性。“克洛诺斯就是相对的诸当前的包裹(encasement),一种对相对的诸当前的盘绕(coiling up),并以上帝作为其极限的圆环或外部的封套(envelope)。”⁴⁷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5页修改) 在克罗诺斯之中有运动,但它总是为“以便在宇宙周期的游戏中,吸收或释放它所环绕的相对的诸当前(拥抱-照耀 [embrasser-embraser])”而运动。⁴⁸(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56-257页修改)
克洛诺斯的双重品格不容忽略:它既能承认一当前被(过去与未来)所扰动,又能(通过另一当前)将之恢复。因此,克洛诺斯并不直接反对过去与未来的扰动。它承认它们,但只能以当前的形式(或包摄着诸当前的形式)来赋予它们声音。
这正是为什么,尽管克洛诺斯愿意承认过去与未来的扰动,它仍不能真正地提出过去与未来的潜能。这些潜能质疑着当前的限缩,而克洛诺斯的本质恰恰在于对这种限缩的执着。这些潜能扰动着当前,但克洛诺斯总是以再供应另一个当前来响应,从而吸纳扰动并重建当前的优先性(priority)。这个新供应的当前继而又在轮到它时被扰动,于是再次需要再供应另一个当前,如此等等……无穷无尽,永不停止,却始终奉限缩之名行事。我们得到了恒常的运动,但它总是被相对的诸当前在一个永恒当前中的盘绕和包摄所规制(but it is always regulated by the coiling and encompassment of relative presents in an eternal present)。于是,克洛诺斯确实“表现了未来与过去对当前的复仇”,却总是“以当前的各个项来这样做——这些是它唯一领会的、唯一受其触动的项”。⁴⁹ (译注:中译本另参见《意义的逻辑》第258页,与原文差异较大)
然而,艾翁(Aion)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当前的理论,另一种时间性的实践。对于艾翁而言:
“唯有过去与未来在固守(inhere[insistent])或续存(subsist[subsistent])于时间之中。 它不再是一个吸收着过去与未来的当前,而是在每一瞬间都切分着当前,并且是同时朝向两个方向无限地将其再切分为过去与未来的一个未来与一个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没有厚度、没有广延的瞬间,将每一个当前切分为过去与未来,而非那些广阔而有厚度的诸当前在彼此相对之中包含着未来与过去。”⁵⁰(译注:中译本另参见《意义的逻辑》第258页,与原文差异较大)
当前不再是一个广阔的、环形的包摄(encompassment),而是一道瞬间的裂缝。这是对当前的“侧身避让”(sidestepping)——但被避让的当前是克洛诺斯式的那种。⁵¹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60页修改)艾翁则提出另一种当前:它属于未来与过去的潜能自身(potentialities themselves)(并因此并非单纯地是当前的)。未来与过去不再被当前所辖制(subjected),相反,当前同时地被生成—未来以及生成—过去所辖制。“不再是未来与过去颠覆着实存的当前,而是瞬间将当前颠倒为固守着的未来与过去。”⁵²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60页修改)与克洛诺斯的、在其盘绕中包容着过去与未来之扰动的圆环相对,艾翁“向两端伸展成一条直线,在两个方向上都不受限”,因为它将当前与其扰动系在一起——这些扰动使当前“永远已然是过去,又永恒地尚未来临。”⁵³(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60页修改)
艾翁式的当前与克洛诺斯式的广袤(vastness)比要小得多,因为在一个本来应该同源(homologous)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它只是一道切口、一个薄片(sliver)或一条裂缝——从而构成一个其间(constituting a between)。然而,重要的是,这是一道真正的裂纹(fissure),时间自身是从同源的发展之中被抽取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翁又比克洛诺斯更大:在其裂缝之内,展开了“一个无限制的过去—未来”,而这是历史的整个循环(诸当前之堆积或总和)之所未曾思及者。艾翁不仅仅是对当前的一种相对化,更是“时间的永恒真理”。⁵⁴ (译注:《意义的逻辑》第260-261页)它之所以引入过去—未来的断裂,恰恰因为它引入了这一永恒真理,即一种纯粹而空洞的时间形式,它先于(prior to)无所不包的克罗诺斯对时间的组织(organisation)。正是在这个由纯粹而空洞的时间形式所制约的破损或裂缝之中,过去成为未来,未来成为过去。有了艾翁,便不再有当前的重建(re-establishment),因为取而代之的是当前向着生成的敞开(opening-up)。
相应地,艾翁式的当前并非时间之中或属于时间的一个时刻,而是时间就其自身(time as such)的引入;时间并非到达某种被规定(determinate)的在场样态,而是以其空洞筛落(winnows out)每一被规定的在场。一片广袤的海洋由此敞开,越过了由那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曾断裂的链条所设下的被持续想象着的界限。但这个“越过”(the beyond)所浮现出来的,除了这个纯粹而空洞的时间本身之外,再无它物。越过与界限相对立,可是越过无非就是时间的内在性本身。时间背负着海洋般的浩瀚,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受限,但这个无限制与有限(finite)又共通起来。“鉴于克洛诺斯是受限制的(limited)而无限的,埃翁则是无限制的——如同未来与过去,但又是有限的——如同瞬间。”⁵⁵ (译注:根据《意义的逻辑》第260页修改)生成的力量并不与有限且偶然的把握相抗衡;也不与之处于零和关系。海洋有其岛屿,空洞而广袤的时间亦拥有其在瞬间中的涌现。
我希望用这种措辞所标示的,是一种无限制的(unlimited)时间——内在性的无条件力量在此涌现——总是与被规定的、个体的存在者的偶然奋斗并置在一起的方式。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将艾翁与克洛诺斯理解为两种时间性实践的看法。无限制者并非一个对象,而是一条通道,它的内强实践可以被个体承行,也可以被其忽略。这种忽略常常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助长,即这样一条通道要求对既定之物的抵抗,或对裂缝的祈请——一道意味着已个体化之存在的裂解(fissuring)的裂缝。
德勒兹在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中,恰恰发现了这种苦行(ascesis)。根据德勒兹的说法,在康德思想之中最核心、最激进的冲力,在于对时间的强调,而这一点恰恰被笛卡尔式的自我所忽略。“从时间理论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比康德式cogito[拉:我思]与笛卡尔式cogito[拉:我思]间的差异更富教益的了。”⁵⁶(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54页)笛卡尔式的“我思”意在充当对实存的规定,但它并未完全成功:被“我思”所规定的“我在”,最终指称的是一个仍然欠规定的实存。为何如此?困难在于规定(“我思”)与被规定者(“我在”)之间的关系的不完备性。笛卡尔没有考虑到对规定活动进行实存论式接纳的可能性的条件。根据德勒兹对康德的解读,我们发现——除了规定与被规定者之外——“第三个逻辑值:可规定者(the determinable),或者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形式,未规定者在其下才被(规定所)规定”。⁵⁷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55页) 若没有可规定性(determinability)的形式,便不可能有对一种作为思想之实存的规定,不可能有“我思”对“我在”的规定,而对于康德而言,“未规定的实存可在其下被我思规定的那个形式就是时间形式”。⁵⁸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55页)
换言之,笛卡尔试图凭借“我思”这一规定活动来规定“我在”这一实存的计划之所以仍不完备,正因其没有涉及时间问题。毕竟,正是时间使得“我思”的规定能够为实存所接纳。一旦这个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被采纳,那么对于德勒兹而言,其回报便是,主体必须不只根据思想与实存来被构成,而且还需根据时间来被构成——事实上,其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时间变得先于思想与实存(后二者依赖于时间)。思想与实存都被时间的中域(milieu)所悬置;它们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这个中域;而就其与这个中域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仍是威被规定的。时间之所以使二者悬置,是因为时间自身仍是未被思考的。于是主体,这个被设想为思想与实存之间的关系的东西,涌现为“从一个末端到另一个末端[,我如同被一道裂痕所贯穿:]它被时间的纯粹空形式割裂。”⁵⁹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56页)在主体之前,有的是时间——或者如德勒兹常说,“唯一的主观性就是时间……而我们内在于时间之中”。⁶0 (译注:根据地《时间-影像》第129页修改)主体并不对时间施加作用,甚至也不是在时间之内行动;是时间打破了主体(cracks the subject),而主体只有就其被打破而言,才能够行动。[译注:根据《柏格森主义》的译法,sujet翻译成主体,subjectif翻译成主观之物/主观的,subjectivité翻译成主观性/主体性,具体根据文本大意斟酌使用]
主体通过这种时间性而进入生成,因为主体关联着时间本身,而时间是不受限的。“时间……将自身分裂为触动者(affector)与受触动者(affected)”,而主体就作为时间的这种分裂而浮现——的确,“自我对自我的触动”(the affection of self by self)成了“时间的定义”。⁶¹ (译注:《时间-影像》第130页)主体因此栖居于时间的裂缝之中,或由时间的分裂所生产。它被时间所触动(时间作为触动者),但这种受于时间的触动开启了主体,使主体进入生成。如此被开启的主体便能够行动,而其行动又环绕回来(loop back),触动时间本身。换言之,这个被打破或被开启的主体,能够基于时间的无限制本性而行动,从而触动时间(时间作为受触动者)。主体将基于同一性的“我”的主体性,换成了时间的主观性,即被断裂的“我”,但在此过程中,它触动了时间自身的建构表达(articulation)。再一次地,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再-表现的力量,此刻是作为无条件力量的一种时间性表现与建构。
这种时间的逻辑与斯宾诺莎式上帝——即内在因(immanent cause)——的逻辑,极为相似:正如原因生产结果的力量与其被结果所触动的力量不可分割一样,时间对主体的触动,也与其被它所断裂的主体所触动,不可分割。

产物的自主性 (The Autonomy of the Product)
然而,仅仅提取出一种时间性主观化(temporal subjectivation)的再表现的过程(re-expressive process)之后肯定其重要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关注该过程所创造的产物,关注时间性主体化这一过程会创造出一个产物这一事实。我之前已经谈到过一种结晶的过程,不过现在我必须对此加以补充说明:晶体是产物的前奏(preliminary to the product),却不是产物本身;晶体必须被打裂。晶体“不是时间,但⼈们可以在晶体中看到时间。⼈们可以在晶体中看到时间的永恒基础,即⾮时序时间(non-chronological time)”。⁶² (译注:《时间-影像》第127页)也正因为晶体让我们得以看见时间本身,它才能够以一种非相互排斥的方式(non-mutually-exclusive manner)将虚拟与现实编织在一起。正是由于将虚拟与现实如此这般地置入时间本身,晶体才会“不断交换构成自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影像,即流逝的当前的现实影像(the actual image of the present which passes)与被保存的过去的虚拟网影像(the virtual image of the past which is preserved)”。⁶³(译注:根据《时间-影像》第128页修改)晶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它促成了一种在截然有别的虚拟与现实这两股时间的喷流(jets of time)之间的摆荡(oscillation),而这种摆荡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两者变得不可分辨(indiscernible)。没有任何潜能被排除在外,因为晶体“吸收了那个……既进入到虚拟,也进入到现实的实在(the real)”。⁶⁴ (译注:在这里,中译本和作者引用明显不同,作者的论述省略了景深的深度影像如何指示出晶体,根据中译本,巴赞在论述《游戏规则》时,阐述了景深如何同时构筑了晶体和吸纳了实在[即景深的实在性],“平⾯影像的镜⼦是真实的,但它不太清晰,⽽深度影像则明确显⽰出晶体的所在,以便让某种物质可以溜到深处或通过深处……但是,景深镜头总是在这个循环中安排⼀个深处,让某些东西溜掉,这就是残痕。”从此可以发现晶体裂开的必要性,见《时间-影像》第133-134页)晶体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回路(circuit),但其深刻性恰恰在于它在所实现的这一过程中的次终极状态(penultimate status)。晶体之后,仍有某物有待生成;某种东西“将从晶体中涌现,一个超越了现实与虚拟的新的实在(a new Real)将会出现”。⁶⁵(译注:根据《时间-影像》第134页修改)
正是为了这个“新的实在”,已经形成的晶体才必须被打破。晶体让我们看见时间,它使虚拟与现实进入回路,但它尚未从时间中生产出任何新事物;它是创造的必要准备,但尚非创造行为本身。超越结晶化,思想必须致力于某种“在晶体内部成形,并将成功地穿过裂缝而出,自由地蔓延开来”的东西。⁶⁶(译注:根据《时间-影像》第135页修改)因此,结晶是创造的一个条件,但我们必须离开——或者说打破——晶体,以便生产出一种“并非预先存在的新的实在(a new reality which was not pre-existent)”。⁶⁷ 流逝的诸当前(现实的时间之流)通过晶体与被保存的过去(虚拟的时间之流)相关联,但它们必须以一种“将自身抛向一个未来,并将这个未来创造为一种生命的迸发(a bursting forth of life)”的趋势,再次从晶体中涌现出来。⁶⁸ (译注:根据《时间-影像》第138页修改)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生产需要结晶,但继而又超越了结晶。
显然,对德勒兹而言,时间的问题总是引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是否有能力时间性地通达并提取出一种可以创造出某种与所予(the given)决裂的东西的力量。这种创造生产出一种新的实在——或一个真实的未来——的方式,在他关于时间的三重综合(three syntheses of time)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明确的呈现,而这三种综合阐明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埃翁式关系(Aionic relation)。“过去和未来并不指向与某个假定为‘当前瞬间’的时刻不同的‘两个瞬间’,而是指向‘当前自身之维度’,就其为‘瞬间之缩合(contraction)’而论。”⁶⁹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30页)此处的关键在于当前内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play);并不存在一个分立的(discrete)当前,因为当前无非是其诸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会被结晶)与这些条件所生产之物(被创造出来的未来)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让我们转向这种相互作用,首先关注其诸条件——即习惯与记忆——的角色,然后再审视那无条件的力量(the unconditioned power)是如何为了创造一个与所予决裂的未来而被再表现的。
德勒兹将习惯视为一种静观,并以此来言说时间的第一次,且是被动的综合(the first, passive synthesis of time)。个体只有在静观中才得以存在,它由其所静观者构成。此综合之所以为“被动”,是因为静观的主体并非先于其所静观之物而存在,反而是由其习惯性静观之物构成。“我们并不静观我们自身,而是在静观中——也就是说,在收缩我们所源自之物中(in contracting that from which we come)存在。”⁷⁰ (译注:根据《差异与重复》第136页修改)因此,习惯的时间性综合,即对所静观之物的收缩,缩合了多重元素,而正是这种缩合(condensation)塑造了当前。
当前由习惯所塑造;被习惯性地静观的东西,便是那被最为收缩者(the most contracted)。习惯,作为“相对于当前而言的瞬间之缩合(a contraction of instants with respect to a present),综合着时间,并由此决定了当前,但它无法解释这个当前何以会流逝。⁷¹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47页)换言之,习惯解释了向一个当前的缩合、某一给定时刻的缩合,但它无法解释这个给定的时刻为何不会驻留。给定的时刻让位于另一时刻,而后者同样是一种缩合,于是习惯再次凸显其作用。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第一个时刻为何会逝去?习惯是每一个当前时刻得以收缩的基础,但它无法成为每一个这种时刻逝去的基础。
正是在这里,德勒兹所坚持的“过去与当前的共时性”(contemporaneity of past and present)观点被提了出来。过去无法从“被收缩的诸当前的流逝”(the passage of contracted presents)中推导而出,因为这样一来,当前之流逝这一事实本身将变得无法解释。
事实上,我们不能相信过去是在其曾为当前之后,或因一个新的当前之出现,才得以构成。“假如过去为了使自身被构成为过去而等待着一个新生的当前,那么先前的当前就永远不会流逝,新生的当前也永远不会到来。”⁷²(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47页)
换言之,过去并非在当前流逝之后才到来。如果过去必须等待当前流逝,如果过去只有在当前逝去之后才生成,那么当前何以会流逝这一事实本身,就将变得毫无道理。必定有某种东西在驱动着当前的流逝(就如一架朝反方向飞行的喷气机)。这个驱动力就是过去:过去并非在当前逝去后才到来;恰恰相反,当当前存在的那一刻,过去就已经在那里了。只有当过去已然在场,当前才会被驱动着去流逝。
这就是为何当前与过去是共时的(contemporaneous): “若非当前’在其为当前之同时’即为过去,则任何当前都不会过去;若非过去’在它之为当前的同时‘即被首先构成,则任何过去都不会被构成。”⁷³(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47页)
因此,过去与当前的共时性解释了当前的流逝。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解释过去与当前的共时性?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纯粹过去”(pure past)。过去,为了能与每一个流逝的当前共时,其自身必须以一种纯粹状态存在——它的存在方式必须既不相对于、也不依赖于当前的流逝。“过去之使某个当前流逝的必然前提,是使另一个当前到来;但它自身却既不流逝,也不到来。”⁷⁴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48页)换言之,过去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当前”(past present),它甚至不是“过去的诸当前”的集合。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当前只要存在,过去就必定已然以某种方式在那里了;它无须等待当前流逝,也非从当前的流逝中派生而来。然而,唯有当过去拥有其自身的存有方式,当过去自主于当前之时,上述情况才可能成立——这便是为何过去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纯粹过去”。作为纯粹过去的过去,因此是时间的一种先验条件(an a priori condition of time)。
它同时也是(时间的)第二次的记忆的主动综合的基础。因此,我们拥有两重协同运作的被动综合,但它们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节奏:
第一次被动综合(习惯)在时间中构成了“活生生的当前”,并使过去和未来成为这一当前的两个不对称的元素;而第二次被动综合(记忆)在时间中构成了纯粹过去,并使先前与当前的当前……成为这一纯粹过去(this past as such)的两个不对称的元素。(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47页。此处中英译文有出入,中译本描述记忆在纯粹过去中构筑了先前的当前与当前的当前或再造中的当前与反思中的未来之不对称性)
第一次与第二次综合分别对应于现实(the actual)与虚拟(the virtual),但还存在着第三综合,它对应于新异之物的生产或者说创造(production of the new, or creation)。一方面,第三次综合超越了前两次综合。现实与虚拟正是通过它才得以被重新表达。就此而言,它命名了一种无条件的、促成与所予决裂的力量(unconditioned power that enables a break with the given)。另一方面,第三综合并不超越(transcend)于前两次综合之外。它内在于(immanent with)它们间,因此我们只有通过重复前两次综合,才能迈向第三次综合。第三次综合是新异之物的生产,但这种生产必须从前两次综合的结晶过程(crystallisation)中浮现(尽管它终将打破这块晶体)。
习惯,作为当前在不同样态中一再地重复,是一种变形(metamorphosis),是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变化;记忆,因为它关涉到每一个当前之中过去的纯粹元素,所以它制约着这些变形运动,并通过再生产(reproduction)与反思(reflection)来重复它们。这两个条件必须被一并肯定并使其结晶化。尽管如此,倘若我们只有这两种重复,那么它们虽然内含活力,最终也只会彼此循环往复。结晶化将是一种辉煌的诱捕(splendid entrapment)。内在性(Immanence),尽管其充满活力,届时也无异于对所予的一场重新洗牌,无异于某种无法真正与所予决裂、无法创造新异之物的东西。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结晶乃是压轴的(penultimate),而非最终极的(ultimate)。终极者乃是第三重综合,它着眼于被晶体所驾驭的过剩(the excess harnessed by the crystal),以便从中创造出新事物。
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生产出新的东西:先在构成过去的样式中重复一次,再在变形的当前中再重复一次。此外,那被生产出来的东西,那绝对新异之物本身,反过来也无非是一种重复:即第三次重复,不过这一次是作为过剩(by excess)的重复。⁷⁶(译注:根据《差异与重复》第163页修改)
这第三次重复,即永恒轮回的重复,它调用了前两次重复,但并不使它们返回。返回的无非是过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第三次重复之产物的过剩。永恒轮回“永恒回归既不使[记忆之]条件回归,亦不使 [变形(metamorphic)之]施动者回归;反而,它要以自身全部的离心之力(centrifugal force)驱离和抛弃它们。”。⁷⁷(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64页) 记忆与习惯因此被它们所准备之物所取代。它们是被规定的条件(determinate conditions),但通过这一重复的通道(passage of repetition),它们被接合到了无条件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unconditioned)上。
时间的虚拟与现实的诸条件(或诸“喷流”)被消解,以让位于纯粹而空洞的时间形式(the pure and empty form of time)。这一形式,在第三重重复之永恒轮回的实践中,上演了“无定形之物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the formless),并“仅使尚未来到者(the yet-to-come)回归”。⁷⁸(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65页) 永恒轮回,就是在被规定的诸制约进程(虚拟与现实,或记忆与习惯)与无规定者的力力量(纯粹空洞的时间形式)的相互作用(interplay)中对新颖之物的构成。
通过第三重综合所创造之物,与那预先实存之物(the pre-existent)决裂,且不可被还原为其,因为第三重综合“构成了产物的自主性,作品的独立性”——它带来了“新的,完完全全的新颖之物”(the new, complete novelty)。⁷⁹ (译注:《差异与重复》第164页)至关重要的是,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通过援引超越之物(the transcendent),而是凭借无规定者的力量,对被规定的(虚拟与现实的)诸条件进行再-表现(re-expression)。通过纯粹空洞的时间形式,这种再-表现以内在的方式(immanently)构造了新异之物。
再-表现的伦理学与上帝的命名(The Ethics of Re-expression and the Naming of God)
再-表现(re-expression)与时间性(temporality)的这种结合是核心所在。
再-表现可以被理解为德勒兹对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海德格尔试图融合内在性与差异这两个主题时所带来的潜能(potentiality)与困难的回应。德勒兹的分化的内在性(differential immanence)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了这两个主题的同一性,即分化性(differentiality)成为了产生表达和对再-表现的内在需求的内强。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内在性是一个关乎再-表现的问题,它才不能等同于对所予(the given)的接受。再-表现的必要性排除了任何趋向于这种接受的可能性。相反,再-表现使得内在性能够想象新的存在可能性。然而,由于这些可能性关乎对已被表达之物的再-表现,它们与那种想要与所予之物(what is given)毫无关系、或在功能上超越所予的新颖性(novelty)的想象无关。再-表现既是拒绝超越所予,也是拒绝接受所予。如果再-表现拒绝了这两种选择,那么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因其所涉及的那种时间性。
这需要我们回想在第一章中的观察,即海德格尔将内在性与差异相联系的做法,在涉及这种联系的时间性构成(temporal constitution)的本质时,陷入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含混(ambiguity)。我们当时注意到,德里达关于延异(différance)的论述是如何试图详尽阐述并处理这一困难的。因此,德勒兹的差异的内在性可以被理解为分享了德里达的关切,因为再-表现的思想需要时间性的思想,尤其是当后者被理解为与一种对时间的埃翁式(Aionic)的栖居(inhabitation)相关联时。正如我们刚才所见,时间性的再-表现所促成的是新事物的创造,在此,被生产性地再-表现之物拥有一种自主性(autonomy),这种自主性可以使其自身区别于过去和现在,即便它是从过去和现在中汲取其材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超越了德里达。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虽可与任何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回归相抗衡,但这样做的时候,它仍然外在于(extrinsic)它所保护的差异。它未曾思及一种与差异的内在关系(intrinsic relation)的可能性,凭借这种关系,差异的盈余(excess)将变得具有生产性,从而创造新事物。德勒兹通过再-表现的埃翁式时间性(Aionic temporality),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与差异的内在关系。对于德勒兹而言,对差异的肯定就是对时间的肯定;这些肯定是直接的,或内在的,以至于对差异和时间的肯定会影响、甚至打破(cracks)肯定者。换言之,肯定差异与时间,就是去再-表现所有的所予,无一遗漏,甚至包括表达的主体本身,但要通过那道裂缝——内强性差异(intensive differentiality)的裂缝,埃翁的裂缝——来做到这一点。在这场碎裂之后到来的再-表现尚不可见,因为它来自对时间本身的肯定。
这些论述让我们得以一窥内在性的伦理学(ethics of immanence)。伦理学对于内在性至关重要,因为再-表现生产新事物的能力取决于个体是否寻求遭遇差异,是否愿意进入内在性的裂缝(the crack of immanence)。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将贯穿于实在(reality)之中的差异化作一件对抗那业已固化之物(what has presently settled in)的武器。在内在性中,新事物的创造离不开一种裂缝的伦理学(an ethics of the crack)。
当我们回想起政治关乎对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时,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伦理学是如何与此政治任务密不可分的。因此,关注政治的这一伦理维度,也就是关注如下事实:寻求改变的政治要求,与回应痛苦、回应不满、回应所予之痛的伦理要求,是不可分割的。这样一种回应,同样是一个再-表现的问题。
因此,对存在的新的可能性的想象,与对痛苦的想象紧密相连。严肃对待这些新可能性的可能性,也就是严肃对待一项任务,即当我们遭遇不满和变革的要求时,要对我们想象力中那些继承而来的习惯(inherited habits of our imagination)进行批判。正如我们在导论中观察到的,除非我们直接遭遇这些所予的坐标的促成性条件(enabling condition),否则就不可能与这些所予的坐标——我们正是用这个坐标轴来想象可能性——发生决裂。遵循尼采的宣告,这个促成性条件就是上帝之名(the name of God)。上帝之名是否必然是超越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否必然排斥(forecloses)内在性——这是我们尚未回答的问题。无论我们如何回答,尝试回答的过程,即审问(interrogating)上帝的命名(这是接下来两章的任务),对于理解时间性的再-表现如何能作用于(be brought to bear on)那些继承而来的想象习惯是必要的。这样的审问也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阐明时间性的再-表现在伦理上展开自身的独特方式。换言之,它与上帝命名中所包含的超越性倾向(transcendent tendency)的竞争,以及与该倾向所主张的“内在性最终无法与所予决裂”这一论断的竞争,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阐明时间性的再-表现用以回应不满体验的独特方式。
Notes
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8. 他在别处也被称为“哲学家的基督”(同上, p. 60)。在以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阐释来引入内在性时,我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德勒兹“历史研究”与其更明显的“建构性”著作之间的区分。当然,鉴于德勒兹众所周知地偏好对哲学史人物进行“修正主义式”的呈现,他本人就助长了这种模糊。但我诉诸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释,并不仅仅是因为德勒兹自有立场的解读方式,而是出于更实质的理由——即斯宾诺莎对于内在性思想的根本重要性(更进一步说,是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释对于内在性思想的根本重要性)。因此,在把握内在性的问题上,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阐释具有极大价值,即便德勒兹“自身”的哲学最终未必会保留某些正统的斯宾诺莎特征(例如实体、属性与样态的三元组结构),而这些特征恰是德勒兹突出的。
2. Gilles Deleuze, ‘Cours Vincennes: Spinoza: February 17, 1981’, available at <http://www.webdeleuze.com/php/texte.php?cle=38&groupe=Spinoza&langue=2>(最后访问:2013年2月18日)。
3. Gilles Deleuze,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Zone, 1990), p. 196.
4. 事实上,这会把我们带回到“多”之问题。
5. 同上, p. 11.
6. 正如德勒兹所言:“God does not produce [substantive] modification outside the modes”(同上, p. 111)。
7.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0.
8. Deleuze, Expressionism, p. 94.
9. 同上, p. 164.
10. 同上., p. 172.
11. 同上, p. 102.
12. 同上, p. 180.
13. 我曾把“再-表现”的观念与“灵性”的观念并置讨论,见 Daniel Colucciello Barber, ‘Immanence and the Re-expression of the World’, SubStance 39.1 (2010), pp. 36–46。
14. Éric Alliez, Signature of the World: What is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trans. Eliot Ross Albert (London: Continuum, 2005).
15. Deleuze, Expressionism, p. 203.
16. 识别并反对“相关论(correlationism)”的任务,如今被视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这一思潮的根本特征。此处不打算与该思潮展开论辩,或更准确地说,不打算回应其对德勒兹思想普遍的冷淡甚至轻视。不过,我对德勒兹如何规避并反对相关性倾向的强调,应被视为一个指示:他的思想并不落入思辨实在论所提出的批评范围。事实上,我认为德勒兹的工作呈现出一种被该思潮过于频繁忽略的思想可能性。
17.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 222.
18. 这并不意味着德勒兹主张某种超世俗性;他的观点并非认为现实之物不真实或相对不重要。恰恰相反,他试图发掘“所给”之内在的可能性条件。比如他说,“差异……乃一切现象的充足理由,是发生之物的条件”(同上, p. 228)。因此,“给定的表现”既不应被压制,也不应被剔除;而应当在其生成论上被理解——那是内强性的。被外展的诸身体不应被其所内蕴者所取代;相反,它们应当发现并把自己卷入那一强度之中,而其身体原已卷入其中。
19. 一种误解似乎支撑着 Peter Hallward 的批评:他认为诉诸“虚拟”无非是一种模糊的神秘主义倾向,至多呼吁一种“出离此世”的运动,即出离现实的身体。Hallward 想强调,“德勒兹的工作远非在描述或改造世界,而是试图逃离世界”的程度。Hallward 断言,“尽管德勒兹把存在等同于创造的活动,但他却把这种活动导向一种沉思的、非物质的抽象”。参见 Hallward, Out of this World: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on (New York: Verso, 2006), p. 7。
20. 现实并非虚拟的“流溢”;实际上,应当沿着 Anthony Paul Smith 所谓“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生态学关系”的方向来把握二者的关系。参见 Smith, ‘Review of Hallward, Out of this World’, Angelaki 12 (2007), p. 154。
21. Alberto Toscano, The Theatre of Production: Philosophy and Individuation between Kant and Deleuz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38。
22.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Zone, 1991), p. 94.
23. 关于德勒兹思想中“差异”的根本“问题性”之数学阐述,参见 Simon Duffy, The Logic of Expression: Quantity, Quality, and Intensity in Spinoza, Hegel, and Deleuze (Surrey: Ashgate, 2006)。
24.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p. 178, 181.
25. 同上, pp. 162, 188.
26. Gilles Deleuze,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Barbara Habberjam, and Eliot Ross Albe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9.
27. Gilles Deleuze, 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 trans. Anne Boyman (New York: Zone, 2005), p. 31.
28. Deleuze, Dialogues II, p. 149.
29. 同上.
30. 同上, p. 150.
31. Deleuze, Pure Immanence, p. 27.
32. Deleuze, Dialogues II, p. 152.
33. 同上.
34. 同上, p. 150.
35. 同上, pp. 150–1.
36. 同上, p. 151.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Deleuze, Pure Immanence, p. 29.
41.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 81.
42. 我当然把克罗诺斯(Chronos)与艾翁(Aion)理解为时间理论,但也把它们理解为“栖居时间的方式”。艾翁的特征在于它能够理论化“纯粹时间”的呈示,即“作为这样的时间”。于是,艾翁的时间实践围绕“纯粹而空洞的时间形式”——也即时间之“无条件性”——而展开。需要申明,时间并非“本质上或自动地”具有创造性,但由于其无条件的性质,“纯粹时间”确实使创造成为可能。艾翁的时间实践,因而指向这样的努力:让时间的无条件性质成为创造的同盟——或使能者。相应地,当时间在克罗诺斯而非艾翁的术语中被理解时,亦会出现与之对应的克罗诺斯式时间实践。简言之,克罗诺斯的时间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并不进至“纯粹而空洞的时间形式”。
43.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63.
44. 同上., p. 162.
45. 同上.
46. 同上.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里把“循环(circulation)”与克罗诺斯 (Chronos) 关联,而非与内在性之创造能力所属的时间性关联。就我所论,“循环”并非善;它更多是一种维持当前的方式,且尤其是通过“流动性”的隐喻来维持之。无论内在性为何,都不应被理解为对“循环”的肯定,而应被理解为对“循环”的断裂。[译注:《时间-影像》第127页,“ 时间应该在它停顿或者流逝时进⾏分叉,它可以分为两个不对称的流程,⼀个让整个现在成为过去,⼀个保存整个过去。时间依赖于这种分解,⼈们在晶体中看到的,就是这种分解。晶体-影像不是时间,但⼈们可以在晶体中看到时间。⼈们可以在晶体中看到时间的永恒基础,即⾮时序时间。它是Cronos⽽⾮Chronos。”]
47. 同上.
48. 同上., p. 163.
49. 同上, p. 164.
50. 同上.
51. 同上, p. 165.
52. 同上.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同上.
56.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 85.
57. 同上, p. 86.
58. 同上.
59. 同上.
60. Deleuze, Cinema 2, p. 82.
61. 同上., p. 83.
62. 同上, p. 81.
63. 同上.
64. 同上, p. 85.
65. 同上, p. 86.
66. 同上.
67. 同上.
68. 同上, p. 88.
69.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 71.
70. 同上, p. 74.
71. 同上, p. 81.
72. 同上.
73. 同上.
74. 同上, p. 82.
75. 同上, p. 81.
76. 同上, p. 90.
77. 同上.
78. 同上, p. 91.
79. 同上, p. 90.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