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袁不帝——中国失落的第二条现代化道路
歷史的三岔口——1916年的迷霧與迴響
1916年3月22日,北京,居仁堂。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絕境中,宣布撤銷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這場僅持續了83天的復辟鬧劇,以一種近乎羞辱的方式草草收場。僅僅兩個多月後,袁世凱在無盡的悔恨與憂憤中病逝。
歷史教科書通常將此事件定義為「倒行逆施」,是袁世凱個人野心的醜陋暴露,是辛亥革命果實的一次重大危機。然而,一個多世紀後,當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重新審視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更為深刻且令人扼腕的問題浮出水面:袁世凱的稱帝,是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失敗,更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次「致命歧途」?它是否斬斷了一條與我們後來所經歷的、充滿動盪與革命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通往現代國家的「第二條道路」?
這條「失落的道路」究竟是什麼模樣?它通向一個怎樣的中國?它的夭折,又給百年來的中國帶來了何種深遠而複雜的影響?本篇將嘗試回到那個歷史的三岔路口,探討那個宏大的「如果」——如果袁世凱沒有選擇黃袍加身,而是作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走完他的任期,中國的命運軌跡將會如何不同。
黎明前的脆弱平衡:民初政局的希望與隱憂
要理解袁世凱稱帝的轉折意義,必須先回到辛亥革命後那個充滿矛盾與機遇的「民初」時代(1912-1915)。彼時的中國,宛如一個剛剛掙脫千年帝制枷鎖、蹣跚學步的巨人,前途光明,卻又危機四伏。
1. 「非袁不可」的政治現實與《臨時約法》的制度設計
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勝利,不如說是多方力量博弈與妥協的產物。南方革命黨人空有理想,卻缺乏足以號令全國的軍事與財政實力;北方北洋集團手握重兵,是當時中國唯一建制化的現代武裝力量;而立憲派士紳則在兩者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調停與平衡角色。
最終,各方達成了「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出任臨時大總統」的政治交易。這一結果,被許多革命黨人視為「竊國」,但從當時的情勢來看,卻是避免國家分裂、迅速穩定局面的最現實選擇。孫中山等人的理想主義,必須向袁世凱的現實主義權力低頭。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將其形容為「歷史的無奈」,一個沒有袁世凱的「北洋之亂」,或許會提前到來,其破壞性未可知。
正是在這種對袁世凱個人權力的高度警惕下,由宋教仁主導設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應運而生。這部憲法性文件充滿了濃厚的「因人設法」色彩,其核心是「責任內閣制」。它試圖透過將行政權力賦予由國會多數黨產生的內閣總理,來架空大總統的權力,將袁世凱塑造成一個種類似英國國王的「虛位元首」。
這便構成了民初政治最核心的矛盾:一個手握軍權的實權總統,與一部旨在限制其權力的憲法之間的對立。這套制度能否有效運轉,不僅取決於法律條文的精妙,更取決於政治人物,尤其是袁世凱本人的政治德性與克制。
2. 宋教仁的議會夢想與曇花一現的「政黨政治」
1912至1913年,是中國歷史上議會政治最活躍、也最接近成功的時期。宋教仁,這位年僅31歲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是這條道路最堅定的開拓者。他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積極投身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他四處演說,倡導政黨政治、責任內閣,其政治才華與個人魅力傾倒一時。
選舉結果令世界矚目:國民黨在參眾兩院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宋教仁將以黨魁身分出任內閣總理,組織一個對國會負責的「責任內閣」。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如果這一程序得以順利完成,意味著中國的國家權力將首次透過選票而非暴力實現和平轉移與制衡。一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國會,透過其多數黨領袖來掌握行政大權,監督手握兵權的總統——這正是英、美等國現代化政治的核心框架。宋教仁的夢想,是建構一個「政黨內閣,和平競爭」的政治生態,將中國的政治鬥爭納入法治與程序的軌道。
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刺刀的力量。對於習慣了乾綱獨斷、視權力為生命的袁世凱而言,一個處處掣肘、甚至可能動搖其統治根基的「宋內閣」,是斷然無法接受的。
血染的歧路:從宋案到帝制,共和的死亡之旅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滬寧火車站。一聲槍響,不僅終結了宋教仁年輕的生命,也擊碎了中國議會民主的脆弱夢想,將剛起步的民國推上了一條通往暴力與專制的軌道。
1. 宋教仁之死:壓垮共和天平的最後一根稻草
「宋案」的真相至今仍有爭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時任國務總理趙秉鈞,以及其背後若隱若現的袁世凱的身影。無論袁是否直接授意,他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並且在案發後百般阻撓調查,包庇嫌犯,這使得他在道義上已然破產。
此案的惡劣影響是災難性的。它以最血腥的方式向國人宣告:在槍桿子面前,選票和法律不過是一紙空文。政治分歧不再透過國會辯論解決,而是訴諸於暗殺與暴力。這徹底摧毀了民初建立的政治互信。孫中山等人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雖倉促失敗,卻開啟了民國「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袁世凱在軍事上迅速平定了「二次革命」,政治上也開始了系統性地破壞共和制度的行動:
「善後大借款」:未經國會同意,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巨額借款,用於內戰與強化個人權力,在財政上綁架了國家。
解散國民黨與國會:以「亂黨」為名,強行解散了國會中的國民黨,隨後乾脆解散整個國會,使最高民意機關陷入停擺。
頒布《中華民國約法》:廢除《臨時約法》,推出為自己量身訂做的「新約法」(史稱「袁記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賦予總統無限權力,且可無限連任,實質上成為終身獨裁者。
至此,共和制度的「殼」還在,但其民主、制衡的「核」已被徹底掏空。袁世凱距離九五之尊,僅一步之遙。
2. 帝制的出籠: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騙局
1915年,在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民意」表演下,袁世凱的帝制之路進入了快車道。其子袁克定偽造《順天時報》,營造日本支持帝制的假象;「籌安會」等組織四處活動,鼓吹「共和不適於國情」、「非君主立憲不足以救亡」;所謂的「國民代表大会」更是全票「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
袁世凱為何要走這步棋?後世分析眾多,大致可歸為幾點:
個人野心與傳統觀念:深受傳統皇權思想影響,認為只有「稱帝」才能名正言順、一統江山,實現強國夢想。
權力合法性焦慮:民選總統的合法性根植於憲法與民意,一旦國會不存,其權力便成了無源之水。他試圖透過「君權神授」的傳統模式,為自己的統治尋找一個更穩固、更「終極」的合法性來源。
應對日本的「二十一條」:1915年初,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在屈辱的談判中,深感國力之衰、民心之散。他與身邊的一些人(如楊度)可能真心相信,只有恢復帝制,才能凝聚人心、強化中央集權,以應對外侮。
親信的慫恿與誤導:身邊人為了「擁戴」之功,不斷營造「萬民擁護」的假象,使其對內外形勢產生了嚴重誤判。
然而,袁世凱及其追隨者們嚴重低估了「共和」二字經過辛亥革命洗禮後,在中國人心中,尤其是在知識份子與地方實力派心中的份量。它已不僅僅是一種政體,更是一種思想解放的象徵,是國家走向文明的標誌。復辟帝制,無異於對時代的公然背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1916年元旦,改元「洪憲」。然而,他等來的不是萬國來朝,而是四面楚歌。蔡鍔、唐繼堯在雲南首舉義旗,組織「護國軍」討袁,各省紛紛響應。北洋集團內部也分崩離析,段祺瑞、馮國璋等心腹大將或明或暗地抵制。最終,這場皇帝夢在唾罵聲中宣告破產。
失落的道路:一個憲政框架下的「強人政治」
現在,讓我們開啟思想實驗,回到那個關鍵的節點。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或者「宋案」能在法治軌道內得到公正處理,迫使袁世凱做出讓步而非走向極端,那條「失落的道路」會是怎樣的?
這條道路,可以被概括為:在憲政框架下,以一個強勢總統和一個責任內閣相互制衡、合作為特徵的,漸進式、穩定的現代化路徑。
1. 制度層面的可能性:總統與內閣的「權力二元結構」
這條道路的核心,是袁世凱的「槍」與宋教仁的「票」之間達成一種脆弱但有效的平衡。
袁世凱作為大總統:他將繼續擔任國家元首和軍隊最高統帥。憑藉其在北洋軍中的絕對權威和處理複雜政務的經驗,他將是國家穩定與統一的壓艙石。在外交、國防等領域,他將擁有巨大的話語權。但他必須接受國會的監督,其任命高級官員、宣戰、媾和等權力,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他的權力邊界,將被法律清晰地界定。
宋教仁(或國民黨代表)作為總理:他將領導內閣,掌握實際的行政權,負責內政、財政、教育、實業等。内閣對國會負責,其政策必須贏得國會多數的支持。國會可以透過預算審批、質詢、甚至倒閣等方式,對內閣進行有效制約。
這種「權力二元結構」在很多轉型國家都曾出現。它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緊張關係,總統與總理之間必然會爆發激烈的政治鬥爭。袁世凱會想方設法擴權,而宋教仁的內閣則會竭力捍衛國會與憲法的尊嚴。然而,關鍵的區別在於,這種鬥爭將在國會、在報紙上、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而不是在戰場上。
這種持續的政治博弈,雖然效率可能不高,但其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現代政治訓練。它能教會政治菁英們如何妥協、如何遵守規則、如何在不翻桌的前提下爭取利益。這正是中國幾千年「人治」傳統中最缺乏的元素。
2. 經濟與社會層面的發展: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
一個不稱帝、不搞獨裁的袁世凱政府,即使磕磕絆絆,也能為中國提供一個比後來的軍閥混戰時期寶貴得多的穩定發展環境。
統一的中央政府與財政:「宋案」後,袁世凱透過「善後大借款」獲得了財政獨立,但也埋下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裂的禍根。在一個合作的政府框架下,中央財政的建立將更具合法性。國會將有機會審查預算,確保資金用於國家建設而非內戰。一個統一的、可預期的稅收和貨幣體系,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可以預期,榮氏兄弟、張謇等實業家的「黃金時代」將會更長久,規模也會更宏大。
法治建設的延續:民初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高潮。以《天壇憲草》為代表的制憲努力,以及大理院的司法實踐,都顯示出中國建立現代司法體系的巨大潛力。如果政治沒有走向破裂,這一進程將得以延續。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能夠保障公民財產安全、契約自由,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軍隊國家化的契機:袁世凱稱帝並敗亡,直接導致了北洋軍的分裂,開啟了「軍閥割據」的黑暗時代。如果袁世凱作為總統終其任,他有機會利用其個人威望,在國會的監督與財政支持下,逐步將北洋軍從一支私人軍隊改造為一支忠於國家的國防軍。軍官的任命與調動將逐步納入制度化軌道,而非全憑個人效忠。這無疑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但至少存在這種可能性。
3. 思想與文化領域的演進:更為平和與多元的啟蒙
袁世凱稱帝的失敗,以及隨後的軍閥混戰,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知識界。共和的幻滅感,催生了更為激進、更為徹底的反傳統思潮,即「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當然有其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其「全盤性反傳統」的傾向,也為後來的思想一元化埋下了伏筆。
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共和體制下,思想啟蒙的進程可能會更加平和、漸進。
改良主義思潮的延續:梁啟超等人的改良主義、漸進變革思想,可能會獲得更大的市場。人們會對制度建設抱有更多的耐心,而不是急於尋求一種「根本性」的文化或社會革命來解決所有問題。
多元思想的並存: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潮,將會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下,以學術辯論、政黨競爭的方式共存,而不是迅速走向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將得到更好的保障。
這條失落的道路,並非一條通往天堂的捷徑,它同樣會充滿荊棘與鬥爭。但它通向的,很可能是一個避免了長達數十年內戰、社會撕裂與「救亡壓倒啟蒙」悲劇的中國。它將是一個在政治上學習妥協、在經濟上穩步發展、在思想上兼容並包的現代民族國家。
現實的軌跡:軍閥混戰、革命狂飆與現代化的畸變
袁世凱的皇帝夢,如同一塊巨石,將中國這輛剛駛上共和軌道的列車徹底撞出了軌道。他死後留下的權力真空,沒有任何一個繼承者能夠填補。北洋集團迅速分裂為皖、直、奉等派系,中國陷入了長達十餘年的軍閥混戰時代。
這是對那條「失落道路」最殘酷的反證。
1. 政治上的全面崩壞:從「偽共和」到「無共和」
袁世凱死後,北京的中央政府名存實亡,淪為各派軍閥輪流控制的傀儡。「府院之爭」、「張勳復辟」等鬧劇接連上演,國會和憲法徹底淪為軍閥們裝點門面的工具。政治的邏輯徹底退化為赤裸裸的暴力邏輯——誰的拳頭大,誰就掌握真理。
國家統一的喪失:軍閥們「據地為王,遍地皆兵」,各自為政,稅收、軍隊、法律皆不統一。這比晚清的「東南互保」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家實質上陷入了分裂狀態。
政治文明的徹底倒退:民初尚存的選舉、議會、政黨、法治等一絲現代政治的血脈,被軍閥們的槍砲、暗殺、賄選徹底敗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強權即公理」成為唯一的信條。
2. 經濟與社會的巨大劫難
軍閥混戰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摧殘是全方位的。
經濟浩劫:連年不斷的內戰,直接破壞了農業生產和工商業活動。軍閥們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隊,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甚至將稅收預徵到幾十年後。他們濫發紙幣,導致金融混亂。民族工業在短暫的「黃金時代」後,陷入了凋敝。
社會失序:兵匪一家,盜賊橫行,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教育被摧殘,基礎設施建設停滯不前。數以千萬計的民眾流離失所,死於戰火、饑荒和瘟疫。
3. 現代化的畸變:服務於戰爭的「片面現代化」
在軍閥時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並未完全停止,但卻發生了嚴重的畸變。現代化不再是為了「富國強民」,而是為了「富帥強兵」。
軍事工業的片面發展:各大軍閥都興建兵工廠,購買先進武器,但這種以服務內戰為目的的工業化,無法形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基礎設施的軍事化:鐵路的修建,往往優先考慮軍事運輸的需要,而非經濟發展的邏輯。
人才的逆向淘汰:在那個時代,善於權謀與征戰的軍閥大行其道,而懂經濟、法律、技術的文人與專家則備受排擠,甚至有生命危險。
4. 思想的激進化
共和理想的破滅,以及軍閥混戰的殘酷現實,讓中國的知識份子陷入了巨大的痛苦與迷茫。他們開始深刻地反思:為什麼「賽先生」與「德先生」(科學與民主)在中國會水土不服?為什麼民國會墮落至此?
這種反思最終導向了思想的激進化。
從制度批判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認為,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某個軍閥或政客,而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儒家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從改良主義到革命主義:溫和的議會道路被證明失敗後,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透過一場徹底的、暴烈的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中國。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崛起:國民黨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開始「聯俄容共」,建立黨軍,從一個議會政黨轉型為列寧式的革命政黨,決心以武力統一中國。而更具革命性的中國共產黨,則應運而生,並最終在與國民黨的長期鬥爭中勝出。
可以說,袁世凱稱帝及其導致的軍閥混戰,為後來的國民革命、國共內戰乃至一個高度集權的革命國家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這條我們所熟知的、由北伐、抗戰、內戰構成的「第一條道路」,其起點,正是1916年那場復辟鬧劇的廢墟。
我們能否走出「袁世凱困境」?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那條「失落的道路」真的存在嗎?或者,它僅僅是後人一廂情願的美好想像?
1. 必然與偶然的交織
歷史沒有「如果」。袁世凱個人的權力慾、守舊的思維,以及當時中國深厚的專制傳統、薄弱的公民社會,都使得他最終走向帝制具有某種「內在邏輯」。從這個角度看,共和的失敗似乎是必然的。
然而,歷史同樣充滿了偶然。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如果袁世凱身邊多一些像梁啟超那樣的清醒者,而非楊度那樣的「帝制推手」?如果護國戰爭沒有那麼快爆發,讓他嚐到更久的眾叛親離之苦?任何一個微小變數的改變,都可能讓歷史的河流偏離原來的航道。
承認這條「失落道路」的可能性,並非要為袁世凱翻案,而是要承認歷史的複雜性與多面性。它的意義在於揭示:中國的現代化,並非只有「激進革命」一條華山險路,它曾經有過一個通往「漸進改良」的岔口。
2. 「袁世凱困境」
袁世凱稱帝的選擇,實質上反映了一個困擾中國百年的難題,我們可以稱之為「袁世凱困境」:即在追求國家穩定與富強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強人政治」與「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
強人政治的誘惑:在一個落後、混亂的國家,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似乎是迅速穩定秩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最有效途徑。袁世凱正是打著「富國強兵」、「維持秩序」的旗號,一步步破壞共和制度。這種邏輯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一再重現。
制度建設的艱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夠制約權力的憲政制度,是一個漫長、反覆且充滿博弈的痛苦過程。它需要政治菁英的遠見與克制,需要民眾公民意識的成長。在「救亡圖存」的緊迫壓力下,這種「慢工細活」往往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空談。
袁世凱的悲劇在於,他試圖用破壞制度的方式來獲取穩定,最終卻導致了更大的不穩定;他試圖透過恢復舊秩序來強化權力,最終卻讓自己的權力與性命一同灰飛煙滅。他以最慘痛的方式證明了:任何繞過制度建設、依賴個人權威的「捷徑」,最終都可能通向災難的深淵。一個現代國家的強大,根基不在於某個「強人」,而在於一套穩定、公正、可預期的制度。
凝視深淵,更要尋找出路
回顧那段「若袁不帝」的可能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百多年前的古人舊事,更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上反覆出現的母題。它關乎權力與法律的邊界,關乎菁英的責任與遠見,關乎一個民族在追求強盛時,如何在效率與公正、穩定與自由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
袁世凱稱帝,讓中國失去了一條寶貴的現代化路徑。這條路雖然未必平坦,但它指向的是一個更加多元、寬容、並且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這條路的失落,使得中國在之後的大半個世紀裡,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經歷了無數的動盪與犧牲,才走到了今天。
歷史無法重來,但可以啟迪未來。今天,當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百年前那個功敗垂成的共和開端,我們更應深刻地認識到,制度的價值、法治的尊嚴、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是國家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現代化的不二法門。
凝視歷史的深淵,是為了更好地尋找未來的出路。那個在1916年春天消逝的「第二條道路」的幻影,至今仍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深刻的警示與無聲的叩問。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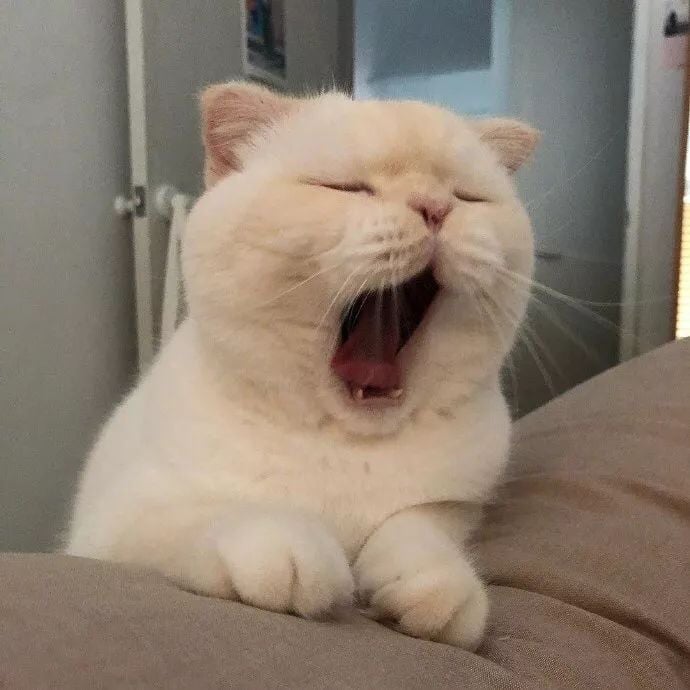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