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孤島,或精緻的牢籠?
一座「無用」的燈塔
在中國的繁華都市中,高聳的摩天大樓與流光溢彩的購物中心定義了天際線。而在這些「有用」空間的陰影下,隱藏著一些「無用」的場所——獨立書店。它們不追求坪效最大化,不販賣快速的消費滿足,而是試圖提供一個緩慢、沉思的「第三空間」。
然而,在當今的中國,經營一家獨立書店不僅是一場商業冒險,更是一場在政治「夾縫」中尋求平衡的艱難實踐。
近年來,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收緊、文化審查的日益嚴格,以及線上電商的毀滅性價格戰和高昂租金的雙重夾擊,中國獨立書店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與「商業」這兩座大山,共同構成了它們難以迴避的現實。
「黃金十年」的終結與「新常態」的降臨
回溯到2010年代前後,中國的獨立書店曾迎來一個短暫的「黃金時代」。彼時,社會氛圍相對寬鬆,公共知識分子活躍,公民社會的概念在都市中產階級中萌芽。
以北京的「萬聖書園」、「單向街」 、上海的「季風書園」、廣州的「學而優」為代表,獨立書店不僅是賣書的場所,更是城市文化生活的客廳。講座、沙龍、辯論在此頻繁上演,它們是思想的交匯地,是自由主義的孵化器,是那一代人心中烏托邦式的文化地標。
然而,這一切在2013年後開始發生深刻的轉變。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意識形態的「緊箍咒」被迅速念響。高校、媒體、出版業首當其衝,「七不講」等內部指令劃定了清晰的禁區。文化空間的「治理」開始強化,「不穩定因素」被逐步清除。
最具標誌性的事件之一,是上海「季風書園」的命運。這家曾以高品質的學術思想講座而聞名的書店,在經歷了多次續租被拒、遷徙、以及「被消防」等一系列打壓後,最終於2018年黯然關閉。季風的消失,被廣泛視為一個時代的落幕——那個允許溫和批評和公共討論的空間,正式宣告終結。
自此,獨立書店的經營者們清醒地認識到,「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常態」:
政治高壓的常態化: 審查不再是偶發的,而是常態的、系統性的。
商業邏輯的殘酷性: 線上折扣與實體租金的矛盾無可調和。
在這種「新常態」下,生存本身,就成了一種「姿態」。
不可見的「紅線」——政治的壓力
對於中國的獨立書店而言,「政治」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具體、細微、且無處不在的日常實踐。壓力來源是多重的,既有來自官方的「硬」監管,也有來自內心的「軟」審查。
「選書」的政治:什麼能賣,什麼不能賣?
書店的靈魂在於選書。但在中國,選書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品味,而是「安全」。
1. 出版物審查的源頭 壓力首先來自源頭——出版業。近年來,中國的書號(ISBN)審批急劇收緊,被認為「有問題」的選題,根本無法進入出版流程。即便是已經出版的書籍,也面臨著隨時被「下架」的風- 險。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書店經營者(化名A先生)透露:「十年前,我們還能進到一些港臺版的『禁書』,或者打擦邊球的社科類書籍。現在,這扇門已經完全關閉了。」
2. 敏感領域的擴大 「紅線」在不斷移動,且日益模糊。從政治、當代史、民族宗教問題,擴展到性別議題、勞工權益、乃至某些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以前我們知道,某些名字和某些事件是絕對不能碰的。但現在,你很難判斷一本人類學著作,會不會因為『不符合主流價值觀』而被盯上。」A先生說。
3. 「自我閹割」的必然 為了規避風險,書店經營者不得不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
迴避「顯學」: 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當代史等領域的批判性著作,幾乎從獨立書店的書架上消失。
轉向「安全區」: 文學(尤其是經典文學)、藝術、設計、哲學(非政治哲學)、生活美學、兒童繪本,成為了書架上的主流。
「選品」的隱喻: 一些書店試圖通過「選品」來進行隱晦的表述。例如,在社會氛圍壓抑時,集中推薦卡繆的《瘟疫》或漢娜·鄂蘭的著作。這成為了一種心照不宣的「接頭暗號」。
「活動」的監管:誰能講,能講什麼?
如果說選書是靜態的風險,那麼舉辦線下活動(講座、沙龍)則是動態的、高風險的實踐。
1. 報備制度的枷鎖 在許多大城市,舉辦涉及公共議題的講座需要向當地文化局、公安局甚至國安部門進行報備。報備的內容包括主題、主講人背景、聽眾規模等。
「這幾乎扼殺了公共討論的可能性。」上海一家小型書店的創辦人(化名B女士)說,「任何稍微『出格』一點的主題,都不可能通過報備。而主講人,如果是『有案底』的學者或記者,更是絕對的禁忌。」
2. 官僚體系的「騷擾」 即便活動本身是「安全」的,也常面臨各種「關照」。
「喝茶」: 書店負責人被有關部門約談,要求「注意影響」、「把握尺度」。
「被消防」/「被衛生」: 這是最常見的手段。在活動舉辦前夕,消防部門或衛生部門會突然上門檢查,以「消防通道堵塞」、「衛生不達標」等理由,勒令書店停業整頓,活動自然流產。
「斷電」/「修路」: 在關鍵時刻,場地周邊會「恰巧」出現市政問題。
3. 向「內」轉的活動策略 因此,獨立書店的活動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從「公共」轉向「私人」: 減少大型公共講座,轉向小型的、會員制的讀書會、分享會。
從「思想」轉向「技能」: 減少社科類主題,轉向花藝、烘焙、手沖咖啡、外語學習等「生活美學」類課程。
從「線下」轉向「線上」: 部分討論轉移到私密的線上社群中,但同樣面臨著「炸群」和監控的風險。
「無形」的恐懼:寒蟬效應
比直接的審查和監管更可怕的,是「寒蟬效應」。
「你不知道紅線到底在哪裡,所以你只能把紅線畫在最安全的地方。」A先生坦言,「久而久之,我們甚至會內化這種審查邏輯,認為某些書『不應該』被推薦,某些話題『不適合』被討論。這是最可悲的。」
在這種高壓下,獨立書店的政治表達空間被極度壓縮。它們很難再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而更多地退守到一個「文化避難所」——為那些在主流敘事中感到窒息的人,提供一個喘息的角落。
「冰河時代」——商業的擠壓
如果說政治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麼商業壓力就是日夜侵蝕基石的冰水。對於獨立書店來說,在「安全」地活下來之後,還必須面對「如何」活下來的經濟問題。
網路電商的「毀滅性」打擊
在中國,圖書市場是一個被電商(如當當、京東、拼多多)嚴重扭曲的市場。「雙十一」、「618」等購物節,圖書的折扣可以低至三折、四折。
「我們書店的進貨折扣通常在六折到七折之間,」A先生苦笑道,「這意味著我們的進貨價,比讀者在網上買到的零售價還要貴。這怎麼競爭?」
這種惡性價格戰,使得獨立書店幾乎喪失了靠「賣書」本身盈利的能力。讀者們往往在實體書店「看樣」,然後轉身在網上下單。
高昂的租金與「網紅化」的詛咒
實體店鋪最大的成本來自於租金。獨立書店通常希望開在人流較多、交通便利、有文化氛圍的區域,而這些地方的租金寸土寸金。
為了解決租金問題,一些書店被迫走向「網紅化」。它們花費巨資進行精美裝修(例如著名的「鐘書閣」),試圖吸引人流前來「打卡」拍照。
然而,「網紅化」是一把雙刃劍。
優勢: 迅速帶來人流,增加了咖啡和文創產品的銷售,甚至可以獲得商業地產的租金補貼(作為「文化配套」)。
弊端: 「打卡」人流(他們被戲稱為「不讀書的讀者」)往往只拍照不買書,干擾了真正的讀者。更嚴重的是,這使得書店的運營邏輯從「選書」變成了「造景」,偏離了書店的核心價值。
讀者習慣的改變
短視頻(抖音、快手)和社交媒體(小紅書)的興起,佔據了人們大量的閒暇時間。深度閱讀的習慣正在快速流失。獨立書店所依賴的核心讀者群——那些願意花時間閱讀嚴肅書籍的人——正在萎縮。
生存之道(一): 「書店+」的複合式經營
面對政治與商業的雙重困境,中國的獨立書店被迫進化,探索出了一系列「曲線救國」的生存策略。其中最普遍的,就是「書店+」的複合式經營模式。
這個模式的核心很簡單:用「不賣書」的方式,來養活賣書的空間。
書店 + 咖啡/茶飲
這是最基礎、最普遍的模式。在中國的獨立書店,幾乎找不到一家不賣咖啡或茶的。
盈利邏輯: 圖書的毛利率極低(甚至為負),而飲品的毛利率極高。一杯咖啡的利潤,可能超過三本書。
空間轉型: 讀者購買一杯咖啡,就可以獲得在書店空間停留一下午的「權利」。書店從販賣「商品」(書)轉向販賣「空間」和「體驗」。
面臨的困境: 隨著連鎖咖啡店的內捲,書店咖啡的專業度和價格並無優勢。很多人調侃,現在的獨立書店,本質上是「裝修成書店樣子的咖啡館」。
書店 + 文創產品
帆布包、筆記本、明信片、香薰、獨立雜誌……文創產品是另一大利潤來源。
IP打造: 一些書店試圖將自身打造成一個文化IP,圍繞IP開發文創產品。
選品延伸: 文創的選品邏G輯與選書相似,體現了書店的品味。
問題: 文創產品的同質化非常嚴重,且供應鏈管理對小書店而言是不小的負擔。
書店 + 藝術/展覽/策展
一些有資源的書店,開始扮演「微型美術館」或「策展人」的角色。
空間利用: 利用書店的牆面和空間,舉辦小型畫展、攝影展。
跨界合作: 與藝術家、設計師合作,提升書店的文化格調。
盈利點: 展覽本身可能不收費,但可以帶動人流,或者通過售賣藝術衍生品獲利。
書店 + 複合業態
複合的程度還在不斷加深。我們能看到:
書店 + 餐廳/酒吧: 如上海的「幸福集薈」。
書店 + 旅宿: 如「在地」 (In-Site) 項目。
書店 + 劇場: 舉辦小型的戲劇朗讀或演出。
「複合式經營」的省思: 「書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書店的生存問題,使其免於倒閉。但這也帶來了一個根本性的追問:當一家書店的主要利潤來源不再是書,它還是一家書店嗎?
B女士對此感到無奈:「我們必須先生存下來。如果空間保住了,書架還在,那麼『書店的靈魂』就還有一個可以棲身的軀殼。如果連空間都沒了,那一切都無從談起。」
生存之道(二):深耕「小眾」與「社群」
在「複合經營」之外,另一條更為艱難、但也更為核心的生存之道,是從「大而全」轉向「小而精」,深耕垂直領域,並圍繞此建立高黏性的讀者社群。
專精化:在「窄門」裡做「深」
既然無法與電商比拼「全」,獨立書店就必須在「精」上下功夫。近年來,中國湧現出一批極具個性的「主題書店」。
詩歌書店: 專注於詩歌的出版、譯介和銷售。
藝術與設計書店: 例如上海的「Closing Ceremony」,專營歐美日的前衛設計雜誌和畫冊。
女性主義書店: 這是近年來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在 MeToo 運動受挫、女權主義被污名化的背景下,一些書店勇敢地以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為主題,為女性讀- 者提供了一個安全、包容的交流空間。
推理/科幻書店: 服務於特定的類型文學愛好者。
這種專精化,不僅是商業策略,更是一種「文化抵抗」。當主流文化日益單一和保守時,這些小眾書店保護了文化的多元性。
社群化:從「交易」到「連結」
獨立書店最核心的資產,不是書,而是「人」。經營者們意識到,必須從「等待讀者上門」轉變為「主動建立連結」。
1. 店主的「靈魂」 與連鎖書店不同,獨立書店的氣質往往就是店主本人的氣質。店主的選書品味、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方式,構成了書店的靈魂。
「策展型選書」: 店主不僅是賣書的,更是「策展人」。他們通過書架的陳列、主題的策劃,向讀者傳遞自己的思考。
「KOL」化: 許多店主本身就是社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 (KOL),他們用自己的影響力為書店引流。
2. 會員制與「共同體」 許多書店推出了會員制。會員不僅是為了折扣,更是為了一種「歸屬感」。
會員專屬活動: 只有會員能參加的深度讀書會、私密分享會。
「儲值」的信任: 儲值更像是一種「眾籌」或「供養」。讀者通過儲值,來表達對書店的支持,確保它能繼續存在。
3. 線上社群的經營 在線下活動受限後,社群經營轉移到了線上。
微信公眾號: 這是獨立書店最重要的發聲渠道。它們不再僅僅是發佈新書和活動信息,而是開始撰寫高質量的原創書評、文化評論。
微信群/小紅書/豆瓣: 用於日常的交流和互動,維繫社群的活躍度。
通過這種方式,獨立書店不再是一個孤立的「點」,而是變成了一個「節點」,連結了作者、譯者、讀者和出版方,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半地下的「文化共同體」。
在「有用」與「無用」之間
獨立書店在中國的生存之戰,遠未結束。它們的困境,是這個時代中國社會的縮影——在追求「富強」和「秩序」的宏大敘事下,個體的、多元的、批判性的聲音,還有多少容身之地?
從商業上看,它們是落後的、註定被淘汰的業態。 從政治上看,它們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需要被規訓和改造。
然而,它們依舊頑強地存在著。
它們從「思想的啟蒙地」退守為「生活的避難所」; 它們從「公共的批判者」轉變為「小眾的守護者」; 它們學會了用賣咖啡的錢去補貼詩集,用隱晦的選書去表達態度,用社群的溫暖去抵抗外部的寒冬。
作家卡爾維諾曾說:「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
或許,在當今的中國,獨立書店的價值,並不在於它能產生多大的「效用」,而在於它的「無用」——它保護了一種非功利的、緩慢的、沉思的生活方式。它像一個錨點,提醒著人們,在抖音和演算法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由文字和思想構築的、更為深邃的世界。
這些倖存下來的獨立書店,無論它們的形態如何變化——是咖啡館、是網紅打卡地、還是女性主義的「安全屋」——它們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姿態,一種拒絕遺忘、拒絕沉默的姿態。
它們是夾縫中的「微光」。微弱,但足以劃破長夜,為那些仍在尋找的靈魂,點亮一盞引路之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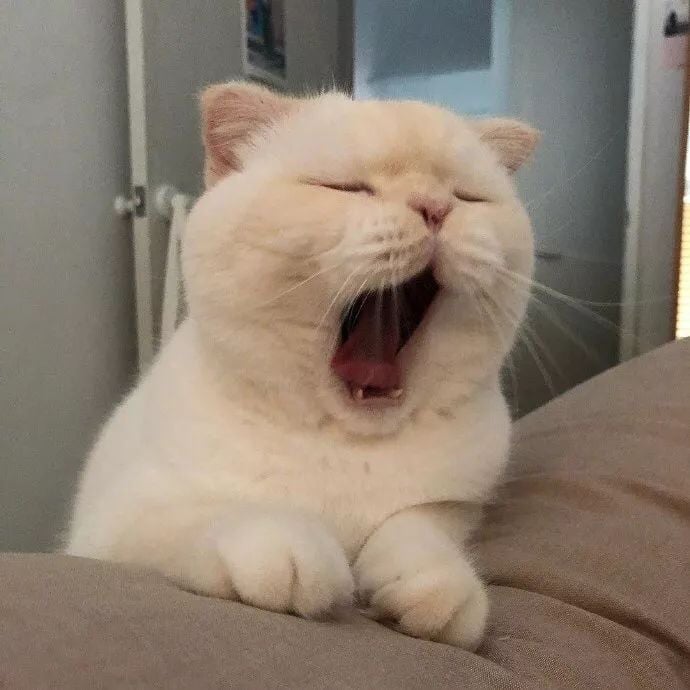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