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審查制度如何侵蝕漢字與語言的根基
消失的詞語與「簡中」的圍城
2020年初,一種後來被稱為「新冠」的病毒在武漢爆發。在最初的幾週裏,一位名叫李文亮的醫生試圖發出警示,但遭到了當局的訓誡。他去世後,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爆發了短暫的憤怒浪潮。人們試圖紀念他,但很快發現,他的名字,甚至「那個吹哨子的人」,都成為了被嚴格過濾的「敏感詞」。
這並非孤例。在當代的中國,「簡體中文」(簡中)網路環境,已經演變成一座巨大的「圍城」。城牆不僅阻擋了外部的資訊,更在內部建立了一套精密的過濾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詞語的「生殺大權」被牢牢掌握。
然而,本文的主旨並非僅僅複述言論自由的喪失。我們要探討一個更為根本、更具侵蝕性的問題:當一個擁有數千年歷史、以「表意」為核心的文字系統(漢字),遭遇了當代最強大、最精密的審查機器時,會發生什麼?
答案是:語言本身開始了「致命的變異」。
為了規避審查,數以億計的網民被迫進行一場永無休止的「語言游擊戰」。他們使用諧音、縮寫、拆字、甚至外語來「繞行」。這場全民參與的「文字雜耍」,雖然展現了民眾的創造力,但其代價卻是高昂的。
審查制度的真正危害,不僅在於它「刪除」了什麼,更在於它「創造」了什麼。它正在系統性地瓦解漢語的精確性、污染漢字的原始意涵、並導致公共話語的極端貧瘠化。這不僅是一場政治壓迫,更是一場針對語言本身的「文化內戰」。本篇報道將深入剖析這場變異的機制、現象及其對漢字、語言乃至國民思維的深遠危害。
審查機器的演進:從「關鍵詞」到「演算法黑箱」
要理解語言的變異,必須先理解那股施加壓力的「外力」——中國的審查機器。這台機器的演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它從笨拙的「守門人」演變成了無所不在的「利維坦」。
階段一:人海戰術與「敏感詞列表」 (1990s - 2000s)
在網際網路進入中國的早期,審查是相對原始的。它主要依賴兩大手段:
關鍵詞過濾: 系統維護一個「敏感詞」黑名單。任何包含名單上詞語的發言(如「六四」、「法輪功」、「民主」)都會被直接攔截或刪除。
人工審核: 平台僱用大量的審核員(俗稱「小管家」)進行事後的人工刪帖。
這個階段的審查是粗暴且滯後的。網民只需稍微變換說法,例如使用「Liusi」或「陸肆」,就能輕易繞過。
階段二:平台的「主體責任」與自動化過濾 (2010s - 至今)
隨著社交媒體(特別是微博和微信)的興起,資訊的傳播速度呈指數級增長。當局意識到,單靠政府無法應對如此海量的資訊。於是,「平台主體責任」被提出。
這意味著,審查的主要執行者從政府轉移到了企業(如騰訊、新浪、字節跳動)。如果平台未能有效「處理」有害資訊,將面臨巨額罰款、下架乃至關停的風險。
為了生存,各大平台投入巨資開發更複雜的自動化審查系統:
擴展的敏感詞庫: 詞庫變得極度龐大且動態更新,不僅包括政治詞彙,還包括社會事件、群體抗議、乃至高層領導人的姓名和相關隱喻。
圖片/影音審查: 系統開始具備光學字元辨識(OCR)和語音辨識能力,能夠過濾圖片中的文字和影片中的言論。
「先審後發」與「僅自己可見」: 許多平台對「高風險」用戶(如公知、維權人士)的發言實行「先審後發」。而更普遍的策略是「Shadow Banning」(影子禁令),即貼文表面上發送成功,但實際上僅作者自己可見,無法進入公共資訊流。
階段三:AI 驅動的「語義審查」與「黑箱」 (近年至今)
當今的審查已進入「人工智慧」階段。這標誌著一個根本的轉變:審查不再僅僅針對「詞語」,而是試圖理解和扼殺「意圖」。
語義分析: 現代的AI模型(如中國版的BERT)被用來分析句子的上下文。這意味著,即使一個句子中沒有任何敏感詞,但如果其「情感傾向」被判定為「負面」或「具有煽動性」,也可能被限流或刪除。
演算法黑箱(Algorithmic Black Box): 審查的標準變得極不透明。沒有人知道具體的「紅線」在哪裡。AI的判斷邏輯是複雜且不可預測的。有時,一篇關於烹飪的帖子,可能因為AI的誤判(例如將「肉末」與某種政治隱喻聯繫起來)而被刪除。
「寧殺錯,不放過」: 由於「主體責任」的壓力,平台的演算法被設定得極度保守。這導致了大規模的「誤傷」。任何可能引發聯想、帶有情緒、或具有集結可能性的內容,都可能被扼殺在搖籃中。
這種高壓、模糊、且全天候的審查環境,構成了語言變異的「培養皿」。當正常的表達路徑被徹底堵死時,語言被迫轉向了地下,開始了其「奇形怪狀」的演化。
語言的「繞行」:一場全民參與的文字「游擊戰」
在「簡中」世界裏,發言如同在雷區跳舞。為了表達,網民發明瞭一套複雜的「黑話」系統,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將其稱為「Algospeak」(演算法語)。這是一場全民參與的「語言游擊戰」,其主要戰術包括:
1. 諧音:
這是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戰術。利用漢語同音字多的特點,尋找「安全」的替代品。
「和諧」->「河蟹」: 這是早期最著名的例子。「和諧社會」是官方宣傳口號,但在實踐中,「和諧」意味著「被刪除」、「被噤聲」。網民開始用「河蟹」來指代這種審查行為。
「政府」->「正腐」/「蒸腐」: 取「腐敗」之意,表達對公權力的不滿。
「刪」->「珊」/「栓」: 「你號沒了」變成「你號栓了」。
「習近平」->「吸精瓶」/「細頸瓶」: 這是極高風險的規避,利用諧音進行嘲諷。
「毛澤東」->「臘肉」: 因其遺體被保存在水晶棺中。
2. 拼音首字母縮寫:
當諧音詞本身也被「污染」並納入審查後,網民轉向了更抽象的符號——拼音縮寫。
「政府」->「ZF」 / 「郭嘉」(國家)->「GJ」: 這是最常見的縮寫。
「傻逼」->「SB」 / 「牛逼」->「NB」: 早期用於規避髒話過濾,後來擴展到政治領域。
「民主」->「MZ」 / 「自由」->「ZY」: 甚至連這些「正面」詞彙,在特定語境下也變得敏感,需要縮寫。
「李文亮」->「LWL」: 紀念的符號化。
3. 拆字、錯別字與圖像:
這是對漢字「表意」功能的直接解構。
「翠」->「習卒」: 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翠」字被拆解為「習」和「卒」(古代指死亡)。這導致「翠」這個本意為「翡翠、青綠色」的優美漢字,一度在網路上完全消失。
「趙」->「走肖」: 來源於魯迅的《阿Q正傳》,「趙家人」被用來指代權貴階層。
故意錯字:「言論自由」寫成「言lùn自由」,「維權」寫成「圍拳」。
「倒車」-> 圖像: 當「倒車」(隱喻歷史倒退)一詞被禁時,網民開始發佈真實的卡車倒車影片,或使用 ◀️◀️ 符號。
4. 中英夾雜與外語:
利用審查系統對多語言混合處理的困難。
「GFW」: 「Great Firewall」(防火長城)的縮寫,已成為中文的標準詞彙。
「Shanghai」->「Shh」: 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間,「上海」一詞變得高度敏感,網民轉而使用英文,甚至其縮寫「Shh」(意為「安靜」)來指代這座城市。
「My duty」: 來自電影《V怪客》的台詞,用於表達抗爭。
5. 萬物皆可「代稱」(Metonyms and Nicknames):
當一個事物的本名無法被提及時,無數的代稱就產生了。
「新冠疫情」->「那三年」/「口罩」/「yq」: 人們用這段時期的標誌性物品或拼音來指代那段創傷記憶。
「習近平」->「那個人」/「他」/「一號」/「皇上」/「維尼」: 由於對最高領導人的審查最為嚴苛,其代稱也最為繁雜,其中「維尼」因為形象相似而成為全球知名的規避詞。
這場「游擊戰」看似充滿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黑色幽默,但其背後,是語言系統的全面潰敗。每一次成功的「繞行」,都是對漢語規範性的一次打擊;每一個新「黑話」的誕生,都在加劇公共交流的隔閡。
漢字的「污染」與「異化」:表意文字的詛咒
漢語的核心是漢字,漢字是「表意文字」。與拼音文字不同,漢字的「形」與「義」緊密相連。一個「字」本身就是一個意義單元,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
審查制度對拼音文字的危害,是讓「詞彙」消失。但對漢語的危害,則更為致命——它在「污染」和「異化」漢字本身。
1. 意義的「覆蓋」與「綁架」
當一個漢字被長期用作政治隱喻或規避詞時,其原始意義會被新的、被扭曲的意義所「覆蓋」。
「和諧」(héxié): 本意是「融洽、協調」。這個詞在儒家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但今天,在「簡中」語境下,它的第一反應是「被審查」、「被刪除」。例如「你的帖子被和諧了」。一個正面的文化核心詞彙,被徹底「綁架」,變成了反義詞。
「正能量」(zhèng néng liàng): 這本是一個物理學名詞,後被官方用來指代一切「積極、健康、向上」的事物。但由於其泛濫使用和對負面現實的強行掩蓋,這個詞已經變成了「粉飾太平」、「盲目樂觀」的代名詞,充滿了諷刺意味。
「韭菜」(jiǔcài): 本是一種常見蔬菜。但現在,它在網路上最廣為人知的含義是「被統治者/資本割了一茬又一茬的底層民眾」。
2. 漢字的「殘化」與「詛咒」
更可怕的是,一些漢字因為其「字形」觸發了政治聯想,而遭到了「放逐」。
「翠」(cuì): 如前所述,這個字因被拆解為「習卒」而遭全網封殺。詩句「一行白鷺上青天」中的「青天」尚可理解,但「翠」字的消失,是標準的「文字獄」。一個承載著「青山綠水」、「珠翠滿樓」等美好意象的漢字,被政治聯想所「詛咒」,變成了不可觸碰的符號。
「瓶」(píng): 因為「近平」的名字,導致「瓶」字變得敏感。在微博上搜索「小熊維尼」和「瓶子」,會發現大量內容被過濾。這導致網民在討論「花瓶」、「瓶頸」等日常詞彙時,也不得不自我審查。
「刁」(diāo): 「習」的簡化字是「习」。一些網民將其拆解為「刁」(diāo)和「...」(省略)。這導致「刁」這個姓氏,以及「刁難」等詞彙,在特定時期也遭到過嚴格過濾。
3. 「表意」功能的瓦解
漢字系統的優勢在於其「表意」的精確性。例如,「民主」和「自由」,這兩個詞的字形和組合,本身就蘊含著「人民做主」和「由自己決定」的深刻含義。
但當這些詞必須被「MZ」和「ZY」所取代時,發生了什麼?
意義的流失: 拼音縮寫是純粹的「表音」符號,它丟失了漢字所承載的全部歷史和哲學內涵。「MZ」不再讓人聯想到「人民」或「做主」,它只是一個空洞的、需要「解密」的代碼。
美感的喪失: 漢語的美感,在於字與字之間的搭配、韻律和言外之意。而「yyds」(永遠的神)、「xswl」(笑死我了)、「zf」(政府)這樣的縮寫,是極度粗糙和貧乏的。
「劣幣驅逐良幣」: 當人們習慣了用「SB」來表達憤怒,用「NB」來表達讚歎時,那些更精確、更細膩的表達方式(如「荒謬」、「無恥」、「精妙」、「嘆為觀止」)的生存空間就被擠壓了。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表意文字」的「拼音化」倒退。漢字的「靈魂」——即它的「表意」功能——正在被審查和規避行為所掏空。
語言的「貧瘠化」與「新話」的幽靈
如果說漢字是漢語的「細胞」,那麼「語言」(詞彙、語法、話語)就是其「組織」。審查制度對漢字的「異化」,最終匯總為對整個語言系統的「貧瘠化」。
這種貧瘠化體現在兩個極端:官方語言的「空洞化」和民間語言的「黑話化」。這兩者共同絞殺了有意義的公共討論,讓人不禁聯想到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新話」。
1. 「新話」的誕生:官方語言的「空洞化」
「新話」的目的是通過限制詞彙,來限制思想的範圍。當代的中國官方話語,正呈現出這種特徵。
正面的「大詞」泛濫: 「高質量發展」、「新常態」、「偉大復興」、「頂層設計」、「賦能」、「抓手」、「閉環」。這些詞彙被大量複製和粘貼在官方文件和新聞報道中。
詞義的模糊: 這些詞的特點是極度抽象和模糊。它們聽起來「正確」,但缺乏任何實質內容和可驗證的標準。什麼是「高質量」?如何「賦能」?
排斥「負面」詞彙: 與此同時,描述現實問題的詞彙被系統性地排斥。
經濟衰退被稱為「負增長」或「轉型陣痛」。
失業被稱為「靈活就業」或「待富人群」。
災難中的死亡人數是「冰冷的數字」,而「感動」和「救援」才是報道的主旋W律。
封城被稱為「靜態管理」或「全域靜默」。
這種官方「新話」的危害在於,它系統性地摧毀了語言「描述現實」的功能。它製造了一個與現實平行的「話語泡沫」。當語言無法準確描述問題時,解決問題也就無從談起。
2. 民間語言的「黑話化」與「圈層化」
與官方「新話」相對的,是民間語言的「黑話化」。
交流的「加密」: 如第二章所述,由於「繞行」的需要,公共討論必須被「加密」。這使得交流變得極度困難和低效。一場關於社會政策的討論,可能通篇由「ZF」、「GJ」、「MZ」、「ZY」等縮寫構成。
「圈層化」與「孤島」: 這種「黑話」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不同群體(如女權主義者、LGBTQ群體、時事關心者)會發展出各自不同的「黑話」系統。
這導致了社會的進一步「碎片化」。公共領域消失了。人們無法再就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有效的、跨群體的對話,因為他們甚至沒有一套共同的、穩定的語言。
「梗」的瞬時性: 網路「黑話」的迭代速度極快。一個「敏感詞」或「繞行詞」可能在幾週甚至幾天內就會失效(被納入新的審查名單)。這導致語言失去了「積累性」。文化和思想無法沉澱,一切都變成了「一次性」的「梗」(Meme)。
3. 「犬儒主義」的蔓延與表達的「降級」
在這兩個極端的夾縫中,一種「犬儒主義」的語言態度開始蔓延。
「感恩」與「贏」: 當網民無法表達反對時,他們轉而使用極端的「反諷」。例如,在任何社會負面新聞下,評論區都會刷起「感恩」、「暖心」、「這一切責任都在美方」、「我們又贏了」。
「哈哈哈哈」: 當反諷也變得危險時,人們選擇了放棄表達實質內容,只留下「哈哈哈哈」或「...」(無語)的符號。這是一種「表達的降級」——從「討論」降級為「反諷」,再降級為「純粹的情緒符號」或「沉默」。
「新話」的最終目的,是讓「異端思想」變得不可能被思考。而當代的審查制度,正在從兩個方向上實現這一點:官方「新話」讓「反對」的語言變得空洞;民間「黑話」讓「反對」的語言變得隱晦和碎片化。
最終,有意義的、清晰的、邏輯嚴謹的批判性語言,在夾縫中窒息了。
心智的「枷鎖」:自我審查與思維的惰性
語言是思維的載體。我們用語言來思考,語言的邊界就是我們思維的邊界。審查制度最深遠、最隱蔽的危害,是它在每個人的大腦中植入了一個「微型審查員」。這就是「自我審查」。
1. 「恐懼」的內化
當一個人生處於一個「紅線」無處不在、且標準模糊的環境中時,他為了安全,會不自覺地擴大「安全區」。
「這個能發嗎?」: 這是「簡中」使用者在發言前最常問自己的一句話。
「算了,不說了」: 這是最常見的結果。相比於花費大量精力去「繞行」、去「加密」,並且還要承擔「解密」失敗後被刪帖、炸號甚至「喝茶」(被員警約談)的風險,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
這種「內化的恐懼」是最高效的審查,它讓每個人都成為了自我監控的「獄卒」。
2. 思維的「簡化」與「惰性」
持續的「繞行」和「自我審查」會極大地消耗心智資源。這會導致一種「思維的惰性」。
迴避複雜思考: 為什麼要討論「憲政」、「司法獨立」或「財政結構」?這些話題不僅危險,而且需要大量複雜的詞彙,這些詞彙大多是「敏感詞」。相比之下,討論娛樂八卦、指責「資本」、或謾罵「境外勢力」要安全和簡單得多。
二元對立的思維: 由於缺乏精確的語言工具和開放的討論環境,人們的思維模式被迫退化到「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如「愛國」vs「恨國」、「我們」vs「他們」)。
喪失論證能力: 當公共討論被「拼音縮寫」、「反諷」和「情緒宣洩」所主導時,個體逐漸喪失了使用邏輯、證據和嚴謹語言來構建複雜論點的能力。
3. 「失語」的一代
對於在「防火長城」和「嚴密審查」環境下長大的一代人(所謂的「00後」、「10後」),危害尤為嚴重。
「歷史的空白」: 他們無法在網路上公開讀到或討論關於「六四」、「文革」(某些方面)或當下的許多社會事件。這些詞彙的消失,導致了歷史記憶的「斷代」。
「政治性抑鬱」: 許多清醒的年輕人,一方面通過「翻牆」等手段了解了外部世界和真實的歷史,另一方面又發現在內部環境中,他們「有口難言」。這種認知失調和表達的堵塞,導致了普遍的政治性抑鬱和虛無主義。
語言的變異,最終導致了心智的「殘疾」。人們不僅喪失了「說」的能力,更在逐漸喪失「想」的能力。當一套語言系統無法再承載複雜、深刻、批判性的思想時,這個民族的集體智慧,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在「加密」的語言中,尋找「意義」的未來
回顧這場由審查引發的「語言變異」,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未來。
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當局看似贏得了「穩定」和「控制」,但他們收穫的是一個充滿「黑話」、犬儒主義、和「測不准」的社會。他們永遠無法知道真實的民意,因為語言的「溫度計」已經被他們親手打碎。
網民看似用「創造力」進行了「抵抗」,但他們付出的代價是語言的「殘疾」。他們在「哈哈哈哈」的狂歡中,逐漸喪失了清晰表達憤怒和訴求的能力。
漢語本身,是最大的受害者。這個承載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語言,其表意的精妙、結構的優美、內涵的豐富,正在被「污染」、「異化」和「掏空」。
審查制度,如同一個「語言的癌症」。它不僅切除了「敏感」的組織,更在體內釋放了毒素,導致了健康的細胞(漢字)發生「變異」(如「翠」、「瓶」),並使整個系統(漢語)功能衰竭(貧瘠化、失語)。
未來會怎樣?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語言強大的韌性。只要表達的慾望還在,人們總會找到「繞行」的縫隙。這種「游擊戰」式的抵抗,本身就是對權力最大的嘲諷。
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繞行」的代價是不可承受的。它正在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侵蝕我們思維的根基。
對於「簡中」世界之外的人們——無論是使用繁體中文的港台、還是海外華人——他們肩負著特殊的責任。當「簡中」的語言功能日益衰敗時,繁體中文(或稱「正體中文」)所保留的語言規範性、詞彙的豐富性和表達的自由度,就成為了整個漢語文明的「避難所」和「基因庫」。保護和使用好這份「未受污染」的語言遺產,就是對這場「語言變異」最有力的抵抗。
因為,當一個詞語在「圍城」內消失時,我們必須確保它在「圍城」外依然被清晰地記住、被有力地使用。這不僅是為了保存漢語的美,更是為了保存我們作為「人」的思考、記憶和尊嚴。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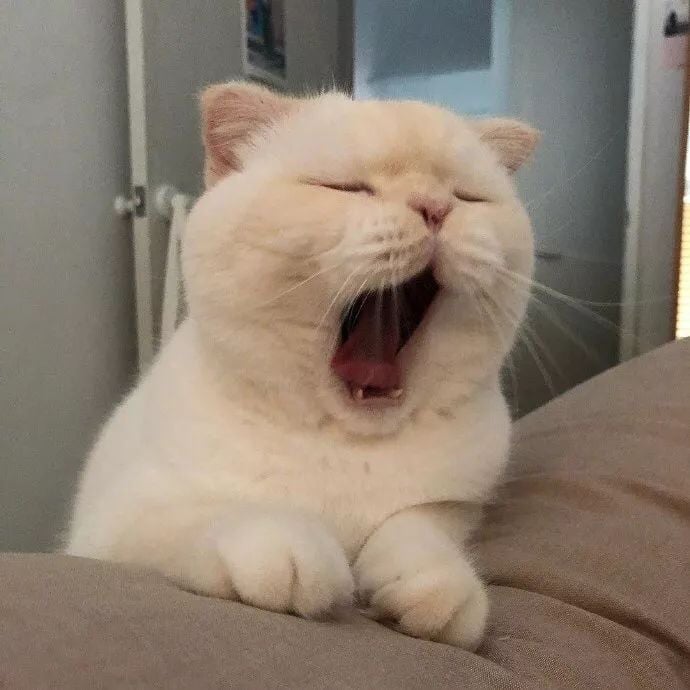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