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在無限可能裡溺水的人
※以下影評含劇情暴雷,請斟酌觀看。
這部片原本不在我的影集清單中,畢竟它是一部2013年的老片了,會有興致突然找來看,也是最近偶然被社群的網友推薦:「看完我整個人都不好了」、「讓藍色週一更不想上班」的失落電影。
至少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人處在什麼樣的情緒階段,通常就會被什麼樣光譜的片子所吸引,《海邊的曼徹斯特》、《天才雷普利》、《燃燒女子的畫像》——你幾乎不需要確認就可以知道,它所散發的氣息就是歐洲人特別愛拍的抒情文藝片,當然,還帶了一點北國人特有憂鬱的氣息。核心都在闡述孤獨、疏離、用眼神和沉默填補的破碎,彷彿下一刻就想讓觀眾和主角們都心碎般,微藍色的天空構成了整部作品的基調。
那它到底講述了什麼樣的故事?就讓我們先看一下簡介。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是由挪威導演 Joachim Trier 執導,改編自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的小說《Le feu follet》。它描述一位戒毒康復中的男子 Anders 在一天中的城市徘徊、見朋友、面試、重訪過去的生活,最終踏上一條讓人心碎的道路。
他最後——是的,他死了。
我想這點不讓你意外,但人們無可救藥走向死亡的故事,總還是能挑起我們一點好奇。
好比,一個剛康復的人為什麼會在離開戒毒所那刻走向滅亡?他是什麼時候就開始計劃的?周邊的人難道都沒有察覺?這些問題並非無解的謎題,導演甚至在最初就明示了死亡的預兆。
開頭,主角Anders來到森林旁的湖岸,天氣明媚,他一步一步走向深潭,表情卻是帶著「我該怎麼處理這件破事的苦悶」。你會看他下水前還有點笨拙地想脫掉外套,但試了一下還是穿上,手指打結、腳步遲疑,還是就這樣走到湖裡看看好了,他可能抱持這樣的想法,最後可笑找了顆巨石抱著,因為這是他那時唯一想到解決水中浮力的方法。然後輕輕地「砰」一聲,他跌入水中時沒有太驚慌,湖中浮起不甚起眼的泡泡。此時的你冷眼旁觀,你知道這只是開頭,他不可能會死——當他從水中猛然浮出的那刻,你們彼此都想著,你用錯方法了,蠢蛋。
之後的鏡頭多少有點狼狽,那還不是最糟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那更之後,還活著的人能體會的痛苦會更加湧上——比深水還要幽深的虛無遲早會把主角吞沒。但這並非因為Anders無人可尋、無依可靠,隨著主角拜訪他的戒毒小組、昔日舊友、血親家人……這人一天的人際關係甚至比我們還豐富,然而周遭的人有因主角曾是毒癮者因此輕視他嗎?
實際不然,至少表面上。他所深待的社會是一個具有教養和知悉良善的社會,在這裡,人們會說:「我理解你的痛苦。」然後擁抱你。在這裡,有社會救濟資源、有接納你的朋友、有熱鬧的派對,卻同樣認為自己生活滿是麻煩和苦痛的人們。人們交談,彼此抱怨,可你偶爾會驚奇的發現一個現象:所有人都在羨慕著彼此。
Anders一邊羨慕著朋友穩定的生活,一邊又已疲於扮演所謂的正常人。朋友關懷他,他則認為沒有人理解他的痛苦;他的生活父母給了他良好的成長環境和選擇自由,他卻怪罪他們從來不對他嚴厲,擁有了太多隱私;周遭的人稱讚他曾滿腹才華,而他如今卻只徒自我厭惡。因為他能感覺到,「康復者」、「前毒蟲」、「正常男性」、「努力求職的人」這些都不是他想要帶上的面具,這座城鎮「成功的人」看上去太遙遠了,他自己甚至快成了那之中一輩子的汙點,他的人生到底該是什麼樣子?
他從來沒在他自己的生活找到答案,而咖啡店的路人女孩卻能滔滔不絕:
「我想結婚、生小孩、環遊世界、買房子、整天只吃冰淇淋、在海外生活、維持理想體重、寫本很棒的小說、跟老友保持聯絡、種一棵樹、從頭開始準備一頓美味晚餐、洗冷水澡、跟海豚一起游泳、辦特別的生日派對、活一百歲、維持婚姻到死、寄很棒的瓶中信也得到同樣有趣的回信、克服所有恐懼、整天躺著看雲、有棟裝滿小東西的老房子、跑全馬、讀一本很棒的書一輩子記得書裡的話、畫表達真實感受的畫……」
而他?他是這麼形容自己的:
「我從來沒做過什麼真正的決定。都是一些半吊子的選擇。我就這樣走到了這裡。」
顯然,這個故事沒有讓人淚聲俱下的慘劇,這一點都不像亞洲人的憂鬱,我們的生活充斥著憤怒、焦慮、倦怠,可北國的天空乾靜、輕盈、帶點迷茫的氣息。在《怒嗆人生》中,角色崩潰時會想在百貨公司停車場想撞死對方。可在這裡,人們幾乎是正確地做了所有該做的事:他能被允許脆弱、他能被理解失敗,他們確實展現了對Anders的關愛。連主角自己都曾自嘲他就像個長不大的巨嬰,這種模糊脆弱的溫柔包覆在這部片的多個角落,要是現實哪個觀眾是Anders朋友,只要稍微誠實點,可能都會直白地說:「拜託,你都這樣幾年了,我們聽你講過幾百次了,拜託你去看醫生。」
或許我沒辦法共感主角的人生,但我能同理那種想把人生砍掉重練的念頭——「我永遠會是失敗者。」那是所有自我厭惡的源頭,來自文明世界「預設角色」的失控,每個人心中曾有過的「活在社會期待下卻無法達標」的代表。
Anders並非沒有選擇的人,相對的,他的選擇太多了,卻沒有一個是正確答案。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片無邊無際的可能裡划出一艘船,多數人會在那裡溺水。在這樣的世界人們很少會意識到:自由其實是奢侈品,意志力是有限資源,選擇太多等於懲罰。
表面上看似我們可以當藝術家、太空人、小說家、鋼琴家、登山家……但實際上大部分人根本沒有通往那裡的資源、背景、體力、精神餘裕、機運或命。大多數時候我們不是在「選」,而是在一堆夢裡自己挑一個看起來比較浪漫的方式失敗。
既然自己已經沒辦法成為兒時期待的模樣,那人為什麼不能定義想要結束自己的方式?
在電影的最後,Anders 回到童年的家,躺在那張熟悉的床上,重回藥品的懷抱。畫面平靜無聲,只留下那些他曾經生活過的痕跡:朋友、愛人、夢想、城市的片段。就像說這些地方都已留下我的腳印。好了,故事也該結束了。
以這樣的觀點去思考,《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主角向死的過程可以說是浪漫(雖然依然令人感慨),他甚至死前還有餘力彈完一首鋼琴!——既然我要死,那我就要死得像詩一樣。那種虛無到極致的儀式感,我不得不說真的超歐洲式。
回望我們身處的世代,現今的文明病則是在幻象中追逐真實感,卻沒有任何東西能停下來。當Andy在鏡頭那端沉默,那個「現實裡無法成為那個有價值的人」的回音,逐漸映照成了另一種空虛:「我根本不知道那個人要怎麼定義,或有沒有必要存在。」
這部片某方面也成為Z世代的另一個預言。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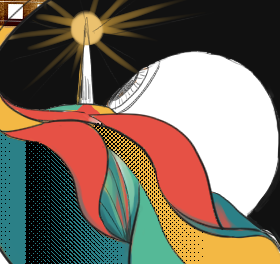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