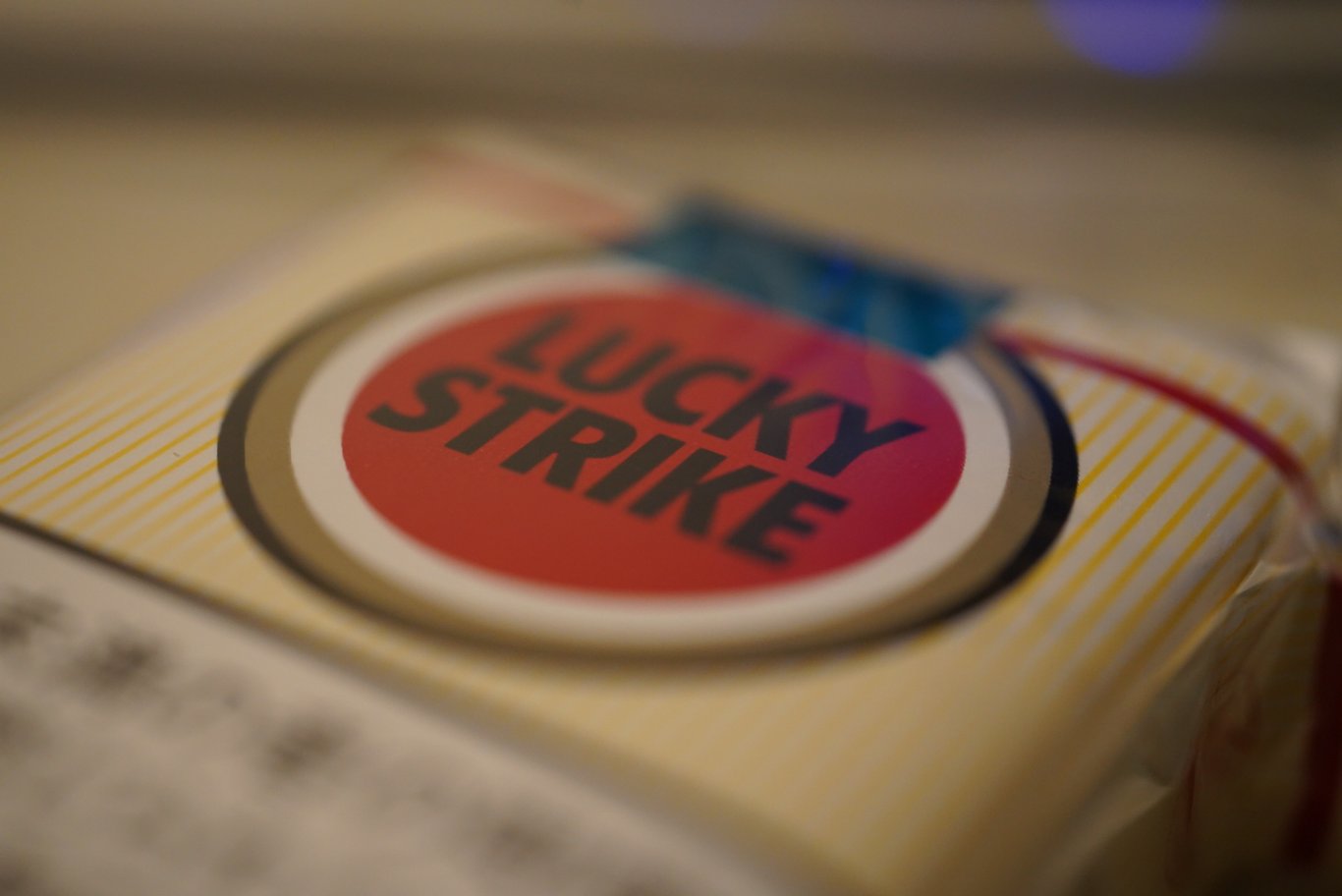国立西洋美术馆与人类幼崽
第一次去国立西洋美术馆大概是8月份,那时候远在加拿大的亲戚回国探亲,中途在日本转机,于是被迫卖父母的人情,就带他们去那里了。
说实话那时候简直是灾难,因为亲戚还带着两个孩子,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最不喜欢小孩的(虽然不至于当面发作,但每每都会憋出内伤)。那两个孩子给我的最大印象一个是多动(看到疾驰来的电车要伸手去抓的那种多动),另一个就是挑食——几乎是吃一家剩一家,点餐前又不明说自己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而我对剩菜这种行为极度敏感,很偏执地认为剩菜不仅有失礼节,而且体现家教不好。所以带着这俩孩子去美术馆,大致是一种亵渎(亲戚点名要去美术馆,我也没办法)。
我记得美术馆那时候有一个关于素描的特展,是一个比较有内容而且相对难得的机会。熟悉上野西洋美使馆的朋友也许会知道:所谓特展,很多展品都是从海外的知名美术馆借来的,可以说过了这家村就没有这家店了。但由于要留神多动的孩子不走丢,还要掌握时间(接下来还有一些景点要走),所以那次美术馆历程可谓走马观花。看了一堆作品,却没有太多时间去仔细阅读说明,导致出了美使馆后就像高考过后马上就撕书的学生——脑袋里空空如也。
不过这次不同了。因为跳槽的关系,所以我有将近20天的休息时间,自然也就有充足的时间去美术馆。其实我对美术可谓一窍不通,其审美来源于最原始的感官,觉得好却又说不出原因的那种水平。但毕竟去那里不需要什么学术门槛,而且如果字斟句酌地去看那些说明,总也能学到点什么东西。何况,在这个满眼污秽的网络时代,去看看前人留下来的画作,怎么说也算是陶冶情操的一种吧?
然而当我抱着稳扎稳打的心情再次来到西洋美术馆时,发现还是低估了自己吸收知识的能力和体力。老实说就算是普通展台,那里也是大得离谱。字斟句酌地去看每一段说明,每一幅画,导致我在三小时里还没看完三分之一的展品。反倒是腰和脚累到不行,总是要找地方坐着休息一会儿。尤其是,馆内为了展出效果所以显得有些暗,在这种环境下读一些蝇头小字就更累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家里把脚放在桌子上看书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不过,即使如此,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提到西洋美术馆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松方幸次郎。起初,就是为了珍藏他的收藏品才建立了国立西洋美术馆。松方本身是实业家,他经营了川崎造船所(与现在的川崎重工有点关系),但同时,他还专注于艺术收藏。目的是让当时的日本人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人。另外,国立西洋美术馆也是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日本的唯一作品,他那种强烈的实用主义令我印象深刻。比如这座美使馆,实际上有“无限成长”可能。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扩建和延伸,相当有预见性。据说勒·柯布西耶当时还要考虑周边环境和建筑风格,从而搞出更大的工程,不过好像最终没有实现(大概是因为经费的关系)。
今天美中不足的是我又碰到了人类幼崽——是那种货真价实的幼崽,真实到了除了嗷嗷大哭不会发出任何多余信号。我十分怀疑把那种幼崽带到美术馆里的人是不是有一些撒旦情结。那种小孩子连玩具零件和吃的都分不清,你跟我说带这种生物来陶冶情操,不如跟我说马粪是朱古力豆。另外,在这种相对安静和严肃的场合下,带幼崽来无疑于给所有观赏的人添堵。不要指望我在这种场合下发挥出什么对小孩子的爱心和宽容,我对于对别人没有爱心和宽容的家长而言就是一头不长眼的梁山野兽,没有当众发作完全是因为这是美术馆,而不是因为我不敢。你们肯定难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场合下听着幼崽鬼哭狼嚎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也试着带上了降噪耳机,但幼崽的哭声完全就是脱壳穿甲弹。好在那只家长可能也觉得自己实在有点太不要脸了,抱着幼崽出去了。
总之,除了人类幼崽的侵略以外,今天的一切还算好吧。只是三小时实在是不够用,估计还要多来几次才能认真看完全部展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