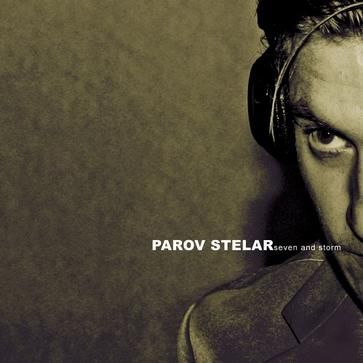當沈默開口:見證、呼喚與主體性的生成
我們常把沈默當成空白。可在創傷、權力與公共生活的語境里,沈默幾乎從來不是空白。它是一件正在發生的事,是知識誕生的現場,是倫理關係的門檻,也是政治主體性得以出現的縫隙。
在創傷證詞里,知識不是從檔案櫃里取出的“現成物”,而是在講述當中被發現。Dori Laub 指出,大規模創傷會擊毀心智的記錄系統,幸存者往往在訴說的過程中才第一次真正“知道”發生過什麼。這裡的沈默,便不再是失敗,而是事件。它標出語言的斷裂處,也標出意義正在生成的邊緣。Shoshana Felman 因此把證詞理解為一種行動,講述不是再現,而是發生。
創傷研究中的“延遲性”提醒我們,沈默有時來自時間。Cathy Caruth 說,創傷以“事後”之形回返。一個人當時無言,並不意味著無事;許多年後,沈默仍在說話。停頓、繞行、卡住,都是敘述的語法。與其把沈默當作“沒有內容”,不如把它當作“內容的形式”。
沈默同樣是倫理的來臨。Levinas 把他者理解為不可被我完全同化的存在。他者的面容,不是一個可供我解釋的對象,而是一種召喚:願不願意回應。沈默正是這種召喚的方式。它在語言用盡之處向我提出請求,要求我承認我的概念不足,並在不足之中仍然負起責任。真正的傾聽,恰恰從這裡開始。不是把對方的故事整理成我熟悉的範本,而是允許對方的沈默成為敘述的一部分,並以此調整我自己的期待與話語。
政治層面上,沈默從來不是中性的。Foucault 早就提醒我們,沈默並非話語的反面,而是權力運作的組成部分。有些沈默被製造、被安排、被訓練出來,成為權力的日常技術;另一些沈默則被主體收編為自我保護與拒絕被佔有的姿態。兩者並置時,才能看清沈默的政治複雜性:既是被強加的禁言,也是主體在縫隙中的策略。Arendt 所說的“出現的空間”,不只靠雄辯來開闢;在被聽見的沈默中,公共性同樣被重新點亮。人們並非非要喊叫才能在政治上出現,有時被認真地傾聽,已經足以讓新的關係與行動得以開始。
關於極限案例,Agamben 指出,見證與其不可能性相伴。正因為有些經驗超出言說的可能,沈默才成為見證的邊界線。承認這條邊界,不是撤退,而是避免以熟悉的敘述框架再次“佔有”他人的經歷。Butler 討論“可被悲憫”的邊界時提出,誰能夠被哀悼,決定了誰被承認為人。沈默往往出現在那些尚未被承認為“值得被悼念”的生命處。當我們接納沈默作為訴求,便同時擴展了可被承認的範圍,讓先前被排除的人進入共同世界。
沈默也是檔案問題。Derrida 說,檔案既是保存,也是權力。誰來建檔,誰來命名,誰來決定什麼算“證詞”?那些被刪改、被折疊、被時間侵蝕的空白,是否也能成為檔案的對象?Ricoeur 談“記憶、歷史與遺忘”的張力時提醒我們,遺忘並非單純缺失,而是一種工作。把沈默納入記憶政治,正是在做這項艱難的工作:為空白留名,為斷裂立卷。
在具體的互動現場,沈默是一種關係的提案。診室、課堂、採訪、社交平台,沈默都在試探: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暫時不說,是否有人願意等一等。回應沈默,不等於逼出細節,而是與當事人一起為難以言說的部分騰出空間。承認停頓,允許非線性敘述,用對方自己的詞彙復述關鍵句,讓對方“聽見自己”,並在必要之處暫緩追問。這種“慢傾聽”,既是倫理實踐,也是公共生活的訓練。
在高度審查與高壓輿論的環境里,沈默尤為顯眼,也尤為脆弱。它記錄了權力怎樣進入身體,進入詞彙,進入時間。它也展示了主體如何在夾縫中保留餘地,把“不說”轉化為姿態。被聽見的沈默,能把私人傷口與公共結構連起來,把個體負擔轉化為共同議題,從而讓政治主體性在縫隙處重新長出。
如果沈默不是空白,而是一種事件,那麼回應沈默也不只是禮貌,而是一種承諾。在沈默處承認界限,在沈默處延緩判斷,在沈默處承接責任。少一些把他者納入熟悉故事的衝動,多一些讓未知保有其未知性的耐心。這樣做並不是退縮,反而是在為複雜的現實留出生長的可能。
或許可以這樣結束。沈默不是對話的終點,而是對話的起點。它讓語言看見自己的邊界,讓倫理得以落地,讓政治重新出現。看見沈默,守護沈默,回應沈默。當我們做到這一點,沈默就開口了。它讓我們成為彼此的見證人,也讓我們在共同世界里,再次成為行動的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