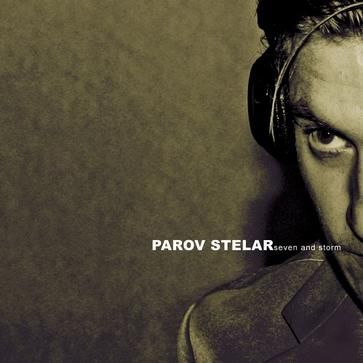為什麼“說出來”能療癒創傷:從心身機制到倫理與政治
創傷敘述總帶著兩層恐懼:一是怕“再被命運擊中”,開口就像把已封存的痛重新釋放;二是怕“說而無人聽見”,在沈默的牆壁前獨自回聲。矛盾也恰在這裡:不說,創傷無法被整合;亂說、或說給不在場的耳朵聽,又可能讓創傷重演。為什麼“說”仍然重要?因為在心理、身體、倫理和政治層面上,開口不僅是把過去搬運到現在,更是在現在創造一種能夠承載過去的關係與世界。
說,是把“碎片”縫回時間的布
重大創傷往往打斷記憶與語言的聯結。許多幸存者說不清事件的先後、地點、細節,卻被氣味、聲響、夢境牽引得心跳加速。這不是“誇張”,而是記憶以碎片、感官、軀體反射的方式被封存。精神分析把這叫作“重復”與“無法表徵”:記不得,但會“做出來”。開口講述,就是把這些散落的碎片納入故事的線索,把“發生過”變成“可被敘述”,讓時間重新流動。沒有敘述,創傷就像一段在體內循環的生影;有了敘述,才有機會被放進可承受的過去式。
說,是把“身體的驚懼”翻譯成“詞語的意義”
創傷首先是一種身體事件。突如其來的威脅讓神經系統學會“隨時警報”,於是睡眠淺、心跳快、稍有風吹草動就緊繃。語言在創傷發生時常常“掉線”,而後才慢慢“補記”。在安全的關係里說出經歷,像給大腦一次“重新存檔”的機會:把原先只會以驚恐回放的畫面,轉換成能被命名、被定位、被界定的記憶。不是講一遍就好了,而是在可控的暴露與停靠之間,逐步把“情緒風暴”變成“有邊界的故事”,讓身體學會把警報調回正常。
說,是把“原始痛感”交給他者去承載
有些東西,一個人說不動。創傷把主體關進孤島,沒有他者的在場,話語很容易墜回自言自語的回圈。一個能承接的聽者,不是法官,也不是新聞編輯,而是“容器”:在場、不搶話、不急著解釋,允許停頓與混亂,幫敘述者把壓抑與憤怒的火力慢慢“降溫”。在這種關係里,說的不是“為了說清”,而是“被聽見”;不是立刻達成結論,而是讓語言恢復呼吸。恰當的傾聽讓“講述”不必淪為再次受創的現場,而能成為把痛交托給他者共同負擔的儀式。
說,是一種“言語行動”,會改變現實
在創傷領域,“說”不是把一個既成事實從腦中取出,而是一種會改變現實的行動。開口的瞬間,講述者從被動受難者,轉為能命名、能定位、能要求回應的行動者;傾聽者則從旁觀者,轉為負責任的見證人。言語的力量不在“陳述”,而在“施為”:一句“這件事傷害了我”,在可靠的關係里,就是重新划下界線、重訂規則、重建自我的行為。敘述使主體感到“我說得上這種痛”,而不是“我只配被這種痛吞沒”。
說,是抵抗“被抹去”的政治實踐
創傷不僅是個人事件,更是公共事件:家暴、性侵、酷刑、政治迫害、戰爭。權力常通過製造沈默來統治:讓受害者懷疑自己、相互隔絕、以羞恥自緘。開口因此具有政治含義:把私人傷口與公共結構連接,讓“這不是我的問題”轉化成“這是我們共同的問題”。當被壓抑的故事進入公共話語,社會的可理解範圍被擴大,原本“不算人”的痛進入可哀憫、可共情、可索償的版圖。說出來,是對抹除的反擊,也是對共同世界的再一次發明。
說,也包括沈默、繞行與藝術性的表達
說,未必總是直說。有時先從寫下幾個詞、畫一幅畫、搭一個隱喻開始;有時需要把沈默當作敘述的一部分,讓“說不出來”被正當化。身體練習、節律呼吸、藝術創作、儀式性紀念,都是“說”的形式。關鍵是把不可言說之物安置在一種可承受的表達里,而不是強迫自己一次講個“乾淨”。“說”不是一次性的卸貨,而是一系列可控的靠岸。
說,必須在合適的時機與邊界內進行
並非任何時候都適合開口。創傷敘述需要先確保安全:沒有持續性的威脅,有基本的身心穩定,有能信任的聽者與明確的停損線。說的目標不是獵奇細節,而是恢復掌控、整合意義與重建關係。若敘述環境只會放大羞辱或爭奪解釋權,沈默反而可能是當下更健康的選擇。每個人都有“不說”的權利;療癒不是靠外部逼問,而是靠內部準備與良好護欄。
說的重要性,也來自“被真正聽見”的可能性
最讓幸存者恐懼的,是把故事一遍遍講給冷漠的耳朵聽。那種無回應、被走神、被轉移話題的“聾”,會把敘述變成新的受難場景。真正的傾聽,意味著願意被影響、被改變,意味著承認“我原有的框架不夠用”,願意暫緩判斷,與敘述者一起尋找新的詞。說的重要性,恰恰依賴這種傾聽的倫理:沒有被承接的“說”,很容易變成“對著牆說”。
說,如何與療法和研究對接
以證據為基礎的創傷治療都在用不同方式為“說”搭橋:穩定安全,再逐步靠近創傷記憶,在可控的範圍內敘述與命名,並且在敘述後回到當下。敘述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可掌控”越好。研究也不斷顯示:當人在一個被尊重的關係里講述,身心的壓力指標下降,回避減少,意義感上升。說,不是“把舊事翻出來折磨自己”,而是“把自己從舊事里領出來”。
說,最終是關於重返關係與世界
創傷把人推入孤島,語言的工作,就是搭橋回岸。說,是把身體的驚懼交給詞語,把詞語交給他者,把他者帶回共同世界。說,讓一個“只剩反應的人”重新成為“可以行動的人”。它讓過去不再只會襲擊現在,而能被安放到能夠承受的過去;也讓現在不再只會重復過去,而有餘地去創造未來。
如果問,為什麼必須“講出來”?因為創傷不是自愈的瘢痕,而是會在沈默里增長的結節。說,並不是把痛擴大,而是給痛一個邊界;不是讓世界知道我弱,而是讓我重新知道我強;不是強迫世界同情,而是召喚一個願意共同承擔的他者與公共。說出來,不等於一次說清,但每一次被承接的開口,都是把自己從創傷的迴路里帶出來的一小步。無數小步,合起來,就是通往復原的路。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