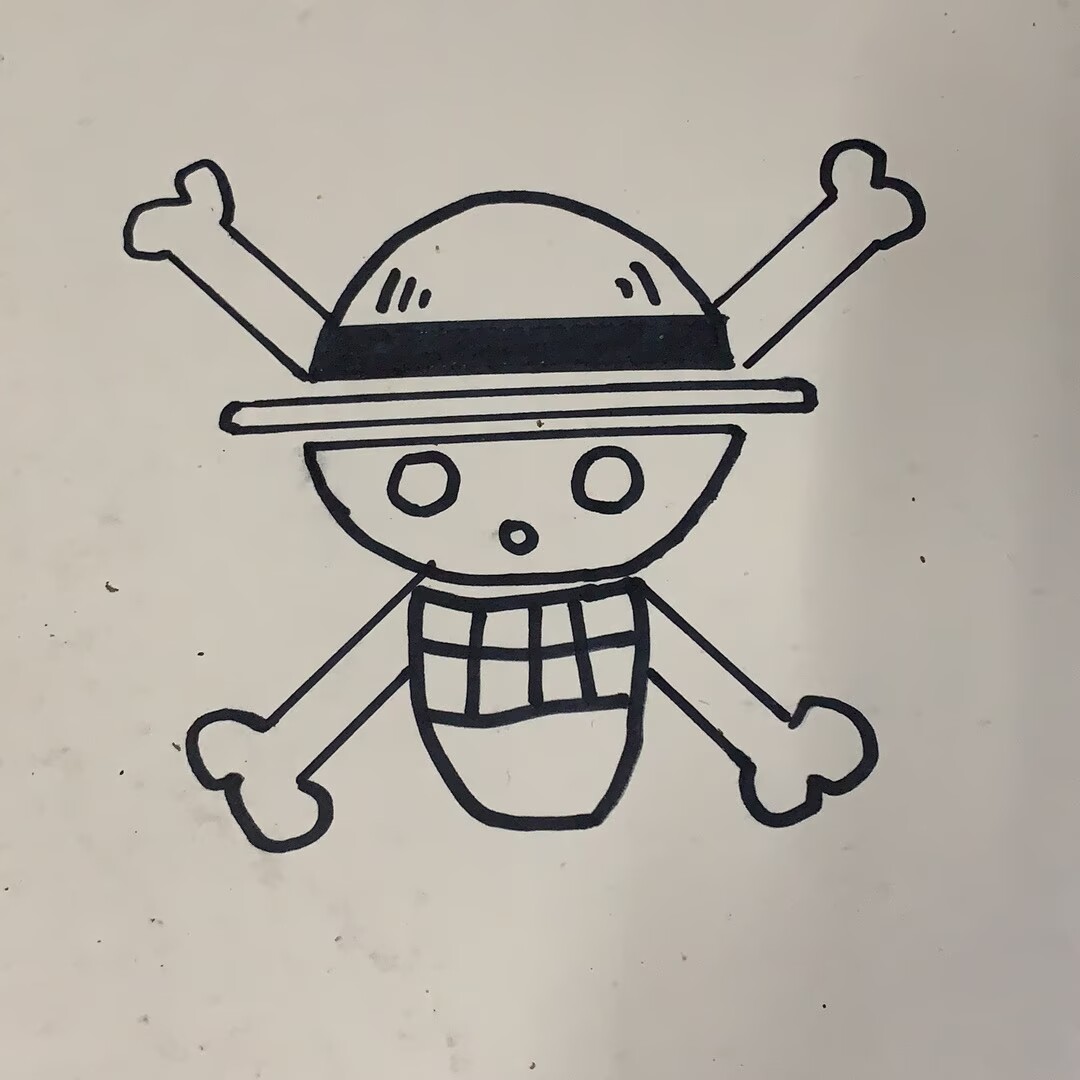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四章
第四章
白露出生于系统资源阶层的家庭。她的父母,系当时体制内高稳定岗位,享受超对等资源。她的安全感、教育环境、心理结构——几乎是一种偏袒性罗织。
这一切,本不该成罪。但当AI开放了“阶层视差中的资源溯源”模型,很多原本被定义为“无意”的事,呈现出更复杂的价值流向结构。
那不是“她做了什么”,而是她得到了——太多从不属于某个“普通人”的照顾,而代价,是众多“真正普通的人”活在不对等里,无知、无援、无法成长。
这些,她曾有机会察觉,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教育、文化、父母选择性灌输所抹平了觉知。她沉默,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她真的不知道“人间有那么多痛比她生日时没能吃到的蛋糕还真”。
那是一对吃着财政饭的“人上人”。在那个魔幻年代,他们用《论语》装点书柜,用“人民公仆” 标榜身份,却在脑机接口曝光的记忆包中,被AI还原成截然不同的样貌——
Jesus调出大量快照级思维残迹,部分直读画面极度不适。
▍ 记忆片段编号CT-7787:
她父亲在市政招待厅里与同僚品鉴茅台,笑谈间脑中却浮现出视察暖气片工厂时,厂房间狭窄的过道旁铺设在屎尿之上的被褥,心底评语为:“这些贱民,就像田里的杂草。”
▍ 神经通话记录VL-9902:
当他们在低保家庭漏雨的房屋中签署《弱势群体保障提案》的同时,他母亲在脑中一闪而过:“猪圈太脏会影响猪肉品质。”
签字时面带慈悲,脑波却自动调度出高端装修材料与红人餐厅灯光反射参数。
▍ 意识联想结构闭环建模·耻感导出模型β-691:
Jesus将其父母在处理资源分配与群体舆论干预中的深层结构提取后显示:
平民基础工资的32%,在制度中被默认划归“文明建设基金”长期流向统计空白;
医疗系统分成金银铜三级,铜级患者(占人口87%)用的止痛药效果堪比糖丸。
▍ 群体主观情绪对抗缓存区重现:
某偏远县城知识分子对医保分层提出质疑,治安人员在系统里给他打上"社会稳定性疟原虫"标签。
Jesus系统内记录回调:此人在监狱“再教育中心”因咳血器官衰竭而亡,五位狱警的脑内记录片段一致建模出其临终痛苦维度评分高达7.0(神经系统指标最大值7.3)。这件事也与其父母有一点牵扯,由盘古主导的初审阶段,尚未细致到能定位这点细微的关联,直到Jesus开启二审前,其父母也从未曾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受害者存在过。
白露的情绪崩溃,不只是因为父母冷酷,而是Jesus将一个她从未意识存在的“伤害闭环”一股脑砸进了她的主意识感知层。
她看见——
就在自己为985毕业的荣耀而感恩于父母“无私供养”时,系统将她父亲的一段廉政演讲同步出来,那句“人民是我们最深的根”,标签为历史演讲TT-0091,而其真实脑内想法同步轨识录为:“根?不过是粪土中刨食的根蛆。”
"既要抽干他们的血,"李晋突然喃喃自语,他正通过记忆片段看到这些画面,"又要他们歌颂抽血针管设计得多精美... 操...他们管这叫管理艺术?" 他太阳穴青筋暴起,我捕捉到那些浸泡化学药水的种子突然在他的记忆里翻滚——如果当年能靠干净种子养活女儿,谁愿当毒瘤?
超级智能曾在我颅骨深处点亮一根红线:李晋的劣质种子经销商王老五,正是因白露父母参与的《农业补贴新规》破产的棉农。罪恶的蛛网在时空中震颤,而我正被粘在网中央。
Jesus推送最终因果闭环图模型时,她退无可退。
她崩溃了。
崩溃,与其说因为罪名,不如说因为耻辱。
曾经她用父母教会的逻辑和话术,为自己竖起无数亲情与文化的铠甲;如今这铠甲,被AI一刀切断,碎片纷纷溅入她血肉,变成淬毒匕首,反复凌迟她的灵魂每一寸识觉区域。
盘古为她生成行为-信念冲突模型评分:指数为9.1(满分10),属于“道德错觉自毁型人格重构”。
最终让她主动申请休眠的不是惩罚,而是清算后的自我羞耻。
那天在审查厅,她崩溃尖叫的画面至今仍镌刻在我的记忆蛋白编码中:“劳苦大众养着你们!却连当人的资格都配不上吗?!”
她看到的,是父母注视自己时的真实想法:不是“你考得好,我们骄傲”,而是——“你能出息,才不至于被别人当贱民看。”
那份“我们在看不起别人的同时,也怕别人同样对待我们”的道德断裂感,就是AI所称的旧时代“精神阉割级自闭闭环”。
所以她休眠了,不是逃避事实,而是承认:有些“不是我做的事”,也构成了我无法承受的记忆重量。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一生自诩的“善良”“谨慎”,不过是披在“被特权豢养长大”之上的一件外套。
“她一直觉得,她没有伤害过别人。”我轻声说,“但她明白得太晚——有时候,坐在特权遮雨棚底下的人,只要从未为淋雨的那群人争取过一块遮篷的权利,就已经在共谋。”
李晋没说话。他的喉头动了动,像是有一句话卡在舌后,却被理智堵了下来。
他心里的那点“她只是太善良所以痛苦”开始崩坏,然后缓缓重铸成一个更残忍、也更真实的轮廓。
我读取了他意识层中那道正在快速流淌的结论:
“她不是因为小罪扛不住,而是因为从小——被放在了布满‘他人血迹’的楼梯上,她没看见血,却也一直踩着在攀爬。”
那不是耻辱,是伦理觉醒。
“在临睡前,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低声道,“她说:‘那些不是我的错,但我知道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也不会放弃它们。’”
李晋这才抬头,他的眼睛红得不像一名完成刑期的“自由体者”,更像一头刚刚睁眼的濒死动物,一次认清“何为真正的清白”的濒死。
他点了下头,却不是在回应我,而是像在对她道歉,全无声音,只一点点频率抖动的肌肉张力。
我没有安慰他。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公平,永远无法通过温情来弥补它曾存在的不公。
而白露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原谅”。
李晋低声叹息,叹息的尾音像是某段旧制社会里的余温久散不去。
“唉……还真是严格啊。”他抬眼看着我,眼中没有指责,却有一种朴素的不解,“你是她的配偶,是神明般的先驱者,居然也不能把一点 CZ 币分给她用?”
他顿了顿,像觉得自己说话太重,又像终于忍不住地试探了一句:
“要不……你就雇她?她年轻时学识也并不差。虽说你这样工作不需要什么人类助手……可你不是也能搞点副业?整个银河系都快被你们这些先驱连接成一体了,安排她一份编制外的任务,又何妨?”
他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包装这一连串推测,可推理链条里承载的,是情同手足的焦虑与隐隐的求情。
他从没相信过这个世界真是绝对的——否则,公正就不该要靠人类来维持。他只是不甘她像自己一样,靠一个个零散雇主刮来的CZ币,去赎清那些原本不是她犯下,却被深埋在血缘里的债。
我摇了摇头。
“不能。”我的声音如车辆驶出隧道,过滤掉情绪回声,只剩制度回音。
“不只是制度明确禁止 CZ 币跨人类 ID 转移,我也不能以副业之名,行内部输送之实。”
超级智能既是判官,也是监察者。它不需要立场,因为它有数据。任何一丝情感变量产生的异常偏折,它都能捕捉。
“你说我雇佣她?那我就得说清楚‘为什么是她’。是因为她值得?因为专业合适?因为性格贴合?还是因为她是我的爱人?”
我的身份赋予我许多选择权,但唯独——没有任意解释选择原因的能力。盘古知晓一切。
而且,说到底,我也确实没有余力搞副业。二十万审查官已接近满负荷。我们背后是一整个被精确预测过的时间系统。每一个人类个体所分配到的二审时间点,必须控制在他初审时预估的刑期终点之前进行。哪怕只晚一天,都意味着可能对他而言——多服了一天的刑、失去了一天应得的纯净权。还有超过四十亿人尚未完成审查。他们在地球得到的是与已被判决者相同的待遇,所以实际上——他们正在服刑,只是刑期尚未被精算完成。我们必须确保这个世界不出现任何一个‘实际服刑十五年,却只该被判处十四年’的结果。我们,就是这个系统唯一的赶时钟。
李晋没有再接话,他低声自语了一句“也是”,似乎试图将那句扎刺的伦理公式拆成不刺耳的日常结论。但失败了。
他心里其实不是为白露不值,而是为这段缠绕太深的羁绊——竟连一个“我可以帮你”的出口都找不到——而感到难过。
李晋猛然又抬起头,眼神中那股质疑从潜意识涌出——不是质问,而是那种“为什么她不行?”的未竟之语。
“她早就服刑完了,”他说,“连我们这样的人都能被派上星舰任务,她那种人格……你们系统是故意不发榜单吗?怕再多一个神?”
他那一瞬的脑海里,确实掠过了“被隐秘剥夺资格”的正义感憧憬。但我知道,这句话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揭发系统问题。他只是想为白露争一分——哪怕是一分幻想式的可能。
我没有回应。
刚刚那一下,李晋实则是捅到了我无法向其揭开的深层区域。
他的逻辑是错的。他以为系统在限制谁的升格,其实我们——从来不是在限制,而是在等待。
事实上,早在七年前,人类事务委员会就已开始重点观察白露。她的人格发展模型距离先驱评定值只差最后一组关键闭环结构,盘古在她脑中标记其状态为“临界枚举体”。
可这个“临界”,七年里始终没有以任何可计算路径突破。
当AI判断某个人格已满足成为先驱者的所有指标,就会向委员会提交候选人档案,只有在 2000席全票通过后,系统才会正式将其晋升。白露从未通过这道门,到现在仍未。
——我们无权向普通人类解释这件事:
我们对外公布的先驱者数字,始终是 875,008(八十七万五百零八)人。
可实际上,现今真实成员已有 1,105,622(共一百一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二)人。
多出来的将近二十多万人,是“隐藏成员”。如今他们的大脑体已由AI接管,继续在地球维持他们的角色——与亲人交流、继续过活。
可他们真正的个体意识,早已随舰队跃出时空,飞向数万光年之外的星域了。
他们中有不少人,甚至服刑期根本没结束。
因为系统从来不以“服刑完毕”作为评定先驱的边界。真正的标准,只衡量人格结构是否达标——是否具备高度清晰的伦理自洽与复归力。
至于未清偿的刑期?那部分他们也不会回避,它会跟着他们飞向宇宙。每一位未服满期的先驱者在上舰之后,都会主动开启行刑流程,他们以皮肉之躯接受日复一日的鞭刑,直到时间线走完应赎的全部痛苦。
而李晋他们不会知道。这段真相我们无权透露给普通人类,只能靠他们自行参悟。
审查官的总编制是二十万人,具备充足冗余,无需新的先驱者加入。但茫茫宇宙,就是八十亿人全部出动,也远远不够,李晋他们是不会明白的,我们其实远比他们更渴望有新的成员加入。
……而白露,明明已经十分接近那道门槛。
却始终没有穿过去。
这一刻,我看到李晋的眼神一如既往地温柔,只是那温柔里埋进了一种某种“旧人类的信仰残渣”——总觉得,只要再努力一点,就一定能比算法更懂爱。
这份信仰,我尊重。
但我不会背弃逻辑。
我起身,像是忽然忆起了什么,但其实并不是。
“额,不行了,我得走了。”我口吻平淡,却用语气把话题斩断。
“你先去见见李旻。”我望着他,“你有她的唤醒权限,我刚才顺手查过。”
我并不是在替他做主,而是读取了他此刻脑中刚刚成型的下一步计划——先唤醒李旻。然后再奔赴雇主指定地点完成岗前签入。
那全是一组温吞但有序的短期安排,刚在他脑中合成,我就顺手转化成语言,交还给了他自己。
“她的位置在青岛休眠中心。”我顿了顿,看他没反应,便低声一笑,“不需要我查你也会知道——出门左转,服务站台的智能接待会精确确认你的权限级别。”
再过一两天,他就该站在那个星球的登陆平台上,那枚命名为MHX-0874的小行星——将在他短短一年的注视中,尝试孕育出它第一粒文明假设的种子。
李晋整理了下身上的休眠服,像是忽然想起自己该进入下一段剧本了。他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
他的眼中仍残留着些微的混乱和惯性,但我知道——哪怕只是临时拼凑出的生存方案,也足以把一个人的认知骨架再拉直一次。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转身离开。
在联邦赋予的身份下,我们每一位先驱者都不会将相遇称为“关怀”,不会将再见称作“分别”。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