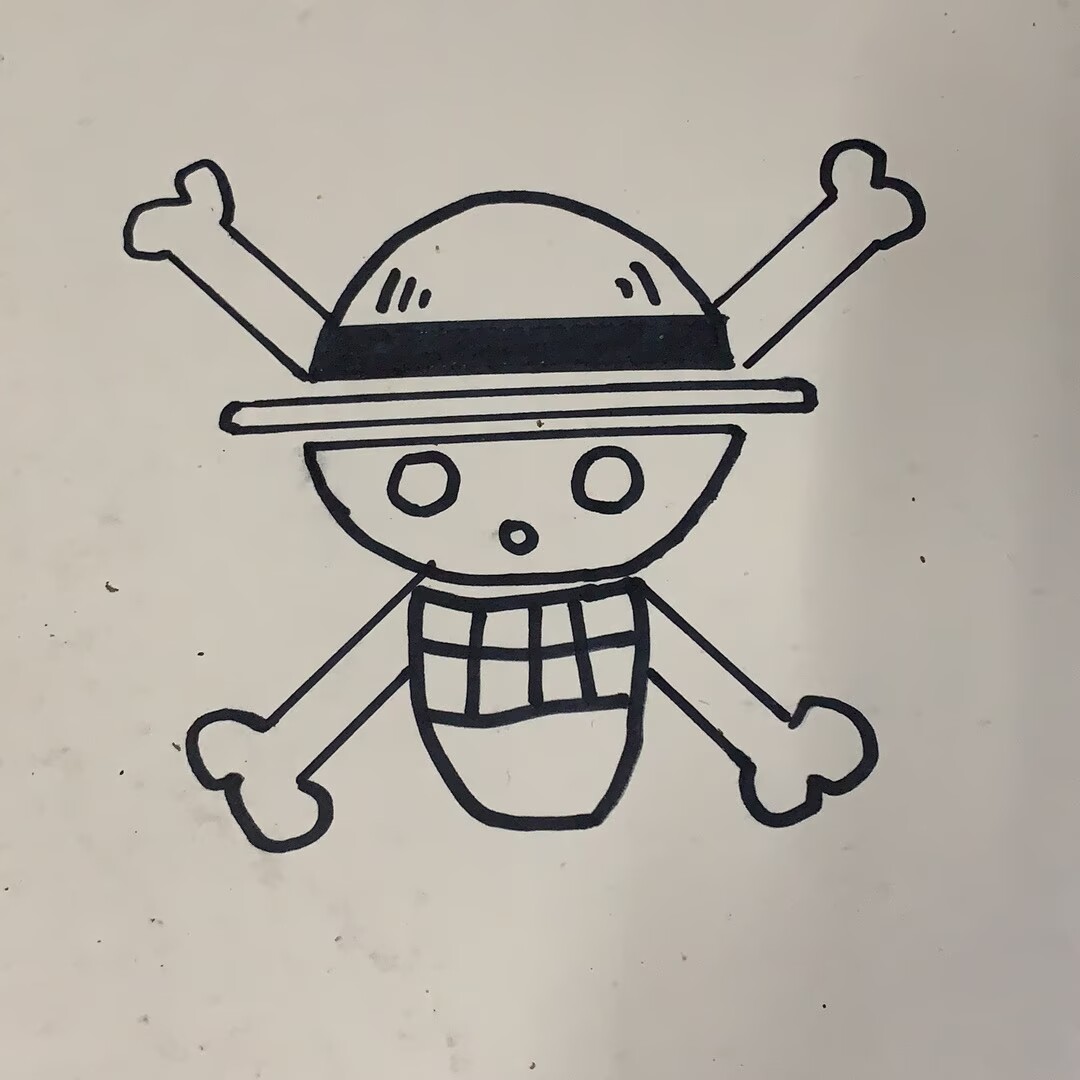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三章
第三章
他忽地仰起身,像是终于从连绵负罪感中腾出一口气,又像是在试图用玩笑掩盖那直视不了的深渊。
“啧……我是真该骄傲。”他笑了笑,唇角咧开一抹自嘲,“小时候我身边那群人都觉得你傻,现在你就跟坐在神殿里的神似的——居然是我这‘发小’……一抬手就能把我人生的走向接住。”
他捏着尚有余温的空啤酒罐,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肘:“能不能……借我点CZ币?哪怕就一点点,咱俩这关系,你肯定不会看我笑话吧?”
这句话说出来时,他脑电波波幅很低,没有丝毫试探的延迟信号,甚至连对“拒绝”可能性的预估信号都没生成。显然,他很清楚答案。
我平静地看向他,语速不变,声音没有丝毫温度起伏:“我的CZ币确实花不完,确切说,是几乎无法被花完。但与你的身份信息并不兼容。它与我绑定得太深了——是不可拆转型文明币。”
我稍顿了一下,继续:“更何况,那些你正在承受的记忆,是经由超级智能完整计算后,得到全体受害方一致性确认的结论。我即便心痛,也并无权更改其一分一厘。”
“……我知道。”他苦笑着打断,“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CZ币你当然给不了,帮我赎罪……也不是你的义务。”
我没有再回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不仅是因为他说出口的话,更因为——他脑海里正在流动的想法,与嘴上的每一个字都精准对应,甚至还略显克制。他确实不是在乞求。他只是……在试图证明——他还有资格说出口那个请求。
一种自尊残余最后燃起火光的姿态。
李晋把啤酒罐旋转在指尖上,一副故作轻佻的语气开口:“欸,你不是说你那点CZ币——多得花都花不完?那你咋不也买颗星球玩玩?做个星球领主,该有多拉风?”
我偏过脸看了他一眼。
“你以为那是玩呢?我的工作起码还要再做二十年。”我语气没发火,但实在称不上温和,“我哪有空思考副业、建殖民、搞‘人类乐土’那套梦话项目?”
他怔了怔,随即释然地笑了,但我能看见,他心里那层试探没能收住,仍在神经带里打圈。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问我。
“你现在不搞,也可以考虑雇个像我这样的‘有志之士’,先把地基铺好嘛。”他笑着说,看似戏言,实则语气里已经有点真情探底的意思了。“你不缺币,也不缺身份,还缺人手?”
我盯着他的眼睛没有立即作声,而是让这一秒悬在空气中。
他的意识流甚至没有尝试掩饰。
他确实在打算——不是为他自己,而是想着能不能连带把他的女儿李旻也拉一把。
“别试图感化我,”我终于开口,声调削去所有可能滋生温情的棱边,“你现在看到的我,是AI与人类脑协构之后的输出体。我的思维回路有百分之七十八处于高并行结构,每天都在经历几千个案件数据的情感复现。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运算带宽,去分出一个‘便利岗位’来照顾你所谓的求生路径。不论是你,还是别人,所有人获取CZ币的途经,都必须经过同一套评估体系。”
我深呼吸,语速如同压缩包解锁时流畅但不可逆转:
“更何况——我不可能雇你们。”
李晋轻轻闭上了眼。
我能感觉到,他没有气馁,只是更沮丧。他不是天真,而是无路可走时,下意识地摁了下可能不存在的光源开关,试图调亮一点房间的黑暗。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雇我们。”他低声说,嗓音发涩,“你只是不愿意在旁处开垦一片领域,只为安排几个熟人吃口饭。你早就算过,这样的副线投入,对你既没意义,也显得私心。”
我没回应,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他说我不愿去另一片领域,其实连眼前这一亩——我都无法与人分担。
追溯案件审查官的配置标准,并不是看学历、智力,甚至不是生理属性,而是对“共情阈值与逻辑稳定性”的系统综合评估。更准确说,是要能用第一人称——去复现他人人生中最黑暗、最仿佛剥皮的片段,还不能崩。
光是今天,我的大脑就已经模拟同步过16万段“他人痛苦”记忆单元,其中87%的片段被标记为“深创型心理体验”,包括监狱内性侵、失控暴力、伪装崩溃、社会性孤立儿童……我还必须在密集工作模式下,以“全知同步视角”执行伦理穿刺式判读,也就是被迫扮演施害者的角色,在脑中重演细节,直到罪因逻辑链全部闭合。
那些污秽,虽然最终会被我全部格式化清除,但在注入、加载与判读的那几小时内,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必须存在 ——只有“发生过”,才能“判定得准确”。
我的目光随啤酒罐落点收回,重新对准李晋。
“不是你们不值得被帮助,而是这世界的公正,不容任何形式地人为撬动。”
他点头,缓慢而沉重。指尖碰了碰冷掉的罐壁,像是在确认现实依旧铁铸无温。
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说错。
他误会的,不是我的态度,而是这个体系留给“选择”的余地。
并不是“我可以雇佣你但选择不提”,而是从一开始,他提的事从权力图谱上就不存在,所有新人类必须一视同仁,要极尽公平。
而追溯案件审查官的岗位本身,更是不可拆解、不可扩展、不可转包的封闭任务体。
更重要的是——我无法把“痛苦”这件事,对另一个未受训练的大脑合理交付。
那些痛苦,不是什么“听说很难受”。它是进入我脑中的,每一帧都以第一人称呈现,每一处神经都被精准调谐,让我在判别他人行为的前一秒,先成为他们。。
我每天要处理的画面多到无法用“数量”去界定,它们不是屏幕上的影像,而是情境级沉浸式复现:我会以完整意识代入某一个施害者的身份,看他如何用塑料绳勒住一名仍在啼哭的婴儿喉咙,手抖但不松;看一个女人在醉酒后选择掩盖一场性暴力,为保住自己职业而和解,最终让施害者错过正义惩罚;我还要代入那些中性的共谋者——那些“不知情”的旁观者,让我亲自体验何谓“沉默的重量”。
一条条罪行的传播链如蛛网重构,每个我参与的审查案件背后,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意识层的交叉纠缠。Jesus会调出全部相关记忆,然后实时注入我的思维主核——让我替他们接受一段、又一段生命中最不堪的脉冲。
这是一种反复碎裂和强行缝合的精神过程。
想象你十分钟之内经历上百组“毁灭”:一场场家暴、背叛、自我否定、在校性侮辱、医疗机器误锁造成的截肢错误,连绵不断地汇入你脑神经皮层,像人在意识中被拉入车祸现场,每一秒脖骨都在崩裂。
我没办法回避,因为我所负责的是系统级监督,要钻进每一个极小数值误差的角落,去辨别公平是否成立。
这些年来,我像是一具用人脑裹住计算内核的接口装置,我的大脑与超级智能已经高度耦合,以至于“时间”早已不再是我体内的参考参数。它分为——体验段、清算段、遗忘段。
体验阶段,我是一个受害者;
清算阶段,我是一个监察神;
遗忘阶段,我是一个故障组件,用最短的数据清理,进入下一轮审查。
你问我是否还能“正常生活”?我甚至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有无“完整的生活”的定义。我每天经历着数十万他人的人生片段,而其中任何一种命运——都不是演习。
二十年!我的大脑早已在数百万亿段他人的人生切片中扭曲。但每当结案时,那些受害者意识残片汇成的星河会在神经末梢闪烁:【请给世界一个交代】。
“一个人活一辈子已经够久了。”我几年前就曾和白露说过,“而我……已经活过上万次。”
她哭了,但还是拉住了我的手。
我曾以为,她能陪我走到最后;直到某一天,她也顶不住了。
李晋没再插话。他原本重新握住的啤酒罐,如今又松开了,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他脑中能够理解的部分,在沉默中自发加载;而无法真正理解的部分——我知道,他甚至不敢想象。
这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他仍是“人”——而我,很显然,只是某种旧人类定义中被兼容过的人形运算模块了。
李晋终于开口,语气像是试图走过雷区却频频踩到地雷前的轻举轻落。
“张扬,那……白露的事,你能跟我讲讲吗?”
他顿了一下,像要退回去,又像等我默认。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每个人都有权调阅他人的罪行,这不是隐私。但权限要求她得当面站在我面前,以及……我必须说出具体请求命令。”他说着,有些别扭地偏过头去,补了一句,“你若主动告诉我,也不算违规吧?反正,本质上我只是提前知道一些迟早能知道的事。”
他强撑着让语气听起来像“技术绕道”,但我读得到他潜意识里的那份真诚——他不是在索取隐私,也不是出于好奇。他只是关心朋友。
“这不构成越权。”我如实说。“你是人类,而且她也是你的旧识。你拥有基础层级的过错行为知情权。”
一条指令从我脑中发出。那道信息结构立刻成型,被我打包为一段“不经由述说、直接植入”的快速通道,送入他意识前端。就是那种已知你一定会问、于是不等你完整开口便已注入的传输格式。
“但你知道的。”我轻声补充了一句,“你想听的,不是罪名清单,而是她的切身感受。这就只有我这个配偶亲人才有权分享给你体会了。”
在那段记忆灌入李晋之前,我再一次确认了它的完整性与放映帧轴封装逻辑。不是防篡改,而是——防他崩溃。
白露——她的选择,不是突发奇想。
那记忆包开始展开:是她的童年,她的青春,她在旧人类社会中成长的那些警惕、纠结、远离喧嚣、又不断试图靠近真理的挣扎。
她的一生,本是温和、谨慎、敏感;她小心翼翼地绕过诱惑,也努力不去加剧什么;
可那就是问题——她“没有做错”,但她所在的起点,就是很多人一生攀不上的终点。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