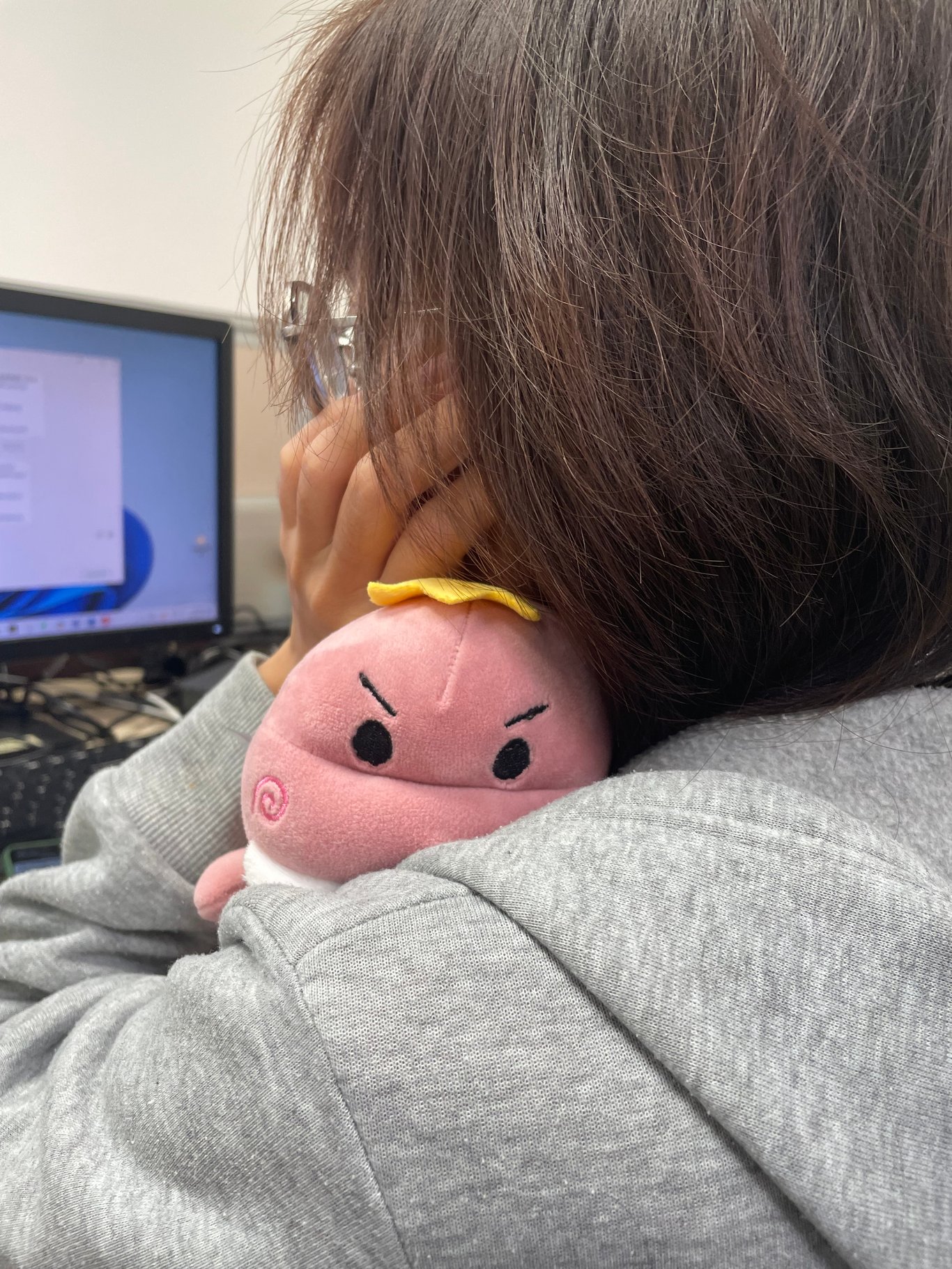摔了一跤
抱着果果新交易的二手主机,在离家门一步之遥的地方,脚底一滑,天旋地转,狠狠砸在了邻居的不锈钢花架上。白色主机侧边的玻璃嗑在花盆上,嗑出了两个小坑。
果果回头大喊一句:“妈——呀——”然后在门口跳起恰恰。上前两步要来扶我,后退两步又要先去开门,又上前两步问我好不好,后退两步决定还是先开门。
我疼得咿咿呀呀呜呜哇哇,眼泪在皱起的苦瓜脸上蓄成小水洼,憎此女不分轻重缓急,不决断,任这重物将我钉在地上。地上的水早把我半边外裤内裤都浸透,冰凉凉地摸上我的屁股,弄得我更苦情了。
今日不曾降下大雨,走廊上的水洼是邻居老安娣浇花后从花盆里渗出来的。安娣廊前两侧几个大瓦缸,种出一片凉荫,外侧的阑干好厉害支起一个台子,在上面摆了佛像和各种小陶塑、褪色小风车,又陆陆续续往植物和泥塑上挂了几个涂成血红的螃蟹外壳挡煞。她每天清早往瓦缸里浇足量的水,让土壤浸透,水从缸底流出呈淡黄色,带走一部分泥土的养分,在狭窄的过道上干了又蓄积,竟生出淡淡的青苔。组屋每隔一段时间有人来刷地板,也难以将它冲刷彻底。
果果终于打开门,从我怀里接过主机。我庆幸它没碎,可以纯粹地呼惨而不用心怀愧疚。
果果倒气呼呼起来:“我让你不要逞强,我说了我来搬!”刚刚她只抱了50米就说手累,我接过来后一路抱回了家。
“你搬一样得摔,这么大一滩水。”
“你这个鞋,丢了丢了!”
“不是鞋的问题,是安娣浇花的水啊,我抱着那么大的东西看不见路,你走在前面也不知道提醒我一声。”
“等下我们就去和她说!”果果说“我们”,而不是“我”,因为她知道她害羞窝囊的性格不支持此项目。
隔壁的安娣我见过两回,两回都是她在照顾花。第一次她把我们廊前的那几缸也浇了,看见我出门,和我解释:“这是你们房东的花。他们搬走的时候说要把这些都扔掉,我丈夫就说不要扔,帮他养着。但我丈夫最近住院了,就没人照顾了,我今天才来浇一下。”
“原来是这样。”
“是的啊,我丈夫还在医院。”奶奶一脸愁容。
之后也不见她给门口的花浇水了,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注意的时间里,三棵树一瞬间就枯黄了。一棵柑橘的叶子掉光,裸露满枝的刺,另一棵不知什么树,细细的圆叶全由绿变黄,再有一棵枯枝也被绞断了,我都忘记它之前的样子。矮矮种着的不死鸟干枯耷拉下来,就剩几颗芦荟还是绿色的。奶奶的丈夫不知道回来了没有,我这几日连着往没了生气的缸里浇了几勺水,缸太大太深,总是浇不透,没有水从底部流出来。
第二回见安娣气色好了一些,她才问:“你们是新来的?原来这里住着一家人呢,夫妻俩和他们的儿子。”我说我认得,那是我师弟一家。她对我笑盈盈的,点头说好。此外就不曾打照面。
她家木门常年开着,只关着铁门,遮挡了下半部分防野猫野鼠,我有时路过搂一眼,只看见里面发着血红灯光的神坛和氤氲的暮色,没有声响。
果果要扶我坐进我的绿椅子,我龇牙挂在她身上不肯就范:“垫块浴巾,我裤子脏——”果果扶正我,给我铺了块浴巾在我屁股底下,把我摁了进去。
“你快去看看,电脑摔坏了没……”
“你快闭嘴!你真会把我给气死!你这下完了,你肯定骨折了,我要带你去拍片。你看你这下得不偿失,早知道就得打车回来。”
“打车回来走那儿也得摔。”
果果白了我一眼,严肃地检查我的伤势。左边屁股疼,左胳膊擦伤两处,下巴擦伤,并不多严重。我深吸一口气,把脚支在桌面,躺在椅子上看《流俗地》,听她分析我的伤情。她分析一会儿转身走出房间,我听到她和安菲在厨房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引得安菲跑过来敲门要看我:“你还好吗?天呐,果果说你摔得满身是血,动弹不了啦。”
“嗯?”
安菲从房间里掏出一串碘伏棉签,碘伏被封在棉签杆部,是她上次脑袋被厨房瓷砖尖角撞破后买的。
果果给我轻轻擦在伤口上,我疼得再次吱哇乱叫,安菲在门口看着:“我其实还有用来消毒的酒精……”
“打住,打住!”我差点跳起来。
果果煮了饭,我食欲大好,把她烤的一盘鸡翅吃了个精光,脱光光躺到床上去看书。果果才开始倒腾她的电脑。
“电脑没坏,还是担心你吧,哼。”
“哦~”我拧开床头灯,调整姿势,让光照在书页上不至于太弱或太强。好久没躺在床上看纸质书了,突然有点因祸得福的滋味。
接下来发生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我完全失去印象了。
“你中途又突然醒来,大喊大叫问我几点了。我说六点多,你说完了完了,要来不及了,说你约了安菲7点吃早饭。我听得云里雾里,和你确认,然后你说,没事了没事了,是在梦里约定的。”
果果一定是胡说八道,这么长一段话,怎么会我一丁点印象都没有。
“你不会脑震荡了吧,我要带你去医院!”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