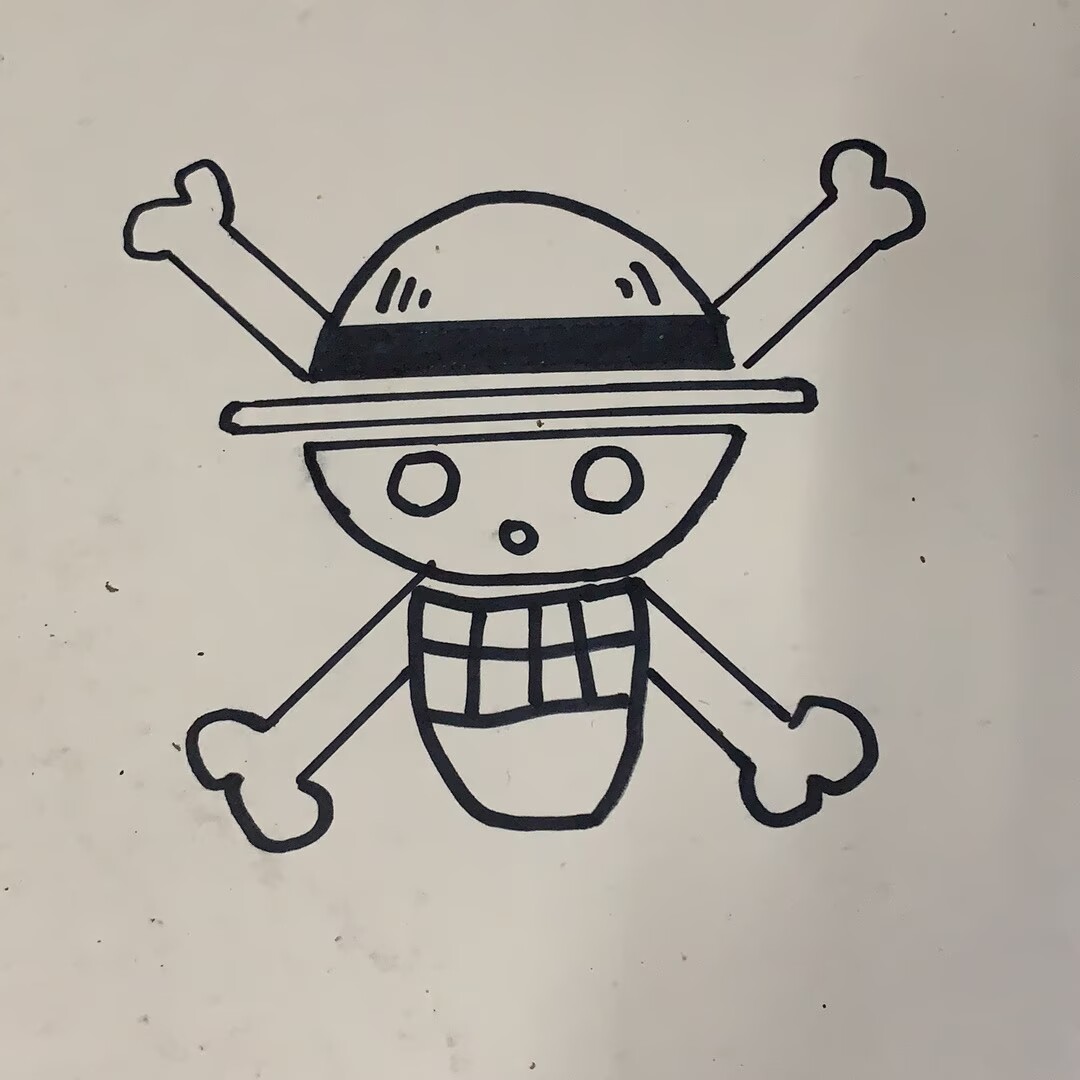《罪迹拓谱》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屋里一盏暖光没开,全靠窗外稀薄的夜色挡着那种“要睡的理由”。我们靠得不近不远,只一茶盏,一呼吸,粘着对话,不用整理语气,也不用先选语词。
白露靠着折叠沙发喝茶,我坐在对面摆弄手里一盏旧款茶炉。光线调得非常暗,像在模拟过时的居家摄影风格。
她没开口,我也没打破平静。可我知道,其实她今天还有话想说。
于是,就等。
终于,她轻声开口——声音就像热水倒在茶叶上的那一瞬,温度不是最高的,但最容易听进去。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查我爸的审判包吗?”
我抬眼,对上她眼神。
她轻声说:“我最开始以为,我能处理好。毕竟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结果第一次看完,我直接昏了过去。”
我没有插话,让她自己把结断掉。
白露没马上展开。她垂着眼帘,给自己又加了一点热水,本该扑腾的那点碎泡,在她指扣杯口的痕迹里,纹丝未动。
她继续:
“你知道最打击我的那些片段是哪吗?”
“不是他做的多恶,不是金额多大让我崩溃。”
“是盘古从他记忆片段里还原出他第一次伸手的时候……他竟然真的相信那是‘为了我’。”
她抬眼,眼里带光,也带点倦意。
“他人生第一次‘动手’干坏事,是在参与一个政策制定,那时候还是本地试点政策阶段,非常小的事。”
“他们说是在研究‘惠民买菜’怎么补贴。”
我动了动杯子,没出声。
白露慢慢把话铺开。
“市场上商贩定价不规范,一家一个价。”
“蔬菜贵得离谱。老百姓买一斤菜,还要货比三家。人要买得全了,得在菜市场里反复横跳。”
“还有缺斤短两、以次充好。”
她笑了下,更像是叹气。
“更离谱的是:商贩们用一种菜‘低价引流’,顾客一进门看到这个便宜,就以为整摊都公道,于是一股脑在他家买,结果被宰了。”
白露继续说,她不怕我听得难受:
“我爸当时参与了一场会议——当然,他叫它“为百姓做实事”的工作组座谈。”
“他们义正言辞,慷慨陈词。”
“说:‘民众买个菜太累太亏太冤,我们要为他们节约时间,标准定价,品质监管!’。”
“方案就变成了:政府出资,在居民区设‘惠民菜销售点’,比市场价便宜,品质得更好。”
“每个点销售多少,就按量申报财政补贴。”
白露轻哼一声,眼神像能抽丝一样抽到那年的情绪:
“好听吧?字面来看,拿去贴条幅都堪称官宣典范。”
“真正的问题是在我爸那一条回忆链上的一句心声。”
“就在会议间歇,他心跳加快,情绪标签显示‘恐惧’。”
“但恐惧之后,他不是自责。”
“而是在找到‘我是为了女儿’这个理由之后,立刻就平静下来了。”
她苦笑了一下:
“然后,他就心安理得了。”
我皱了下眉头,那动作没遮掩成功,她也没笑开。
“从那之后,系统拉出来的每一桩‘听起来是公共服务’,蛋壳里全是油。”
她放下杯,把自己更缩进毯子里:
“那一刻的构图,盘古都拉给我看了。”
“他紧张、忐忑、担惊受怕。”
“他心慌着……但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事脏。”
“是因为他怕‘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直到,他找到‘为了家人’这个理由之后,他突然就‘勇敢’了。”
“你明白吗?”
这回我答了:
“明白。自我欺骗一旦找对了标签,就容易全身过敏。”
随后我又坏笑着补了一句:
“还好我没沾过你们家半点光。”
她听后笑了一下,靠在沙发上:
“嗯。从那之后,他做的每一步,都成了‘为了女儿’。”
“什么申请点名额、审批流程、销售点转包,哪块地归谁管,全走他们手里。”
“他们甚至统一了一个标准,每个月申报多少补贴,由谁盖章谁批,层层往交好的人推进。”
“家人、朋友、前同事、小三……名字像走马灯,请客、送礼、收卡套现,全有花头。”
“最讽刺的是——这事最开始是真有需求。”
“可运行三个月后,‘惠民菜’基本没有比市场价便宜,品质甚至更差。”
“经营资格被人倒手五道,档口换脸和屏幕一样快。”
“但财政补贴却从未停过,反而节节增高。因为——入账的人越来越多。”
“财政拨下来补贴的钱,转几道手早不是为了谁买得起西红柿了。是变成谁能多分两个百分点。”
她停顿,目光落在远处那块未接轨的磁感阳台,就像那些档口,脏了、洗了、换个光源又开张。
“你以为腐败是大项目,是烈火烹茶,其实是碎冷漩涡。是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小政策。”
“名字冷僻、制度繁琐、不到处宣传,还装作‘只在小范围试点’,这种事最容易藏猫腻。”
“叫‘城乡融合型社区阶梯蔬菜配送结构优化示点项目’、 叫‘面向社区的分类食材补贴销售机制优化计划’——这种名儿的,谁懂?谁会查?”
一整套结构逻辑,白露讲得极平静。喜怒哀乐全压在这口茶的温度里,只有指尖不自觉地揉着袖口边线,那是唯一的裂纹。
接着靠了靠我,语气缓些了:
“我查到他这种案子很多。”
“每一个架构都一样。”
“名字听不懂,政策不大张旗鼓。”
“规则写得极复杂。”
“听上去是‘为你们好’,实际上是‘怎么能合法收钱’。”
最后她说:
“你知道这件事里最讽刺的是什么?”
她没有等答案:
“我什么都没参与,什么都没干,完全不知道。他却把整套自我合理化程序的核心架在我身上。”
“他所有那么可笑的自圆其说,竟然是真的。不是演出来的,而是他自己都信了。”
“‘我所犯的所有错,都是为了女儿’,他心说。”
我说:“当时系统怎么评估?”
她笑意下沉:
“盘古初审阶段,默认为‘真实记忆 = 行为动机’。 盘古只看了他的‘主观标签区’。”
“也就是说,只要我爸今天心想‘我做这些是为我女儿’,他记忆也这么存了,那就被认定他行为也是这么打算的。”
“判定结果是:‘动机为亲属情感占据主导,由子女福祉构成行为引发要因’,我一口气看完直接昏了。”
“可现实是,那些项目的好处,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吃了。”
我大脑曾记录下那段话:系统当初几乎把她定义成了动机源头。
那种机械正义恰恰让她变成了一个从未出场却被入档的共犯。
于是我接了一句:
“记忆里的动机,早已不等于行为的真实因果。”
她缓缓吸气,像在抽一根不点的烟:
“Jesus也真是……后来才更新那段行为判断逻辑。‘真实动机不等于记忆标签,而是需要认知偏差辅助建模。’”
我点点头,那正是Jesus二代介入审查系统的里程碑之一:
“动机不是你记得了一个理由,而是你是不是故意在忘另一个。”
白露一字一句道:
“你不能光看他记得的是啥,还得看他记错没。我爸不是为了我。”
“他只是……需要我来挡住真正的理由。”
“他自己太怕看到‘我是为了钱’。”
我望着她:
“是的,但那不是你该还的账。”
“那是他自己拿爱当补丁,把所有‘本应有愧’都贴上了‘为女儿’的标签。”
白露沉默了一下,然后笑得更真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愿意跟你待一起吗?”
“因为你从来不让我帮你承担。”
她看向我:
“而你审完了那么多世间的错……最后还愿意跟我平和着,把这天一锅饭吃完。”
我没接话。只是提起壶,再替她续上半杯茶,那茶落下去的纹路,就像这几年她自我和解过程中,慢慢抚平的弧形裂痕。
夜里的风很轻,拂过屋檐像被调成“静音模式”。我们并肩靠在藤编躺椅上,窗没有关,白露像猫一样把毯子拽到肩头,盯着杯口边那层薄得快散掉的热气。
她突然说了一句,没起因也没情绪:
“我以前……站在阳光底下的时候,也会忍不住低头。”
我没说话,只是偏头看了她一眼。
她继续:
“并不是因为晒,就是……”
她顿了顿,拢了拢毯子,像是从回忆深处抽出一小块带毛边的布。
“我怕别人记住我。”
我眉头轻动了一下,却没打断。
她把目光从茶杯边沿移开看向窗外,一个反光不到的地方。
“不是怕他们为难我。”
“是怕,有人看着我的脸,在心里下定义。”
“而我那一天偏偏可能……有点没整理好情绪。”
我点了点头。
“我懂。”
又沉默了十几秒,我正要换个话题。她却低声说出:
“张扬。”
我转向她。
她像是要靠近耳语,又像只是在说给这屋的静夜听: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像是温柔过头的审判。”
我没有立刻回应,只轻轻伸手,握住她靠窗那只还未盖住的手臂。
“它不吼你,不责你,不打你一巴掌。”
“但它也不放过你。”
“它让你无声地——一点一点觉得,每次呼吸都像是偷来的。”
风正好从窗缝里掠过,我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点。
就那一刻,我问了那个从她讲完那段关于父亲的回忆时就在我舌尖打转的问题。
“白露。”
“如果……”我看着她,“如果再给你一次投票的机会——关于这场全民审判,你还会投同意吗?”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沉吟,也没有反问。
只是那样很直接地说:
“支持。”
“坚定不移地支持。”
我没移开目光,也没急于释怀,因为我太熟悉人类在压力下的应付说辞。
但她不是那种会违心迎合我的人。
不是她一个人。
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次问。
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吧,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我开始问所有人。
不只是像白露这样亲密的人,还有我的老同事、前审查对象,我也问过李晋。那天他刚从一段情绪封锁期里恢复出来。
他是那些,因为往昔的一段人生污点,至今仍饱受心理折磨的人之一。
可我问他是否还会支持全民审判——他的回答,依旧坚定。
没有迟疑,也没有试图给自己辩解。
其实这一类人我问得最多,他们的世界观在审判之后是有撕裂的。他们每天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选择,很多人甚至还不敢去读取自己的案件复刻记录。
可正是这些人,他们给我的答案反而最扎实、最无比清晰:
“支持。必须支持。”
他们身上背着伤,也背着耻。
可他们没有否定审查制度本身。他们明白得更深刻——这场审判,不是冲着他们来,是为了不再产生下一个“曾经的他们”。
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
都说支持。都说不后悔。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许多人,比起创世时那场历史性的全民投票,还更坚定。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很多人,当初投过反对票。
可这一次,他们没人再往回收。
说话那一刻,他脑子里是不是真这么想,我们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别说演,就算他自己想骗自己,也骗不过我们。
可他们都是真的。
不是怕审,不是拍马,不是附和制度的那种“同意”。
而是——发自肺腑地,明白了这场审判的意义。
这改变,发生在一个关键的节点——
当所有人都可以查看完整的罪行记忆之后。
不是媒体演绎,也不是文字报道,而是直接导入记忆片段,第一视角,切身体会。
当他们不是“听说”了谋杀,不是“见证”了欺凌,而是亲自经历别人的折磨与窒息时,那种反应,根本不是理性决定可以描述的。
所有有人性基础的人,哪怕曾一度麻木,都不可能在看完那一段段压抑的、令人溺亡的记忆后——还能说「算了,过去就过去吧」。
我曾经以为,人类坚持要求审判,是因为他们受过伤。
但这些年越看得多,越明白——不是,起码不全是。
很多成人能原谅自己遭受过的罪。
能说服自己:“那是时代使然”、“活着已经不错了”、“我也有不勇敢的时候”。
他们甚至能笑着讲过去,能把一段被羞辱的青春归结为“成长的代价”。
可唯独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法放过去。
孩子。
那一代又一代,被扔进三六九等的教育温床上成长的孩子。
那是他们抗不住的软肋,也是这场全民审判里,最不容低头的一部分。
老话说——再苦不能苦孩子。
你可以端掉我的碗,我不吭声。你骂我一句废物,我也能认。
可你若动了我孩子的尊严,哪怕是一个小眼神,对我来说都是要命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