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忘不了:《無痛失戀》與愛的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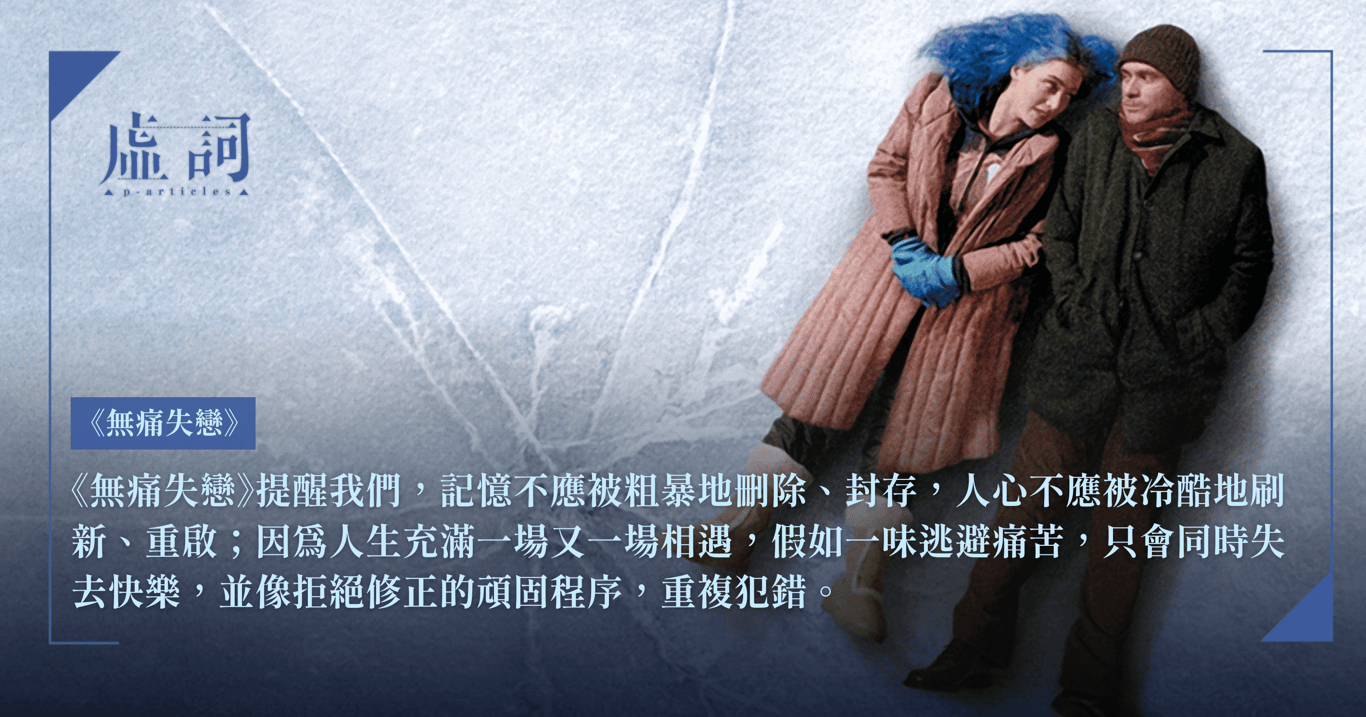
文|黃紀真
失戀時最常聽見的話,不外乎「忘了吧」;忘了那個人,忘了那段時光,彷彿就能忘掉悲傷。記憶似是痛苦的根源,就算戀愛的點滴本身極其美好,在求不得的當下,甜美頓成苦澀。然而忘記的過程總是漫長的折磨,反反覆覆,讓人在捨不得與留不住之間搖擺。如果可以一鍵刪除,把舊情人帶給你的喜怒哀樂通通忘掉,變回相遇之前無憂無愁的自己,你會按下那個按鈕嗎?沒了記憶,也就真的不愛了嗎?
在經典科幻愛情電影《無痛失戀》(Eternal Sunshine of a Spotless Mind)(2004)裡,Jim Carrey飾演的Joel憂鬱靦腆,老實卻不木訥,內心敏感細膩;Kate Winslet飾演的Clementine活潑搞怪,桀驁任性,瘋狂又自由。看這兩人在火車上相識的幾分鐘對手戲,就知道後來的戀情是opposites attract的結果,也能預示衝突的頻發。
對於劇情的展開,想必失戀過的人多多少少都感同身受:對愛情的期望與現實有落差,累積失望爆發衝突,分手後從心碎中生出不甘和憤怒,又因為傷痛難以忍受,終將踏上漫長而痛苦的遺忘之路——但在現實中,這種遺忘是過渡式的,像揚起的塵埃慢慢沈澱;也是選擇性的,只淡化剮心的片段。電影的背景設定卻十分巧妙:一間生意火爆的忘情診所可以提供徹底清除記憶的服務,把人腦當電腦,前度愛人當癌細胞,一鍵刪除,無痛失戀。
於是,Joel在與Clementine爭吵後,還苦惱著怎樣和好,卻驟然得知Clementine已經消除了有關他的記憶,開開心心地開始了新戀情。他陷入不解與痛苦,然後一氣之下選擇了以眼還眼。代入想像一下,他當時的感受大抵是這樣的:你可以離開我,可以不再愛我,但不可以忘了我——如果你必須要走,至少我們共同擁有的記憶與感受是種斷不開的連結,我們將在過去裡永遠一起;若是連這虛幻的連結都失去,我就真的一無所有。
遺忘程序一旦開始就無法中斷和逆轉,Joel卻在腦內遊走這段戀情的美好回憶時後悔了。就這樣,他開始了一場浪漫的即興逃亡,帶著Clementine躲進一段段本不屬於她的場景和片段,想把她牢牢鑲嵌進自己整個人生,哪怕是最不堪回首的時刻。諷刺的是,那些本應在現實中戀愛時做到的事,譬如溫和地溝通、向愛人展露脆弱,Joel 通通只在拒絕遺忘的夢裡後知後覺地做到。
電影的最後,在腦海裡與自己和解,停止逃亡,忘記一切的Joel翌日醒來,卻再度在命運驅使下與Clementine重新相遇相愛,重複的場景終於揭示了電影精妙絕倫的時序結構,為故事賦予「命定之愛」濃重的宿命感。
記憶與成長
但電影其實不全是宿命愛情的科幻故事,更多是在叩問記憶與自我成長之間的關聯。
《與愛因斯坦月球漫步》(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2012)一書很有意思,明明在講超強記憶法,卻有整整一個章節寫〈世界上最健忘的人〉。一個總是樂呵呵的男人患有嚴重健忘症,只有半小時左右的短期記憶,既無法形成新記憶,也無法提取舊記憶。因為沒有長期記憶,他無法比較今天與昨天的感受,無法建立對於自我和身邊人的連貫敍事,於是也無法為妻子提供最基本的心靈依靠——對一個永遠在「現在」中輪迴的人,妻子完全沒有辦法觸及他的感受和思想,自然不可能與他建立任何有意義的親密關係。他只能依靠大腦和身體裡殘存的生活習慣來體驗世界,病態地「活在當下」,成為困在老朽肉身裡的彼得潘,永遠無憂無慮,卻也失去成長的可能。
這個患者的例子如同電影中忘情診所的技術一樣極端,卻在說明同一個道理:不加篩選的全盤忘記只會使人停滯不前,重蹈覆轍;所以患者會一遍遍寫下一樣的日記,而Joel也會一次次愛上一樣的人。
事實上,在歌頌記憶的世代,也許遺忘才是生命的真諦。思考即忘記,我們由此篩選出對自己重要的事物,才能認知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定位。遺忘是內化的過程,當有關痛苦的記憶被慢慢溶解,被徹底感受,像雨水緩緩滲入泥土,才是在以一種健康的方式滋養靈魂。我們從中學會生命中不如人意的必然性和鍛鍊承受痛苦的韌性,和過去和解,為未來做準備。《無痛失戀》提醒我們,記憶不應被粗暴地刪除、封存,人心不應被冷酷地刷新、重啟;因為人生充滿一場又一場相遇,假如一味逃避痛苦,只會同時失去快樂,並像拒絕修正的頑固程序,重複犯錯。
當一個人離開你的生命,而你不得不接受,便唯有鄭重地選擇忘記,並為這個決定負責任,才能真正學習、療癒、成長。忘記應該像大掃除一樣,並不是一鼓腦兒扔掉所有物,而是仔細挑揀去留,重新規劃如何擺放或收藏捨不得的東西,同時去除負擔,重整旗鼓,成為更從容的人。
永恆輪迴的苦、樂、愛
雖說如此,Joel與Clementine舊情復熾,也未必是旁觀者清的觀眾能用一句「重蹈覆轍」蓋棺定論。
驟眼看來,Joel的愛情獨角戲確實有些自欺欺人——回憶是可以編造的,整場逃亡便是證據。他腦海裡的Clementine是自己具象化的留戀對象,所以才會特別美好,二人在夢裡合作無間,氣氛鬆弛,言語間是滿滿的諒解與耐性;但這一段終究只是他所提取記憶中美好的部分。撇除那一趟在腦海裡自編自導自演的浪漫逃亡,生死與共,Joel可以回歸現實的庸俗日常,改變自己並接受她的全部嗎?他腦海裡的Clementine說自己是一時衝動才去消除記憶,但其實這明顯是Joel自己犯的錯誤,只是在潛意識中投射到Clementine身上;也許現實中她是經過深思熟慮做的決定,而Joel打從心底不願意接受這個可能性。所有出於她口的感人台詞,都是他渴望聽到的,或者渴望說出口的。觀眾不由得懷疑:他真的了解這個女人,並準備好愛她的一切好與壞嗎?一廂情願的浪漫鬥爭,孤獨時才捨得鼓起的勇氣,對現實中的破碎愛情而言,意義其實不大。(題外話:電影開頭,Joel的內心獨白說自己不是個衝動的人,卻莫名翹班去蒙托克;後來才發現,原來他所有出乎意料的衝動,包括決定消除記憶,全都關於所愛的她,切合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裡所形容的「隱喻式的瘋狂」。)
但這對宿命戀人最後選擇雙雙輪迴,還是有種當局者迷的純粹;愛情最不含雜質的模樣,在成年人慣於權衡得失的世界裡尤為動人。
相愛從來都是一場永不停歇的考驗,至死方休。對於重修舊好,誰都不能斷言他們注定重蹈覆轍,因為有了深刻的記憶(哪怕部分虛構)就有成長的空間,體會過遺忘的不捨才會有愛下去的覺悟。同樣地,誰也不能斷言他們會幸福美滿,因為只靠感覺與衝動維持的關係難以長久。說到底,也許一路磕磕絆絆走過,快樂多於悲傷,期待多於失望,感恩多於遺憾,便是幸福。
電影尾聲,Joel面對Clementine「一切還是會重來」的消極質問,一句it’s ok看似不經腦子,但其實背後是釋懷的勇氣。沒有動人的海誓山盟,卻教人信服:既然試過忘記,又捨不得忘掉,那就努力排除萬難,哪怕面前是分分合合的輪迴。尼采說過,如果得知生活無論悲喜,將以同樣的時序同樣的方式永恆輪迴,我們仍然渴望一遍遍重來,那便是對自己命運的愛。忘記使Joel停滯不前,忘不了卻帶給他尼采式的超人意志,堅定他去愛的信念。因為愛,所以甘願把無論悲喜的記憶通通鎖進密封的沙漏,接受愛裡的庸俗與高尚,難堪與動人;不完美的兩個人,合成一份完整的愛,在一個不再空虛的世界裡,沿著無數既定軌跡變化流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最後那兩盤播放對彼此失望與憎惡的錄音帶,像命運垂憐這對有情人,送他們一個打破輪迴的契機:一場猝不及防、毫無顧忌的坦白。他們懷念完美麗,謾罵盡醜陋,還是選擇重新開始;我便願意相信,他們在這一次的輪迴裡,終會得到善終。
「無瑕的心靈永遠陽光明媚」
戲名引用了蒲柏的詩句,但修道院裡的阿伯拉與哀綠綺思尚且無法擺脫凡心,何況無心出家的我們。沒有誰的心靈可以真正一塵不染;本是紅塵中人,哪能不惹塵埃。哪怕Joel與Clementine刪乾淨記憶,還是因為身體的習慣或靈魂的渴望,冥冥之中重新邂逅相愛;無法被動忘記的我們,失戀後彷彿只能迷失在濛濛細雨。但無論是甘心輪迴還是超脫苦海,其實本質都是改變和前進。唯有直視痛苦,好好忘記,提煉回憶,才能安葬舊情,走進晴天。認真生活,專心忘記;終有一天,失戀的人也可以從容地欣賞陽光下飛舞的塵埃,微笑著邂逅下一個或上一個情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