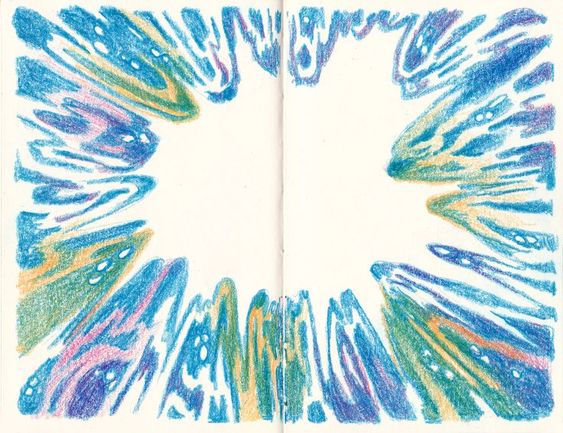短篇小说|「台风来临前那夜」
文中含坠落与死亡场景,请读者自行斟酌。
据气象台报道,这次台风的规模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网络上各大小媒体也在反复强调这场台风过境将会带来何种危害,不断叮嘱民众尽早做好防范。
下午四点,政府甚至发出通告,要求全市各单位今天晚上九点停止营业。
医院各部门也陆续收到院方的通知,到九点还逗留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即使已经下班的,都不得离院。
余淑芬这周在住院部轮值白班。眼看已经过了五点的下班时间,瞧了眼窗外,天色比以往更早地昏暗下来,树枝无序地大幅度摇晃。她跟夜班同事交接完工作,换下护士服,匆匆赶回家。
家里除了大米和调料,什么都没有,她要赶在台风登陆前把接下来两天的肉菜买回去。
她本可以在回家路上买好食物。下班途中家婆打电话给她,说家公不肯吃抗凝药,叫她快点回来劝他。
淑芬的家公两年前脑溢血,虽经抢救保住性命,却失去行走能力,性格还变得更加执拗。连续请了好几个保姆,家公都不满意。家婆不得不亲自照料他。家婆已经八十多岁,这两年操劳过度,背脊愈发佝偻。大小家务事便全落淑芬一人身上。
家婆怕儿媳推辞,在电话那头好言相求,你在市三甲医院当护士,经验足,更有说服力啊。淑芬听罢,只得叹口气,先回家一趟。
等她好不容易把倔强的家公安抚下来,才注意到窗户一直被风吹得哐哐作响。见天色已晚,她提醒家婆尽快贴上胶布加固窗户,同时打开鞋柜,随手套上一双人字拖,匆忙出门。
从小区后门出去,再往左拐,就是兴洲市陆港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廿年前,丈夫阿杰便看中了这个小区。他说,虽然这里的房子楼龄不小,但都是当年香港侨胞集资修建的,质量可靠。即便大多数人更青睐新楼盘,他仍决定在此买下一套二手房。
直到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仍然排在陆港区前五。可见丈夫确实有眼光,也有独立的判断力。
只是最近他的项目遇到了问题,人也愈发沉默寡言。几天前,他突然说要去邻市洽谈业务。丈夫一向不对家人谈及工作,但她知道甲方总部就在邻市。他出门那天神情木然,并非以往即将谈拢项目时那样精神抖擞。出差这几天与他在微信上联系,也回复得语焉不详。
她不敢往下细想,快步走进华灯初上的街道,汇入如织的人流。
再往前走一百米,是两条干道的交汇处,菜市场的入口在斑马线的斜对面。流动摊贩聚集在入口附近,从远处便能望见人头攒动。只是今天情况特殊,换作平日这里早已打烊。
平时没有留心,今夜走在街上,她才察觉到两旁的店铺更迭得越来越快。这里原是一间开了许多年的时装铺,却已关门。先是换成咖啡店,没撑过一年,如今又成了奶茶店。旁边那家老牌美容院,也早已换成烤串店。
她对照着记忆,发现一些五金店、士多店纷纷变成云吞面馆、港式茶餐厅。
这些本地口味的餐饮店在温黄的街灯下栉比鳞次,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餐加盟店在其间见缝插针。她终于意识到这条多年历史的商业街,不知不觉间成了一条食街。
街角偶尔还能见到几个吉铺,生锈的卷闸门在风的撕扯中吱呀作响。卷闸中央贴着一张黄色纸,上面红色大字写着:“旺铺招租”,与往日的百业盛景形成鲜明对比。
街道的变迁勾起了她对丈夫这些年变化的回忆,胸腔仿佛被风压住。那个曾经冷静、稳重、几乎从不出错的男人,似乎已离她越来越远。
淑芬踏入高楼间的一片广场,楼间风骤起。她低下头,快步穿过,目光紧紧落在尽头的斑马线上。
她不喜欢这个广场,和它后面的大厦。她刚搬来没多久,目睹了一件可怕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广场上。
她心头一晃,街头巷尾的喧嚣仿佛重现。
那年,整个兴洲市都沉浸在不可抑制的股市狂潮中,连家公也被那阵股市热带着进去。幸好阿杰劝阻,家公提前全身而退。后来牛市一夜转熊,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她在斑马线前停下脚步,摇了摇头,试图甩开纷乱的思绪。
红绿灯响起心跳般的节奏,不仅没有停下回忆,还勾起那可怕的画面:陌生男人喉咙深处咕咕冒出的黏稠气泡声,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刺鼻血腥味。
那个晚上,她值完晚班,阿杰开车接她回家。到家附近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两人打算停车找个小店吃夜宵。
正当他们路过那栋当时还在修建的大厦,忽然一记沉闷的巨大撞击声在空气中爆开。刚开始,他们和四周的居民还以为是车祸,很快就发现,声音是从大厦前的广场传来。
她已经不太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走到那具已经严重变形的躯体前。她只记得闻讯而来的建筑工人和队长用她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喊着,围观人群害怕又好奇的脸,还有几个避之不及的女人的尖叫。
她凭职业反应迅速检查他的瞳孔和呼吸状态。阿杰站在她身旁,捂住口鼻,强忍呕吐,冷静地拨通了120和110。
她记忆里最后的片段,是白布覆盖的人形,以及阿杰温柔的安慰。
几年后的某天,一位病人出院时把一本美术杂志遗忘在床上。她随手翻开,被其中一幅画吸引。画中有两个脸上蒙着白布的人,他们脸傍着脸,身挨着身,从衣着上看像是一男一女,背景是一堵冷峻的建筑外墙。画的底下写着一行字,《恋人1号》 勒内·马格利特。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日后的岁月里,她的记忆逐渐把这两个场景交织在一起,每次和阿杰经过这个广场,她都会想起那幅画。
后来,她听到很多关于那个不幸的男人的猜测。其中一种说法——就这个菜市场门口卖菜的大姨说,那人是这栋大厦的老板,挪用了工程款去博一把,结果钱在股市里蒸发了。
大姨抬起圆厚的肩膀,指了指那栋建到一半的大厦。你看,都烂尾了,肯定是笔巨款啊!
真相讳莫如深。
而那栋大厦,确实在这件事后烂尾了十多年。后来换了个开发商重新动工,几轮招商引资下来终于把大厦盘活,还成了这条街的新地标。
但是因为那件事,她至今不爱往里走。
回顾这几年的变迁,她察觉这个地标的光辉也随着商业街的式微逐渐变淡。前几天她才听家婆说,最初进驻的那批国内外大牌服装店,在这几年陆续撤场。高层办公室的空置率也在上升。
也是在前几天,她从卖菜大姨的抱怨中得知,最近好几个年轻的客人失业了,他们对菜价的上涨异常计较,但转身又跳进股市。大姨摆手说自己不敢再玩了,当年亏进去的,都还没平仓。
这时,她忽然想起一整天都还没跟阿杰联系过,于是趁红灯还没转绿,掏出手机,点开他的微信头像。
台风这两天就登陆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她清了清干涸的嗓子,小心翼翼地发送语音。
如同大部分夫妇,淑芬和阿杰在婚姻初期的各种摩擦在所难免。但淑芬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阿杰的生意也越来越忙碌,两人能呆在一起的空闲时间不多,磨合期不知不觉便渡过了。
婚后第七年,女儿出生。两人的生活重心除了各自的工作,逐渐倾斜到女儿身上。现在女儿升到初中,夫妻间的话题,更是去芜存菁地围绕着女儿。至于夫妻感情,说是形成默契也行,说是逐渐平淡也可。
即便如此,她始终认为,阿杰是个称职的丈夫。他性格稳重,既是家中经济支柱,也是自己心理依靠。
非要说有哪里不足的,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不会表露自己的想法。她只能靠日积月累的相处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揣测丈夫的情绪。
回家进门时,如果他多花几秒把鞋子整齐推进鞋柜,多半是工作上遇到了难以抉择的事;若是回家路上特地给女儿捎份DQ雪糕,则意味着手上的项目进展顺利。
红绿灯的提示声从缓慢转成快板的节奏。身旁的行人哗一下拥向马路,把她的思绪拉回现实。她重新提起精神,踩着间隙穿过行人和疾驶的电动车。
菜市场内的鱼档和禽档在打扫卫生。猪肉档只剩最后一块瘦肉,肉质很干硬。档主喃喃自语,好像在跟她解释,明天市场关门,想买都买不到了。她权衡片刻,还是把肉买下。另一侧的蔬菜档全收摊了。她记得进来时入口两旁的临时摊贩还有绿叶菜在卖,快步往市场门口走去。
风把市场的塑料布吹得咧咧作响。两个二十出头的男生拎着一大袋薯片和方便面在她面前掠过,讨论着明天停工在家要怎么过,兴奋得就像空中飞舞的树叶。
淑芬直奔人堆,俯身挤进去,不再嫌弃那堆干瘪的菜心。有总比没有好。
她快速抓起一把菜心往塑料袋里塞。一晃神,直觉身心就跟手里的菜心一样奄奄一息。家婆担忧的眼神,家公颤巍的步伐,女儿伏在作业堆的背影,还有阿杰还没回复的微信,走马灯似的在脑海中闪现。疲惫感夹杂在风中从四面八方袭来,人怔怔地站在那,如风中的老枯树。
手机铃声及时响起,将她拉回现实。她拽住救命稻草般立刻把手机扶到耳边。
阿杰?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脱口而出。
您好,我是XX银行给您来电,鉴于您是我行优质客户,现有一笔无抵押贷款可以免费……淑芬丧气地掐掉AI客服的声音。
重新打开手机微信,阿杰仍然没有回音。
她下意识地抿紧唇,思忖丈夫不回信息的原因:高速上不方便接电话;在谈生意没空看手机;邻市离台风风圈近,他正在户外听不见……她实在想不出更多了,其他可能性超出她对丈夫的了解。
不安在胸腔里缓缓积聚,越积越浓。
付完菜款,她把手机收回口袋。定了定神,抬头四处张望还有什么能买的,努力不去联想跟丈夫有关的事情。她强迫自己思考接下来两天的菜式,试图用细碎的生活仪式驱逐心中的阴霾,却仍忍不住想起丈夫沉默的脸。
菜市场旁新开了一家面店。男店员卖力地给路人发宣传单,争取在晚市时间招徕客人,完全没注意自己正站在被风吹得嘎吱作响的招牌下。淑芬望着他,犹豫要不要提醒。
正当两人目光相对,她突然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很快认出他竟是阿杰合作多年的下游建材供应商。
嘉乐?你怎么在这?
阿嫂?好久不见。这是亲戚开的店,我在这打工。嘉乐也认出她,有点羞愧地挠挠头。
听他这么一说,淑芬才想起,阿杰曾说过嘉乐也住在陆港区。
阿杰那几笔二一年的尾款,到现在都还没给我。现金流一断,我公司实在撑不下去,干脆关了算了。
淑芬这时想起,自二零二零年的年中起,阿杰就陆续收到行业内的不详的小道消息。
那段长时间被封在家的日子里,丈夫坐立不安,电话不断,情绪日益低落。有一次,她碰巧听到阿杰躲在洗手间打电话,他准备把自己名下的几处房子卖掉,用来周转资金。
自那后,她的心头悬起一块巨石。
二零二一年底,当地一家大型公司宣告自己不能如期支付债务。
阿杰收到消息那天,无力地瘫在沙发,任凭手机铃响,直到电量耗尽。家里人都感受到乌云压顶般的压抑气氛,家婆不敢惊扰阿杰,只能在儿媳旁边试探性地了解他的状况。淑芬意识到自己能为这个家做的,就是替阿杰抵住家公家婆的担忧,同时在女儿面前维持家中的表面秩序。
她带着歉意和同病相怜的心情在嘉乐的店里下单了三份牛腩伊面和两份云吞面。不知为何,她忽然有种模糊的感觉,阿杰也许已经回到兴洲了,于是顺手在外卖里也算上了他那份。
嘉乐给淑芬打包的时候告诉她,附近几家新开的餐饮店老板都是各行各业的人失业后掏家底投进餐饮业的。
没办法,转行没那么容易,只有餐饮行业门槛最低。要是有别的出路,谁愿意走到这一步呢。嘉乐苦笑着摇头。
嘉乐的话让她想起,卖菜大姨那天也说过一句——这次股市还没爬到当年的一半高度就又掉下来了,看来又得摔一批人了。
即使知道嘉乐可能比自己更了解丈夫的资金状况,但她一句话都不敢问。她只感到全身被寒意笼罩,连掏手机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阿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在回来了吗?风越来越大了。要是在开车,注意安全。她再次发送语音,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
天色已经彻底变暗。她抬头远望,错落有致的楼宇隐藏在璀璨的街灯后面,暗得几乎与天空融成一片。一股风刮过,吹乱她的头发,发丝紧贴在脸上。
就在此时,她隐约望见紧挨着那栋大厦的苍蓝色天空中,出现一个快速直线下坠的黑影。
她的呼吸猛地一滞,心脏像被紧紧摁住的弹簧,下一刻就要冲破胸口。
还没待她反应过来,巨大的撞击声骤然响起,将城市的喧闹声全部掐断。
“有人跳楼!”
风卷起尘屑和尖叫声,一股脑横扫而来。
她只觉心脏一炸,耳里嗡嗡作响,手指因缺血而冰冷。
一个强烈的不祥的念头瞬间占据了她的脑海——阿杰不回信息,会不会是……
她的理智警告自己不要靠近那栋大厦,但双腿像有自己的意识。
她丢下嘉乐,外卖都忘了拿,不顾一切地冲过斑马线,直奔广场。
广场里挤满看热闹的人。他们高举着手机,对准那个可怜人。有人惊叫、有人退缩,议论声如蚂蚁啃食腐叶。
她气喘吁吁地推开围拢的人群。双脚踩在坚硬的石面上,却像陷进棉花堆,只能用力站稳防止摔倒。她伫立在最前排的看客身旁,死死盯着那人的身躯。
扭曲变形的躯干,一只手臂已经从身体分离,脑袋以惊悚的角度卡进自己的白色衣服,看不到脸。
不像。不像他。她着魔一样在心里默念。
然而,她在那身白衣的轮廓里似乎寻到一丝熟悉。肩膀转折的弧度,缓缓渗血的裤子,像极了前年她买给他的那条……可她从来不曾料想,那个熟悉的身影会以这般骇人的姿势出现在眼前。
不对。不是他。绝对不是。她摇着头要甩掉眼前的画面。
狂风骤起,将她的头发再一次吹乱,像一层布蒙着她的脸。
虚构之作,若有相似,皆属巧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