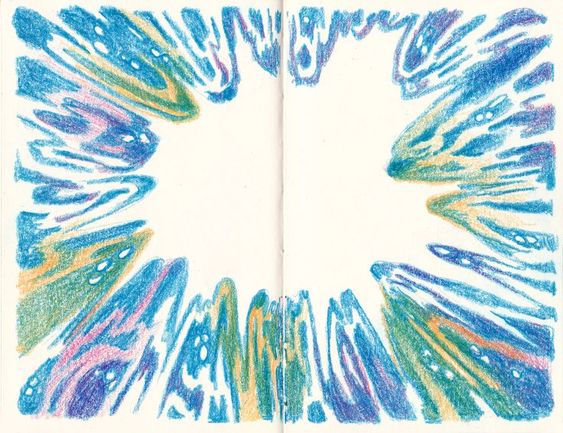短篇小说|「中阴夜谈」
我从黑暗中苏醒,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最后的记忆,是麻药注入静脉那一阵灼痛。
前几天朋友L约我周末去打室内棒球。打完球没多久我就感到腹部剧烈疼痛。L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黄体破裂,于是安排我第二天立刻手术。
再醒来时,所有的疼痛消失了,意识像从雾里被一点点拭净,我缓慢地打量四周。
房间不到二十平方,消毒水的气味在空气中浮动。柔和的月光从窗外渗进来,整个房间浸染在幽蓝的夜色里,安静得不像人间。
我的意识仿佛还在四处飘散,没完全落回身体。
“现在几点?今天星期几啊?”我喃喃自语,尝试发出声音。感觉自己上一次说话是遥远的上辈子,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还能不能发出来。
“现在是星期一凌晨四点。”一把女声从旁边病床传来,温柔地把我的意识召回。
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病床的扶手挡住视线,腹部的创口还隐隐作痛,我扭着头抬起下巴朝声音方向张望。
她平躺在床上,身材娇小,盖着被子仍显得单薄,加上光线太暗,我之前才没看见她。
“谢谢。”我说。
“不客气。”她回了句,语气温和。
看来是个很有礼貌的女孩子。
此时,我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心想——天还早,不如再睡一会儿,很快就能到天亮。
可谁知,再也睡不着,甚至无法自如起身。手被点滴瓶牵制着,其中一个创口还插着管子,管子连着的引流袋挂在床边。连翻个身都困难,只能干瞪着眼,偶尔微微扭动四肢。难受得几乎发慌。
冷不丁传来少女一句呢喃:“嗯……明天……我知道的。”
“嗯?”我下意识地接话。
“啊,你醒了?”她愣了愣,反而愕然地问。
“可能已经睡够了。”我心生疑问,又猜想应该是麻药残留,让我耳朵产生幻听。
“应该是。下午三点多护士们把你送来,你就一直睡到现在。”她平静地说。
我在心里默数了一下时长,原来睡了十几个小时。我试着找到能活动的姿势,慢慢地伸了个懒腰。僵硬的关节缓和了不少,还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她忽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莫名其妙,转头看向她。
“很抱歉,我想起你刚刚被送来时,”她话说到一半,突然话锋一转俏皮地问,“你记得当时你说了什么吗?”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努力搜索大脑中的记忆碎片。当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傻事,我也忍不住笑了。
“几个护士把我搬到病床上,我睁开眼看着离我最近的护士的脸,哈哈哈,”腹部的伤口抽着疼,只能忍住笑,“麻醉药效还没完全过,明明神志不清的,居然张口就对她说我认识她,还曾经一起喝过早茶,其实入院前根本就没见过她。”
“可能是上辈子认识她吧。”我顺口说。
听到我的回答,她只是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心想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不再作声。
病房的气氛迅速安静下来。只听见病房的吊瓶滴答声停了几秒,又重新落下。
她的声音忽然穿过夜色:“你听说过梦中阴吗?”
听到“中阴”两个字,我毫无缘由地背脊一凉,没料到她会这样问,有点被吓到。
“啊……你是说‘鬼’吗?”话一说完,我甚至推测,接下来她告诉我,她是鬼。
想到这,我的声音抑制不住地抖动:“有……有听过,但平时很少会聊这个话题……”
“确实不是日常聊的话题,尤其是在医院呢。”她一边说一边拉了拉被子,换了个睡姿。
我看着她做出这番像人的小动作,才稍微放下心,定了定神,假装轻松地说:“对呀,只有小时候才会聊,你也知道,小孩爱比胆量嘛。长大后还聊这些话题就太不现实了。”
我只顾给自己的慌乱辩解,说完才发现失言,连忙补救:“但其实一直对神秘话题挺感兴趣的。你有了解?”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呃,怎么说呢……”她没在意我的失礼,反而害羞起来,“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
“没事的,反正我们都睡不着,随便聊聊嘛。”我突然觉得此刻像极了小时候盖着被子蒙头聊夜话的场景。
“嗯。‘梦中阴’不是鬼的意思。换句话说吧,做梦的时候就是在经历‘梦中阴’了。”她很认真地解释。
“哈,这么来说,一点也不可怕啊。”
“嗯嗯,其实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清醒的时候呢,也是在经历‘中阴’哦,叫‘生中阴’。”
我忍不住插嘴:“我现在睡醒了,也是在‘生中阴’?”
她点点头:“你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中阴就是我们意识的一种‘中间状态’, 会随境遇而切换。很多人以为意识会中断、会结束——像是晕过去、入睡、甚至死亡。可我不这么看。”
她两只手抓起被单的边缘轻轻前后交替画圆。
“我认为意识是连续不断的,只是在切换状态。”
“那就是说,生死之间的切换叫‘生中阴’和‘死中阴’?”
“嗯……虽然死亡看起来只是刹那的事。可依我理解,临终时陷入意识模糊的那段时间其实很长,那叫‘死中阴’;而死亡后走向轮回的过程,叫作‘投胎中阴’。”
在凌晨的医院里听到这些话,我非但不再感到害怕,甚至觉得这个理解角度非常清奇。我暗自琢磨这几个“中阴”之间的关系,小时候曾经听家里老人讲葬礼和祭祀的相关事情,那时不是很理解,还有点敬畏和害怕。被她这么一解释,可怕的气氛完全消失了。
她发现我不说话了,自责地说:“对不起,是不是我说的话吓到你了。”
“没有没有,”我连忙安慰她,“我觉得你说的东西很有意思,我只是在想,虽然‘中阴’状态有很多种,但是‘投胎中阴’之后,意识就消失啦。
她摇摇头。
“很多人都认为,人死了意识也没有了,我觉得啊,我们这辈子经历的可能仅仅是意识的其中一段。意识比一次生命还要长;它,不只属于这一辈子。”
这个少女的话又让我眼前一亮。“意识比生命长?有点难理解呢。”
她翻了个身,把脸朝向我。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也想了好久才想通,要是我说得不够清楚,你别介意哦。”
一双单眼皮的眼睛折射出年轻的灵光,月光的阴影在她鼻梁中间划出一条明暗分界线,高光凝聚在小巧的鼻尖上,薄薄的嘴唇棱角分明,是一张秀气的脸,看起来不过20岁上下。
“不会的,你说吧。”这么乖巧的女孩子,无论说错什么都值得谅解吧。
她把头抬起来,用手掌挡在嘴侧,好像这样我就能听得更清楚。
“你知道吗?意识呢,其实是没有时间线的。”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意识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别,意识一直都存在,人还没出生时,意识就在了;人死了,意识依然存在。”
一只飞蛾扑棱着窗外的街灯,影子在她眼里晃动。
她继续说:“没有时间线,生死就不是前后关系啦——生和死,其实是一起存在的。
“你意思是我现在看起来是活着的,但同时我已经死了?”虽然我睡得够充足的,但大脑还是免不了混乱起来。
她又摇了摇头,重新躺回床上,一只手无意识地转动另一只手腕上的医院手环。
思索一番后,她问:“你会下棋吗?围棋。”
“只会一点点。”
她双手在空中比划一个方形:“那我就用围棋来比喻。比如你面前放着一个棋盘,它叫‘意识’。棋盘上有两种颜色的棋子,一黑一白,对不对?”
我点点头。
“我先问你:昨天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你还记得吗?”
“有些会记得,但肯定不可能都记得住啊!”
“你说得没错。意识就像有觉察能力的棋子,能觉知并且还记得住的,是白子;记不住的,是黑子。”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确认我听懂后才接着说:“同样,上辈子和下辈子的棋子也同时在棋盘上,能记住的是白子,记不住的是黑子。”
“我们怎么可能同时有上辈子和下辈子的记忆呢?”我耸了耸肩膀反问道。
“刚做完手术时,你不就想起自己认识护士了吗?”她笑着提醒我。
我惊讶地深吸一口气,好像在浓雾里划亮了一根火柴。
她又补充道:“既然你能看见上辈子的黑子,也有可能在某个时机下看见下辈子的黑子哦。”
“那不就是看见未来咯?”我恍然大悟。
“嗯,是的呢。你的理解力真好。”她雀跃起来。
听到一个年龄比我小的女孩称赞,我心里居然漾起一丝小学生听到老师表扬时的激动心情。
“上一辈子的意识和这辈子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你昨天认出护士,是意识刚好在中阴切换状态时看到上辈子的黑子。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的意识不是孤独存在的。”
她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清澈明亮。
“意识之间也有相互碰撞甚至交缠的时刻,甚至会多次相遇哦。你和护士的相遇就是一个例子,在这辈子的昨天你们又遇上了,你的意识恰好也认出她,只是她没认出你。”她替我感到遗憾。
一段急促的电子铃声从隔壁房传来。我们没有说话,仔细听着。不多久,门外传来由远到近的碎步声和护士护工的交谈声。
待外处声音渐弱,我问:“我能看见的是白子,也就是我拥有的意识只属于意识的可见部分,而且还有上辈子和下辈子那些现在看不见的黑子。那就是说,白子的数量比黑子少很多?”我好像逐渐理解她的逻辑了。
“是的,黑子是被封存的潜意识和不可见的意识,确实比白子多很多。可能是意识为了保护我们吧,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在维护内心的边界,才看不到黑子。”
“就像潜意识会封存一些伤痕记忆,为了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我感叹着点了点头。
“嗯,记得太多事情,会让人变得沉重……”她的睫毛垂了下来,眉头微颦。
天色渐白,晨光在冷暖光影间流转,这个时刻既像在做梦又真真切切。我愈发对这个早慧的女孩产生强烈的好奇。她在言辞间散发出年龄之上的通透智慧和松弛气息,似乎已经活过百年。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的手指颤抖了一下。
她犹豫了片刻,轻声说:“因为……我能看见所有黑子。”
“你能看见?”我激动地握住了拳,随后又觉得合乎情理。
“嗯,但不是每次都能看见全部。跟白子一样的,只有遇到跟它有关的事情,才会唤醒记忆。不过偶尔我会看到黑子自己冒出来。”
晨光揉合街灯的光晕轻抚着树叶的每一个小动作从窗外透进来,在天花板投下忽蓝忽黄的痕迹。
女孩翻了个身仰面躺着,目光跟随着天花板上的阴影流动起来。
我顺着她的目光方向看向树影,随后转过脸看着窗外摇曳的树枝。
“它们长什么样子?还是说像投屏播放?”我揣摩着黑子的各种形态。
她的声音几乎融进夜色,只剩气息在空气里律动:“怎么形容呢?那不是黑影,也不是白光,是两者叠加后留下的形。有点像……像……棋盘坍塌后留下的光锥。”
“它们有多大?”我希望更具体地想象它们的模样。
“没有固定,有的只有小小一个,有的就很大。”
“每个人都有?”
“嗯,不但人有,小猫小狗也有,所有东西都有。”
“所有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
“嗯,是的。”
“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有意识吗?”我挠挠头,没想明白。
“它们没有意识,但跟生物一样,同样由原子构成呀,只是在化学式上有不同的组合差别。在质量守恒过程中,反复被组合、拆解,也累积了大量的记忆和经历,只是我们听不见。”
她语速不快,我依然似懂非懂。
“现在,在这个房间,你能看到那些光锥吗?”我睁大眼环顾四周,真希望能看到一点点像锥形的痕迹。
“很可惜,现在看不到呢。”她看向我,依稀看到她的目光落到我身后那扇关着的窗户上。
她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在床的嘎吱作响声中坐了起来,蓝色条纹的病服松垮地包裹着瘦小的身体,像一团揉皱的单行簿稿纸。
她摸索到床头柜上的水杯,抿了一口:“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在两年前。当时跟几个朋友在白云山徒步。当我们经过水库时,原本干燥的大晴天不知什么时候聚集厚厚的云,不久后就下雨了。雨很密,像从天上落下一张巨大的帷幕。当雨把每一片叶子、每一寸山石都淋湿后,越来越多小光点出现在雨雾中,最终折射出一道道锥形的光。”
“你的朋友也看到了吗?”
“他们看不到,我也没告诉他们,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相信看不见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光锥就像排兵布阵的军团:在嫩叶上旋转,压低枯萎的荷叶;水面的小波浪、远处的山峰上,也都顶着各自的光锥;每颗雨滴上也悬着一颗,雨滴落下时拉扯成细线。”
她往杯子里倒水,发出清脆的水声。我似乎从中听到淅沥的雨声,想象她描述的光锥。
“它们漫山遍野,连万物都仿佛成为了它们的倒影。太美了。”她感叹。
“真羡慕你能看到它们。”我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能力。
她的神情变得忧伤:“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反而会经常感到孤独。别人看不到,你能看到,说出来别人只会把你当怪物,相信的可能会害怕。”
我不解:“有什么可害怕的?”
女孩低下了头,嘴角努力挤出一个平静的微笑,眼睛却没有笑意。
“随着它们出现的次数和场合多了,我逐渐摸索到一些规律。”
“什么规律?”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我的问题似乎滑进漫长的时空甬道,半晌才有回音。
“‘中阴’切换的规律。就像信号灯转换,它们其实一直在闪烁,只是因为闪烁的频率很高,所以看起来像一块固体。如果我在‘中阴’切换前用心注视着它,就能通过它闪烁的频率知道它将进入哪个中阴状态。”
她把杯子放回床头柜上,用一根手指慢慢拨弄着杯壁,让它原地打转。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非常专注,一分神就又要重来。所以一开始掌握这个技巧时很容易累,后来越来越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就容易看清了。”
我似乎懂她的意思了,试探性地问:“你能看到人会在什么时候死?”
她点点头。我倒吸一口气,察觉到自己手臂有几根汗毛立了起来,可马上又似乎感受一点点伤感。
“你会经常看吗?比如看自己的,看别人的?”我看着她手中的杯子转动时带动的光泽。
她的嘴角不再刻意上扬,眼神倒是流露出一丝真诚的笑意。
“一开始会的,还曾经尝试阻止我外婆的意识切换到‘死中阴’。不过后来就想开了,反正我们的意识始终还会再遇到的,何必执着手上的白子呢。”
天越来越亮了,云层稀薄地挂在远方,清冷的阳光穿过洁净的空气给每一栋建筑和每一条街道掸去睡意。房间里,我已经能看清墙上挂着的时钟,指针指向清晨的6点一刻。房间外走廊开始有人走动和说话的声音了,听起来像护士们在巡房。
女孩重新躺下,看了眼时钟,然后长长舒了一口气,小声地说:“能跟你再聊一次天,真好。”
我原本没在意这句话,过了几秒才听出里面不同寻常的意味。刚想张口问点什么,一个女护士开门推着一辆不锈钢的小推车进来。我认出是那个跟我喝过早茶的护士。
护士进来后看到我醒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昨天的胡话把她逗乐了,对我特别亲切和蔼,细心检查了我的刀口,引流管的出血状况,还有点滴瓶的速度还有尿量记录等等,然后给了我一个冒着雾气管子和口罩——做手术时做了气管插管,咽喉黏膜因此受刺激,会引起咳嗽——咽喉雾化治疗能缓和这些不适。我赶忙按照护士的嘱咐把口罩罩上。
护士料理完我的事情后转去女孩床边,同样麻利地做各种检查,然后女孩起身跟着护士往病房外走。
我瞪着眼看着她,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她。
女孩似乎读懂我的想法,转头对我嫣然一笑:“我现在要做手术前的准备了,医生给我安排了上午的手术。我们还会再见的,到时再聊吧。”
我点点头,跟她挥了挥手。她也轻快地给我挥了挥手。
她在我记忆中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她离开房间的那个娇小的背影,不一会就像雾一样消失在走廊尽头。
她没有再回到病房。
后来我听说,她那天的手术出了意外。没人告诉我细节,也许没人知道。只是那张床很快换上了新床单。
出院后,我回到以往的生活节奏,每天规律的工作和生活,周末跟朋友们聚会吃饭。 L仍旧偶尔约我出来,但不再约我去运动,而是去看比赛或者看展览之类休闲的活动,有一次他饶有趣味地端详着我说感觉我出院后性情变柔和,是不是在医院遇到什么事了。
我只对他笑了笑,并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跟他谈起这个女孩以及她跟我说的那些事。就如我和女孩说的那样,这些话题在成年后几乎不会再谈起。成年人只谈自己的工作消遣,只谈别人的生活感情,只谈公司的策略业绩,只谈国家的政策形势。
我只会在那些睡不着觉的深夜,静静地打开手提电脑。在网络中逐条搜索关于光锥的信息,可惜从来没找到过类似的词条和解释。
随着时间缓慢地流逝,每次回想起这段短短几小时经历,都会觉得很虚幻不实,怀疑是不是手术醒来前的一场特殊的梦。奇怪的是,我对她的记忆却愈发清晰和深刻,每当我想到她对意识、生命的理解,她能看到死亡的预兆,也许,她早就看见了那颗属于自己的黑子。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重新翻出小时候买的围棋。两手各抓起一把混在一起,握在掌心。窗外的日光正斜斜照进来,照在冰冰凉的棋子上,折射出点点锥形芒光。
我握着棋子,仿佛捏着我们的意识——那些交缠过的白子与黑子,或许正闪烁着,等待再次相遇。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