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穿越錄:行過兩界千山,皆有佳人回盼,第三章 落在雁坡村的「仙門弟子」

沈硯是被——安靜吵醒的。那是一種奇怪、陌生、不屬於新埔市的安靜——
沒有機車聲、沒有電線杆的嗡鳴、沒有吵架聲,也沒有樓上鄰居摔椅子的悶響。只有鳥鳴、晨風,還有柴火輕微的劈啪聲。
他睜開眼,看見昏黃木梁、粗糙土牆,再往旁邊一偏——竹格窗透進來的,是柔和而乾淨的晨光。
接著,他看到正彎腰換水的小小身影。
阿筠。
昨晚昏昏沉沉的時候,他其實就見過她的臉。
但那時意識模糊得像隔著一層霧,只記得一雙冷靜又溫柔的眼、一道帶著鄉野煙火氣的柔和聲音。
真正清醒後再看——他才第一次看清這個少女的模樣。
阿筠大概十五、六歲,身形纖細、線條柔和,像山野裡自然長成的竹枝。
眉眼清秀、乾淨,不帶一絲城市人那種長期壓力堆積出的焦躁。
睫毛很長,眼神明亮卻不刺人,帶著一種樸素而安穩的溫度。
她穿著洗得發白的麻布上衣,袖口補過幾針,卻被她收拾得整整齊齊;下身是一條草青色長裙,同樣乾淨清爽。
髮尾用麻繩隨意束成低馬尾,幾縷髮絲垂在頸側,被晨光照得柔軟。
她不是那種一眼驚豔的美人,卻是那種看久了會讓人心安的顏色——清綠、柔暖,又安靜。
和昨晚半夢半醒間看到的模糊影子相比——這才是真正的她。
阿筠發現他醒了,放下水盆,走近兩步,語氣很平常:
「你睡得還好嗎?現在感覺怎麼樣?」
沈硯喉嚨乾澀,聲音有些啞:「……這裡是?」
「雁坡村。」阿筠道,「你在村口倒著,是我弟先看到你的。」
——弟?
昨天那個抱著燈籠的小孩?
正想著,門外傳來兩下急促又裝大人的敲門聲。
阿筠抬頭,語氣溫和:「進來吧。」
門板被推開,一個瘦瘦的小男孩探頭進來——正是昨夜他在半昏迷中看到、提著小燈籠、站在木柵旁邊那個孩子。
阿樺一看到他真的醒著,小臉瞬間亮起來:
「你、你真的醒啦!姐姐還說你可能要睡很久的呢!」
阿筠帶著笑意替兩人正式介紹:「他是我弟弟,阿樺。」
阿樺立刻挺起胸膛,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小大人:
「我叫阿樺!昨天……就是我先看到你的!你拖著步伐、全身是血,我還以為你是……嗯……」
說到這裡,他偷偷瞄了姐姐一眼,縮了縮脖子,小聲補一句:
「……反正我被嚇到了,就趕快去喊我姐,還順便去拿桃木劍。」
說完自己也覺得有點丟臉,小耳朵悄悄紅了。
阿筠失笑,伸手揉了揉弟弟的頭髮:「別亂說,沈公子身體還虛著呢。」
她說話的語氣柔柔的,不是責怪,反而帶著安撫意味。
阿筠一邊把藥草鋪在簍裡晾,一邊問:「你……有沒有想起些什麼?」
沈硯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腦中閃過的畫面零碎得像被撕碎的膠片——
刺目的光、扭曲的金屬、狂暴的風壓、失重的墜落、矮樹叢、泥土和血味。
他揉了揉額角,聲音低啞:「我記得……很亮的光、很大的風……然後就掉下來了。其他的……真的想不起來。」
阿樺湊過來,小聲補一句:「你從靈舟掉下來的吧?村裡這幾天都在說那件事。」
沈硯愣了一下,抬頭看向姐弟兩人:
「……靈舟,是什麼?」
阿樺一臉「這也要問」的理所當然表情:「就是仙人搭的那種,會飛在天上的大東西啊!」
阿筠瞪了他一眼:「別亂講,我們又沒見過真正的仙人。」
嘴上這麼說,她還是低聲補了一句:「只是……老人們都說,靈舟是仙門弟子才能乘的。」
仙門?
仙人?
修仙?
這些曾只存在於小說、傳說、網文裡的詞,此刻硬生生砸進他的現實。
那艘他墜落的巨大金屬怪物……他到現在仍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可在村民口中,它竟然被稱作——「靈舟」。
如果這裡的人以為他是從靈舟掉下來的……
沈硯耳邊嗡的一聲,有種說不出的荒謬感。
阿筠和阿樺對視了一眼。
阿樺最先忍不住,小聲問:「那……哥哥你到底是不是仙門的人呀?」
沈硯怔住。
他心裡亂得像被翻過一整箱雜物。
陌生的世界、陌生的詞彙、陌生的常識——
什麼仙門、什麼靈舟,他根本毫無概念。
他張了張嘴,卻說不出肯定,也說不出否定。
最後,他低著頭,聲音帶著沙啞與迷茫:
「……我……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這句話是真話。
他真的不知道。
甚至連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都不明白。
然而——
阿筠的眼睛輕輕顫了一下。
阿樺倒吸一口氣:
「哇……原來是這樣……!」
兩人臉上的表情變得複雜——
有震驚、有敬畏、有惋惜,還摻著一點對陌生人的心疼。
阿筠咬了咬唇,輕聲道:
「難怪……你看起來那麼迷糊。」
她又補了一句:「靈舟墜落,你又從天上掉下來……記不得也很正常。」
阿樺猛點頭,像終於抓到關鍵:
「對啊對啊!肯定是受傷太重……所以忘記自己是哪個仙門的弟子了!」
沈硯:「……?」
等等。
等等等。
他什麼時候說過自己是仙門弟子了?
他甚至連「仙門」具體是啥都還沒搞清楚!
但阿樺語氣篤定得像在背課本:
「姐姐,靈舟可是仙人用的東西耶。
普通人怎麼可能坐那種東西?更不可能從那麼高摔下來還活著啊!」
阿筠點頭,語氣變得輕柔而堅定:
「你能活下來……想必是有道行保了你一命。
只是現在傷得重,才會記不清自己的來歷。」
沈硯:「…………」
他已經想不出任何吐槽的話了。
因為這對兄妹不是在開玩笑,
而是——真心這麼認為。
阿筠輕輕握住他的手腕,掌心溫暖:
「沈公子,你別著急。等你身體好些,也許記憶就會慢慢回來。」
阿樺拍了拍胸口,信誓旦旦:「村裡的人都會幫你的!仙門的哥哥才不會被丟著不管!」
沈硯感受到那雙柔軟的手,嘴唇動了動。
「我……不是……」
他想解釋。
可話才剛出口一半,就被阿筠溫柔打斷: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休息。」
她的語氣平靜卻不容反駁,「其他的……等你身子好些再說。」
阿樺也一臉「姐姐說得對」的表情跟著點頭:
「對!你現在腦袋肯定還昏著!」
沈硯:「………………」
他忽然有種非常清楚的感覺——
事情好像朝著一個很不得了的方向滑走了。
…
……
………
時間在茅屋裡過得特別慢,又特別模糊。就這樣又過了一天。
第二天清晨,陽光還沒完全爬上山頭,屋外已傳來村人的腳步聲與雞鳴。
沈硯靠坐在床頭,胸口還一抽一抽地疼,但頭比前一天清楚了許多。
他望著窗外的山坡、竹林、木柵,沉默了很久。
這裡——
沒有手機訊號。
沒有電線。
沒有柏油路。
村民燒柴、提井水。
衣著、用詞、作息,都像他曾在紀錄片裡看過的「古早山村」。
這一刻,他才真正開始接受一個看似荒謬,卻又幾乎不容他否認的事實:
自己很可能……穿越了。
「……這裡不是我原本的世界。」
他低聲喃喃。
更要命的是——他好像穿到了某種「修仙」存在的世界。
學生時代他也看過不少這類題材。
小說裡的仙門、靈根、飛劍、金丹,
民俗故事裡的修道求長生、山中有高人……
但那些,對他來說一直只是「故事」。
而現在——他整個人被塞進了一個,跟那些故事極其相似的地方。而且陰錯陽差,還被這對姊弟用力腦補塞了一個「仙門弟子」的身分。
偏偏他也根本反駁無力。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真相。
就在這時,門被輕輕推開。
阿筠端著一碗熱湯走了進來,步伐一如既往地安穩。她走到床邊,把湯碗放好,又習慣性地伸手搭上他的手腕:
「沈公子,你現在最重要的是休息。記憶……等你身子好些,自然會回來的。」
跟在她後面,阿樺這小子也屁顛屁顛跟進來湊熱鬧:
「對啊!仙門哥哥不要怕!」
沈硯低下頭,指尖微微顫抖。
——三天了。
算一算,從印章破裂、光芒吞噬、墜落昏迷,到現在醒來能下口喝湯,已經過了三天。
三天沒上班。
三天沒回家。
三天所有熟悉的一切,和他徹底失去聯繫。
他的呼吸忽然亂了。
手機還在公寓桌上嗎?
還是早就被房東當垃圾清了?
公司那邊……
是不是已經把他當成曠職解僱?
信用卡賬單、保險業績、月底的房租——
是不是已經全部炸開?
那些壓得他喘不過氣、每天逼著他咬牙活下去的現代壓力,
此刻卻像幾條死蛇,冰冷又噁心地纏住他的心口。
他那狹小潮濕的出租套房、那張沒鋪好還皺成一團的床、
那幾包最便宜的泡麵、桌上來不及吃的罐頭——
是不是已經成為亂七八糟的垃圾堆?
他記得房東常說:
「一個沒繳租金的打工仔,算哪門子房客?」
也許現在,他的東西早被粗暴地丟出門外,
扔進垃圾房、被別人撿走、或被雨水淋成一團爛泥。
而公司呢?
如果三天沒去上班——
以主管那種最愛抓人小辮子的性格,
解雇通知大概已經印好,只等他回去收件。
想到這裡,他胸口一陣窒悶。
不是因為捨不得那份工作、那間破房。
而是——
他的人生像被硬生生切斷,一切未完的事、未還的債、未消的焦慮……
全都變成了留在另一個世界、再也收不回的爛尾。
沈硯緩緩閉上眼。
阿筠誤以為他傷勢又發作,忙拿起一旁準備好的溫布,輕聲問:
「沈公子……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他沒有回答,只是深深吸了口氣。
當他再睜開眼時,瞳孔深處多了一層混著恐懼與茫然的濁光。
——我真的回不去了嗎。
這句話像一顆石頭,悄無聲息地沉到心底最深處。
偏偏就在這時——
阿樺忽然來了一句,把他僅存的一點心理防線也順手踹了一腳:
「反正哥哥你是仙門的人啦!等你恢復記憶,就會有人來接你了!」
沈硯:「……」
有人來「接」他?
如果真有那樣一群人出現——
他連仙門的規矩是什麼都不知道。
一句話說多了少了,說不定都會要命。
他喉嚨乾澀,艱難擠出一句:
「我……我真的不太記得了。」
阿筠輕輕點頭,那溫柔像一張細網,把他牢牢裹住:
「沒關係。我們會照顧你。等你想起來,再告訴我們也不遲。這陣子就先安心住在這裡吧。」
沈硯只覺得喉頭發緊,什麼都說不出。就因為這兩姊弟的隨意腦補,害得他現在陷入了一個非常尷尬的情況。
在他於阿筠家休養的這幾天裡,風聲便不知從哪一戶開始傳開。
最初只是窄巷中的兩名婦人,一邊挑水,一邊壓低聲音:
「聽說阿筠家救回一個從山裡掉下來的陌生人?」
「嗯……聽阿樺那孩子說,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天上?」
兩人對視一眼,臉上同時浮現驚疑。
其中一人又往前湊了些,聲音壓得更低:
「會不會就是前兩日那個……靈舟?」
那一句「靈舟」像火星落進乾草堆。
另一名婦人瞳孔一縮:
「你、你是說……仙門的——?」
「噓——小聲點!」
先開口的那人連忙四處看了看,確定附近沒人,才繼續壓著嗓子說:
「我家男人前天去山腳撿柴,說遠遠看見天上掉下一大團火……肯定是靈舟。」
「那……那孩子救回來的那個人……?」
「十有八九,就是從靈舟上掉下來的。」
雁坡村不大,消息傳得比山風還快。
不到半天,村頭織草鞋的老人知道了;
在河邊洗衣服的姑娘知道了;
甚至連在樹上抓鳥蛋的小孩,都知道了。
到了第三天黃昏——
整個雁坡村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一件事:
「阿筠家住了一名從靈舟掉下來、重傷又失憶的仙門弟子。」
有些村民心生敬畏,遠遠望著阿筠家的屋頂,不敢靠近。
有些則滿是好奇,悄悄躲在柵欄後討論他的模樣。
還有老人搖著頭,感嘆:
「仙門弟子……落到咱們這種小山村……」
「這是有劫啊,仙門的事,咱們可管不了。」
另一名老人則捻著鬍子,慢悠悠地說:
「若真是仙門人,留在雁坡,對咱們也算是一樁好事。
說不定……能帶咱們村走走運呢。」
而孩子們最直接,圍在一起興奮亂講:
「他一定會飛!」
「我娘說仙門的人都能劈雷!」
「我想看他施法!」
「笨蛋,他失憶啦!」
「失憶了會不會突然變壞?」
「不會啦!姐姐說他溫柔得很!」
——議論聲此起彼落。
…
……
………
屋內。
沈硯坐在床邊,背靠著牆,聽著屋外時不時傳進來的壓低談話聲與腳步。
他聽不清具體在說什麼,
但不用想也知道——
那些聲音,說的都是他。
阿筠端著藥碗走進來,見他眉頭緊皺,微微蹙眉:
「……外頭的人又來偷看了吧?」
她語氣有點無奈,卻依舊柔和:
「別理他們。村裡傳話快,你又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大家自然會好奇。」
沈硯抬起頭,喉嚨有點乾:
「他們……都在說什麼?」
阿筠想了想,沒有選擇欺瞞,坦坦蕩蕩地說:
「說你是仙門弟子。」
沈硯:「……」
阿筠又將聲音壓低了些,補充:
「還說你受了重傷……可能連自己是哪個門派的,都一時想不起來了。」
沈硯額角抽了一下:
「我是……想不起來沒錯……」
「我知道。」
阿筠輕聲打斷,眼神裡是認真而溫柔的理解。
她把藥碗放到他手邊:
「不過,能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還活著……
也只有仙門弟子做得到吧。」
——這句話,像一根細針,無聲無息地刺進沈硯胸口。
他不知道該怎麼反駁。
因為連他自己都不明白:
為什麼那樣恐怖的高度、那樣離譜的墜落,他竟然還活著?
阿筠垂下眼,語氣柔得像春風拂過:
「你先把身子養好。其他的事……不急。」
她伸手,輕輕把藥碗往他面前推近了一些:
「等你想起來了,再告訴我們。」
就在這時,屋外突然傳來幾個孩子跑過去的腳步聲,伴隨著壓不住的興奮:
「快點快點!仙門哥哥吃藥了!」
「看到了嗎?那碗就是仙門喝的藥!」
「你小聲點!被仙門哥哥聽到會羞死!」
沈硯手一抖,湯面跟著晃了一圈,胃口瞬間消失了一半。
阿筠忍不住失笑,搖搖頭:
「孩子們……口沒遮攔,你別放在心上。」
可對沈硯來說,這幾句不經意的童言童語,卻像把整件事釘了最後一根釘子——
——仙門弟子。
——失憶。
——從靈舟墜落。
謠言之外的人越是篤信不疑,
身在謠言中央的他,就越無處可逃。他垂下眼,指節在碗沿微微收緊。
…
……
………
屋外的童聲逐漸遠去,只剩風穿過竹葉的沙沙聲。
沈硯低著頭,指節在碗沿上微微發白。他還在消化「仙門弟子」「失憶」「靈舟墜落」這一整串莫名其妙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
正覺得胸口越來越悶的時候——
砰——!
院門像是被人一把推開,撞在牆上發出一聲巨響。
緊接著,是急促得有些發顫的腳步聲,幾乎是用「衝」的,從泥地一路踩到門前。
「阿筠!阿筠——!」
一個粗啞的男人聲音在屋外炸開,帶著明顯的慌亂。
阿筠眉頭一皺,把還未端走的空碗放下,快步走出去:
「梁叔?怎麼了?」
門板被人猛地推開,獵戶梁叔滿頭大汗地站在門口,臉上帶著她從未見過的凝重。他的目光在屋內一掃,很快落到床邊的沈硯身上。
那一瞬間,他眼底閃過一絲複雜的光——像是遲疑,又像是抱著最後一線希望。
「阿筠,」梁叔壓著嗓音,還是止不住喘氣,「村長叫我來請人。」
阿筠愣了一下:「請誰?」
梁叔看了她一眼,又看向沈硯,像是做了一個不容易的決定,咬牙道:
「請——仙門的沈公子。」
屋內的空氣微微一凝。
沈硯心臟重重一跳,那個他最不想碰到的情況還是來了。
還來不及開口,梁叔已經跨進半步,朝他拱手,粗聲粗氣卻滿是焦急:
「沈公子,還請……還請你一定得出來看看!」
他努力把態度壓得恭敬,卻怎麼也按不住聲音裡的慌亂:
「村裡出了點不對勁的事,大家都說,這種情形……也只有仙門的人,才弄得明白。」
他深吸一口氣,像是怕被拒絕,又像是怕浪費一瞬間:
「不管你記不記得自己是從哪個門派來的,只要你還願意出個聲、走一趟——」
梁叔的拳頭在身側緊緊握起來,指節泛白。
「——這回,雁坡村全得靠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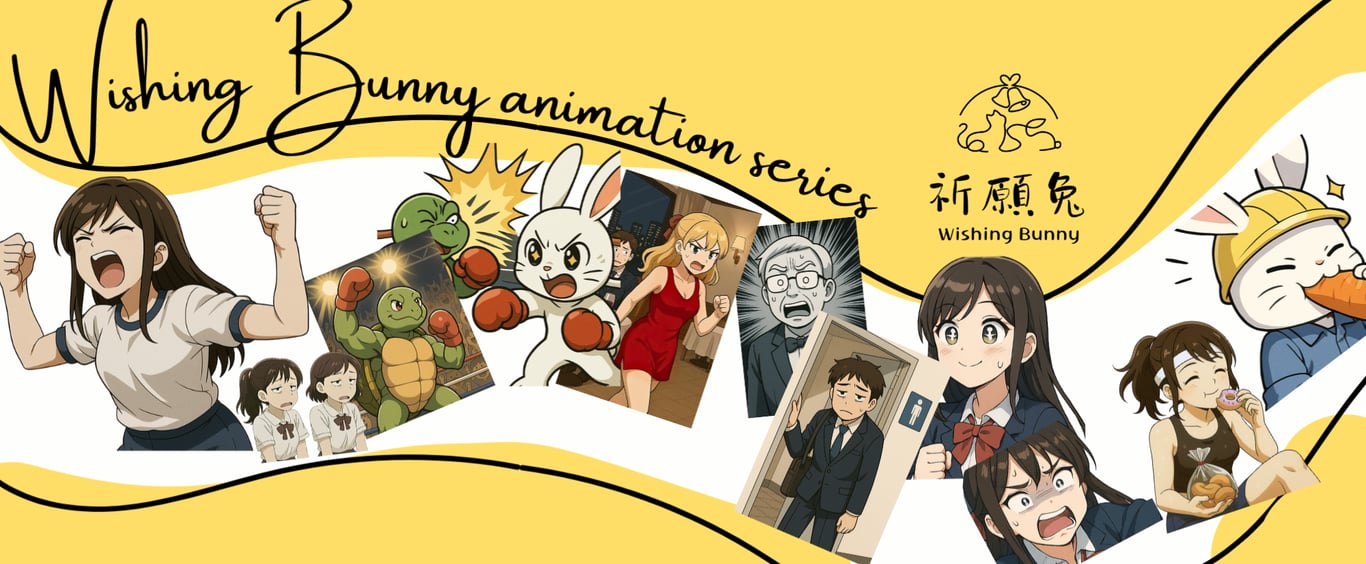
祈願兔商場:shopee.tw/ayasuzu827
祈願兔YT:www.youtube.com/@wis...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