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在英港人:艰辛起步,重建公民社会

撰文 傅晨 丢替
编辑 于长夜
平台编辑 覃山
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共超过万人被捕,当中截至今年7月底,超过七千名被告仍未结案。当年选择抗争的香港年轻人,有一大部分不是被囚禁在监狱,就是已离开香港,英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地。
英国于2020年起推出“救生艇”计划,允许在1997年回归前在香港出生、曾经或继续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简称BN(O)护照] 人士,可以通过申请BN(O)签证移居当地,因而成为港人移民的热门国家之一。根据英国内政部今年11月公布的数据,自计划开始,已累计批出21.6万例签证申请。

资深社运人士林正轩,属于最早一批搭乘“救生艇”的移英港人。他曾经见证过香港社运界的黄金年代,如今的他不得不向过去诀别,在伦敦从零开始,转行当了专业灭虫人士。
成立支援港人的海外社运组织“细叶榕人道支援基金”服务中心(下称“细叶榕”)的阿政,因为有被捕风险,只身前往英国,期望将反修例运动后激起的香港人身份认同传承下去。除了举办教育活动、给香港在囚人士家庭发放补助金,“细叶榕”还设立了面向大学生的奖学金,“旨在促进民主人权发展和香港文化传承,持续栽培年轻世代对振兴香港自由民主价值的使命感”。
在“细叶榕”的活动中心,我见到了20多岁的情侣煲儿(Bowie)跟阿星。逃离香港时,阿星因不满足BNO资格,不得不申请政治庇护。如今等待审批期已经近三年,阿星的身份没有着落,没有在英国工作的资格,就在细叶榕义务帮忙,以期帮助更多身处危急的港人。阿星说,他也并不十分焦虑,对他来说,在英国至少不用担心随时有人上门拘捕。煲儿有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她为了随阿星逃离香港,不得不中断学业,如今她只能靠自由职业维持生计。
他们怀着对香港局势的失望离开,出发的激烈决心犹如石子落水后激起的浪花。但抵达彼岸的激动消退后,他们还要面对离散后的漫长人生,后怕与恐惧逐渐涌出,摧毁他们的安全感,激起自我怀疑。他们对逝去的故土充满哀悼,对深陷牢狱的故友饱含身为幸存者的愧疚,在这些情绪的重压下,他们还要爬起来,活下去,在异乡重建身份认同。
在难民与国民之间
11月21日,我来到曼城,推开“细叶榕”的大门,那是一块不足20平米的空间,在一个社区艺术中心里的小区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煲儿,她穿着浅灰色的宽厚大衣,双手提满了大袋小袋的物品,显得有些狼狈。男朋友阿星高大一些,穿着薄薄的蓝色圆领卫衣,长发扎在脑后。

跟我见面这天,煲儿跟阿星罕见地叫了外卖。阿星的政治庇护签证还未获批,尚属黑户,还不能打工,两人的收入主要靠有合法签证的煲儿。叫外卖的消费标准是什么呢?掌管“财政大权”的煲儿说,主要根据今天银行账户的余额来决定。

平时两人点外卖,大多是在替“细叶榕”筹办长时间活动时,用公款为出席的志工安排餐饮。这次他们自费点餐,各自点了一个主菜:韩式牛肉、泡菜猪肉,再加粉丝跟饮料,平均每人大概花不到15英镑,以当地物价来说,算合理消费。想再省一点,就不点饮料,只喝水。
26岁的煲儿比男友小2岁,总是安静地忙前忙后。与大多数20多岁的香港青年一样,煲儿和阿星的政治启蒙来自于10年前的雨伞运动。彼时还是青少年的他们,被120万人参与的“要求‘真普选’”示威运动的热情感染。 阿星说,当时尽管他只有16岁,但对于“真普选”和“港人治港”还是会有一定的认知。雨伞运动宛如种子,令他心里萌生“站出来”的萌芽。这令他在2019年,与煲儿一同在6月12日加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下称“反修例”运动)示威,阻止香港立法会恢复草案二读辩论。

本来平和的示威,在警方不对等的暴力镇压下变得激烈。阿星成为上万被捕者之一。当时两人都还没有大学毕业。阿星被捕之后,煲儿本打算留港继续完成学业,以等待阿星服刑完毕。2021年,阿星获得无罪释放后,因担心律政司会上诉,她决心牺牲学业,与阿星一同离港。二人带着问朋友借来、仅有的两万块港币,买了机票前往英国。
被迫离开香港时,阿星和煲儿都尚未完成自己五年的大学课程。他们的专业分别是教育和艺术教育。2022年,刚到英国几个月的阿星,循着街坊议论的“教育奖学金”联系了“细叶榕”。“本来是想帮煲儿申请奖学金,能让她在英国继续学业,没想到创始人阿政在招募义工”,阿星说,他因此与阿政结识,并凭借自身此前在香港的社区工作经验和教育专业的背景,成为无薪的工作人员。

“细叶榕”于2021年10月1日在英国成立,成立初期的名称为“细叶榕在囚及更新人士支援基金”,专门为“反修例”运动被捕或在囚人士及其家属提供人道紧急经济支援。阿星回忆,两年前他刚到“细叶榕”帮忙时,组织援助的个案只有十几个人,如今已经累积到400多人。包括创始人阿政和阿星,整个组织只有四名常驻的工作人员,本来根据阿政的设想,其余三人皆有分工,比如有人负责管理捐款,有人负责跟进个案,而阿星最初被招募则是负责奖学金的发放。但如今随着需要援助的个案激增,四个人日夜连轴转,很多时候仍然需要互相补位。如今阿星还要去社区给孩子们上课,联系举办活动,布置场地,也要亲力亲为为临时帮忙的志愿者订外卖。
今年11月21日是“细叶榕”在曼彻斯特中心办公室启用的时间。前一天的11月20日,煲儿和阿星两人刚从跨城举办的活动回到曼城,就连夜留在中心整理物资、摆放家俬、布置置物架,直到21日天亮才回到住处。11月21日下午见面时,阿星热情地向我介绍中心布置:有港人捐赠的沙发,置物架上有义卖的杂志、纪念品,还有即将发售的“细叶榕”月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抬起头看到,天花板有一处凹凸不平,水泥层层剥落,他说之前漏水了,需要维修,中心因而获得一个月租金减免。

作为等待政治庇护批准的难民,阿星不符合资格与机构签署工作合同,因此他在“细叶榕”的身份只能算“义工”。他把“细叶榕”当事业的寄托,全力负责举办社区活动、教育及文化发展工作;煲儿平时靠做自由工作者赚钱,接一些与画画、设计相关的工作。
抵英两年来,煲儿和阿星的生活逐渐跟曼城有了连结。不同于其他港人通过“救生艇”计划,暂将英国当做中转站,煲儿和阿星两人期望将来在英国获得永居资格与入籍。入籍意味着有了英国国民身份,两位年轻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们要为新的国家做贡献,但这也不等于彻底舍弃香港。
他们失去了随时回家的权利,但思念过往的情绪总是涌动。自己究竟是香港人,还是英国人?这是在英港人普遍都会遇到的纠结。阿星提出了一种中间状态,即通过区分为法理上跟自我身份定义,成为“英国香港裔”的可能性。 但煲儿则想摒弃宏大的国家观念,倾向于以居住社区安放自身的归属感。不用工作的时候,她主要的业余时间都给了乒乓球。 “我的身份认同是曼城不是英国,例如我晚一点会去打球,我会说我是曼城的乒乓球人,又或者我是曼城的艺术家”,她微笑起来。
煲儿第一次觉得自己是新社区的一份子,是到2022年9月,那时她加入了本地的乒乓球球会。她一共参加了两个球会,一个是香港人举办的,另一个是英国人举办的,但都包括了不同国籍的球员。球会每星期都有比赛,她有时间就去小学校园的球场里练习。有一次聚餐,一个英国叔叔问她和另一个香港人为何离开香港,他们两人同时间回答“forced to leave”(被迫离开)。球会里也有大陆移民,和英国人聊天时,总能轻松地表露“平时都会回中国”。这样的时刻提醒着煲儿,身为香港人的不同寻常的处境。
不过,当本地人听到香港人的回答,大部分都会展现出同情心。煲儿回忆,像问她问题的英国叔叔,就告诉她说,如果不想的话可以不用回答。“本地人问的问题可以很尖锐很直接,但他们的內心是很温柔的”。
大监狱与小监狱
在距离曼城东南约300多公里的伦敦,持BNO从香港移居到英国已经3年的林正轩已经有了趋于稳定的生活。我们会面在伦敦的初秋,一个工作日的下午2点,林正轩已经在伦敦市中心完成一天的灭虫工作。

林正轩个子瘦高,穿着衬衫,说话干练果断。“就算你们是中共统战部的人,只是见个面,你会抓我吗?那就见一下,反正我没有成本的。”
下午时分坐在咖啡厅,就像当地人悠闲地聊着天,这种松弛的状态,大概是林正轩以往全职投身社运期间无法做到的。林正轩曾为“民间人权阵线”(下称“民阵”)副召集人、前议员助理。他也是英国2020年“救生艇”计划推出以来,逾21万名已抵达英国的港人之一。

为了抗争要远走他乡,回想起来,林正轩说,一直以来无论是关注LGBT权益,还是2019年关注“警暴”(指香港警察对示威民众施暴),都是为了争取公义发声,比起其他人,自己的牺牲微不足道。 “我现在在这里也算有饭吃,也算有屋住,其实那些牺牲是很少的,与此同时我的旧老板(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坐牢,有些朋友2019年的时候自杀了,我对比他们的牺牲基本上是不能类比的,根本是九牛一毛。如果你后悔,那就是你没想清楚才做(参与社运与抗争)那件事。” 抛下一切选择离开,并不代表真正自由,“现在我走其实是(住进)另一种监狱,是一个小监狱和大监狱的分别,这个代价都是自己决定的 ”。
到了英国后,林正轩考取了专业执照,靠捉老鼠和灭虫赚钱养活自己。他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开了专门的账号,就叫“我在伦敦捉老鼠Catch Mouse in London”,偶尔分享自己的灭虫工作、日常生活趣事,如嘲笑身穿工作白袍的自己像防疫“大白”,还会分享获得公司全队最优秀员工的喜悦、点评餐厅的早餐。
不同的是,曾积极参与社运十多年的他,“捉老鼠”的专页仍会不时转发香港人或事的消息,包括“被消失”在公众视野很久的政治人物,或者近日的“47人案判刑”

落差感总是有的。对包括林正轩在内的大多数港人来说,移居英国后,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是首要困难。尽管是从香港社运界人物“滑落”到伦敦的工薪阶层,林正轩却说,他庆幸自己到英国后算是“适应得不错”。比起事业,更令他忍受不了的,是欧洲寒冬的长夜引起的情绪低落。 “四点就日落,第二天可能到八点才天亮……直到现在真的稳定下来,(气候)可能才是真正的考验。”
与“小粉红”交锋
脱离了香港温暖的土壤,林正轩感受到的寒冷不止来自气候,还来自于失去组织的支撑,只能以个人名义“单打独斗”地表达政治主张。在伦敦,他要一手包办展览,包括收集T-shirt、购买物资、安排运输、联络志愿者、布置场地等大小事务,要独自面对的可能还有发声的代价,尽管他认为自己已比昔日低调许多。
抵英后接受过访问的他,后来被立场亲共的网媒攻击他抹黑香港, “在抖音里剪到我好惨(难堪)”。而今年年初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被爆出雇用间谍跟踪在英流亡人士,也引发了在香港异议人士群体的关注。但比起在举办现场活动时被暴力对待,被间谍跟踪只能算程度较轻微的骚扰。

林在香港时已经习惯了被骚扰恐吓。 “以前我们就算最简单去摆个街站(指一般为表达组织立场,呼吁民众关注某政治民生事件而在街头摆设的临时摊位),一样有对面的人来拍照,骂你两句,甚至是推你桌子的东西、恐吓说想动你、想打你。”他说,面对这些因为暴露在街头而随时可能遭受暴力的风险,唯有躺平。“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去保护自己” ,林正轩说,“难道去习武吗?哈哈”。
在英华人政治光谱复杂,煲儿和阿星也深有体会。“细叶榕”扎根的曼彻斯特区域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总计人口有280万,是港人及其他华人聚居的热门地。土黃色磚瓦的建筑上,会发现掛上紅底白字或白底紅字招牌的中式餐館,招牌上的中文甚至比英文更显眼。不用特别靠近唐人街,走在市中心,自然就会听到普通话或广东话。阿星在参加政治性活动时,发现许多港人倾向低调,移民后不愿谈论政治。

阿星认为,或许有部分人还在适应期,尚未脱离对白色恐怖的恐惧,因而会自我审查,或在政治表态上造成分歧。对待这些人,需要有同理心去互相体谅。 “如果我们要走独裁那套,要求别人一定要选(抗争)这件事才是正确的,我们跟他们(独裁者)有什么分别呢?”
一直存在的中港矛盾也延伸到海外。 2022年,在英港人团体在中国驻曼城领事馆附近示威期间,被一些来自大陆的华人殴打。但跟真正住在当地的大陆人相处下来,阿星也认为各有不同。他说有认识到可以聊天,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遇到对政治活动反感、甚至鄙视香港的“小粉红”。

2023年6月11日,阿星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頓(Southampton)出席纪念2019年香港“反修例”集会的时候,遭到一名白衣男子的骚扰,那位男子用英语说“香港是中国的”(Hong Kong is China),又用普通话问他们听不听得懂,还破坏了贴上香港人打气便利贴的连侬墙(Lennon Wall,指粘贴民主标语等讯息的海报拼接墙)。那名白衣男子还举起中国国旗,对香港集会者恶语相向,持续十几分钟,而在集会结束后,多名香港人还遭到一名可疑红衣男子的跟踪和袭击,受了轻伤。
“后来听说那个(红衣人)回中国了,但是过了一个月后又再回来英国,街坊认出了他,再报警抓他,最后警察还是把他放了,没事了” ,阿星说。当地警察称这是一起 “与仇恨相关的袭击”。
阿星还提到,今年“细叶榕”在曼城市中心举办年宵市集时,也有小粉红来破坏大会的连侬墙。“他(小粉红)的说法是‘只是撕一些我觉得不对的东西’。我们跟他说这是私人财物,加上其实我们连侬墙很欢迎任何人写下你的想法,拿了一张纸和笔给他,让他写下他觉得对的东西贴上去——我感觉我们的做法对这位“小粉红”来说,算是一种文化冲击。”

阿星说,在英国的香港人集会时,经常会被“小粉红”打断。 “我问他们,为什么大陆人可以到处说自己是上海人、四川人,为什么香港人不能直接说自己是香港人,一定要说中国香港人?他们就会说,‘这是应该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双重标准。”
除了“小粉红”,阿星也在集会中遇到过同情港人的大陆人,他对这些人的存在表示庆幸,“我们很感谢这些人,大家都是一起在极权下受苦,也很开心见到中国还有一些有正常思想的人。”
持BNO护照在英国念书的威廉,曾经积极参与大学的学运。他发现每逢抗争周年或六四等纪念日子各地都有集会,但在英港人不太热衷出席,可能基于有家人在香港,或者自己会回香港,所以不希望被发现在海外参与“表态”。

“对我来说这好像一个cycle(循环),运动热情退却了,大家回到原来的状态。但不代表未来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建设起一个强大的海外公民社会,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 ,威廉说,“我们要想的是,在重建抵抗的这段时间里,香港人如何熬过去,还有如何去装备自己”。
来不及告别
威廉曾因“反修例”运动短暂坐过牢。2023年底刚到英国时,隔着8小时的时差,他每每从新闻里看到正在坐牢的朋友的消息,那是他最想念香港的时候。

离去的人不少,但威廉仍有许多朋友无法获准离开。他们有人被限制离境,还有人因曾经入狱被取消专业资格,无法再当医护律师,又或者有人获释后想重回校园,但最终因收到投诉而被大学取消录取。他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没有资格说自己有过牺牲。
到了英国后,每年11月初的烟火节(Bonfire Night)是林正轩最难熬的日子。
三年前,他第一次在英国参加烟火节仪式。在抬头看到绽放烟花的夜空之前,林正轩满脑子都是突如其来、一下又一下爆炸的巨响。那些创伤的回忆来自于5年前,在2019年香港的街头,当警方施放催泪弹,烟雾弥漫。

采访期间正是“47人案”判决的日子,45人被判刑,当中法律学者戴耀廷被判刑10年,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判刑最重的被告。香港媒体《法庭线》将此案与“厦门聚会”的许志永、丁家喜的刑期比较,全部港人被告的最终刑期比他们低,但部分人比“709律师”的王全璋高。

“47人案”是港人决定离港的其中一大转折点。在2021年3月,林正轩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那时,香港政府继大规模拘捕47名组织及参加民主派初选人士后,便再传出要取缔“民阵”。因为担心自己可能在下一批的抓捕名单中,林正轩仅用不足一日便决定离港,“我当时是‘零认知’,因为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就收拾东西、买机票、做抗原检测、然后过来(英国),由入境再到‘家长屋’那里。”(“家长屋”是在紧急情况下为到达英国的香港人提供的临时住宿)。
“就是当飞机离开,轮胎收起,你就知道你会很长时间不能再回到香港。飞机上我旁边坐着很多大陆留学生在聊天,但因为不知道他们的立场,我也不知道同一程飞机上有没有像我这类(因政治避难远赴英国的)人,我就只能默默地躲在那里哭。 ”
煲儿和阿星也是被恐惧驱赶着,匆忙中断学业离开香港。“我们是用排除法的……我们选择不要坐牢,一起生活这条路,想要满足这个条件,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唯有的选择就是离开香港 ” ,煲儿说。
煲儿第一次离开亚洲,就已是移居到英国,但其实台湾一开始才是他们的首选。 “那时没有信心可以在一个我没去过的国家生活,想找个文化相近的亚洲城市。” 其后因为台湾封关,他们转到英国定居。
当时正值疫情,香港机场采取特别限制措施,前来送别的朋友,只能把他们送到距离机场最近的车站。要道别的还有住了二十多年的家,煲儿说最不舍的就是收拾房间的时候,亲手弄乱自己的房间,看着它逐渐变得空旷。
辗转到达英国前,比起未知的将来,煲儿和阿星更害怕在机场被截停,无法离境。“那种的恐惧就是,你不可以100%肯定这一刻你没有被人看着,相比之下,我对未知的恐惧不是那么大。”阿星说,现在他们不敢回去香港,为了缓解思乡之情,如今他们能想到的比较容易实现的计划,就是跟很多香港人一样,努力存钱到日本旅行。
传承香港公民意识
与煲儿和阿星想法一致,阿政也打算以后到日本旅居,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这个30岁不到的男人,正是“细叶榕”的创办人。我通过视频访问了他,荧幕中的他身处自己的卧室,正后方的窗帘拉开到一半,透出来的阳光折射在他背后。

需要工作时,卧室就是阿政的办公室,除非是机构有活动需要出席,他基本上足不出户。 “其实我没有在英国生活过,我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只跟香港人说话”,阿政毫不讳言地说,自己只是暂时停留在英国,去等下一个“转车”的地方。 “无论如何,你都是一个香港人,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香港人的特色” ,他想让下一代学习香港语言、喜欢香港,这也是他创办“细叶榕”的初衷。
“细叶榕”提出重视教育的理念,可能跟阿政上一份工作有些关系。他作为一个理科生,凭着对文学的热诚,被大学取录念了中国文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在“非主流”学校任教,教少数族裔学生。
直至他在“反修例”运动中被捕,学校不再与他续约。他失去工作,又面临国安约谈,在衡量风险后决定离港。他在离开之后,才发现原来香港很多地方他都没去过,譬如每逢秋冬都会有芒草盛放的大东山。
从香港跨越近一万公里来到地球北端,气候、饮食、交通、文化等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引来网上社交平台不时有港人抱怨,并讨论“回流时间线”(指回到香港)。阿政认为,“移民就像爱情一样不能勉强”,“唯一(支撑自己)的方法就是给自己希望,告诉自己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需要强行逼自己适应……”
寒暄过后,阿政开始细数近月工作:筹办活动收集民间捐款;举办文化、语言班;安排内部工作......他想做的仍然有很多, “问题是我没有资源,我知道怎么做,但我没有钱”。正如机构网页的“联络我们”一栏提到:“由于基金人手有限,可能需时数天才能回覆,敬请见谅”。
港区《国安法》落实之后,在港关注在囚人士权益的组织“石墙花”,选择结束运营。“细叶榕”被视为填补了支援服务空白的海外港人组织。机构为有需要的在囚人士家庭提供财政支援,经审批后,会向每个家庭发放每月380英镑的援助金,今年第二季受助个案有100多个。他指出,考虑到风险因素,部分人就算有需要也未必敢去申请,“现在(他们)的心理压力大成什么样?你点开那个(申请援助的)文本框也担心会被国安抓,如果你在香港就会明白了。过度惊慌之后你就会过度保护自己……(反过来看)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都会来申请的人,的确是很有需要的人。”

雨伞运动是阿政的政治启蒙,直至5年后他成为“勇武派”2。2021年到达英国后,最让阿政困惑的,是愿意投身社运的港人出现断层,他形容是“青黄不接”。“以前是一代接一代,有“本民前”(“本土民主前线”,属于本土派组织,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宣布解散)、“学生动源”(本土派学生组织,同样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宣布解散)之类的学生组织,但是你现在去到海外,是找不到(愿意投身社运的)下一代的。”
他认为这种断层导致公众过度寄望于比较知名的社运人士——这种现象并不可取。他又举例去年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宣布弃保,流亡至加拿大后,大家对她有很高期待,期望她会重投社运,“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她出来才有人做事呢?”

他担心香港公民意识下降,决定针对人道、教育、艺术和商业四个方向,希望能够填补现有的空隙,培养下一代香港年轻人。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香港成为minority(少数派),想在国际增加更多声量。
“并没有被彻底打败”
威廉的愿景是建立起强大的海外港人公民社会,但现实是,要争取香港议题再次受到关注,都并不容易。 “毕竟因为地缘的关系,英国比较多重点都放在中东,或者是乌克兰的议题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个关注东亚地区的人,在英国的就业空间并没有那么大。” 他要先寻找一个自己的位置。
“反修例”运动五年之后的今天,在英国邀访离散港人,被拒绝、没有回覆,都是预期之内。恐惧仍是普遍感受,作为邀约者,如何让他们感觉安全是最大考量。研究中国政治多年的学者曾锐生对记者表示,大部分离散英国的港人,为了避免被政权拘捕,只能专注于照顾自己、家人及朋友,并试图保护非政治的个人自由,意味着他们将会有更多的自我审查。但他认为,不应低估了香港人的韧性和企业家精神,“他们可能受到打击,但并没有被彻底打败”。
现在是需要韧性的时间。变为灭虫专业人士之后,林正轩不得不将过去全职的社运生涯转为“免费兼职”。他说自己仍未准备好投身于海外社运,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资源都没有准备好。他目前希望继续在当下的行业努力,未来或许能自组社会企业,聘请有需要的港人。
今年年中,林正轩用了4个月的业余时间筹备及完成了首个个人展览,展出香港民间团体在以往各种示威抗议中,特别印制的抗争口号T-shirt。回望整个展览,他认为意义在于让参观者重新回顾香港历来的抗议行动,从中反思在英国的抗争模式。此外,他也借此表达对昔日投身民主运动的战友与前辈们的尊敬,“我感觉大家都很喜欢看政治明星……其实很多事情是背后的人做的,才能打造出一个(社运)明星。”

“我最向往的仍然是在一个我很熟悉的香港,去教我想教的香港的下一代。” 抵达英国近3年后,阿星仍没有放弃成为教育者的梦想。当老师的念头来自阿星小时候的经历,他说,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他曾因沉迷电脑游戏而荒废学业,“就是有所谓的网瘾”。他回忆,初中一年级开始,有一个很好的社工开始陪伴他,教他如何在学业和游戏之间做平衡,这位社工成为了他的榜样,让他期盼自己能成为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人。
2019年,已在大学就读教育学的阿星,把决心实践在社运和行动上:“我想要做一个出去捡小孩(回家)的老师” ,他认为,在示威期间,老师们留在学校照顾学生固然重要,但他想付诸行动,成为一个榜样,“遇到不公不义的事要发声,要站出来,而且外面也有不少年纪更小的学生,我想如果可以我出去保护学生,或者呼唤理性和平的示威,这样可能起到的作用更大。 ”
如今“细叶榕”成为阿星实现理想的地方。他一手操办了许多社区活动,开设免费画班,从中向参与者传播香港人的传统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煲儿偶尔也会帮忙。 “教会学生懂得选择,希望他们会发声,希望他们做一个好人,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不要当看不到,你不要把香港变成‘小悦悦2.0’。”阿星所指的“小悦悦”事件,是2011年广东佛山一名女童发生车祸,而当时经过的17名路人没有施以援手,导致错过最佳救援时机。阿星说,在2019年上街的时候,他最害怕的是香港人变得冷漠,“像‘小悦悦’事件的那些路人一样,见到不公义的事情视而不见。”

隔着近万公里的距离,阿星在英国的小小努力或许很难再传递到香港的土地上。但他认为,即使离散在外,香港精神的火炬没有熄灭,仍有传承。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他在曼彻斯特教孩子们创作时,有一堂课是要求画“人链”(指人们手牵手站在街头和平示威),来自香港移民家庭的小朋友们一听到“人链”,就自动画出了2019年示威时,香港人和平抗争和抗议警察暴力的人链。下课后,有家长向他抱怨“为什么教孩子画这些东西?”他无比坦然地回答:“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
(本文采访对象除了林正轩之外均为昵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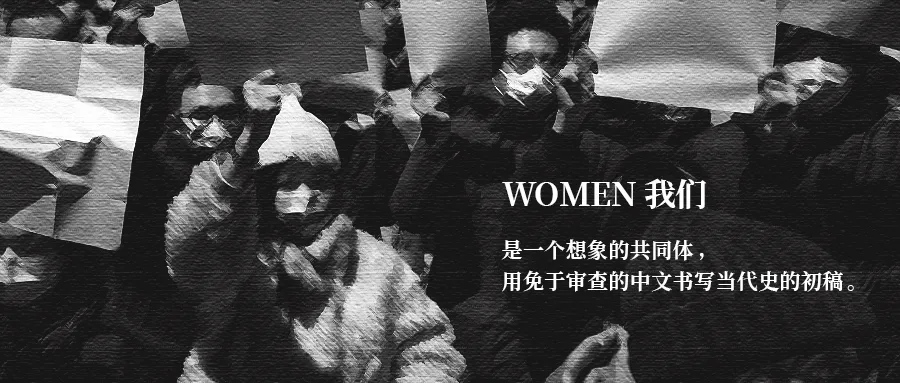
香港47人案,是香港2020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案参与者被指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这是自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警方发动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引起香港及国际媒体关注。审讯历时118天,31人认罪。2024年5月30日,法庭宣判,16名不认罪被告中李予信和刘伟聪罪脱,其余14名不认罪被告均罪成。2024年11月19日,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45名罪成被告入狱4年2月至10年不等。其中,以香港法学学者戴耀廷遭处10年监禁最多。
勇武派,是香港于2014年雨伞革命后,从非建制派中崛起的新兴政治派别,以其提倡包括暴力及直接挑战纪律部队执法等的激进手段争取普选的主张而著称,常与香港本土主义共生。
“WOMEN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用免于审查的中文书写当代史的初稿。欢迎您订阅我们,并帮助防火墙内的朋友邮件订阅我们;也欢迎您捐助和分享我们的文章。请联系[email protected],为报道提供线索或加入我们,成为撰稿人。我们会努力保证您的信息安全。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