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雷|游戏、商业、政治、阶级斗争与战争
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埃马纽埃尔·泰雷(Emmanuel Terray)
埃马纽埃尔·泰雷,1935年 – 2024年,法国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代表人物。早年出身贵族家庭,后来背离家庭,在考入高师后受到老师阿尔都塞影响而走向马克思主义。1961年以哲学专业从高师毕业后,他到达喀尔的法国驻军中服兵役,借这个机会,他得以实地研究了塞内加尔的工团主义,正是这一研究和人类学家乔治·巴兰迪耶(Georges Balandier)的影响,让他后来走向了人类学领域。他和克劳德·梅亚苏(著名哲学家甘丹·梅亚苏的父亲)一道在人类学领域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他还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家,曾因为同情科特迪瓦独立势力而被迫召回巴黎。他虽然在70年代早期加入过社会党,但是因为其毛派倾向,迅速退党,但仍然积极为维护移民、工人等被压迫群体的权益而奔走。他在80年代曾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究主任。(人物资料是在网上抄的)
本书是泰雷的克劳塞维茨论,因为其左翼背景以及探讨的议题比较有趣(新左派评论式托派会较为关注的议题),在此译出第三章,强行搞了一点马克思文本学,另外建议读一下佩里·安德森《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第一章和第四章。

第三章
游戏、商业、政治、阶级斗争与战争 Le jeu, le commerce, la politique,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a guerre
克劳塞维茨在为战争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并在精确界定其范畴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去探寻它与其他社会活动——如游戏、商业、政治——的相似之处。因此,战争一方面以其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被把握,另一方面又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集合之中,在其中,它如同一个“属”下的“种”。这种双重动态所产生的张力,也体现在经验层面:一方面,力量的狂暴宣泄与死亡幽灵的无处不在,使得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战争一旦爆发,日常秩序便被中断,生活仿佛陷入停滞,一个与此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新时期就此开启。自从无休止的地方性战争时代结束以来,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之间便存在一道清晰的界线,克劳塞维茨对此着力加以强调 (702, 673)。另一方面,就其引入的社会关系、运用的才能以及滋养的激情而言,战争又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有相似之处:我们不难对克劳塞维茨的列举加以补充,哪怕只是加上许多作者首推的“狩猎”。由此,我们又回到了战争确切边界的问题——一个在梳理战争隐喻时便已提出的问题。在重新审视此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这些类比做更深入的探索。
游戏与战争 Le jeu et la guerre
将游戏与战争相提并论的做法,在《战争论》(Vom Kriege)第一卷第一章中就已出现。作者援引了两大特征来证明此说法的合理性:其一,是对概率的估算在战争中所占的位置;其二,是在指导军事行动时所运用的智识与道德资源的性质。就第一个特征而言,它使得战争可以被比作一场纸牌游戏:
“因此我们看到,战争中那种绝对的、近乎数学的要素,从一开始就找不到任何可靠的依据来作为兵法计算的基础;其中即刻就混入了可能性与概率、好运与厄运的游戏,这个游戏贯穿于织成战争这张大网的每一根或粗或细的经纬线,并使得战争成为最像纸牌游戏的人类活动。” (65, 32)
至于战争所要求的能力,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到了勇气(der Mut)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果敢、对成功的信心、无畏、刚猛 (64-65; 32)。在“对概率的明智估算”这种智识才能与“勇气”这种道德德性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正因为战争只提供机遇,只提供一些不确定而脆弱的可能性,抓住它们才需要勇气。在分析1799年春奥地利军队在瑞士的战役时,克劳塞维茨批评卡尔大公不够有“赌性”:
“看到卡尔大公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说,他的指挥方式,至少在这次战役的这一阶段,缺乏那种善于利用有利时机的魄力。战争不纯粹是方法与手段的产物,它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因此,战争指导不能缺少这一要素,而对这种博弈没有足够偏好的将领,就会做得不够,并且会因未能取得战果而犯下比他自己所想的更大的罪过。” (1979: 409)
拿破仑的天才也是通过同样的类比来描述的:“以决定性的打击开局,并利用由此获得的优势发动新的打击,总是将赢得的赌注押在同一张牌上,直到庄家破产——这便是他的全部方法。可以说,他享誉世界的巨大成功,都归功于此。” (1987: 202)最后,卡尔大公和拿破仑的登场足以向我们表明,在战争的三位一体(trinitaire)定义中,正是其第二个要素——作为指挥特征的“灵魂的自由活动”——引发了与游戏的比较:“在充满概率和偶然的领域中,勇气和才智的发挥空间有多大,将取决于指挥官和军队的特性。” (69, 37)
借助赫伊津哈(Huizinga)、凯卢瓦(Caillois)以及更近一些的科拉·迪弗洛(Colas Duflo)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对克劳塞维茨初步建立的这种联系做进一步的推进。在《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中,赫伊津哈探究了游戏与战斗的关系,并在一番细致的语言学考察后,他总结道:
“我们不应草率地将用于指称严肃战斗的游戏性术语视为纯粹的诗学隐喻。我们有必要将自己置于一个原始的观念领域中去理解:在这一领域里,真刀真枪的严肃战斗,如同竞赛或竞技(agon)——其范围可从最无聊的游戏延伸至血腥致命的搏斗——与游戏本身一同,被归入一个基本范畴,即一种遵循规则、相互承担风险的机遇博弈。从这个角度看,将游戏性术语用于战斗,几乎算不上是一种有意识的隐喻。游戏即战斗,战斗即游戏¹。”
我认为这一论断颇具启发性:战斗与游戏一样,都是确定性(即规则)与不确定性(即机遇)不可分割的混合体。本着类似的思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游戏描述为一种催生事件的结构²;战争亦可作如是观。在游戏中,结构由一整套规则所赋予,这些规则界定了场地、器材、可能的行动以及需要达成的目标;在战争中,结构则源于地理、经济、历史和政治为军事行动所设下的种种约束。在前一种情况下,结构是自由选择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我一旦参与游戏,便意味着我接受了它们;在后一种情况下,结构是强加于我的,因为它取决于一个由事实构成的环境。但无论哪种情况,它都开启了一个充满多种可能行为的场域,而我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最终的结局将取决于我的决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取决于我根据对手的回应和局势的演变而必须做出的一系列连续决策。因此,结构催生了事件,但并非预先决定了它;在其核心深处,就包含着一道不确定性的裂隙。
由此,我们可以像区分游戏一样,在战争中也区分出“情境”(situation)与“进程”(process)。“情境”建立在竞争,即竞技(agon)的原则之上;对峙的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完全平等的关系³。在那些没有偶然因素的游戏中——如跳棋或国际象棋——初始的平等也并非完全,因为对弈的一方拥有“先行”之利:他走第一步。当偶然性介入时,它固然会造成一种开局的不对称性:发牌之后,有些人拿到“好牌”,有些人则只拿到烂牌;但从定义上说,在牌张分配的偶然性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⁴。就战争而言,不完全平等同样是常态,因为“战争需要双方才能打响”;诚然,战争中势均力敌的对手实属罕见;然而,如果弱势方不认为自己尽管处于劣势,却仍有可能——即便不能取胜,至少也能抵抗,那么它就不会拿起武器,而宁愿选择屈服;敌对行动的爆发本身就证明了双方都相信自己有获胜的可能。
从这种相对的平等出发,游戏和战争的目标都在于拉开差距,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列维-斯特劳斯说:“游戏呈现出一种分离性(disjonctif):它最终在个体玩家或阵营之间制造出一种差异化的差距,而他们在开局时本无高下之分。然而,在游戏结束时,他们将被区分为胜者与败者⁵。” 显而易见,此番论述完全可以逐字逐句地应用于战争。因此,这两种活动都遵循着一个被克劳塞维茨称为“两极性”(Polarität)的原则。两极性有两层含义:从广义上讲,当发生的不是对惰性物质的改造,而是“两个生命力的碰撞”(54, 20)时,“对阵的每一方都为另一方制定法则”(33, 19)。我的行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因此我无法完全主宰自己:我的行为无法被预先确定。但更确切地说,克劳塞维茨在“零和博弈”的格局形成时,称之为“真实的两极性”: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一方的优势意味着另一方对称且等量的劣势。克劳塞维茨接着指出,真实的两极性只在局部支配着战争;它支配着会战,因为“在一场会战中,双方都想获胜;这便是一种真实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会抵消另一方的胜利”(62; 28-29)。相反,战争的整体并不服从于它:例如,一方固守防御阵地,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就必然有兴趣采取进攻,其原因在于进攻方与防御方这两种“姿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不对称性,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谈。国际象棋的实践者深知,这一评论在何等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棋局。在此保留之下,相互作用仍是战争与游戏的一个本质特征,它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真实的亲缘关系,远超简单的相似。
同样,游戏的目的与战争的目的也可以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如前所述,在开局时,结构为对阵双方打开了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因此,每一方都拥有一系列可供自由选择的行为。于是,竞争便在这两种相互对抗的自由意志之间展开;一连串的招数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必须在它们之间制造出差距。因此,每一方的努力都旨在维持并扩大自身的行动自由,同时遏制并削弱对方的行动自由。能够自主决定其目标的一方,便是优势方;其行动完全为对方所迫、沦为只能招架其攻势的一方,则处于劣势。到了终局,一种自由意志——胜者的自由意志——坚守其存在,并扩张至主宰一切的境地;而另一种——败者的自由意志——则已荡然无存⁶。“将死”(échec et mat)与无条件投降指代的是同一种境况:从最初平等的两方,一方变得无所不能;而另一方面前,所有的大门都已逐一关闭,最终沦为一件毫无生气的物体。
当游戏或战争的进程结束时,最初的不确定性便消散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一开始就只是表象或幻觉。实际上,无论如何,它都与对手的相对平等相关,并且只有当他们之间的不平衡加剧时,它才会退去。迪弗洛(Duflo)很好地指出了,“游戏的使命在于制造不确定性⁷”;事实上,对于玩家和观众而言,游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其趣味;他补充说,游戏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旨在破坏我方行动的对方行动,另一方面,一旦规则为偶然性留出空间,也源于偶然性本身。另一方面,在前一章分析“摩擦”(friction)这一概念时,我已经阐明了克劳塞维茨在何种程度上将不确定性视为战争得以展开的环境或要素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且我们已经看到,其来源与迪弗洛就游戏所指出的来源并无二致。从不确定性的这一核心作用中,在我看来,可以得出两个互补的结论。
首先,游戏或战争活动的一个决定性部分是计算,是对概率与风险的评估,同时也是——借用迪弗洛引用的勒内·托姆(René Thom)的表述——对时局中各种潜在趋势的“诡诈的反思”⁸。实际上,之所以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因为这些趋势相互冲突,且它们之间的对抗胜负未分。此外,说到不确定性,就意味着表象与现实之间的混淆,意味着难以辨别何为海市蜃楼,何为实体。在竞争或冲突的情境中,可见之物总应被怀疑可能只是一个诱饵:这又是一个需要借助诡计(ruse)的理由。简言之,不确定性的挑战,只能通过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米提斯”(mètis)的才能来应对,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J.-P. Vernant)和马塞尔·德蒂安(M. Détienne)所描述的那样:即洞察力、机敏、审慎、灵活性、对时机的关注以及抓住机遇的迅捷。在此视角下,奥德修斯(Ulysse)成为了战争家的典范;而阿喀琉斯的勇猛,仅仅使他有资格参加战斗而已。
在我们承认计算应有地位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并强调其局限性。严肃对待游戏和战争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就是承认任何预先的计算都无法将其穷尽,或者换言之,可能性的领域无法被理性的预测所穷尽。人们可以争论这种无能为力的原因:可以将其归咎于所需计算量过于庞大,并因此视其为一种实践上的不可能;也可以援引发明与自由的无穷资源,它们能够挫败所有的排列组合。对我们的主旨而言,这样的辩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看到在计算与现实所承载的全部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实践中,要辨别出何时应当停止计算,因为再计算下去只会成为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的借口。如何填补这种预测中不可化约的赤字?在此,我们回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论述,也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并可以回答:通过勇气的介入。这里的勇气,不应被理解为面对可见危险时的身体上的英勇,而是在黑暗中做出决断、在问题仍被迷雾笼罩时就敢于下注的决断精神。克劳塞维维茨说:“决断,正是在统帅被不确定性包围时必须展现出来的性格特征。”(1979: 530) 迪弗洛所言并无二致,他强调了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最易于计算的游戏中,意志也依然无限地超越理智⁹。
诚然,我刚才所做的比较主要着眼于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被视为一种情境还是一种进程,游戏和战争都呈现出显著的同源性。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忘记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我再强调一下,游戏的结构是由被自由发明和接受的规则所提供的,而战争的结构则是由现实强加的;游戏的纯粹性(gratuité)因此与战争的严肃性形成对立。但我们应注意到,一旦规则被接受,并且只要它们被遵守,游戏的结构就和战争的结构一样具有强制性,因为玩家除非退出游戏,否则无法逃避规则。规则的概念引出了第二个区别。对于赫伊津哈而言,战争只有在遵守最低限度的、被共同遵守的规范时,才与游戏有相似之处;否则,剩下的就只有野蛮暴力的泛滥¹⁰。诚然,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种条件下,游戏与战争只不过是一系列连续的中间状态的两端,而肆无忌惮的暴力可被描述为“游戏的零度”。如果我们强调战争与游戏不同,是由暴力构成并被死亡所萦绕,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我并不否认这一双重特性赋予了战争独一无二的特异性,但在我看来,如果我在游戏世界内部为体育或狩猎也保留一席之地,我本可以更好地展示,各种不同等级的层次是如何让我们循序渐进地——即便不是不知不觉地——从游戏的愉悦过渡到战争的灾难的……
商业与战争 Le commerce et la guerre
在将战争定义为“一种通过流血来解决重大利益冲突的斗争”之后,克劳塞维茨继续写道:“与其将它比作任何一种艺术,不如将它比作商业,因为商业也是一种利益和人类活动的冲突。”(145; 112-113) 这并非一句孤立的、“顺便”提及的论述;除了这一总体上的类比,在《战争论》中,战争与商业还在两个更具体的方面被两度比较:首先,据称,战斗之于军事行动,就如同现金支付之于商业交易 (79, 48);此外,战争——如同商业——遵循一种总体化原则,该原则禁止局部的评估和过早的总结 (187-188; 155)。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这两个命题:我在此提及它们,只是为了表明,在克劳塞维茨眼中,商业作为一个比较对象,其重要性不亚于游戏。最后,商业与战争都被描述为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登场表明,此刻被讨论的,是战争的三位一体定义中的第三个要素——政府及其目标。
在克劳塞维茨写作的年代,将商业与战争联系起来或许会令人惊讶,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一段历史中来理解。粗略来看,商业被视为两个独立方之间的关系,每一方都试图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是截然对立的:在市场上,买方想廉价购入,卖方想高价售出;价格是妥协的结果;根据价格的高低,买方或卖方占得优势。根据这种只考虑孤立交易的方法,商业确实呈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对买方有利的因素——如供给充裕、市场透明——便对卖方不利,反之亦然。而我们已在游戏的情境中看到:零和博弈的模型必然会引出与战争的类比,因为它必然意味着利益和目的的矛盾;一旦人们将其作为思考商业的首选工具,商业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就变得不可避免,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正是17世纪重商主义思想所发生的情况:正如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醒的:“柯尔贝尔(Colbert)将商业视为一场永恒的战斗,而乔赛亚·柴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则视其为一种战争形式¹¹。”
但恰恰是18世纪,似乎与这种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决裂:此后被强调的是战争与商业的对立;这两种活动是相互对抗的,因为它们运用的是截然相反的德性。例如,我们来听听孟德斯鸠的看法:“商业精神必然伴随着节俭、经济、克制、勤劳、审慎、安宁、秩序和规范的精神¹²。” 因此,“商业可以消除毁灭性的偏见,而且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凡是有温良风俗的地方,便有商业;凡是有商业的地方,便有温良的风俗¹³。” 总而言之,“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导向和平¹⁴。” 相反,商业的缺失则会滋生盗匪行径。然而,柯尔贝尔与孟德斯鸠之间的对立,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小:实际上,在《论法的精神》中,商业被视为一种文明的产物,其影响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评估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它催生了和平。但孟德斯鸠似乎也愿意承认,如果我们将视线降至个体交易的层面,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商业精神联合了民族,但它并不同样地联合个人¹⁵。” 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商业的驱动力依然是贪婪和对利益的渴望;就其本身而言,它仍然与征服、盗匪和掠夺有亲缘关系,而孟德斯鸠也承认,这些行为归根结底也只不过是“获取财富的方式¹⁶”。简言之,商业的两幅肖像——作为战争的煽动者和作为和平的缔造者——可以同时为真:存在于每笔交易中的紧张与对抗因素,一旦我们考察整个社会,便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和中和了,因为在社会整体中,商业的普及反而有利于和平。顺便一提,这真是对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所钟爱的“私恶即公益”(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绝佳诠释……
邦雅曼·贡斯当的功绩,则在于将这两个方面——和平的一面与好战的一面——置于一段历史之中,从而既解释了它们的对立,也解释了它们的关联;我们必须全文引述这段非凡的文字:
“战争与商业,不过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两种不同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占有自己渴望之物。商业无非是占有的欲求者向占有者的实力所表达的一种敬意。这是一种试图通过双方同意的方式,来获得人们已不再指望通过暴力去征服的东西。一个永远是最强者的人,绝不会产生商业的念头。正是经验,向他证明了战争——即运用自身力量对抗他人力量——会遭遇各种抵抗和各种失败,才促使他诉诸商业,即一种更温和、更可靠的方式,去引导他人的利益来同意符合自身利益之事……
“因此,战争先于商业。前者是野蛮的冲动,后者是文明的算计。显而易见,商业的趋势越占主导,好战的趋势就必定越衰弱¹⁷。”
因此,如果说商业与战争相互对立,那它们就像一对同母所而生的兄弟——尽管彼此敌对,却依然有着共同的起源……
如果我们将“商业”的概念替换为“竞争”,我们便会逐一重现那些我们已确认的、为游戏和战争所共有的特征。在竞争中,市场上对峙的是自由且独立的参与者: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卖或不卖,买或不买,以何种价格交易;他们相互独立,因为没有任何支配或从属关系将他们联系起来;他们拥有的资源无疑不尽相同,但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至少在形式上,他们是平等的。在现实中,这种平等总是相对的;无论是在个体交易中,还是在竞争的全局领域,这一点都得到了验证。在前者中,参与者之间的完全平等需要供需之间严格的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从未达到,除非是作为一段长时期内的平均值。价格之所以不断波动,正是因为供需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久的不对称,时而对一方有利,时而对另一方有利;在任何时刻,总有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另一方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不对称性可以与战争中防御与进攻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诚然,在战场上,不平衡总是对防御方有利,但在一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战争中,对阵双方往往轮流扮演防御者和进攻者的角色,因此最终会达到一个等效的结果:商业伙伴和军事对手从未处于实际平等的境况;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一种差距,哪怕极其微小,对其中一方有利。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竞争的全局领域:在企业家之间的竞赛中,优势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而一项新优势的引入——一项技术创新的出现,一个此前封闭的市场的开放——并不会同时且均等地惠及所有人;在任何时刻,总有一些人掌握主动,另一些人则处于被动;一些人处于攻势,另一些人则处于守势。
在商业与竞争的舞台上,所有参与者都努力增加自己的收益。众所周知,在增长时期,只要我们只考虑绝对数量,他们可以共同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方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的退步,因为“生意”的总量在增加。但增长也有黯淡之时,而长期的安全则要求采用另一种评估标准:即“市场份额”的分配,而不论市场规模本身的变化。然而,一旦企业家将扩大市场份额定为目标,我们便又回到了零和博弈的格局:他只能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来达到目的。此外,很明显,在对峙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两极性原则;每一方都受制于另一方,因为他的决策取决于他对另一方意图的揣测,或是另一方的主动行为。例如,如果一方决定大幅降价,其他人很快就会被迫跟进,否则他们的地位就会崩溃:一种真实的依赖性因此平衡了形式上的独立性;然而,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参与者最初的平等因此得以维持。
如同战争和游戏一样,竞争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展开,其原因也相同。多个自主决策中心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的第一个来源。每个参与者都竭力对其资源和计划保守最严格的秘密:在竞争中,如同在战场上,出其不意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每个人都致力于挫败他人的预测,甚至在必要时采取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在此,协议(entente)作为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特权工具介入,但它恰恰是对竞争本身的否定,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不确定性与竞争是何等地密不可分。此外,偶然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式是各种事件——气象灾害、科技发现、社会与政治危机——这些事件严重影响着竞争的进程,尽管它们发生在竞争之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并遵循着与竞争法则大相径庭的规律。参与者几乎无法预见这些事件,更不用说对它们施加影响了:用纸牌游戏的语言来说,它们属于“发牌”,是玩家必须承受并适应的。
长远来看,竞争者之间的差距有时趋于消失,但有时一个累积过程也会启动;差距不断扩大,变得不可逆转、不可逾越;最终,我们见证了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毁灭。换言之,任其自然发展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中,即弱者的消失:他们要么被淘汰,要么放弃自主权,被更强大的对手吞并。从这个角度看——请原谅此言之平庸——竞争类似于生存斗争;在其中,必然关乎生死,而死亡的定义与游戏中一样,即“出局”。
战争与商业:它们的关联在时间的迷雾中早已难寻踪迹。与其看向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不如让我们转向古代中国,那个战国时代:“战争与商业,”让·莱维(Jean Levi)写道,“是深刻影响中国、并在公元前六至三世纪间引发其历史上最剧烈变革的两种现实。这两种活动密不可分。如果说,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极像一场商业行动,那么在中国的商业则酷似一场军事行动。它们都需要同样周密的准备,同样的企业家精神,同样对有利时机的选择,同样对适宜环境的等待,同样果决的决策,同样迅速的执行,同样精于算计和规划的狡黠精神¹⁸。” 由此,我们最终又回到了一个与古希腊“米提斯”极为相似的德性:“战争与商业,”列维又说,“共同签署了一种狡黠智慧的诞生证明,其特征是眼光与行动的迅捷,以及思维的敏捷,其领域涵盖一切不稳定、变动、流转之物¹⁹。” 于是,奥德修斯和他的中国表亲又一次登上了舞台的中心。
政治与战争 La politique et la guerre
诚然,如雷蒙·阿隆所言,克劳塞维茨并不允许将其著名的公式颠倒过来,并因此拒绝将政治描述为战争的延续或工具,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公式——即便以克劳塞维茨所赋予它的形式——本身就蕴含了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连续性的假设。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的特殊性在于诉诸一种特殊手段,即武装暴力,以及这一手段所带来的主要后果,即战争所浸淫其中的那个独特“环境”的形成。但手段只是行动的诸多方面之一。行动本身,也预设了一个它在其中展开的场域或舞台、一些承载着理智与意志的行动者,以及这些行动者所追求的目标。尽管战争运用的手段具有独特性,但如果说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连续性,那正是因为,在这两者中,场域、行动者和目标是相同的。这便是为何克劳塞维茨在将战争比作商业之后,能够写道:“它更像是政治,而政治反过来,至少在部分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大规模的商业。”(145, 113) 因此,我们尚未结束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因为现在需要阐明的,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政治”一词有多种含义,根据我们所采纳的含义,战争与政治相似的论点,其显见程度也会有所不同。首先,“政治”可以指对外政策,即一个国家或民族与其邻国维持的关系。在这一领域,断言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相似性,几乎不成问题。战争与外交都展现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它们都由以主权者自居的国家和政府来主导,并且都以国家的安全或扩张为最终目的。这无疑是对克劳塞维茨公式的其中一种可能解释:“只有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才能产生战争,[而且]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以另一些手段的继续。”(703, 674) 稍后,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战争“是一种用会战代替照会的政治”(706, 678)。在此,连续性与相似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从外交到战争的过渡可以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尽管在制度层面上,战争与和平被明确区分,但有限战争往往“不过是一种更为紧张的外交,一种要求更高的谈判方式,其中的会战与围城[充当]外交照会。”(685, 656)
但是,当我们赋予“政治”一词更普遍的含义,特别是将国内政治也包含在内时,战争与政治的相似性又当如何理解呢?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克劳塞维茨是否会接受对其论点的如此泛化,尚不确定。首先,他只承认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相对松散的联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并非机械地源自、也不能从其政治体制中推导出来:“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只与其宪制有间接关系,在本质上并不与之相连。”(1976a: 404) 从积极的方面看,有两个内部因素对国家对外事务的执行有显著影响:“当一个大的社会不再能安于内部的平静生活而必须作为国家对外行动时,有两件在平静生活中很少需要考虑的主要事情便会凸显出来:其一是政府机器的效能,它使大众成为一个统一体;其二是人民的精神,它赋予整体以生命和神经力量。”(1976b: 15-16) 政府机器的效能与公共精神:我们所理解的国内政治的全部内容,是否可能被归入这两个范畴之下?我不这么认为:前者让我们想到的是行政而非政治;至于后者,则既过于片面又过于模糊,无法涵盖国内政治的所有方面。最后,在他写下的最后几篇文稿中,克劳塞维茨得出了一个幻灭的结论:国家内部的幸福与繁荣,以及其宣称的意图之纯洁,都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外部能与邻国和平和谐地相处。“如果说政治和宗教秩序的原则与观点通常与物质利益和外部安全相结合,但它们永远无法取而代之;就算我们承认,所谓的专制主义已完全消失,所有民族都像此刻[1831年]的巴黎一样自由幸福,像几个月前的德累斯顿一样,难道民族之间的关系就会因此变成田园诗般的和平,而那不断威胁其外部和平的利益与激情的冲突,就会因此归于沉寂吗?当然不会;因此,我们不应在信条中寻找民族间的对立,而应在其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去寻找,在这一点上,更应该去叩问历史。”(1976a: 483)
说实话,甚至不能确定克劳塞维茨是否会同意将国家的内部生活视为他所理解的政治。这是因为,在他眼中,国家——无论实行何种政体——只能以个体主体的模式来思考;我们在此不妨回顾他对政治的定义,即“人格化国家的理智”(68, 35)。因此,其内部的任何分裂、任何冲突,都被视为病态。国内政治无非是对普遍利益的开明管理,是对“公共福祉”的理性经营。相反,派系的繁衍、政党的林立及其为夺取权力而进行的对抗,都只是政治的堕落与歧出形式;它们无疑提供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奇观,但对于作为其舞台的国家而言,这场奇观是毁灭性的。关于这一点,只需参考克劳塞维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极具启发性的篇章即可:“那里有生命的丰饶与活动的繁盛,有阴谋与对抗,有斗争与成功,有恐惧与希望,有恐怖与欢乐,有朋友间的团结和对敌人的穷追猛打,有那种能振奋个人并带动他人的热情,最后还有这样或那样既巧妙又暴烈的干预——这整个丰富而悸动的生命,让人想起古罗马的广场和雅典的公共集市。与这样一幅公民生活的景象相比,悄无声息地忙于私人事务,必然显得停滞不前。”(1976a: 406) 但克劳塞维茨随即反问道:“对国家的参与,难道就不能是别的,而非每个个体意识对政府源头的这种直接兴趣吗?如此多的骚动,如此多谋求整体领导权的阴谋,难道不更是一种病态的行为偏离吗?”(1976a: 406)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轻率的骚动,这种对政府的无序而偏私的参与,将最活跃的人囚禁在一个持续沸腾的圈子里,是一种真切的反常状态,是模仿某些极为动荡的小共和国的形象而来的。”(1976a: 407) 于是,我们今天视为政治核心的东西,就这样被贬低为一种反常状态。我们在此看到了对政治的某种蔑视,这不仅是普鲁士的,也是德国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近一个世纪后,这一传统将启发托马斯·曼写下他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Considérations d'un apolitique),并让他写出:“我不要那种用政治毒害整个民族生活的议会和政党管理……我不要政治。我想要的是客观、秩序和体面²⁰。”
话虽如此,我们并无义务也去接受这样的偏见,并且我们可以追问,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相似性的双重假设,对于我们理解政治意味着什么。在探索过这一假设的思想家中,我们必须首先提及卡尔·施密特。众所周知,在施密特看来,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连续性,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冲突;实际上,正是朋友与敌人的对立,奠定并支配着政治秩序:“政治性的特定区分,亦即一切政治行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的区分,便是对朋友与敌人的辨别²¹。” 施密特明确指出,这一区分的意义仅仅在于“表达联合或分裂、缔合或分离的极致程度²²。” 这也就是说,它并不指向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领域:“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类型的对立,一旦其强度足以引发人们在朋友与敌人之间进行有效的重新组合,便会转变为政治性的对立²³。” 这极大地拓展了政治的领域:一旦一场冲突——无论其源头为何——变得足够激烈,以至于对立双方转变为敌人,它便因此而具有了政治性质;同时,赋予“敌人”这一范畴以核心地位,也就将战争引入了政治的核心。
因为此处的敌人,即是那个他者,那个异邦人,与他之间可能发生一些“既无法通过一套预先确立的普遍规范来解决,也无法通过一个被认为是无涉其中且公正的第三方的裁决来解决²⁴”的冲突。
通过这条路径,我们重又触及了施密特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主题。首先,与如此定义的他者的对抗,确实是一种“例外状态”,因为,恰恰在于它无法被置于任何规范之下。面对这样一种情境,在场的每一方都是唯一能够决定对方是否构成一种威胁、以至于必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的一方,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切手段来与之战斗,包括在必要时诉诸暴力手段。而我们应记得那句著名的定义:“决断例外状态者,便是主权者²⁵。” 因此,政治这出戏剧的主角,其本质上就是主权性的集体;任何一个集体,只要宣称自己是主权者,它就实际上成为了主权者,并同时转变为一个政治行动者。此外,政治冲突是至高无上的对抗,因为在其视野的尽头,战争与死亡是必然被铭刻的。这里的战争,既指涉对外战争——即已然构成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也指涉内战,即在一个共同体内部,该共同体随即也因此而瓦解为两个或多个新的单元。因此,政治存在与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利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战争只是敌对状态的最终实现²⁶”,而敌对状态正是构成政治秩序的关系。“凡是在实力较量的视角下形成的组合,皆为政治性的,”施密特又说²⁷。
由此可见,此处既不存在战争与政治的融合,也不存在它们的混淆;战争被设定为政治的“本质界限”:当政治的逻辑被推到其终点时,它便导向战争。因此,“战争远非政治的目标、目的,甚至也不是其内容,但它正是那个假设,那个可能的现实,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决定了一种特定的政治行为……政治性并不存在于斗争本身之中,因为斗争有其自身的技术、心理和军事法则;它存在于由斗争的实际可能性所支配的行为之中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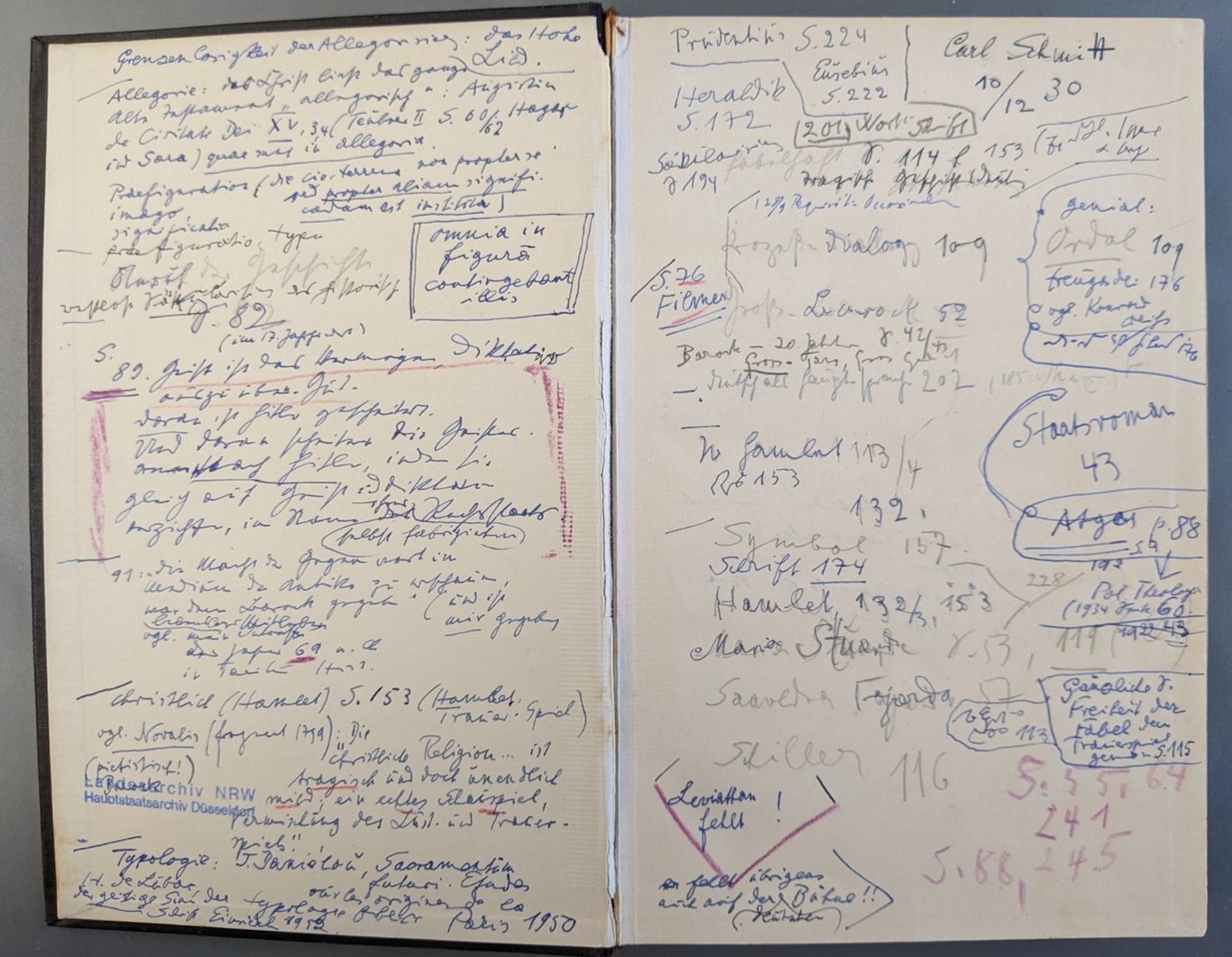
在其思想进程中,施密特很自然地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相遇,并不得不对其表明立场。表面上看,他们二人的论点是相反的: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它从政治中获得其意义;而对施密特而言,恰恰相反,是战争赋予了政治以意义,因为正是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定义了后者。许多评论者——包括最近让-弗朗索瓦·凯尔韦冈(J.-F. Kervégan)在他那本关于黑格尔与施密特的著作中²⁹——都固守于这一对立。然而,施密特本人对此并不满意。在《政治的概念》——我刚才介绍的那些概念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被阐发的——的一条注释中,他写道:“对他[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工具。当然,它确实如此,但对于一个试图确定政治本质的人来说,这个定义并不能穷尽战争的意义。此外,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在克劳塞维茨那里,战争并非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它是敌友格局的终极手段(ultima ratio)³⁰。” 如果相信施密特所言,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便非简单的外在关系,如同一个目的与其“众多”手段之一的关系那样,后者对前者而言本质上是陌生的、无差别的。战争之所以能成为政治的一种手段,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前定之和谐”所联系。那些强调克劳塞维茨将战争与政治区分开来的人忘记了,“连续性”和“相似性”这两个概念必然是相互的;当人们使用它们时,不仅是在对被比较的一方——战争——做出判断,也是在言说另一方——政治——的某些特质。在断言了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相似性之后,克劳塞维茨继续写道:“此外,政治是战争在其中发展的母体;在政治中,战争的雏形已然潜藏,如同生物的特性潜藏在其胚胎之中一样。”(145, 113) 如此,战争的特性已然以潜在的、萌芽的状态在政治中运作:施密特所言,难道有何不同吗?
那些将政治秩序建立在契约之上并将其置于法律帝国之下的理论,忽视了战争与政治之间这种本质的亲缘关系、这种有机的联系。友与敌的辨别,作为政治与战争的构成性要素,首先使各民族及其国家相互对立;换言之,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其本质上是一个朋友的共同体。更确切地说,国家作为能够裁决战争与和平的主权行动者的存在,以及其制宪权的行使,都预设了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且同质的政治存在者的预先存在,这同时意味着公民之间的平等和观点的一致。因此,社会契约并非国家的基础,它至多是国家的产物或结果。这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要么民族是上述意义上的同质的,那么社会契约便是多余的:为何要将事实中已然达成的共识形式化?要么它是异质的,也就是说,在决定性的领域被深刻而持久的分裂与冲突所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一份契约并不能使其获得政治存在所要求的实质性统一。我们可以通过另一条路径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份契约,根据定义,只能约束自主的、自由加入的缔约方,但因此,它永远只不过是在持续敌对的背景下一次或长或短的休战:“单凭‘契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这句口号,是无法建立起任何国家统一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社会群体作为缔结合同的主体,本身就是决定性要素:他们利用契约,而只受契约关系的约束。他们作为自主的政治实体相互对峙,而所存留的统一性,仅仅是可撤销的联盟的结果,如同所有联盟和所有契约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契约的功能仅仅是在缔约的群体之间缔结和平,而缔结和平总是——无论各方是否愿意——包含着对战争可能性的参照,即便这种可能性或许遥远。因此,在这类契约伦理的背后,总有一种内战的伦理³¹。”
对契约的这种批判,很自然地伴随着对法律的批判。法律总是对一种事实状态的记录和批准,而这种事实状态的生成则发生在别处。归根结底,法律的起源和基础在于一个政治决断,一个由权力掌握者做出的决断;在成为规则之前,它是命令和意志。同时,“法的统治从来都只是那些制定并适用法律规范的人的统治³²。” 同样,“法的至上性无非意味着对某个特定现状的合法化³³”,即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而建立的那个现状。总而言之,施密特提醒我们,“总是具体的属人团体,以法、或人道、或秩序、或和平的名义,与其他具体的属人团体进行斗争³⁴。” 此外,作为法律最初源头的决断,不仅施加于行为,也施加于言辞:“这甚至是人类法律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谁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谁就定义了词语和概念。凯撒是主,且在语法之上(Caesar Dominus et supra grammaticam)³⁵。”
因此,契约与法律被揭示为一些屏障,旨在掩盖那构成政治秩序之基础与经纬的不可化约的敌对状态。在此视角下,战争与政治几乎成了外延相同的概念,施密特在泛化战争概念,区分“行动之战”(guerre-action)与“状态之战”(guerre-état)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后者,他写道,“意味着在直接而暴烈的敌对行动停止后,一个持续存在的敌人的存在³⁶。” 在我看来,世界在1945年至1989年间所经历的冷战,就很好地诠释了施密特所说的“状态之战”。但是,如果我们同意将热战与冷战仅仅视为同一属类下的不同变种,那么将几乎全部的政治关系都归入战争的范畴就成为可能。我们前面看到施密特致力于避免战争与政治的任何混淆;而在此处,他似乎反而接受了这种风险:“凡是源于敌对状态的,无论是行动还是状态,皆为我们在此处所理解的总体意义上的战争³⁷。”
归根结底,政治秩序因此本质上是复数的、分裂的;政治行动者的内部统一与凝聚力,以及将其成员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团结关系,因此都是超政治的(次政治的或元政治的)现象。民族与国家的多元性是不可化约的:“政治的特定属性导致了国家间的多元主义。任何一个政治统一体都意味着一个潜在敌人的存在,从而也意味着另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共存³⁸。” 因此,一个统一且和解的人类将不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人类’不是一个政治概念³⁹”。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éo Strauss)⁴⁰所洞见的那样,政治的这种原始分裂,最终根植于一种神学观念。“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施密特观察道,“都预设了一个败坏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危险的存在者⁴¹。” 事实上,正因为人是败坏的,他才总能成为他人的敌人,而这正是政治秩序存在的原因。但这种败坏,反过来,又是原罪教义所表达的一种形而上学败坏的反映或结果。撒旦,作为上帝和人类的头号敌人,潜入了伊甸园;于是,园中盛行的和平终结了;于是,园中居民所生活的永恒当下被中断了;于是,历史——我们的历史——开始了。
在法律的起源处,施密特,正如我们刚才所见,邀请我们去发现决断,并因此发现决断者的权力。米歇尔·福柯则通过一条不同的路径,得出了相近的结果。如果权力关系归根结底是力量关系,并且如果“战争可以被视为力量关系的最大张力点,其最赤裸的状态⁴²”,那么权力关系确实可以被置于战争的范畴中来思考,而战争则显现为权力的核心与真相。换言之,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来看,战争都处于支配的开端。最初,曾有一场对抗,它留下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自此以后,一种权力关系便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但公开敌对行动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获胜的一方现在制定法律,但“法律并非和平化,因为在法律之下,战争在所有权力机制内部,即使是最常规的机制内部,仍在继续肆虐。正是战争,驱动着制度与秩序:和平,在其最微小的齿轮中,都在悄然进行着战争。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和平之下解读出战争⁴³。”
因此,福柯毫不犹豫地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将政治视为战争的延续。事实上,他提出,克劳塞维茨的公式本身,不过是对一个更古老原则的颠倒,即“一种自17、18世纪以来便流传的、既模糊又精确的论点⁴⁴”。我们在此姑且不论福柯论证的历史层面,只保留其结论:“因此,我们彼此处于战争状态;一条战线贯穿整个社会,持续不断且永久存在,正是这条战线将我们每一个人置于这个或那个阵营。不存在中立的主体。我们必然是某个人的对手⁴⁵。” 在此,我们不难辨认出卡尔·施密特所钟爱的敌友划分。同样,也不存在普遍的真理;任何真理都位于分割社会的那条边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真理是一种只能从其战斗位置、从其所寻求的胜利出发才能展开的真理。” 对于这种社会战争的论点,福柯很好地展示了那些表面上最热衷于此的拥护者,实际上是如何致力于限制其范围并消除其影响的。马基雅维里便是如此,他首先从中提炼出“一种可置于君主手中的政治技术⁴⁶”;霍布斯更是如此:首先,“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虚假的战争,没有会战,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一个阵营获胜,它将不经任何其他程序便建立起其至高无上的统治,而那个催生了利维坦的契约便将毫无意义。根据霍布斯的说法,无论是通过创设获得的主权还是通过获取获得的主权,权力都源于一种普遍的厌倦和恐惧,这促使人们放弃战斗,从而放弃他们自身的自由和个人权利;因此,这些人是自愿选择了那个压迫他们的巨兽,而国家的至高权力是建立在他们的同意之上的,无论这种同意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于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持续进行的潜在内战,便被贬谪到阴影之中。
让我们对走过的路程做一个总结。一方面,克劳塞维茨坚定地维持着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区别,但他所说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外交;另一方面,他承认这两种活动之间存在相似性,并指出一种活动的特征可以在另一种活动中以萌芽状态被发现:他由此为更深入的类比开辟了道路。施密特则将敌友关系视为战争与政治的共同织物,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敌对的强度。然而,作为政治舞台上行动者的共同体,其内部构成自身仍旧不属于政治,因为,恰恰在于,政治是在行动者之间而非在其内部上演的;鉴于民族和国家是享有特权的政治行动者,国内政治便再次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除非它是在内战的前景下发展的。最后,福柯超越了对外战争与内战之间的区别:正是政治本身,可以被解读为一场战争。因此,所有的法律和所有的制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和平——都有可能被描绘成战争机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为福柯找到先驱;例如,我们来听听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论及普选制和民主的多数决规则时所说的话:
“从来没有人真正相信,在一次投票中,多数人的意见仅仅因为它占了上风,就也是最明智的。这是一种意志对抗另一种意志,如同在战争中一样;这两种意志中的每一种,都必然坚信自己拥有更优越的权利和自身的理性;这种信念很容易找到,而且不证自明。一个政党的意义,恰恰在于保持这种意志和信念的警醒。在投票中被击败的对手,绝非因为他突然不再相信自己的正当权利而屈服,他只是承认自己被打败了……最好的候选人,即胜利者,是那个表现出最强者姿态的人。最强者是那个拥有最多选票的人。如果支持他的17,562人列成军队,对抗追随其对手的13,204人,他们必胜无疑⁴⁷。”
阶级斗争与战争 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a guerre
在那些以冲突为标志来思考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理论家中,并且因此而倾向于使用战争类比的理论家中,我们当然必须算上马克思、他的同伴以及他的后继者。我们应记得《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⁴⁸。” 当然,阶级斗争本身并非一场战争,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演变为战争。为了思考这一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使用了显性与隐性的对比;阶级冲突被描述为“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⁴⁹”。在记述工业无产阶级的起源与发展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⁵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与阶级战争之间仅仅存在一种可见度的差异:这种可见度只是强度增加的一个标志,它导致了冲突模式的质变。因此,马克思的公式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阶级斗争与阶级战争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们可以在何种基础上建立起区分它们的标准?此外,如果相信《宣言》作者们的说法,阶级斗争在某个时刻必然会转变为阶级战争:一个统治阶级,即使日渐衰落、力量削弱,也绝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一场武装对抗,无论多么短暂,都是夺取权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这一突变在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发生?
首先我们应回顾,对马克思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定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⁵¹。” 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必然会引发一场阶级斗争。当“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时,当那些在特定生产方式中“客观上”行使相同职能、占据相同位置的个体联合起来,构成一种“主观力量”,一个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集体思考、决策和行动的共同体时,阶级斗争才得以发生。当然,这种转变绝非一劳永逸;大多数时候,被压迫者的反抗表现为局部的、零散的、分散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称之为阶级斗争;斗争必须发展为全国性的,从而成为政治性的,这一称谓才具有合法性。况且,阶级并非先于其对立而存在;是斗争创造了阶级,而非相反:“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 此外, 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⁵²。” 【译注见本段末】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其两极分化和分裂,形成了两个敌对的极端:“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⁵³。” 于是,阶级斗争达到了其顶峰:从此,迪斯雷利(Disraeli)的“两个民族”正面相对;然而,战争的时刻尚未到来。
请注意俄文版全集、MEGA1阿本、中文本全集第一版(1960年),这段话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B.1(首先原文稿并不存在B节和B.1小节标题字样)下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系版本进行了大量文本调换以将《形态》分为清晰连贯的多部分。另外,中文世界里节选本、选集本(以及多个文献版)的排序是正确的,这一段来自由多个稿件杂糅层叠而成并且存在客观残缺(如[2]-[5](S.3-7))的誊清草稿部分(大束手稿,纸张[6]-[11](S.8-29), [20]-[21](S.30-35), [84]-[92](S.40-72)),该段位于 [87](s.54-55)),由于文字有草稿和片断性质,前后页存在文字佚失,所以这一段会被排在错误的位置。*[]内数字是印张编号(这里由恩格斯标记),S.是马克思在草稿上标记的原页数是什么阻止了被推向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立刻转变为内战呢?首先,敌对的阶级被包含在、并且继续被包含在一些更广阔的共同体之中,这些共同体限制了它们的对抗。在这方面,两种共同体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宗教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这两种共同体都不是以阶级标准来招募其成员的;因此,它们是“跨阶级”的集合体,它们所产生的团结关系阻止了阶级对立发展到其断裂点;宗教或民族的忠诚削弱了阶级归属的影响;结果,阶级未能获得那种使其成为主权者——即能够自行决定战争与和平——所必需的凝聚力、自我封闭性以及判断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才要攻击宗教——“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和民族——“工人没有祖国”;这些公式虽以陈述事实的面目出现,却更像是“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其目的在于清除一些阻碍被压迫阶级走向战争道路的障碍。
但最重要的是,阶级所嵌入的那些包容性共同体,其统一性与力量源于一种支配结构。我在此仅讨论民族共同体,其作用在今天至少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其他阶级则从属于它。统治阶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并掌握着政治权力;更确切地说,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权力的定义本身,就是作为一个阶级至高无上地位的工具:“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⁵⁴。” 权力又包含两个方面或环节:它首先是强制的能力,并以此资格,通过国家这一中介来行使。被赋予了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并且,由于国家拥有合法暴力的垄断权,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在享有这一垄断权。换言之,在“正常”时期,在阶级斗争的“常规”形式中,强制手段——以及非常具体的,武器——都掌握在其成员手中。阶级斗争要成为战争,就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破他们对武器的排他性控制。
但政治权力也是说服的权力,在其内部,强制的环节必然与同意的环节相结合:即使被统治阶级对其某些方面提出异议,他们也默认或顺从于自己的从属地位。换言之,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统治者也是领导者,他们不仅掌握着“专政”(dittatura),也掌握着“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egemonia)。这种领导权是支配的直接结果;正如马克思在一篇著名的文本中所写:“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⁵⁵。”
领导权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同意;一方面,它将既定秩序呈现为符合事物本性的,这并不仅仅是宣传,更不是欺骗。统治阶级,马克思说,只有在它“迫使整个社会都接受它的那套生意经⁵⁶”时,才成为统治阶级;反之,当它“再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条件当做至高无上的法律强加于全社会⁵⁷”时,它便受到了威胁。因此,正是生活和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本身被如此安排,以至于某个特定阶级的统治条件,表现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条件。这种信息无需言辞,它被铭刻在社会的建筑结构之中。因此,既定秩序变得必要,因为它被设定为自然的。当资产阶级民主最终确立时,第二种同样有效的方法也加入了进来:既定秩序现在被描述为构成社会的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里同样,这不仅仅是思想的问题:诚然,社会契约哲学断言社会及其法律最终建立在一个契约之上;但这一论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其回响:在前者,个体通过一份真实的“劳动合同”与其雇主相联系,人们可以向他声称,他是自愿签订这份合同的;在后者,普选制与议会制的联合机制,给予所有公民一种感觉,即他们至少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行使着间接的控制。最后,与葛兰西有时所持的观点相反,承认一种分工,将强制归于国家,将领导权保留给公民社会及其制度——家庭、学校等——将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至少就资产阶级民主而言,国家独自掌握着强制力,但它在制造共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普选制和议会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⁵⁸。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稳妥地推导出阶级战争的可能性条件。阶级斗争要转变为战争,被压迫阶级就必须获得思想和政治上的自主。因此,首先必须打破同意。既定秩序必须被构想为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的结果,因此是脆弱和短暂的,如同一切受制于时间帝国之物一样。在契约的表象背后,必须揭示出真实的优劣势和强制关系,它们使得所谓各方的自由与平等变得虚幻。从积极的方面看,渴望统治的阶级必须反过来能够将其自身的解放条件,呈现为所有人的解放条件。最后,国家的强制手段必须失去其恐吓和威慑的力量。

同意与强制这对范畴,以及公民社会与国家这对范畴——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并非完全重合——为葛兰西提供了思考阶级斗争模式在历时和共时层面上的历史多样性的工具。首先,它们使得区分一种“正常”状态和一种“例外”状态成为可能;“常规”的阶级斗争优先考虑同意的环节;强制力保持潜在,只在危机时期,当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威胁时,才浮出水面。换言之,同意像一个屏幕一样掩盖了强制,而必须打破这个屏幕,强制力才能登场。此外,东欧国家——在那里,国家和强制占主导地位——可以与西欧国家——在那里,公民社会和同意占据首要地位——形成对比⁵⁹。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可以辨别出两个时代: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前,既定秩序的主要捍卫者是国家及其镇压力量;1871年之后,公民社会接过了接力棒,并从此通过说服来行动。但是,当葛兰西想要描述阶级斗争在这些不同情境下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时,他从战争的概念世界中借用了他的术语:在国家和强制扮演主要角色的地方——危机时期、在东方、或1871年之前——被压迫阶级必须进行“运动战”:其直接任务是准备、发动并成功进行起义;相反,在公民社会和同意占优势的地方——“正常”时期、在西方、以及1871年之后——被压迫阶级则被迫进行“阵地战⁶⁰”:它必须通过局部的攻势以及只能在中长期才能产生效果的教育和宣传努力,来逐步削弱统治者的领导权,摧毁他们的威望和权威。
在纯粹的军事层面上,最能体现运动战与阵地战对比的,是拿破仑战争与1914-1918年战争之间的差异,这也证明了,在这个领域,演变同样是从前者导向后者。一方面,决胜是通过机动、通过灵活性、通过大规模且快速的位移来达成的,这些位移使得力量得以集中,以迎接关键的考验;另一方面,战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是交战双方相对的消耗使得天平倾斜。本世纪初,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比较拿破仑战争与腓特烈二世战争时,曾将“倾覆战略/歼灭战”(strategie de renversement)与“消耗战略”(strategie de l'épuisement)对立起来,而考茨基则借用了这些范畴来指称葛兰西稍后将称之为运动战与阵地战的东西⁶¹【译注见本段末】。但两人共同的倾向,是将这些对立视为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实际上,它们的各项是互补的。国家与强制只有在起义前夜才真正被揭露出来,而统治者的领导权并不会随着他们的倒台而消失;它以思维习惯或惯常行为的形式,在他们被赶下台后,依然继续发挥作用。因此,运动战并不能省去阵地战。反之,如果统治者确实从不自愿放弃他们的帝国,那么阵地战只能在运动战中找到其结局:炮轰并不能免除冲锋。简言之,阵地战本身是无力的,但运动战只有在经过阵地战的准备后才能成功。当我们考察克劳塞维茨的战斗观时,我们将会看到,这恰恰是其两个环节——摧毁与决胜——之间的关系。
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十六章,“1910年,他们[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对立在为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这个问题上公开爆发。那时,考茨基阐述了strategie d’usur(消耗战略)这一战略哲学,以消耗敌人(Ermatungsstrategle)来反对推翻敌人(Niederwerfungsstrategie)。这是事关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考茨基的路线是越来越彻底地适应现存制度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下,“耗尽”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工人群众的革命理想,所有的庸人、所有的官吏、所有的名利之徒都站在考茨基一边,他在为掩盖他们的本来面貌而编织着思想遮羞布。(接下段)战争爆发了,政治消耗战略被战壕所排除,考茨基就像当初适应和平一样地适应了战争。而罗莎·卢森堡则表明她知道忠于自己的思想……”
另见托洛茨基《军事学说还是伪军事教条主义》7.革命政治与方法主义,“不幸的是,在我们新出现的教条主义者中,不乏一些鼓吹进攻的头脑简单之辈。他们打着军事学说的旗号,试图将那些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以“进攻理论”的形式达到顶峰的片面“左倾”倾向,引入到我们的军事领域中来。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那么(!)共产党就必须执行进攻政策。将“左倾主义”翻译成军事学说的语言,就意味着使错误成倍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坚持进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这一原则性基础的同时,又以其非凡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而著称——或者用军事语言来说,就是机动能力。与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及方法与形式的灵活性相对立的,是一种僵化的方法主义。它将诸如我们是否参与议会工作、我们是接受还是拒绝与非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达成协议这类问题,都转变成一种绝对的方法——一种据称适用于任何及所有情况的绝对方法。”(根据英文版文集托洛茨基军事著作[THE MILITARY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Volume 5: 1921-1923]译出)列宁对“革命时刻”——即革命可能爆发的历史关头——所下的定义,完美地阐明了这种互补性:“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⁶²。” 事实上,革命的所有条件在此都得到了总结:“必须要‘下层’不愿……”;共识必须被打破,被压迫者必须从此拒绝他们的处境;“必须要‘上层’也不能……”;强制力必须被瘫痪;必须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打击削弱了它的力量;领导权必须被如此深刻地侵蚀,以至于士气低落的统治者失去了自信和行动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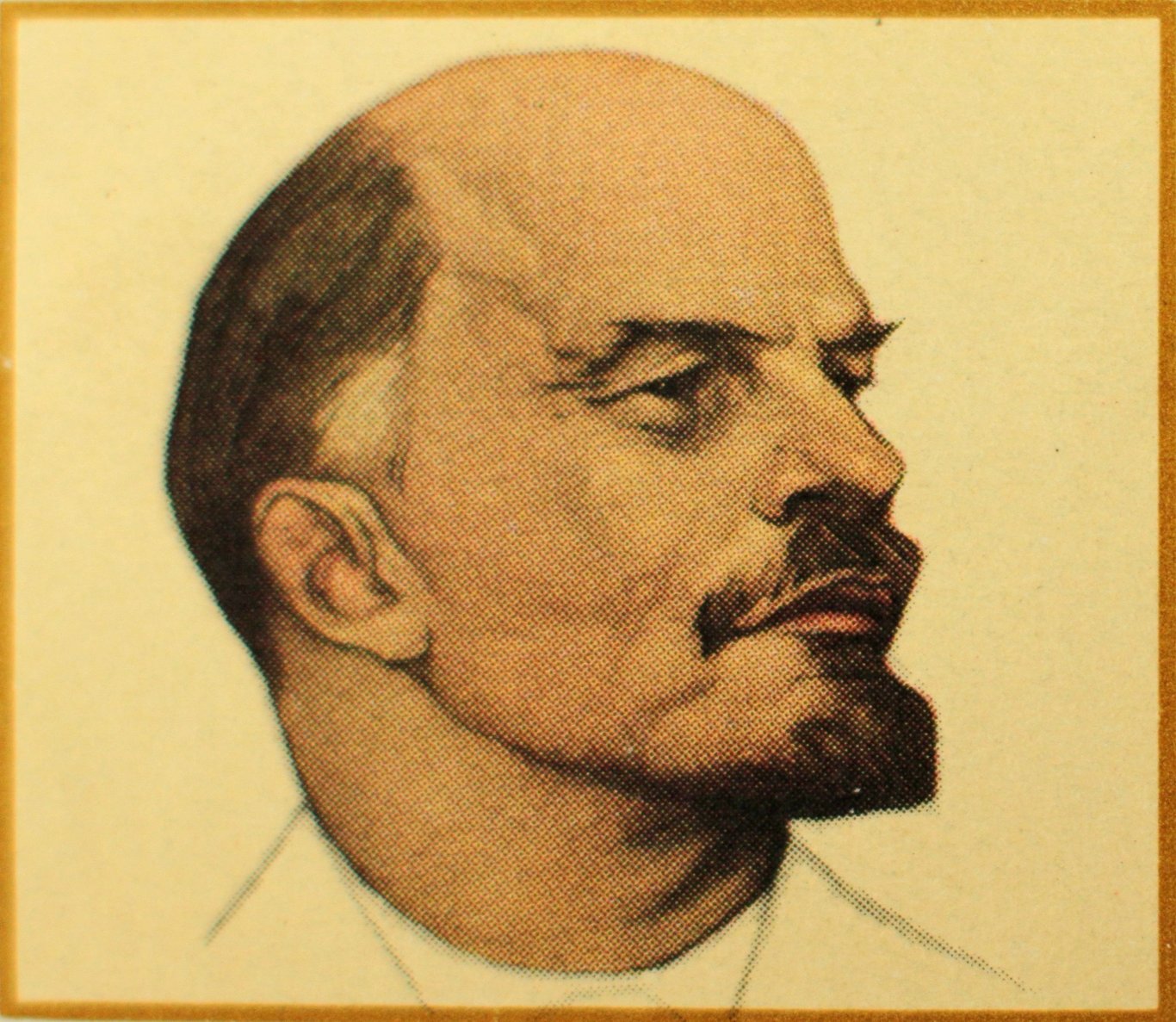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葛兰西说道,在东方,国家相对于一个萎缩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优越地位,导致了运动战的首要性。而从这一论断中得出全部结论的,将是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以一种非常经典的方式开始,将战争定义为“[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⁶³”。因此,从政治通往战争的道路具有一种趋于极限的性质;毛泽东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公式——他是通过列宁发现的——并补充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⁶⁴。” 可以看到,此处克劳塞维茨正统得到了完美的尊重:行动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而战争只是一种特殊的手段,用以弥补常规手段的不足。

但这些普遍的公式之后,紧接着是对西方与东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差异的精确描述。在前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制度”;因此:
“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⁶⁵。”
我们在此认出了葛兰西所描述的阵地战。相反,毛泽东继续写道: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⁶⁶。”
换言之,在中国,政治立即且完全地就是战争,毛泽东在别处还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⁶⁷。因此,我们确实又回到了葛兰西所划定的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同时,毛泽东描述中国国情的方式,也使他显著地改变了他对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定义。说在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完全是战争,并不意味着前者消失以为后者让位:接受这样的解释,就等于将它们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其中一个必须离开其位置,另一个才能来占据。此处所断言的,恰恰相反,是政治与战争之间如此深度的融合,以至于它们——除了一个区别之外——几乎变得无法分辨。毛泽东用一个非凡的公式写道: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⁶⁸。”
在我看来,这句话的对仗与对称表明,流血——克劳塞维茨会称之为武装暴力——的存在,并不会改变它所介入的整个过程的性质;无论血流与否,这个过程都保持其本质的同一性,而流血只具有一种偶然属性的地位。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没有它自己的逻辑”(703; 675),它的逻辑是从政治那里得来的。通过将战争设定为一种“流血的政治⁶⁹”,毛泽东在使这两种活动达到近乎完美一致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必须注意到一个悖论。如果说,对葛兰西而言,西方无产阶级在投入运动战之前被迫进行一场持久的阵地战,是由于其最初的弱小:同时受制于领导权和支配,它必须先摆脱前者,才能解放于后者。但为什么东方无产阶级——其力量起初要小得多——却能直接进入运动战呢?总的来说,阶级斗争在其所有变体中,都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战斗;至少在最初,根据定义,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物质和思想上的优势。在西方的情况下,这一特性表现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阵地战的优越地位;那么在东方,它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明确的:东方的战争,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一场运动战,但它采取了两种轮流扮演主角的形式:游击战和正规战。游击战确实属于运动战;其中没有稳定的战线,机动性是其绝对规则;游击队的法则,是出其不意和速战速决,然后迅速撤退。但游击战,正是弱者的战争。当弱者变强,当均势趋于建立时,便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完全没有后方到建立根据地,从无处不在到划定解放区,简言之,从游击战走向正规战⁷⁰。总而言之,在东方,运动战在整个对抗过程中确实独占鳌头,但在其中,游击战之于正规战,就如同在西方,阵地战之于运动战。
这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的短暂考察,印证了我们从与施密特和福柯的相遇中已经得到的认识。克劳塞维茨断言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连续性与相似性,但他所说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外交。如果说国家内部的生活也与战争相似,那只能是一种可悲的歧途所致。基于这一信念,他得以在战争与政治之间维持一道鲜明的区别。相反,那些将冲突视为政治存在——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模式的思想家,则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模糊乃至削弱这一区别。人们可以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大大偏离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然而,正是克劳塞维茨为他们打开了这扇门。
循着克劳塞维茨的启示,我们将战争与游戏、商业和政治进行了对照。在此过程中,我们汇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之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都面对着一种竞争结构,它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既非完全平等、也非绝对不平等的混合关系;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这种结构都催生了不确定性与不明确性,这既源于相互作用的特性,也源于偶然性的闯入;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提了出来,因为失败者将被逐出由该结构所展开的场域。这些共同特征确实定义了一个“属”,而战争在此便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种”。对阶级斗争的引述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当社会被描述为冲突时,斗争与战争之间的界限便趋于消弭。最终——这个结果当然不足为奇——正是那赤裸的暴力,或如毛泽东所言的“流血”,构成了战争的特有标志。剩下的问题是,需要明确这一标志的确切效力与强度;它附加于我们刚刚看到战争与其他许多活动所共有的那些特征之上;它的存在本身,是否就足以抵消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些相似之处的意义?它是否赋予了“战争事实”一种独特的“色彩”、“味道”与“内涵”,以至于尽管存在这些相似之处,它仍然构成一个独立的宇宙,一个不可化约地迥异于并脱离于我们曾试图将其联系起来的那些社会生活领域的宇宙?由此可见,只有对暴力进行新的反思,才能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有效地提出这些反思之前,我们必须在我们探索战争国度的旅程中迈出新的步伐。

注释:
1. 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游戏的人》(*Homo luden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51年,第76-77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普隆出版社(Plon),1962年,第47页。
3. 科拉·迪弗洛(Colas Duflo),《游戏与哲学》(*Jouer et philosopher*),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UF),1997年,第225页。
4. 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袖珍版”(Folio)系列,1967年,第56-60页。
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前引书,第46页。
6. 科拉·迪弗洛,《游戏与哲学》,前引书,第231-232页。
7. 科拉·迪弗洛,《游戏与哲学》,前引书,第169页。
8. 同上,第144、150及152页。
9. 科拉·迪弗洛,《游戏与哲学》,前引书,第180页。
10.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前引书,第168-170页。
11.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欲望与利益》(*Les Passions et les Intérêts*),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UF),1980年,第74页。
12.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七星文库”(La Pléiade)系列,1951年,第五卷,第六章,第280页。
13. 同上,第二十卷,第二章,第585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586页。
16. 同上。
17. 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论征服的精神》(De l'esprit de conquête),载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编《现代人的自由:政论集》(*De la liberté chez les modernes, Écrits politiques*),巴黎:Le Livre de Poche出版社,“多元”(Pluriel)系列,1980年,第118页。
18. 让·列维(Jean Lévi),《神圣的官吏》(*Les Fonctionnaires divins*),巴黎:瑟伊出版社(Seuil),1989年,第22页。
19. 同上,第30页。
20. 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个非政治者的思考》(*Considérations d'un apolitique*),路易丝·塞尔维森(Louise Servicen)译,巴黎: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1975年,第222页。
21.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的概念》(*La Notion de politique*),M.L. 施泰因豪泽(M.L. Steinhauser)译,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Calmann-Lévy),1972年,第66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77-78页。
24.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67页。
25.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Théologie politique*),J.-L. 施莱格尔(J.-L. Schlegel)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88年,第15页。
26.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73页。
27.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80页。
28. 同上,第74及78页。
29. 让-弗朗索瓦·凯尔韦冈(Jean-François Kervégan),《黑格尔,卡尔·施密特;思辨与实证之间的政治》(*Hegel, Carl Schmitt ; le politique entre spéculation et positivité*),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PUF),1992年,第75页。
30.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201-202页。
31. 卡尔·施密特,《议会制与民主》(*Parlementarisme et Démocratie*),J.-L. 施莱格尔(J.-L. Schlegel)译,巴黎:瑟伊出版社(Seuil),1988年,第149-150页。
32.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113-114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114页。
35. 卡尔·施密特,《论政治》(*Du politique*),J.-L. 佩斯泰尔(J.-L. Pesteil)译,皮伊索:帕尔代斯出版社(Pardès),1990年,第99页。
36.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165页。
37.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166页。
38. 同上,第97页。
39. 同上,第99页。
40.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致卡尔·施密特的三封信》,载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著《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et la notion de politique*),弗朗索瓦丝·马南(Françoise Manent)译,巴黎:朱利亚尔出版社(Julliard),1990年,第167-172页。
41.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前引书,第107页。
4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巴黎:伽利玛-瑟伊出版社(Gallimard-Seuil),1997年,第40页。
43. 同上,第43页。
44. 同上,第41页。
45. 同上,第44页。
46.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前引书,第145页。
47. 埃利亚斯·卡内蒂(Élias Canetti),《群众与权力》(*Masse et Puissanc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60年,第200-201页。
48.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著作集·经济学卷I》(*OEuvres. Économie I*),M. 吕贝尔(M. Rubel)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七星文库”(La Pléiade)系列,第161页。
49. 同上,第162页。
50. 同上,第173页。
51. 同上,第170页。
52. 卡尔·马克思,《著作集·哲学卷》(*OEuvres. Philosophie*),M. 吕贝尔(M. Rubel)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七星文库”(La Pléiade)系列,第1107页。
53.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著作集·经济学卷I》,前引书,第162页。
54.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前引书,第182页。
55. 卡尔·马克思,《著作集·哲学卷》,前引书,第1080-1081页。
56.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前引书,第172页。
57. 同上,第173页。
58. 关于这一切,参见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著《论葛兰西》(*Sur Gramsci*),D. 勒泰利耶(D. Letelier)与S. 尼梅茨(S. Niemetz)译,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Maspero),1978年,第69页及后。
59.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6至9卷)(*Cahiers de prison (6 à 9)*),M. 艾马尔(M. Aymard)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1983年,第183-184页。
60. 葛兰西,《狱中札记》,前引书,札记1,第118-121页;札记6,第118页;札记7,第183页;札记13,第409至413页及418-419页;札记15,第121至124页。
61. 关于此点,参见佩里·安德森,《论葛兰西》,前引书,第108至114页。[指《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已有中译本。在书中,被翻译作“击倒战略”和“消耗战略” 。]
62. 列宁(Lénine),《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a Maladie infantile du communisme*),载《列宁全集》第31卷(*OEuvres, t. XXXI*),巴黎:社会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1961年,第80-81页。[中译本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6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200页。
64.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前引书,第163-164页。
65.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前引书,第235-236页。
66. 同上,第236-237页。
67. 毛泽东,《论持久战》,前引书,第187页。
68. 毛泽东,《论持久战》,前引书,第164页。
69. 同上,第167页。
70.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前引书,第77-116页。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