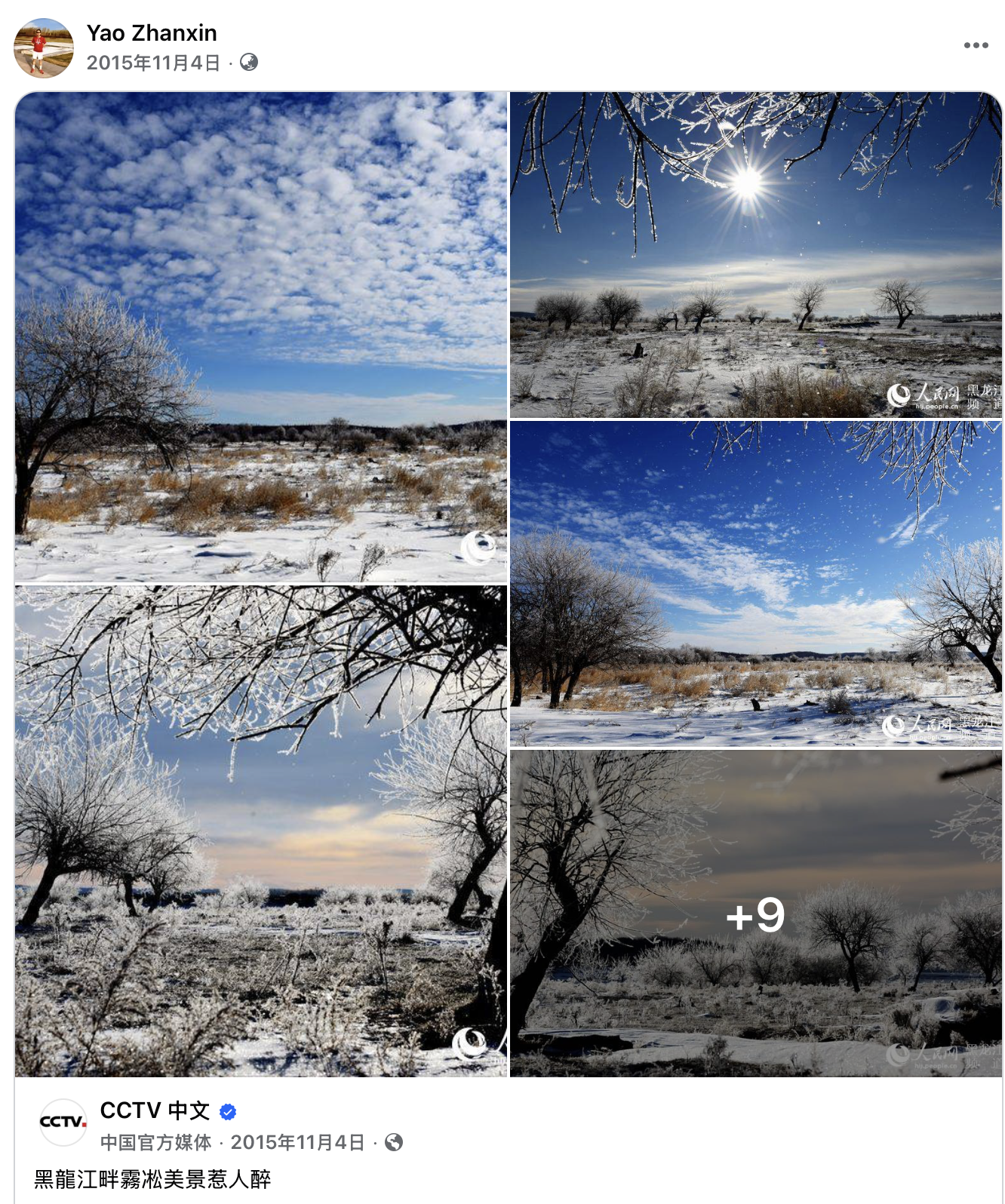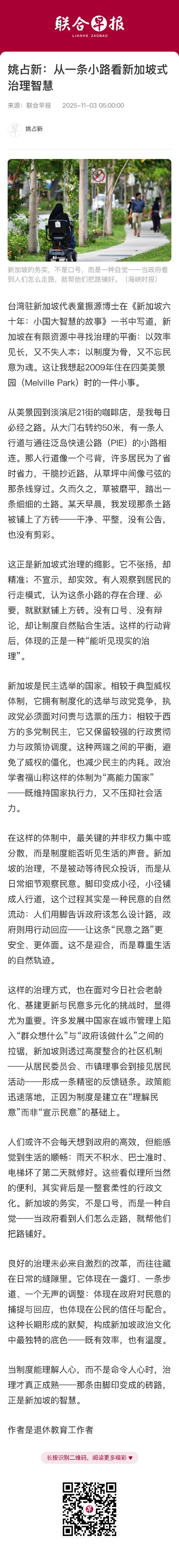James
歌詞:《慢慢跑,一起走》
寫下人生中第一首歌詞,送給一起慢跑的妻子。作曲的朋友正在為它譜上旋律——期待有一天,這段屬於我和妻子的旋律,也能唱進大家的生活里。

不自由的民主:從鄭麗文談普京說起
“普京不是獨裁者,他是選舉產生的。”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日前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的這句話,引起軒然大波。批評者指她為威權辯護,支持者則強調她只是說明“程序正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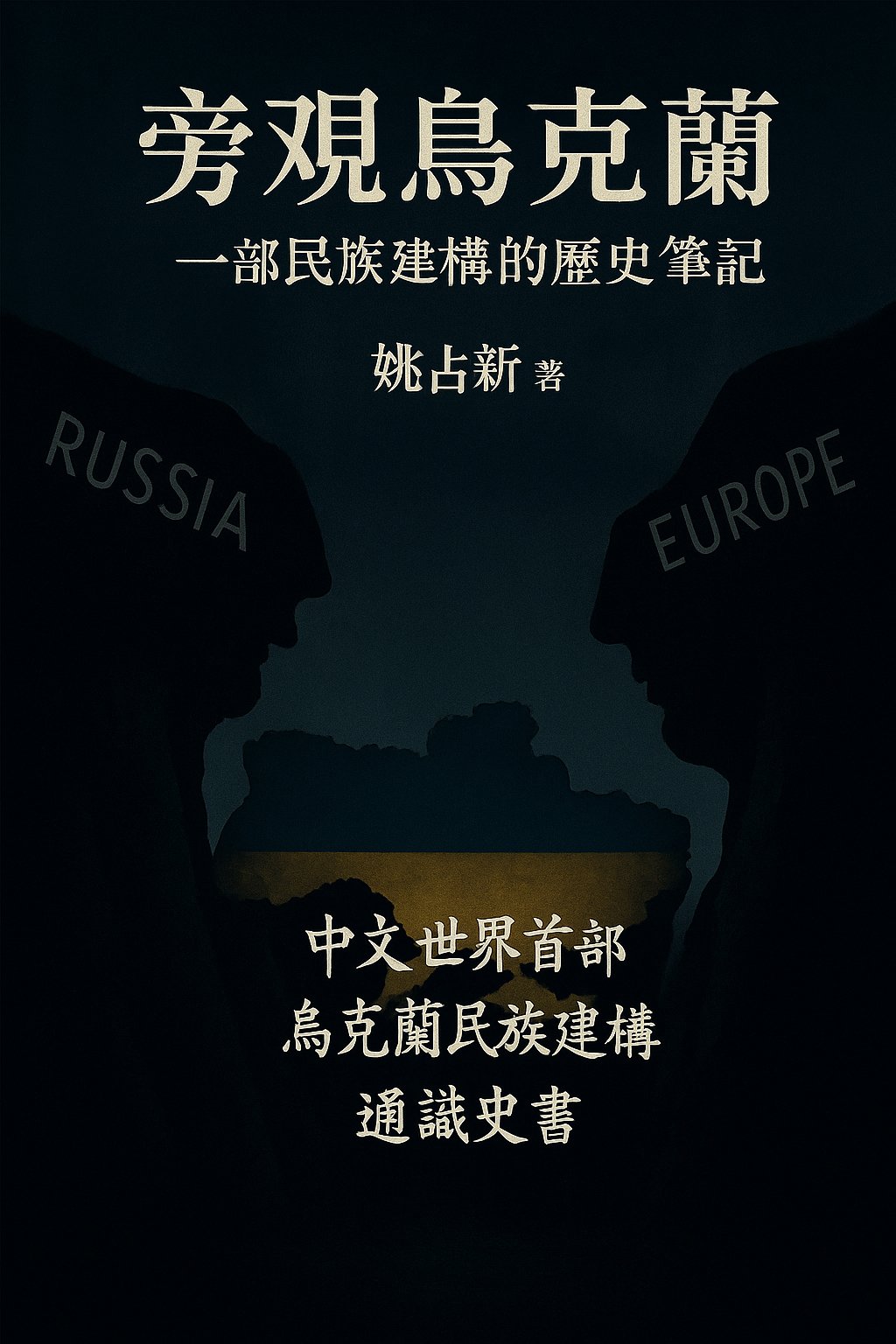
詩歌:霜降(三)
霜降的夜, 月亮是一枚冰冷的印章, 盖在每个句子的额头上。 他们像枯枝上的乌鸦, 互相取暖 语言在掌声里化为雾, 落地前就消失了。 那些头衔, 像挂在网上的露珠——闪亮, 却颤抖。 蜘蛛还在中心, 四肢僵硬, 梦也结成丝。 有人说诗在燃烧, 我却只听见雪在写字。 每个字都在颤, 像一枚银币的冷光。 霜降的清晨, 我看见窗外的阳光, 在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缝。 也…

詩歌:霜降(二)
你问我,霜从哪里落下—— 从人与人之间, 从那一瞬的迟疑里, 从伸出的手慢慢收回的动作里。 街角,一个老人倒下, 他的影子比身体先落地。 人群像潮水, 退到各自的岸。 有人说:他也许是骗子。 有人说:世界变了。 没人去搀扶, 怕善良成了证据。 霜在阳光里闪烁, 像一次短暂的怜悯, 很快消失, 只留下更冷的光。 曾经,信任是一盏灯, 照亮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现…

詩歌:霜降(一)
在人心的冬天 你问我,霜从哪里来—— 从人心的深处。 那里,恶意比冬更早, 一个眼神就能结冰, 一句话就能碎裂。 街上的荧幕比月亮还亮, 语言学会了取悦。 它在掌声里闪烁, 像结霜的镜子, 映出每一张孤立的脸。 有人喊自由, 有人喊秩序。 风在两边吹, 没有人听见回声。 那只看不见的手, 关掉枪栓, 开启荧幕。 我们彼此瞄准, 却只看见自己。 霜降的清晨, 万物都在…

安穩之後談改變:新加坡的下一個60年
2025年8月9日是新加坡建國60週年。作為東南亞最穩定且高效治理的國家,新加坡在外交、經濟、行政等領域長期獲得國際贊譽。但隨著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結構變化,政治參與、選舉制度與公眾信任等層面正面臨新的張力。

“日本人优先”的背后:参政党与文化防卫民族主义的兴起
对于日本而言,关于“谁是日本人”的辩论已经开始。而对于整个亚洲来说,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在多元共处中,建立新的“我们”?
民族是誰的?——柬泰邊境衝突的歷史張力
要真正化解衝突,除了法律與外交手段,更需回到歷史敘事本身:承認歷史的多重性,接納記憶中的複雜與不確定,拒絕將民族簡化為二元對立、榮辱線性的發展劇本。唯有當“民族”不再被視為邊界的守護者,而是成為共享歷史與文化的起點,Preah Vihear 才有可能不再是戰爭的起源,而成為和平的象徵。

在多元中说“我们”——Singlish与“Singaporean”认同的细微连结
从民族建构理论来看,许多国家的民族认同之所以牢固,往往源于共同的苦难记忆或外部压力。例如,美国的民族认同诞生于独立战争,印度的民族认同成型于反殖斗争。相比之下,新加坡虽然历经脱离马来西亚、国家独立、经济腾飞,但缺少足以凝聚深层身份认同的“共同磨难”或“外部敌人”。当然,这也是新加坡的幸运。但正因为没有这种共同记忆…

谁决定了我们如何记住?——看《南京照相馆》
我原本是不太看这类电影的。抗战题材,常常不是热血过头,就是苦情泛滥。这次《南京照相馆》一上映,朋友劝我:“不一样哦,这回是冷静、克制、小人物。”我咬咬牙买了票,结果,看完更迷茫了。 这部片确实不一样。镜头漂亮、节奏紧凑。一家照相馆,一卷底片,一群普通人。导演极力避免喊口号,也不撒狗血。你甚至会觉得,那些日本兵像是AI剧本里的NPC,走来走去…
这不是笑话:缅甸军政府通过新法,批评选举者可判刑入狱。
刚刚在《联合早报》的即时新闻里看到一个消息:缅甸军政府通过新法,批评选举者可判刑入狱。 官方媒体用严肃语气报道了这件事,他们说得义正词严,像是在捍卫民主原则。 逻辑很简单:选举神圣,不容置喙。谁批评,谁犯罪。 在这个国家,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批评选举,坐牢;第二,不批评选举,继续生活。 但问题是,一个不让你说话的地方,早晚连“生活”也成…
我不懂大是大非,但我知道心痛
我一向是个胆小的人。说话、做事、写文章时,总会先在心里自我审查。凡是有争议的、可能带来麻烦的,我通常不敢说,也不敢写。 比如一些敏感词、敏感人物、敏感国家,我都会尽量避免提及。 但我心里始终有一杆秤。 这杆秤,与人们常说的“正义”、“邪恶”、“进步价值”或“保守立场”无关。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太复杂了,而且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也很懒,不…
只是想写个动态,真的不是文章
因为动态的文字只有240字,写多了,舍不得删掉,就当作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