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女性:民族主义中被忽视的性别角色

编译:芥芥子、虾
较对:芥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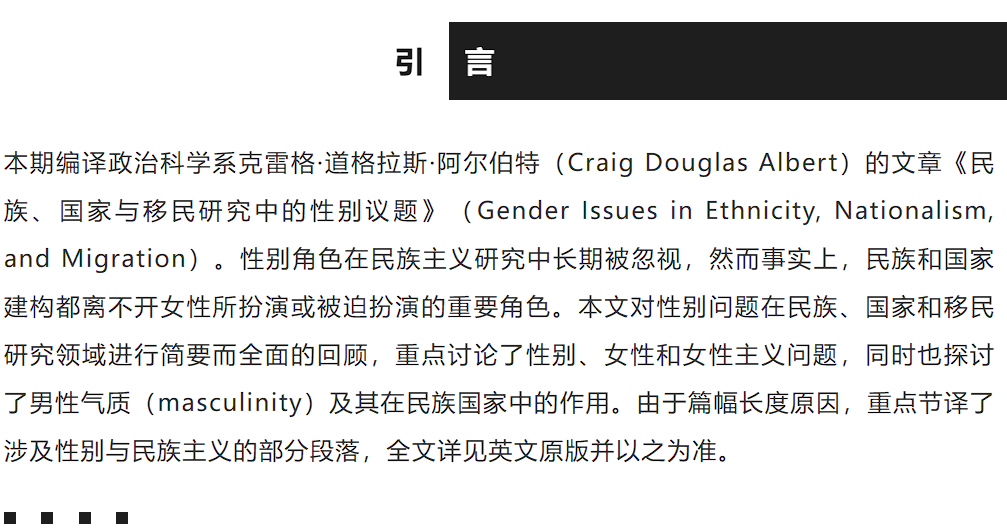

直到最近,女性在民族主义与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才得到学界关注(Yuval-Davis,1997),这或许是因为历史上男性几乎垄断了对民族与国家的控制权。这种状况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女性创造了民族/国家。尤瓦尔-戴维斯(Yuval-Davis)阐释道:"正是女性在生物学、文化及象征层面再生产着民族"(1997:2)。然而,治理活动始终定位于公共领域,因此民族主义的焦点自然落在该领域的主导者——男性身上。由于传统上女性被定位于家庭领域,她们长期被排除在治理研究之外,被视为缺乏政治相关性(Yuval-Davis,1997)。自女性主义研究兴起之初——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哲学思想开始——学者们就指出,男性主导地位源于一种认知,即自然赋予男性适应公共领域的基因构成,而赋予女性适合处理家庭事务的生理特征(Wollstonecraft,1988)。彼得森(Peterson)写道:“多数西方政治理论家认为,女性的生育能力不仅使她们更适合从事育儿等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同时也使她们不适合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1999:131)。然而,最新研究对生理决定性别差异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性别角色是通过男性支配被建构、制度化并得以维持的(Anthias and Yuval-Davis,1992;Enloe,1993;Zalewski,1995;Peterson and Runyan,1999;Goldstein,2001)。
尤瓦尔-戴维斯(Yuval-Davis)与安西亚斯(Anthias)(1989)撰写了关于性别如何与民族进程相关联的开创性著作。鉴于其重要性,必须基于尤瓦尔-戴维斯(1997)完善的分类,探讨性别/民族关系的若干维度。性别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将按照尤瓦尔-戴维斯的分类细分为若干子议题。虽然作此划分,但文中也将讨论其他重要学者的观点。
第一个类别是女性作为民族的“生物学再生产者”(biological reproducers)。女性通常被视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母亲,这主要源于她们肩负着为民族生育和抚养后代的责任(Palmary,2003)。正如斯派克·彼得森(Spike Peterson)所阐明:“女性被劝诫应通过生育子女来服务群体繁衍,以此履行对国家-民族(state-nation)的义务”(1999:44)。尤瓦尔-戴维斯进一步论述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部分或全部育龄女性会被要求——有时通过利诱,有时甚至通过强制——生育更多或更少的子女"(1997:22)。女性肩负着生产民族的责任,从而确保民族的延续。相反,当她们被胁迫生育或违背意愿终止妊娠时,压迫便由此产生。
因此,政府往往试图通过调控以下方面来控制女性的性(sexuality):堕胎权利、婚姻实践(包括相关期望),以及女性实际的性生活。政府对其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关注,也可能导致其控制避孕实践(Gilheany 1998:61)。彼得森指出,政府可能限制避孕知识的获取,可能限制堕胎权利,也可能提供生育的物质奖励(1998:43)。避孕可能不被允许,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男性对国家的支配也意味着对其公民身体的控制。巴里·吉尔希尼(Barry Gilheany)写道:“国家一直是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策略的主要目标”(1998:60)。由于系统性的政府限制,女性被剥夺权利,从而遭受不平等((Peterson 1999)。维斯娜·尼科利-里斯塔诺维奇(Vesna Nikolil-Ristanovil)这样解释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在战争时期,作为士兵生产单位的女性身体成为政治斗争场所。将女性美化为民族生物再生者的同时却忽视其作为人的价值,导致女性生育权利和母性情感遭到大规模侵害”(1998:235)。
男性主导的国家(masculine state)同样掌控着女性的婚姻权利。在大多数国家,正如后文将讨论的,女性的性权利受到控制,她们被迫通过婚姻来生育。非婚生子女或许会被国家接纳,但母亲的名誉与社会地位却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男性主导的文化也决定着婚姻权利——政府往往为维护传统而漠视法律规范。其中最骇人听闻的陋习莫过于抢婚(wife kidnapping)。洛里·汉德拉汉(Lori Handrahan 2004)记录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抢婚现象。本文认为,相较于其他学术论述,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能更清晰具象地呈现抢婚实质。虽然这个案例并非随机选取,但其他类似行为同样值得关注。
据汉德拉汉描述,抢婚通常表现为数名醉酒男性在街头劫持女性,甚至直接从其家中掳人(2004:209)。令人震惊的是,有时施暴者竟已备好全套婚宴。更可悲的是,若女性试图逃脱,往往会被家人排斥——逃跑被视为对社会传统的挑衅,更是对民族身份与群体认同的否定(2004:222)。事实上,正如汉德拉汉所述:“许多男女声称被抢婚是一种荣耀,因为这被视为对女性价值的终极肯定(ultimate confirmation of a woman's worth)”(2004:209)。汉德拉汉列举了吉尔吉斯斯坦男性控制女性的多种方式:首先是彩礼制度(kalym),即新郎用金钱、财产或牲畜购买妻子;其次禁止寡妇再婚,除非对象是亡夫的近亲;第三是当男性无力或拒绝支付彩礼时发生的抢婚;最后,一夫多妻的合法化赤裸裸地彰显了性别不平等(2004:209)。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陋习并非由政府创设或合法化,而仅是默许——但这种默许实质上纵容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吉尔吉斯斯坦的压迫性实践中可以清晰看出,女性被视为二等公民,既遭受男性主导政府的歧视,更被当作财产对待。
尤瓦尔-戴维斯的第二个类别,涉及女性在集体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核心参与,以及作为民族/国家差异标志符号的角色。女性的家庭职责不仅要求其生育后代,更肩负着向子女传递民族认同的使命。她们需要向下一代灌输民族信仰、传统习俗、文化实践、忠诚观念、象征符号及民族语言(Peterson 1999)。正是基于此,女性被视为民族象征意义与实际意义上的母亲,必须受到强大男性的保护与支配。特里夏·库萨克精辟指出:"民族延续的重担由女性承担,但家族的主导权通常仍掌握在男性手中"(2000:543)。因此,任何涉及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族群冲突的斗争,都会形成性别分工的格局:男性负责为保卫"母国"而战,女性则承担民族繁衍之责。马拉蒂·德阿尔维斯对此论述道:“民族国家(即母国)通过特定的母职建构来形塑公民主体:以养育照料公民为交换,获取相应的回报”(1998:254)。
这种结构导致女性缺乏主体性。是男性代替女性行动,他们为捍卫女性的自由、荣誉和群体身份而行动。乔安妮·纳格尔(Joanne Nagel)指出:“女性不被指望保卫我们的国家、管理我们的国家或代表我们的国家”(1998:261)。女性只扮演秘书、情人、妻子等辅助角色(1998:261)。朱莉·莫斯托夫(Julie Mostov)补充道:“民族神话借鉴传统性别角色,民族主义话语中充满了将国家比作母亲、妻子和少女的意象。”她继续写道:“因此,民族主义将男性和女性的建构自然化:女性在生理上繁衍民族,男性则保护和为民族复仇”(1998:89)。英格丽德·帕尔马里(Ingrid Palmary)进一步阐述:“男性是士兵,因此是英雄;女性支持他们,并成为受害者”2003:6)。女性与民族合为一体,对她们的保护体现了民族荣誉。因此女性必须接受自己的角色,因为拒绝这一角色会给自己带来耻辱,进而给民族带来耻辱。当然,耻辱的定义权掌握在男性手中(Nagel 1998)。女性的主体性被抹除,因为男性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
第三个类别,讨论的是女性在移民和公民身份管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定位。女性通常被视为间接公民,因为她们被限制参与公共/政治领域——而对男性来说,这才是唯一重要的领域(Elshtain 1993)。此外,在男性看来,家务劳动远不如公共生活重要(Rousseau 1964)。因此,这些社群中的女性公民身份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她们被纳入公民整体;另一方面又总是存在专门针对她们的规则、条例和政策(Yuval-Davis 1997:24)。女性若要被视为直接公民,就必须参与公共领域。参与公共领域能增加获得完整公民身份的机会。萨拉·本顿(Sarah Benton)指出:"社会契约——这个关于起源的神话——创造了公民。它创造了作为公民的男性。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家庭领域,在那里进行着维持和繁衍生命的日常事务。而作为户主的男性,就是公共领域中的公民"(1998:40)。
菲德尔玛·阿什(Fidelma Ashe,2007)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参与公共政治抗议活动,将自身作为受害者和家庭照料者的刻板建构转化为优势。她并不认为这些刻板印象总能奏效,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促进社会进步。女性参与民族主义冲突具有高度复杂性:当她们踏入公共领域时,实际上是在挑战"女性仅适用于家庭领域"的固有认知,从而在传统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获得话语权(2007:767)。在解释爱尔兰政治抗议活动时,阿什指出,传统意义上“男性主导公共领域/女性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认知构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身份建构的基础(2007:768)。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性往往通过利用其作为受害者、母亲和家庭照料者的身份来进入公共领域(2007:773)。因此,这一过程既使她们获得了更完整的公民身份,又可能同时强化了其被建构的传统家庭身份。
由于男性主导公共领域,他们将继续基于自己对女性的看法来定义女性运动,这一过程不断重建并维持这种看法。阿什(Ashe)解释道,因此,女性政治行动的这些表现实际上可以同时破坏和再生产民族主义中的性别二分法(2007:767)。另一个复杂性在于,女性在民族主义项目的对立方阵中,例如阿什在爱尔兰的解释,可能会妨碍女性主义的目标,因为一些女性会支持女性主义问题,而另一些则会支持民族主义事业,而这两者通常是对立的。因此,女性事业的成败可能取决于所追求的民族主义项目的类型以及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时机和形式(2007:784)。
一个极具代表性且富有启发性的案例发生在英国,它清晰地展现了上述理论观点。当然,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但笔者发现格林汉姆事件最具典型性。1981年,一群女性为抗议美国在英国格林汉姆军事基地部署核弹头巡航导弹及驻军,在该基地外建立了和平营地。这种抗议形式将英国女性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领域,被视为一种间接政治行动。抗议者时而破坏围栏、自由进入军事基地,其影响力甚至促使她们在奥尔德玛斯顿武器工厂外建立了第二个和平营地。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2000)指出,这场运动使女性得以直面彼此,以及与士兵和警察对峙(2000:77)。她进一步阐释道:"和平营地为重新思考公私生活的分野提供了契机"(2000:77)。这完美印证了阿什的观点:女性能够通过公共抗议活动,介入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
尤瓦尔-戴维斯关于性别与民族主义交集的最后一个类别,涉及“性别化的军队与战争”这一概念。战争通常被视为男性或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现象。然而尤瓦尔-戴维斯指出,尽管女性在民族主义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她们在非战区仍遭受不平等对待。她写道:“军队中的性别分工往往比民事部门更加形式化和僵化”(1997:93)。女性通常以非战斗角色被纳入军队,主要担任秘书、护士和教师等职务。这种性别分工源于男性对女性平等的偏见与恐惧。因此,通过军队对女性特质的强调,女性被控制并与男性同僚区分开来(Yuval-Davis 1997:101)。如果男性对“男子气概”定义权(包括冲突、战斗、保护与牺牲)被女性夺取,他们可能会感到被去男性化和不够阳刚。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写道:“对现代战士而言,女性既可能是慰藉,也构成威胁。女性就像敌人一样需要被摧毁”(2000:74)。弗朗辛·达米科(Francine D'Amico)提出了类似观点:对于参军男性而言,存在一个“男性化”过程,其中女性特质和女性气质被定义为“他者”,因而被视为低等(1998:123)。霍莉·艾伦(Holly Allen)指出:“女性获准参战的前景也会破坏备受珍视的男性气质形象”(2000:318)。
正是平等(这一观念可能使军事事业对女性具有吸引力。它常常是女性赋权的来源之一。根据弗朗辛·达米科(Francine D'Amico)的说法,一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将女性战士的形象作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证据(1998:120)。然而,不幸的是,女性在军队中经历了大量性骚扰,这些骚扰可能得不到惩罚(Feinman 1998:133)。这种性骚扰表明,男性即使在女性担任等同的军职时,也不视她们为平等的存在。男性士兵仍然比女性士兵更受重视,因为是男性主导了体力上的战斗,因此他们面临的风险比女性更大。
军队中的性别分工所造成的不平等在全球化世界中或许正在减少。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战争通过高科技计算机和现代武器在战场之外进行,战场上取得成功所需的男性特质概念已经弱化。尤瓦尔-戴维斯解释道:"这些技术创新不仅使体力在战斗角色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还导致许多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手工文书角色不复存在"(1997:114)。因此可以说,军事平等是一种性别化的平等(D'Amico 1998:123)。在美国,军队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正因如此,"军队内部的性别条款和性实践受到严格管制"(Allen 2000:310)。
V. 斯派克·彼得森(V. Spike Peterson)与安妮·鲁尼安(Anne Runyan)指出:"社会习得的性别是通过履行规定的性别角色而获得的身份。此外,由于社会对男性化和女性化行为赋予不同价值,性别也成为不平等的基础"(1999:5)。英格丽德·帕尔马里(Ingrid Palmary)进一步论证道:“民族议程通过其普世性伪装,实际上由特权男性掌控和决定,并反映着文化建构的男性气质”(2003:5)。男性对公共领域的控制是通过建构性别差异来维持的。然而,这些所谓的差异是由社会关系建构的,不能归因于自然。反过来,民族主义方案强化了这些想象的性别建构,将女性禁锢在家庭领域的不平等地位中。男性控制公共领域是基于这样一种神话:男性更强大,因此比女性更适合统治;而被动的女性则被设定为属于家庭领域。
民族主义中对女性的一种潜在压迫在于:要成为爱国者、被视为好公民,女性必须教育儿子们树立在重大冲突时期用身体保卫祖国的观念。事实上,为被视为合格的公民-母亲,女性往往必须欣然将儿子送上战场。洛林·巴亚尔·德沃洛(Lorraine Bayard de Volo)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成为好母亲的标准包括服从国家意志并甘愿为战争牺牲儿子”(1998:242)。韦斯娜·尼科利-里斯塔诺维奇(Vesna Nikolil-Ristanovil,1998)的研究显示,在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试图通过反战挽救儿子生命的女性被贴上叛徒标签。德沃洛进一步强调,战争时期的异议声音——尤其是母亲们的抗议——必须被压制,以维持民族团结的表象。
对女性主体性的限制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并纵容男性实施压迫与压制。事实上,主体性的缺失剥夺了女性与民族国家建立政治纽带的权利。彼得森指出:“作为父权制家庭和家庭工资模式的结果,女性仅能通过父亲/丈夫与国家产生联系;社会期待女性仅能通过男性、并与男性共同建立这种纽带”(1999:43)。因此,女性仅被视为实现男性定义目标的民族财产(Peterson 1998)。朱蒂·普里(Jyoti Puri)阐释道:“若要总结关于女性与民族关联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女性被视作民族的象征,却未能在民族主义话语中获得平等体现,也未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平等公民”(2004:113)。

当然,一篇关于性别的文章不能不讨论男性或男性气质的一面,直到最近,这一方面在女性主义圈子里一直被忽视。性别化民族主义的延续和重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男性身份以及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二分建构。这个建构已经制度化。因此,为了成为一个男人,为了被视为一个男人,为了感觉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男子汉,他必须将自己与女性对立,并且必须继续维持定义男性气质的传统角色:对女性的控制(Connell 1995;Steans 2006)。不幸的是,由于女性被局限于家庭领域,而不在公共/政治领域,她们被视为间接公民或半公民,因此,因此遭受不平等对待(Cusack 2000)。
男性特质的概念本质上压制着女性的性,要求女性接受被建构的性别角色,否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压迫与疏离。乔安妮·纳格尔(Joane Nagel 1998)指出,关于男子气概存在规范性和霸权性的概念化定义,这些定义规定了男性必须如何行事才能被视为阳刚。民族主义的兴起始终伴随着男性气质的崛起。因此,霸权男性气质与霸权民族主义理念高度关联。霸权男性气质与民族息息相关——民族国家是由男性主导、男性创建并由男性构建的制度化统治体系。故而,民族本身即具阳刚特质,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必须体现民族原则并誓死捍卫其民族。男性因而彼此较量,对被贴上"不够男人"的标签惊恐不已。所谓男子气概,意味着捍卫民族;捍卫民族即意味着保护女性;而保护女性实则意味着控制女性。
实际上,妇女和儿童反而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这与男性的初衷形成讽刺性反差。J.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驳斥了"战争是为保护妇女、儿童等传统弱势群体而发动"的神话,并指出"当代战争中平民伤亡率居高不下"的事实(2001:48)。相反,女性可能在和平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的性别越平等,特别是当女性能够担任政治职务和接受高等教育时,国内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Melander 2005a)。此外,女性在高层职位中的代表比例越高,国家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就越少(Melander 2005b)。玛丽·卡普里奥利(Mary Caprioli 2005)论证指出,性别不平等可作为国内冲突的预警指标。
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能否结合以促进女性平等发展?辛西娅·科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提出存在两种女性主义:本质主义(认定差异与特质是固定的)与反本质主义(认为差异与特质是静态或建构的)。她阐释道,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都不是静态概念,二者都具有多元性,因而会产生多种变体。科克伯恩认为,这些变体可能兼容也可能对立(2000:628),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吉尔·维克斯(Jill Vickers,2006)指出,与非西方女性相比,西方女性对两者兼容性的认知截然不同——西方女性常排斥民族主义,视其为女性事业的干扰;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反而可能助推女性主义,因其能催生妇女运动并提升组织效能。维克斯强调,只有当民族主义有助于女性组织化时,才能促进女性主义事业。其中关键在于民族主义运动初期女性的组织化程度(2006:95)。此外,女性权益是否得到提升,还取决于女性主义类型、运动形式、组织架构及其在不同民族主义项目中的关联。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必须置于民族主义项目的特定阶段或语境中分析,这些阶段包括:边缘化阶段、西方民族国家阶段、移民主导民族国家阶段、现代化阶段、反殖民民族项目阶段以及后殖民民族国家阶段(2006:96)。
赫尔(R.S. Herr,2003)指出,在欠发达国家,女性往往反对民族主义项目,因为这些项目通常将民族主义置于女性主义之上。男性常以平等承诺激励女性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然而一旦目标达成,便会抛弃女性诉求。殖民时期的抗争史已充分展现民族主义与性别议题的冲突。赫尔认为,多数女性主义者主张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论述中彻底摒弃民族主义,转而接纳更受认可的跨国主义进程——该进程使全球女性能够围绕共同议题形成联合阵线。这似乎预示着民族主义已然过时。但赫尔强调,这些国家的女性不应轻易否定民族主义:若以非本质主义方式重构民族主义概念,它仍可为女性主义事业所用。这一新范式要求将民族主义解构为双重目标:对外追求民族自决及国际平等地位,对内构建成员平等协作的民族共同体(2003:149)。根据民族主义性质差异,跨国性别平等可通过妇女运动与组织的跨境联动得以推进。跨国性别关系既能提升性别议题能见度,也可能最终促进女性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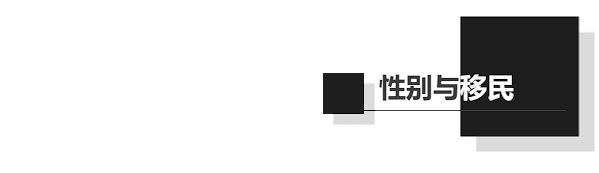
移民问题与性别议题直接相关,因为女性和男性在出入境方面享有的权利并不平等。男性通常可自由迁徙,而女性则受到更严格限制。埃莉诺·科夫曼(Eleonore Kofman,2004)指出,全球化为女性(尤其是高技能女性)提供了更多移民机会。因此,学者需要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分工与性别、阶级及种族的交叉关系。随着移民形态日趋多元化和阶层化,女性的移民经历也呈现差异化特征——这可能促进性别平等。法里德·海亚特(Farideh Heyat,2006)以阿塞拜疆为例,阐释了全球化与性别平等的关联。她认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结合催生了新的性别不对称现象,加剧了性别与家庭关系中的张力"(2006:396)。西方影响尤其体现在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上,这些观念在城市地区快速蔓延。问题在于,社会性别平等理念、代际权利扩大以及族群/性别角色中的自由平等观念,既挑战了伊斯兰教的传统角色,也导致阿塞拜疆家庭关系日趋紧张(2006:408)。
富朗与席勒(Fouron and Schiller,2001)指出,全球化新时代的民族主义可能持续制造性别与国家关系中的差异。他们以海地为例,证明某些关系仍在维护压迫女性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卡彭特(Carpenter,2005)也认为,跨国网络可能通过刻板化、建构和强化当代权利规范而损害性别事业——这些规范本身也是被建构的产物。因此,它们延续了既有体系,遵循既定议程而非开创新议程。但富朗与席勒同时强调,跨国主义促进了女性社会正义斗争和赋权运动的普及。聚焦这套新兴跨国价值观,使学者们期待男、女与国家的关系将逐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此外,跨国联系(特别是移民家庭间的联系)有助于构建性别关系的新认知,并为女性创造更多实现公平的机会——尤其是通过积极参与家庭领域中的"政治性角色"。跨国家庭网络正将跨国意识带入家庭内部。富朗与席勒提醒人们不要期待即时平等,因为性别与(跨国)民族主义的关联最终仍由国家掌控。但全球化无疑增加了实现更大平等的可能性。
*地鸣是一个共创小组,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一起尝试聚焦一些议题,拓展写作的空间,欢迎私信我们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事件洞察,理论批评,进步之声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