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荷蘭的耶拿學校-Jena XL
一、環境
結束荷蘭的北邊的學校,我們搭著鐵路往南來到了荷蘭東部的Zwolle,這是一個比較小的城市,總人口約13萬左右,相較於Groningen又是一個感覺更加悠閒的存在,同時也不會因為有了悠閒,而失去生活應有的機能,想到的各種大小用品,都能在這個城市找到。
Janny載著我們前往Jena XL時,發現了許多大卡車,這是前兩週在路上沒有看過的風景,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這是以工業、商業和物流中心為主的城市。兜兜繞繞一圈有種回到高雄的氛圍。來到校門口停好車,走進校門看見裡面的風景,忍不住地在心裡吶喊
「這根本就是一間大學。」
學校派了兩個英文好的學生來跟我們介紹,一個是國一的男孩,另一個是國二的女孩,跟著他們的步伐從大廳開始這間學校的旅程。大廳裡坐了很多學生,在八點半上課以前,學生都會集中在這一區吃東西、聊天、滑手機,學校有規定吃東西及聊天的地方只有這裡,因為走廊的其他地方是自習區。大廳有許多座位,有圍圈的沙發也有四人對做的木頭桌椅,沿著大階梯走上二樓也有兩張可以看見窗外風景的高腳桌座位,看出去是隔壁的體育場,那裡有許多人在踢著足球。主要階梯很大,是可以讓三十人都坐在上面的那種,我們經過時看見階梯的角落也坐滿了學生。
這裡上課的時間是八點半,時間一到所有人就會慢慢地收拾東西走進教室。在這一週觀課的過程發現學生在休息時間幾乎都會往大廳移動,很少看到留在教室的,雖然他們有固定可以進行開始圈的教室,但似乎不會像台灣的學生一樣窩在裡面,彷彿這間教室從來都不是屬於他們的。學生自己的個人物品不是隨身攜帶,就是放進走廊置物格裡,每個學生都有一張感應卡,一個人會有一個置物格,東西放進去關上格子後會自動上鎖,總算在學校看見一個能上鎖的置物格。
我們在巡迴校園的過程能看到還是有少數的學生仍坐在大廳,又或者自在地進出校門口,實際上後來進入班級的課堂觀課,也發現學生如果並不想待在教室,他們可以隨時離開,如果他們在教室吵鬧影響課堂,老師經過幾次的討論都無法改善後,也會直接請他們離開教室。
這間學校沒有太多戶外的空間,只有一塊可以踢足球跟打籃球的地方,但似乎沒什麼人在用,校內的空間雖然很大,卻沒有圖書館,只有在走廊上自習區的盡頭看到一個小書櫃,裡面大概只有十來本書,那些書實際上也不太會有人去借。想要查找資料,學生還是喜歡用手機跟電腦,只是相較於之前在耶拿小學裡總會看到的「閱讀時間」,在這裡就沒看見了。
這裡的廁所很乾淨,學校的廁所主要會請清潔公司來校園清掃,一天兩次。廁所的男女生的圖示是用同一種顏色,得靠圖示的人是穿裙子還是褲子來分辨,就連男女混用廁所,也是將一個人的左半邊穿褲子,右半邊穿裙子。關於男生與女生究竟應該如何標籤,又或者應該去標籤化,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在群體生活之中,似乎還是得或多或少地做出「他」與「她」之間的區別,畢竟生理的構造就是有顯著的不同,不同的身體自然也會有不一樣的需求。
另外一個發現是學校的廁所很小,一次只能容納兩個人,沒辦法像以前台灣的中小學一樣,大家下課可以互相揪團去廁所。除此之外學校的熱食部也只是一個小小的攤位,只有在午餐時間才會營業,賣的東西也只有冷食跟烤餅,不是那種台灣福利社的樣子,讓大家可以揪團一起去逛的那種。
學生期腳踏車來學校後會上鎖,再把鑰匙交給老師,主要目的是避免孩子離開校園去到太遠的地方,只是在這樣的規範下,想著會不會有孩子偷打備份的鑰匙?不過逛了逛校園外,發現其實也沒有太多可以鬼混的地方,不像台灣有許多賣點心、賣飲料的小攤販,也沒有便利商店,更沒有看起來像是網咖的地方,當然在現在這個智慧型手機解決一切的年代,應該沒什麼學生會去了。
繞完了校園一圈後回到了教師休息室,是一個很乾淨很舒服,很像家的空間,有一台各種咖啡品項都有的義式咖啡機,也有各種口味的茶包,想喝鹹的也有即溶湯包,意外地發現這裡的冰箱裡面有啤酒瓶,後來一問才得知週五晚上老師有時也會有小小的慶祝活動,大家會聚在一起吃吃東西,喝點小酒。在這同時思考的是老師這個職業在現場很多時候是孤單的,得獨自面對課堂上發生的一切,校園如果能有個讓老師們好好休息,並且互相扶持的環境似乎挺好的。
課堂上的人數大約2-20人,座位主要會以四張桌子組成一個小組桌,教室內大約會有四組。上課的過程整體的感覺跟台灣相似,也就是老師講課,學生聽課,可能會有討論,但主要還是會以講課為主,不像小學會有很多在課堂上練習的時間。從小學畢業來到國中,荷蘭的學生會先經歷什麼課都得修的一年級和二年級,在升上三年級前,會依照個人的志向及前兩年的學業成績來決定未來要走的升學管道。
主要有VMBO(四年制、技職類為主)、HAVO(五年制,技職+理論)、VWO(六年制,理論類為主)三大升學路徑,不管選擇什麼途徑都還是會參考個人的成積,因此定期還是會有考試,主要也是檢核學生學習的狀況,讓學生對於未來適合選擇什麼樣的系統能有初步的概念。其中有一個班上只有2人的班級,就是選擇VWO系統的學生,據說全校只有5人選擇走VWO。在荷蘭的研究型大學只有14所(VWO途徑的選擇),相對於台灣是少的,台灣有百間「大學」。不確定是因為人口數量的差異所導致的結果,還是因為台灣的大學多半混合實務與理論研究。
二、課程
一、二年級必修課有Kring(圓圈討論)、Xperience(跨領域專案)、Verwerking(學習整理與鞏固)、Nederlands(荷蘭語)、Engels(英語)、Wiskunde(數學)、Techniek(技術)、Kunstvakken(藝術課程,包括視覺藝術、戲劇與音樂)、Lichamelijke Opvoeding(體育)、Plannen/Evalueren(計畫與回顧)、Maatschappijleer(公民與社會),二年級的必修課則會增加德文課、法文課。課程會依照難易度,有些會分年級上,有些則是一、二年級混齡上課。但整體來說到了知識逐漸專業化的階段,要像小學一樣三個年級混齡在一起的難度也隨之增加,當分齡來上的課變多,能夠混齡一起相處的時間也變少,進而帶來的影響也就是各年級之間的隔閡越明顯,想要真正地實踐共同體,盡可能地創造全校的共同經驗似乎還是重要的。
一開始很好奇第二外語為什麼只有德語跟法語,畢竟荷蘭的右邊緊鄰著德國,下方則是比利時,理論上應該要學比利時語,但查了資料才發現比利時過去曾是荷蘭的一部分,但後來獨立了,所以他們的主要語言也是荷蘭語,比利時的下方則是法國。這些都是歐盟的國家,歐盟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輕易地開車往返,相對於台灣,連去個澎湖、金門或者馬祖都像在出國。思考著關於國土之間的疆界事隔著陸地還是海洋,與我們看待第二外語的態度相對沒那麼積極似乎有某種程度上的關係。
跟Jena XL的歷史老師聊到荷蘭的政治問題,才知道最近在國內其實有許多關於大量國際移民的議題,右派支持著禁止,左派著相信著應該要多元包容,老師在平常的聊天之中能夠談論政治,學生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場與老師討論,但他們也提到大家在檯面上也許會支持著左派的多元包容,但實際投票也可能選擇禁止移民,台灣看待著獨立與否的問題似乎也是類似的狀態。於此同時思考著台灣一直號稱是多元包容的國家,但我們在面對東南亞移工的問題,似乎也有許多群體跟荷蘭的右派政權一樣採反對態度。
一、二年級除了必修課外,也有選修,每週要選四小時的課,包含創作、科技、語言(德文、法文以及他洲的文化探索)、生活技能、表演藝術、自然探索。在這裡講課型的課程(如數學、語文等)一堂會是30分鐘,而實作型課程則是一堂60分鐘,相較於荷蘭一般學校每堂課都是50分鐘而言,只有30分鐘可以講課程需要教授的內容,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要如何結合課綱來安排課程對老師其實是一個挑戰。
課程時間縮短,老師努力想要讓有限的時間,讓課程既有趣且包含應有的知識點,可以看見老師在課堂上的努力,但隨著知識逐漸專業化的過程,還是能看見學生已經開始無法享受知識學習帶來的樂趣,那些沒有選擇離開教室的學生,有部分是看著窗外發呆,或是跟旁邊的同學聊天打鬧。老師看見這樣的景象,也不是舉起手,等待所有人也舉起手而安靜,主要還是用「噓」的聲音來提醒。當然還是有很厲害的老師讓課程變得有趣,像我們就有看到一堂荷語課,就是採用辯論的方式來學習。實際上「論證」是荷蘭學校裡學習語言的正常過程,也有出版社出版教科書,即便「論證」是有趣的,但還是有照著教科書念,把課上得很無聊的老師,但不在這間學校就是了。
唯一有看到舉手來調整秩序的場合,只有中午休息時間的酒精與香菸講座看見,這個講座並不是常態性的,但剛好被我們碰上,其中就有曾經上癮著電子煙的老師在講座上現身說法。相對台灣,荷蘭是一個對吸菸者包容度高一些的國家,但實際上荷蘭的國家政策是走向減煙甚至禁煙的,除了調高菸品關稅外,也會不斷宣導各種菸品可能造成危害的衛教知識。
三、世界導向學習
每個人都有自主學習時段,要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題目做專題研究。看著這些一樣也有升學壓力的荷蘭學生,會因為要挪出準備考試的時間來做專題研究而感到困難嗎?以前求學期間沈迷漫畫、電動、籃球及樂團,但後來為了考試而放棄了這些興趣。或許這個問題的答案,能從荷蘭其實幾乎沒有針對課業而開立的補習班的這個現象當作答案,在當地課後有的大多是才藝班,主要為了學習各種興趣。
老師有邀請學生跟我們分享他們的專題研究內容,發現學生在表達英文上雖然不算太流利,但其實大致上都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或許是荷蘭語跟英文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就好像中文跟台語很多時候也是很類似的,像台灣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能聽得懂台語,只是不一定說得流利一樣。
專題研究的部分會有導師引導他們思考並往更深入的方式發展,一個導師大約負責25個學生。
,主要負責在每天的開始圈與學生討論近況、生活以及專題研究等等,除此之外導師也會協助處理學生在課堂上遇到的問題,和科任老師討論如何解決。
四、電腦與手機的使用反思
這裡的學生可以帶手機,上課期間基本上不能使用,但他們會帶電腦,電腦的目的是為了要輔助課堂資聊查找使用,但還是能看到少數打開電腦,眼睛看著螢幕裡與課堂無關的影片及社群。Robert老師與我們討論手機對於學生的使用於否的問題,心裡沒有明確的答案,有時覺得社群可以是海洋,我們能夠在其中冒險,又或者能潛入深處找到寶藏,如果是這樣,提早開始玩水,學習如何游泳似乎也是重要的,但同時社群也可能是毒品,使我們深陷其中無法自拔,究竟是找到寶藏,還是淹死在大海,仍需要時間去實驗及驗證。
五、耶拿教育的延續性
Robert老師自己的小孩現在正就讀小學,但並沒有因為自己是耶拿學校的老師,就將他們送進耶拿小學,他的小孩就讀的事家裡附近的一般小學,爸爸希望孩子能與平常玩在一起的鄰居一起在學校相處。對他來說耶拿教育是一個很棒的體系,但同時在成長的過程似乎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可以考量。
一間耶拿國中,究竟需不需要講究血統的純正性?台灣的華德福學校一口起包辦了國小到高中,從其他體系轉進來的比例是相對少的,但在這裡似乎並沒有「血統」的要求。老師說學校由二年級的學生帶一年級認識校園文化建立的算是完整,因此即便不是從耶拿學校上來的孩子,也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耶拿教育的學習風格。
嘗試在不同的視角裡面穿梭,使得觀課的日子來到第三週變得非常疲憊。觀課的現場我只是一個旁觀者,紀錄發生的一切,嘗試站在老師與學生可能身處的文化脈絡,去思考我們看見的事情是如何發生,藉由理解這個過程,好讓我們回到台灣以後,能夠真正轉化成台灣的「耶拿學校」,只是這一切最大的難題還是在於我們始終不是這裡工作者,也不是這裡學生,嘗試用自己的過去經驗來感受老師的視角,實際上還是陷入自身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上的盲點。身為一位觀課者,我應該如何在這裡?作為一個觀課者,我也是學校的一部分嗎?我仍是耶拿學校的共同體裡的一員嗎?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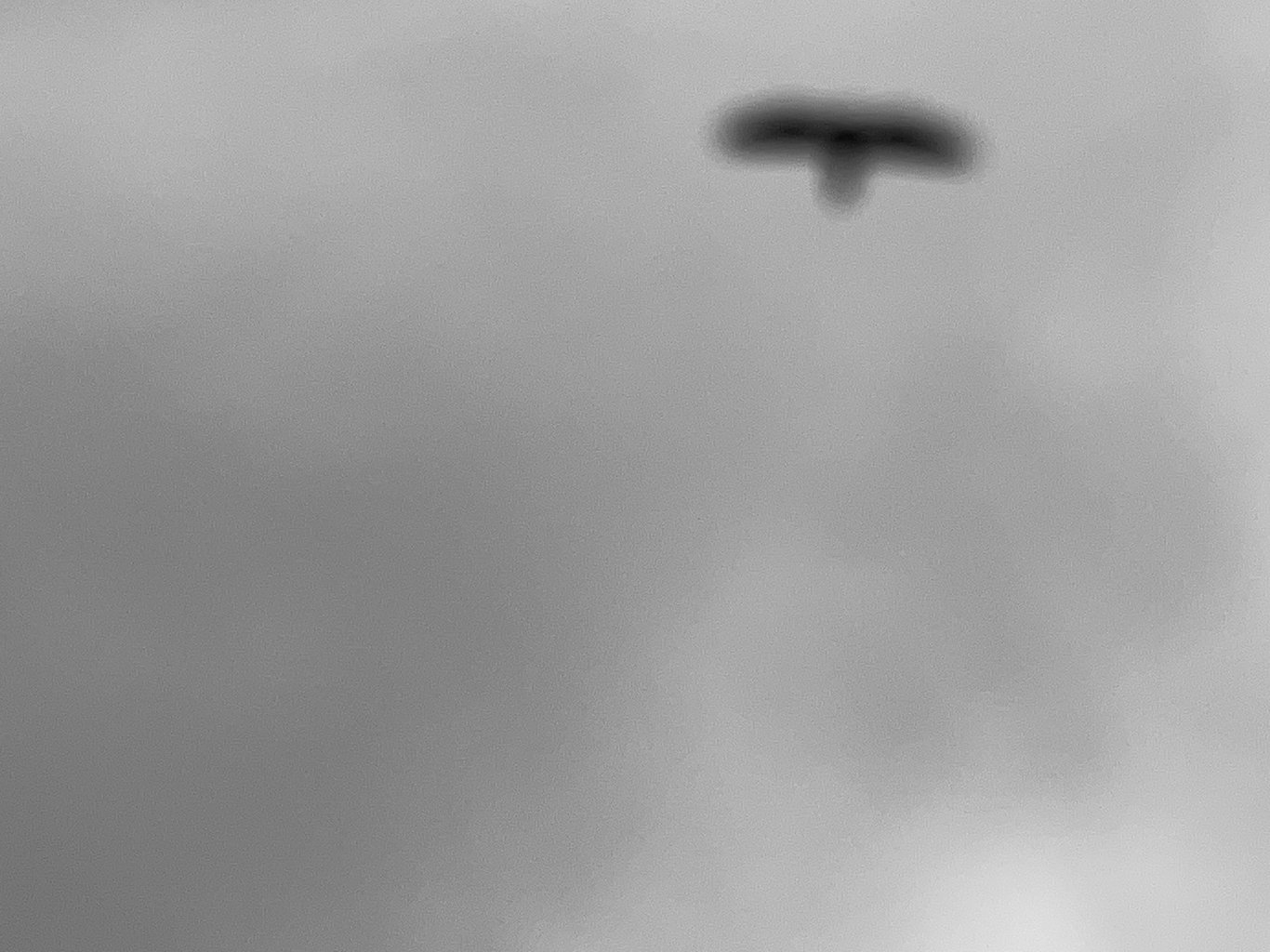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