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泥路驶向黎明

据说我出世那年,全国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
有人说是老天动容。
反正我是听说的,真假不好考证。
但小时候我信,觉得这场雨是为我而下的,给我这人生开了一场预告片。
这也给我的身世平添了一层“神秘感”,直到上了幼儿园,那年出生的人满教室跑才明白
我并不特别,只不过是那场大雨中的一滴,随风落地,安静发芽。
我念的那所幼儿园离家很远,在我还是个没上过高楼的小孩时,
去那里上学的路,就像一场小型远征。
那是KLCC还只是个跑马场的年代,今天你看到的八车道,当时只有双车道,
一辆车擦着泥水过去,能溅你一身社会地位。
家离幼儿园十多公里,正常开车十来分钟。
但对一个幼儿园小孩来说,凡是走路走不到的地方,就是异度空间。
我爸妈非要我念那所学校,是因为它有个传说:
“要进那间名校小学,先上它的幼儿园。”
这个逻辑,叫做人生预购制。从小圈地,划分命运。
那幼儿园坐落在城市中心,不是“村外市区”,而是有大草坪、红绿灯和洋房的真正市区。
我们五点半起床等校车,天还未亮,村里的鸡都还没打卡。
校车每天五点多准时到,车身旧得像战后幸存者,
司机像个闯关游戏的主角,穿越坑坑洼洼的泥路,一站一站点人,
每停一站,就把一个孩子的名字高喊出来:
“阿明!阿娣!阿发!”
全村人听得清清楚楚,想低调都难。
那时候的“叫车服务”,自带“公共广播”功能。
每个上那间学校的新村孩子,从小就没有隐私。
你住哪一间屋,坐哪一辆车,几岁几点出门,全村人都能报出来。
不过我们也习惯了——谁让我们是从木屋、板屋、洋灰屋一路走过来的。
出了村,校车才真正开始“上路”。
我们从泥巴地开到柏油路,像游戏角色通过了第一关。
从新村到街场,是第一道结界。
这段路上还能见到一些老店和摩哆修理铺,人烟稀少但有生活气。
过了警察局,是第二道结界。
路边忽然变干净,车子也变得整齐,招牌少了,草坪多了,
到了兵营和前殖民地洋房的区域,整个世界像换了一套滤镜。
这时候,你会看到那种房子:
大圆柱、大草地,门口得转两圈车才到门,白石膏外墙,看着像西装笔挺的老绅士。
我后来在《上海滩》里才知道,那种是洋房,里面住的不是大亨就是机关枪。
再往前,就是金刚的主场了。
摩天大楼一栋接一栋,反射阳光的玻璃像刀一样割人眼睛。
我那时候常幻想,金刚会不会突然爬出来,把这大楼拆了再原地坐下来抽根烟。
我们的学校就坐落在这些巨物之间,
过了KLCC十字口的左边,一栋全红砖建造的“黎明女校”。
我不知道这名字是不是校车司机取的,
但每次从黑暗中出发,刚好在那抵达的瞬间天光微亮——
你会相信,“黎明”两个字不是随便起的。
进入学校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变优越”了。
我口中所说的“高楼大厦”,对村里孩子来说就是另一种童话。
上那所学校的我们,就像吃了营养午餐的高阶猴子,
可以说得出某栋楼叫“广场”,某种笔叫“自动”,
还可以辨认商场里的电梯声音是不是“叮”的那种品牌。
有一栋楼,特别亮。五层楼高,两座学校那么大。
顶楼有个游乐场,五光十色,无边无际。
据说它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购物中心。
现在拆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它是城市版的迪士尼。
每次校车经过,车上总有人说:“我上星期去过!”
我坐在一旁,冷眼旁观,心想:
“还有谁没去过?”
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校车的窗口,是我们的Instagram。
窗外一幅幅光景,是现实也是诱饵。
它们在催促我们这些幼儿园的孩子——
快点长大,早点搬出去,住进那栋你天天路过的大楼。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阶级”。
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却都在参观一座阶级陈列馆。
你想不看都不行,因为那是开在你命运路线上的广告。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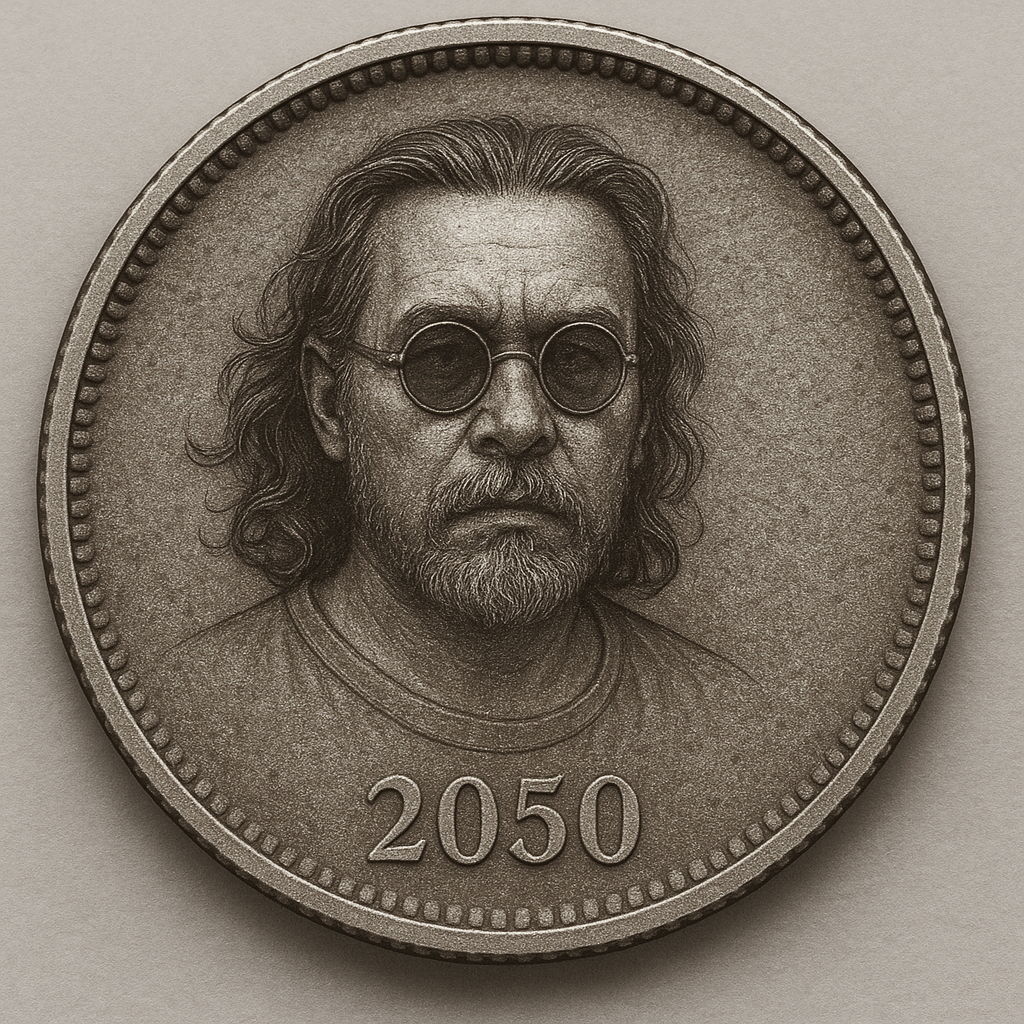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