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識地邁向不可逆的民族形成
來自盧卡奇的提醒「組織做為理論與現實的中介」。
看待任一個人或團體有無「促進民族意識」?端看「具體的實踐」。
「具體的實踐」:不僅是各類文本的表態、或權力制度中的抉擇,而是與群眾締結真實的關係,建構一系列的行動模式,也就是「組織」,得以使群眾就本身對現況的認識,透過民主機制,主動地形成集體行動方案,展現其能動性,而進入一種不間斷地、螺旋向上地意識深化及鍛造意志的過程。各位細細觀察,眼前任一個組織(動態的運作過程),是否是有意識地去建構上述過程?
在盧卡奇的思考裡,就算經過科學的的理論論證,或對國際形勢進行研判,未來理想的政治目標會實現(對他而言是「無產階級革命」),但不能認為一定會發生,而走入歷史宿命論的陷阱裡;而且,就算理論演繹出具有能動性的群眾,來自特定對象(例如:無產階級),若沒有組織者(例如:「共產黨人」的政治領導,也不會讓群眾自覺,而在關鍵時刻採取必要行動去給政權一擊;但組織者的政治領導,關鍵在於如何讓群眾的自發性展現出來。盧卡奇提到:「只有當一個共同體內全部的行動成為每一個參加者最關心的個人事情時,才有可能消除權力和義務的分裂,這種人與他自己的社會化分離,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會力量肢解的組織表現形式。」我無法回應,眼前哪一種組織(一系列地行動、動態的運作過程),能夠使群眾主動積極地與其他人共同行動,但我只能提醒,直觀地想,如果在具體的實踐中,並無嘗試與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群眾締結真實的關係,縱然因為統治菁英趁地緣政治的形勢而達到理想目標,卻可能因為群眾並未透過本身的能動性去深化意識與鍛造意志,不僅可能無法在關鍵時刻採取相應的行動,也可能無法守護運動的成果。這也是目前台灣人在民族意識上的危機:我認為,這就是台灣人透過選舉運動「奪取」中華民國政權,但卻仍有雙重民族認同的原因,這讓台灣人面對戰爭的可能性時,甚至會放棄台灣認同。
「有意識地」條件,如何讓「組織」真的成為「理論」與「現實」的中介
「意識」不應建構在思想上的邏輯推論,應針對在現實中的生命經驗:以台語文社群的實踐經驗為例,由於理論上認為,族群語言做為某族群在地生活的歷史沉積,體現了族群的世界觀及道德倫理,為了抵抗外來殖民者讓族群順服的政治意圖,因此嘗試拾回「母語」。但語言做為一種認同,必得與他人往來才有真實意義,因此創造一個使用母語的社群,這就需要組織(一系列的行動)去達成。這陣子「做伙來講台語、sńg kah 烏 mà-mà 好無?」協會,就針對一般家庭舉辦全台語的親子營隊,營造全台語使用的環境,透過數日短暫的全台語實踐,激勵家庭回歸社區時,仍能在家庭與社區生活中使用台語,並且使認同台灣民族主義者目睹,進而參與此類實踐。另外,此協會在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成立,便與內政部官僚周旋,成功「爭取」以台語文做為協會正式名稱。目前正爭取以台語文名稱去銀行開戶。此協會做為一個「組織」,便是「理論及現實的中介」的展現。
「意識」也不應被個人的生命經驗所限制,應從自我認同(民族、族群、性別、地域、階級等認同)出發,在此之上,橫向地理解他群的生命經驗,縱向的理解我群在真實生命經驗中繼承的歷史記憶:我們個人的生命在誕生時就透過家族的社經地位座落在既得利益者設定的位置上,因此形塑本身的性格,並發展生存的對策。既得利益者以社會性的手段,看似自然地使人經驗一定政治性的安排。我們個人很難透過對自己經歷的認識,就能理解整個統治秩序,僅能因為自身追求人性尊嚴的動機(這動機也來自自身曾面對人性或是去人性的對待而生),而去同理同時代的其他人的生命經驗,這需要與他人建構相互信任的關係才能達成,藉此也才能拼湊出,當前以特定意識形態為基礎,建構的統治秩序,其真實的運作樣貌。而縱向地理解「我群」,也以自我認同出發,挖掘過去「與己擁有相同認同的人」(這決定於形成特定「認同」的當代定義:例如某語言使用者就是某族、擁有某個性徵就是某個性別,辨識出自我認同的歸屬)面臨的苦難,使己探索當代統治秩序的發展的歷史性,洞察其制度演化的路徑依賴,並探究形成眼前秩序的動力,及其在物質上與意識上的機制。(其實「認同」亦是統治秩序的一部份,我們不能無條件接受眼前認同的定義,例如台灣族群分類就是日人站在實際的統治需要,在「科學的」人類學研究基礎上進行分類)
「意識」也不應該由單一個人的敘說,去形成集體的版本。如同各種藝文創作的單一文本,都僅能呈現一時一地的經驗,個人生命的敘說亦然,且敘說角度就具有高度政治性,易於為了當前政治目的去操作成封閉敘事。但也如同同一語族的多元繁雜的藝文創造,呈現出一個民族的精神內容,「意識」應在以真實關係所根基的社群裡,由於成員共同對現狀質疑而針對不同文本(藝文創作,或是之前成員的故事與回憶)進行討論,使這些文本被敘說,被傳遞,這就是「作者已死」,但不是為了美感體驗,而是為了在當前的政治實踐過程中,成員透過對先人經驗的當下詮釋,將願景與透過敘說而得以認識的先人意志連繫在一起,讓我群的價值追求得以具象化,易於理解,成為發想行動的指引,並修正往後實踐的倫理原則。
以上的思考是被盧卡奇的文本啟發,只不過盧談得是階級意識。「意識」絕非個人對某一文本上的思想對話,或是某一知識社群操持某些用語的內部交流,而是政治性地去回應當錢更廣大人群的壓迫處境,因此「有意識」,我認為是「對於真實生命處境的全面理解」,而這個意識過程,應是在介入現實的過程中,嘗試以跳脫個人或是我群本位的他者關懷,在集體裡頭對不同生命敘說,進行多版本的詮釋與理解,但此動力是來自於,為了在介入現實的過程中,確認我群仍以維護人性尊嚴的原則而行動,並未為了政治目標的實踐而迷失,甚至喪失人性。
小結:走向「意識」獨:
從「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的啟發。菲律賓國父黎剎的小說,與黎剎的生平,提醒我們,民族主義「既在地又全球」,而在百餘年後,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裡,網際網路造就的共時性,讓「殖民」不用透過物理性的直接統治,去侵蝕「民族獨立」的意識(已經不用透過出版審查,空飄傳單或是心戰廣播,而是滲入日常的資訊戰),而我等台灣民族主義者,如何「意識」獨立,僅能透過上述形成「意識」的過程,也就是在自覺的行動過程中,本身做為群眾的一員,凝結成組織(一系列地行動、動態的運作過程)。
我在第二部份,其實已經藉由對「意識」的探討,暗示組織,應具有指向現實的、關照多種處境的、多元卻回歸集體的對話過程。形成這樣的組織過程,該有如何的權力架構?顯然,從真實壓迫出發、尊重差異,對等互動及民主決策,可能是此權力架構的幾個特徵。篇幅有限,我無法贅述過去投身運動過程中的「組織」實驗。
最後偏題提醒各位,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台灣人壓迫的根源,我們可以同情「中國人」被其蠱惑,但無須為其找出解放的道路,反而若要解放中國人,台灣人必得先從中國民族主義下解脫出來。這個道理其實來自於左派的教益:若要推翻資本主義,再打倒資本家的同時,其實無產階級也消滅了自己:因為不存在資本家與無產者的社會關係了。而當中國人認為收復台灣,等同讓中國從帝國主義「解放」,台灣人無可選擇的只能消滅中國民族主義,才能真正獨立。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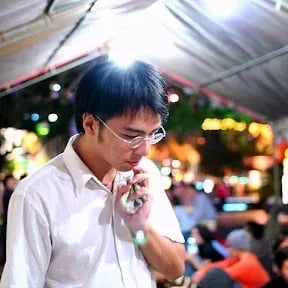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