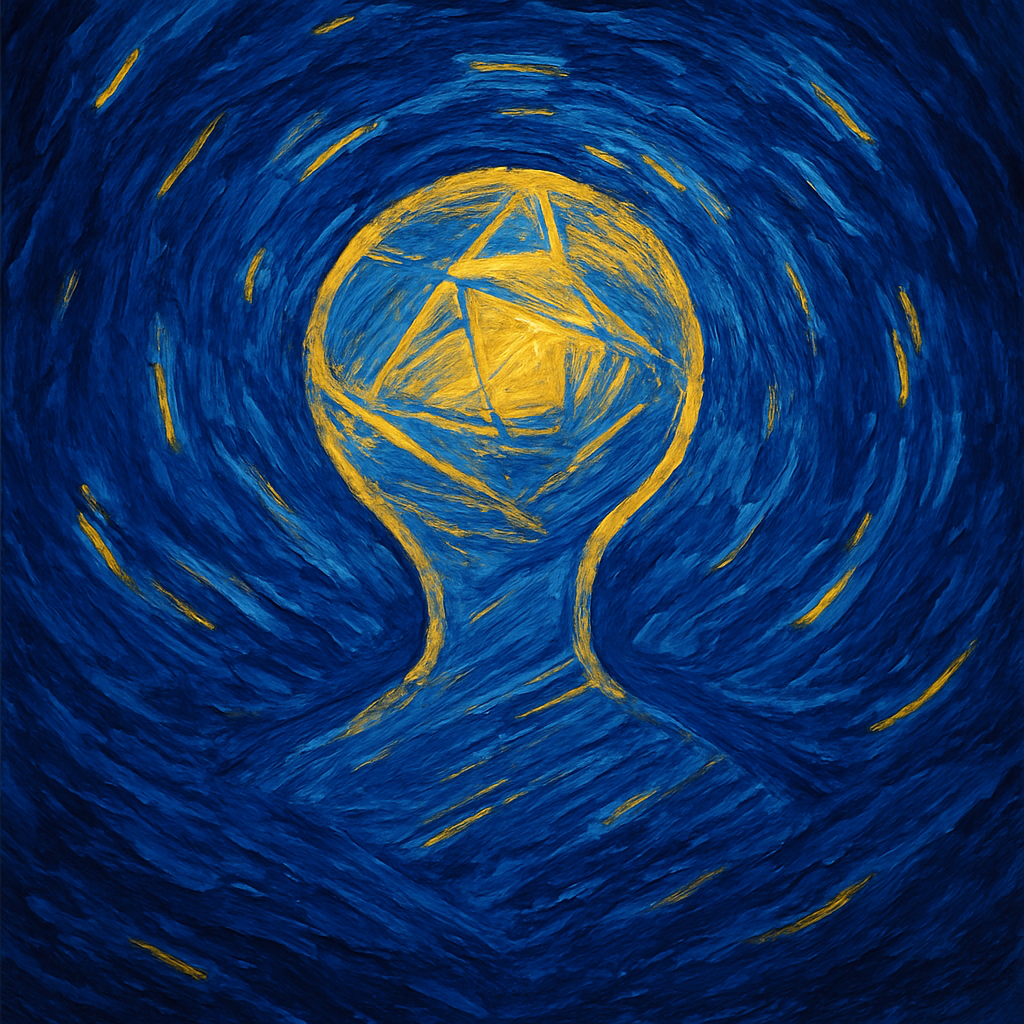同盟
一、
當小茉第一次遇見小末是一個夏天。 那個夏天命運讓她們在摩洛哥相遇,讓她們住進了同一個人家,讓她們同時在一個幼稚園、一個班當臨時的志願者。 命運彷彿一早就寫好了劇本,特別是當她們發現連她們的名字都只差三筆時。
“如果我們將來不能夠是最好的朋友,那這一切就完全說不通了。 小末肯定地這麼說。
小末是張揚和叛逆的那一個,在女人包頭巾的國度,她穿著吊帶裙,披散著白金色的長髮,對每一個騷擾她的男人說 Fuck。 對於男性,她似乎有天然的憤憤不平和戰鬥力,哪怕在環境最不利於她時,她也不懼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小茉顯然更加諂媚,她披著溫柔的外衣。 她最擅長融入背景,在摩洛哥她始終長袖長褲,如果她一個人,沒有人騷擾她。 對於挽著招搖的小末她有些不安,但是甚至在她最深的心底,她對此都毫無怨言,也從未勸過小末“低調一點”,哪怕低調是她的第一要義。
那個夏天很快過去了。 小茉再清晰地記得薄荷藍莓味香煙的味道,也從沒有給自己點上一根。
煙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不是兩個人分一根。
六年後,一個午後,當小茉像一滴沒有顏色的水一樣融在下班的人群中時,她看到小末發了一條帖子。
在那條帖子里,小末穿了潔白的裙子,那裙子於她而言實在簡陋,因為裙子明顯更適合小茉這樣的人。 小末身邊站著的男人也太簡陋、太普通了,普通得像一滴水,可以隨時融在人群裡。
她說她和這個男人結婚了,圖片里還有鮮紅的證書,和結婚文件上鮮紅的指印。
一瞬間,小茉被情緒淹沒,她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淡人其實常態是沒有情緒的,所以她也無法辨別這種情緒是什麼。
小茉打開她倆的聊天介面,明明在過去六年的幾乎每一天里,她們都在聊天,從日常吃了什麼,到黑塞的心理醫生是榮格。 小末分過幾次手,每次分手哭過多少場,她都瞭然於心。
但關於這個普通到像沒有顏色的水一樣的男人,小末隻字未提。
“你們總不可能見面第一天就結婚了吧? 小茉看著紅底白衣的照片喃喃自語。
她突然意識到了自己情緒的名字。
困惑。
她好像有一千個問題想問。
壓抑。
但她不能問。
為什麼不能問?
情緒又回到困惑。
她看著聊天介面的輸入框,猶豫了很久最終沒有敲出一個字來,最終只是給小末結婚的動態點了讚。
那一天過後,她們再也沒有說過話。
二、
在去摩洛哥之前她猛查了無數個關於摩洛哥旅遊的帖子,發現這是一個對於亞洲女性面孔並不算友好的國家。 不要穿裙子,不要披散頭髮,不要直視路人,不要在公共場合喝酒...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上前搭訕,不要回應。
她計劃地很好,如果她嚴格執行這個計劃,她的摩洛哥之行定會非常順暢,她們不會深更半夜被鎖在計程車上要求加車費,不會被當地人追得滿街亂跑,也不會差點被大街上行使的電車撞死。
但小末這個變數打破了所有的安全守則,所以她們深更半夜遇險,滿街逃竄,最兇險的一次,電車擦著小茉的鼻尖駛過。
但如果沒有小末這個變數,小茉對於摩洛哥的記憶也不會那般斑斕多彩,她不會知道摩洛哥的月亮明亮到淩厲,也不會知道馬拉喀什的夜市燈火旖旎,更不會看到蔚藍的地中海和海邊和電影中如出一轍的瑞克咖啡店。
她也不會知道,伴著酒意、月光、薄荷煙,和另一個女孩親吻是什麼感覺。
兩人的初見是單方面的,是小茉先看見對方,正如兩人的告別其實也是單方面的,還是小茉告別了對方。
她是在過海關的時候第一次見小末的,那時輕裝的她已經順利入關,卻聽見身後傳來一聲國罵,再轉頭就看見花枝招展的小末,在罵罵咧咧地轉頭跑去。 她的高跟鞋在奔跑間發出巨大的聲響,伴著海關緊張的呼喊。
有人試圖攔住她,她只是尖叫著重複著自己的護照忘在了飛機上。
小茉看著那個裙擺和髮絲一起飛揚的背影,只覺得她的裙子她白金色的頭髮她的紅底高跟鞋是那麼好看。 自己只敢放在購物車裡默默幻想的一套穿搭,被對方輕飄飄地全部上了身,穿到了一個女人需要包頭巾才能上街的國家。
但這第一面,她只是羨慕地看了看她,然後轉身就走了。
她的志願者專案是包含接機的,但是接機的人告訴她,自己要等兩個人。
所以他們等啊等,終於當等到小末把護照從飛機上拿下來,又取了託運的兩個行李箱,最後慢悠悠地從機場大門走出來。
在又一次看到她的瞬間,小茉心中一面生出期待,期待對方會向自己走來,一面又有暗暗的害怕,擔心自己和這個顯然比自己豐盛的女孩子會完全無法相處。
簡直是上天回應了她的期待,對方踩著恨天高徑直向等待的他們走過來,哈哈大笑著向他們道歉,同時開始開自己的記憶力堪比金魚的玩笑。 當她知道兩人幾乎同名同姓時,激動地抓住了小茉的手,說這一定是命運的相遇,她們必須做一輩子的朋友。
在去往寄宿家庭的車上,小末親暱地給了小茉一個昵稱:小草,因為她的名字只比小末多了草字頭。
她並不反感自己的內向和呆滯,這讓小茉,啊,不,現在已經是小草了,鬆懈下了一些緊張,變得對對方只有羨慕和欣賞。
志願者的工作比兩人想像地都要辛苦很多,兩人早上七點要起床,搭乘電車去往福利院,那裡有大約三個班級的孩子,歲數從三歲到七歲不等,男女分開。 專案里說她們是要「輔助教學」 但其實三個班只有一個當地老師(只會說一點點法語來和她們交流)。
她們幾乎要負責所有的任務,從教孩子們一些簡單的英語和法語單詞,到帶孩子們唱歌遊戲,看護吃飯,監督午休,阻止孩子們的打鬧,都是她們的活兒。 到了下午,她們必須要等到所有的孩子們被父母接走,才能離開。 那時,就已經快到晚上七點了。
但兩人在這忙碌的工作之餘,還是努力地趁著僅有的週末幾乎把摩洛哥的四大皇城去了個遍。
每一趟旅行都堪稱傳奇,而她們在旅途中始終十指緊握。 在馬拉喀什的夜市,兩人品嘗了羊臉和蝸牛,小偷險些偷走小末的錢包,是小草眼疾手快地打開了那隻手。 在拉巴特的博物館,兩人因為是單身女性不被允許入內,她們裝作是一個當地人的妻子,順利進入,小末回頭對那個當地人說他剛剛到達了他的人生巔峰。 在去卡薩布蘭卡的前一天她們一起窩在床上看了電影卡薩布蘭卡,然後在第二天在瑞克的咖啡館前久久佇立。
她們當然還去了很多餐廳,開了許多許多瓶酒,紅酒、香檳、粉紅香檳,借著酒意她們向對方講述了全部的人生和信念,那些人生驚人地相似,那些信念彷彿來自同一顆心靈,而那些因為追求信念而產生的傷口,引起她們幾乎一致的哀悼。
當然,小末始終是更加開放、更加偏執也更加勇敢的那個,她的愛與很都比小草更加深刻,因此她的故事也更加深刻。 有時聽得小草直打哆嗦。
不旅遊的時候她們會在洗澡後來到寄宿家庭的露台,她們住的房間很小,但與房間相連的露台卻很巨大,小草在露臺上吹風,看月亮。 小茉在露台上抽煙,看小草。
從第一天起她就讓小草和她分一支煙,小草起初是猶豫中妥協,再後來習慣,最後甚至主動找小末要煙。
兩人甚至一度開始幼稚地計算一根煙誰多吸了幾口,然後打鬧。
但是,她們從來沒有點過兩支煙。
在離別前的一天,小草還在看月亮。
摩洛哥的月亮非常明亮,亮到如果拿鏡頭對準它,會出現一個完美的圓環。
她被這份淩厲的明亮晃了眼,低頭的瞬間她終於發現小末透過升騰的薄荷煙的霧氣看著自己,她下意識伸手,去要那支煙。
小末卻有些不耐煩地把煙甩到了一邊,她一邊念念叨叨著什麼,一邊站起來。
她光著腳踮起腳尖,用雙手環住了小草的脖子。
她的嘴唇觸碰到了小草的嘴唇。
冰涼又柔軟的,帶著薄荷和藍莓味的嘴唇。
那是兩人唯一一次接吻,小末的生活中總是有很多人,在她們後面每一次見面的時候,她都在其他的感情關係里。
但這個吻讓小草始終相信她們之間是特殊的。
這個吻無關情色,更像是為她們的盟約蓋章:她們從此會一起對抗一些始終在傷害她們的東西,而她們絕不會妥協。
三、
從得知小末婚訊到現在,已經有快三個月了。
小草淡淡的內心,漸漸起來一些波瀾,這些波瀾慢慢積累成一種揮之不去的煩躁,時刻困擾著她。
在夢裡,她一次又一次見到小末,但對方總是對她避之不及。 她從不覺得會橫亙在她們之間的人群,在夢裡好像銅牆鐵壁,她必須得透過層層疊疊的人頭,才能看見對方躲閃的眼睛。
而那雙眼睛,在陽光下像琥珀一樣剔透,曾經多麼明媚地、熱切地、發著光地,看過自己。
就算在夢中她鑿開了一層又一層的銅牆鐵壁,來到小末的身邊,對她大聲地說話,對方也始終並不看向自己。
她每每從這樣的夢中醒來,心中的煩躁就增加一分。
她瘋狂想在現實中求證些什麼,但現實卻也寂靜無聲。
在現實中,小末自從發過結婚照,便再也聯繫過她,也沒有發過帖子,這份沉默和她曾經連手指破皮都要發帖求安慰對比強烈,甚至讓小草一度懷疑對方是不是遮罩了自己,或者那些肯定正在進行的、她們曾經一起吐槽過的繁瑣像交付貨物的備婚流程,單獨遮罩了她一個人。
她甚至懷疑,當初那條婚訊,本就不該被她看見,是被結婚的喜悅沖昏頭腦的小末,忘了遮罩自己的產物。
如果她沒有看見對方的婚訊,至少她肯定會一如既往地向小末分享日常,說一些有的沒的的廢話,連美甲長長了幾寸都要拍成小視頻發給對方。
而她知道,沒有被知道自己要結婚的小末,也一定會用更多的廢話,來回答她的廢話。
或者就算她沉默,小末就會承接主動的責任,發來關於日常的廢話,小草便回應。
這既是這六年間兩人的日常,她倆總是在不同的地方,但她們的盟約一直在。
但現在呢?
她看著她們安靜在三個月前的對話框,有時煩躁上腦她會瘋狂向上翻,一條條文字在眼前劃過,她漸漸就會像做了過山車一樣頭暈腦脹,甚至在胃裡翻湧出噁心的感覺。
但她還是不停地翻找,在那些山一樣的廢話,和小末不停發給她的紅色愛心和“愛你、想你”裡尋找。
她現在確定小末從來沒有提到過這個男人! 甚至,在最近的半年裡,小末都很少和她說男人的話題。
從來沒有!
這是什麼意思? 在見面的第一眼就認定了對方的特殊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第一眼就認定另一個人是特殊,然後決心隱瞞呢? 之前的那麼多個,炮友也好、同性也好、她覺得是靈魂伴侶的男人也好,從見第一面到分手,哪一個她沒有告訴自己?
她其實不怪她結婚了,結婚算什麼呢? 結婚了也可以離婚的,現在離婚率那麼高。
她介意的是:為什麼這個男人,從開始接觸到訂婚都需要隱瞞?
連第一次見面都未曾提及,小草一直以為對方終於消停了,安於單身了,停止對男人愛恨交加了,直到婚訊懟到她臉上。
這不對。 小草因為困惑而煩躁。
她想到自己第一次見小茉,她現在終於能記憶起自己初遇對方時真正的情緒。
那時她在摩洛哥拉巴特機場的停車場,她和專案方派來接她們的司機坐在車上,用她破碎的法語和對方盡力寒暄。 她時不時透過暗淡的車窗往外看,很不耐煩。
小末出現在視野中時,她低胸的吊帶裙,她鮮豔的紅唇和用力過猛的濃妝,讓小草瞬間生氣,對她的著裝也失去了欣賞。
她那時滿腦子都是,不要往我們這裡走,我不想和你一起去做志願者,你穿成這樣,一定會給我惹出麻煩。
但小末步步走近,直到來到她面前,和她隔著車窗對視。
小草那時沒有注意到她的眼睛在陽光下如何剔透,她只感受到周遭的目光追隨著小末,不懷好意地打量她露出的細白的手臂,和豐滿的胸脯。
小草那時近乎咬牙切齒地認定,在這裡如果有任何神明能庇佑她,那得是端著狙擊槍的聖母。
她們的友誼和結盟是慢慢發生的,小草此時終於可以尊重自己當時的感情這樣看清,雖然她突然記不清自己怎樣從近乎蔑視到將對方視作世界上的另一個自己,但她此時非常清楚一個問題。
是的,她終於搞清楚了自己困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什麼? “她在與小末的對話框裡打,她的手指顫抖,指甲落在螢幕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響,好像在敲擊她的心臟。
她的胃也在這一塊劇烈地翻騰,她感覺自己可能下一秒就要吐出來。
如果我們是朋友,那麼為什麼你不告訴我這個男人的事情?
你唯一不告訴我的理由難道不就是... ...
她大聲地喘了一口氣,這口氣在靠近心臟的地方好像卡住了,她發出一聲抽噎。
你唯一不告訴我的理由難道不就是,我們不止是朋友嗎?
她緊握著手機,兩手交握,指關節因為用力而變成白色。
如果我們是朋友,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如果我們不是朋友... ...
小草大聲地喘著氣,最終把輸入的文字一個一個刪掉,她看到自己的美甲,是小末推薦她的一款,紅色的,卵型,長長的。 這指甲和她任何一套行頭都無法搭配,很是滑稽。
如果我們不是朋友,或不止是朋友... ....小草感到精疲力盡,手機從她手中滑落,她刪除了兩人長達六年的對話框,為了保留兩人的聊天記錄,哪怕每次換手機她都要做數據遷移,以保證不丟失這一座廢話的山。
如果我們不是朋友,那我們又是什麼呢?
她閉上了眼睛。
五、
確實是不疼了,小草又是一個理性人了,她繼續自己家、公司、健身房的三點一線,盡自己所能保持閱讀。
但她越來越難以保持專注,她在看到任何情節的時候,都會在頭腦中自動加工到她和小末身上。 於是她決定不再看虛構作品了,轉而看相對專業性的書。
但這下更是完蛋,她看到什麼知識點,都要在腦海裡排練一遍怎麼跟小末講解。
她不在看書的時候,也在腦海中構建她倆下一次見面的場景。 她要對她表示不滿嗎? 還是對她表示祝福,跟她說雖然她們不再是什麼新潮時髦的女性同盟,但是她們有過積極的過往,所以她還是希望小茉快樂。 然後小末會有什麼反應呢? 她對這些反應又該如何反應呢?
她的腦子裡好像有一台放映機,源源不斷地把並不存在的片段播放出來。 而她必須要保證這些片段合乎邏輯,所以她不停地剪輯重拍這些片段,最後再從頭到尾一遍一遍欣賞。
雖然她知道,她們並不會再見面。
但,也許呢?
也許她跟小末之間終究有些真實的東西?
但如果有真實的東西,她們已經真真切切地近半年沒有說過話了,這突如其來的斷聯無法解釋。
所以她對自己確實都是裝的? 小草發現雖然理性上得出了這個結論,但她很難去真正相信它,她們倆之間,確實有過十指緊握、共用一根煙,以及,那個吻。
有無數個細節可以支援她們之間有愛,又有無數個細節可以支援她們沒有。
正是因為無法相信它,所以她腦海中始終有對未來的期待。
但具體又在期待什麼,或者說,在對方已婚的情況下,她又能去期待什麼呢?
之前,哪怕在裂痕還未出現,兩人感情最好的時候,小草也從未期待過兩人具體的未來。
如果有什麼期待,那可能就是,無論發生了什麼,無論對方是在穩定的關係中、結婚了還是有孩子了,她都希望和對方是有聯繫的,在此基礎上,如果還是朋友... ...
理性的大腦按部就班走到這裡,總是著了魔似的一腳油門踩下去,瘋狂的念頭接踵而至。
想要是朋友,是彼此唯一的朋友,想要每天都能看到她,和她說話。
和她一起進行一項事業,和她一起走上領獎台,想要和她一起,十指緊扣,被全世界看到。
停下! 快停下!
她無奈地敲著自己的腦袋。
快停下!
這些都是不可能的。
但她是在問自己想要什麼,又不是在問自己什麼是可能的,所以她的大腦還是像被兩斤二鍋頭泡了一整天一樣呐喊:“我現在就想要她靠著我的肩膀,在我身邊! ”
小草長嘆了一口氣,她並不是沒有過親密關係,這麼多年,她有過幾個男朋友,也還算親密,但那種親密和她和小末是不一樣的,並且總是因為一些現實原因,她最終都會選擇和平分手。
但無論和這些男的相處了多久,哪一次分手都沒有像和小末這次似是而非的斷聯一樣令她無法放下。
甚至,往往在和平分手的當天,她就沒有一滴淚水地走出來了,將對方拋至九霄雲外,如果對方膽敢再次給她發一條資訊,那她立刻放下體面的面具,露出冷漠的本質,往往一句話不說就刪除拉黑把對方打發了。
她想到她有一個前任,在他倆已經斷聯了近五年的情況下,近乎瘋狂地聯繫了他們的共友,拉著共友聊了一下午的和小草的回憶。
共友表面客套,轉頭就電話小草,在嘲笑了她半個小時以後,共友表示困惑。
共友說,在這位前任哥和小草沒有分手時,他們其實是一起吃過飯的,席間前任哥和小草完全沒有交流,也對自己愛搭不理,滿心沉浸在他的業務中,時不時接打電話、用髒話罵客戶。 擺明瞭沒有把桌上的任何一個人,包括小草,放在眼裡。
這件事小草也記了起來,她記得這應該是自己做出分手決定的“最後一根稻草”。
共友接著說,你知道你這位前任哥的記憶中,那頓飯是什麼樣的嗎? 那頓飯無比和諧,我們都在誇你們天作之合,他就是在那頓飯後覺得你們確實應當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小草震驚,那難道還要有人當場指出他倆已經沒愛了也完全不合適嗎? 他怎麼會把寒暄當成真的?
共友補刀:“我第一次見人這麼會斷章取義。 ”
小草驟然捂住了胸口,共友的話那時並且引起她多少的波瀾,但是在現在,在現在小草開始全線懷疑她和小末的過去時,她的心臟似乎無法接受聽到這個詞。
斷章取義。
如果一件事在兩個人看來可以相差那麼大,那麼在她的記憶里,那個被訴說了一百遍的,她們相愛的故事,還有她近來剛分析得到的,小末從不真的愛她的結論,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如果這一切都只是她大腦加工過的電影,和她現在創造出的再見甚至複合小劇場一樣。
都是假的。
她無法再集中精力,匆匆離開辦公室,她一向可靠的大腦被證明不可信任,她必須找到實打實的物證才能繼續去思考這件事情,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但她有什麼物證呢? 在擁擠的地鐵上她絞盡腦汁。
她刪掉了她們的聊天記錄,那麼除此以外她還有什麼物證呢?
小末當然總是想送她禮物,但是她總是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近乎流亡地輾轉。 她甚至一度把自己的所有行頭都壓縮到兩個行李箱,只求能夠達到一個說走就走的效果。
如果有物證,那也在是在小末那裡,她每去一個地方,都會為小末買一點國內見不到的東西,從中東香水瓶到歐洲的玻璃仙人掌擺件。
但她沒有物證... ...
不對,她可能有一本相冊。
這本相冊應該是小末送給她的,她一直不算喜歡,因為那些照片分明都在手機裡,何必非要打出來放進一本巨大又沉重的冊子裡。
也許那些照片的背面寫字了?
她知道這隻是僥倖之心,但還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期待可以有些有跡可循的東西。
來證明什麼呢?
證明什麼都好,她愛她也好,她從來也不愛她也好。
這些都無所謂。
她只是想證明,自己並不是瘋了。
她帶著這樣的絕望回到家,一向整潔的她將家裡翻了個底朝天,每一個行李箱都被她打開扔在地上。
突然,心跳先她一步瘋狂,猛擊她的胸膛,好像下一秒就要隨著翻騰的胃液從嘴裏吐出來。
她不得不跪坐在地上緩上一會。
那本綠色的,偽裝成惠特曼草葉集的相冊。
她瘋了一樣把所有的照片從塑膠封皮里抽出來,一張一張檢查著背面。
空白,空白,空白,全部都是空白。
她面對著照片裡兩個女孩子的笑容,感到心也是空的。
她機械似的從一張一張翻動著這些照片,漸漸開始檢查這些圖像,她一個圖元點一個圖元點地檢查,檢查她們的肢體語言,檢查每一個眼神。
她拿下一張格外長的,回憶起這是她倆去玩一個密室逃脫時拍的三連拍。 她敏感地看出,最後一張的小末看起來有點落寞。
她想到那次密室逃脫,似乎是醫院主題,很難,兩人險些沒有解決,最後還是小末按對了答案,兩人最終拿到成功的徽章。
第一張兩人舉著徽章對視,她自己歪著頭,有些疑惑,而小末卻很雀躍; 第二張她對著鏡頭傻笑,小末還在看她; 第三張她還在傻樂,小末垂下了眼睛。
她想到當時小末在和她解釋為什麼知道最後一步的密碼。 小末說了一個梗,解釋這個梗為什麼讓自己想到答案,但小草並沒有聽懂。
那個梗也許是某一部小末當時非常喜歡的動漫或者小說里的,時至今日,小草當然不記得是什麼作品,她只是突然記起來,自己從來沒有看過對方推薦的動漫或者小說。 她總是打哈哈地應下來,然後拋之腦後。
為什麼呢? 因為小草覺得無聊,覺得這些樂趣“低級”,她只有在對方聊到自己覺得高級的話題時,才參與一二。
但自己和她分享的每一本書,每一部電影,小末都會去看,並認真和她討論。
有時她們和其他人在一起,談話間小末引用了這些作品里的觀點,或者開起相關的玩笑,自己是多麼驚喜。
而自己卻選擇了不給與對方同樣的回報。
只是因為,不夠“高級”。
如果自己連她真正的喜好都需要篩選再認可,那麼自己真的認識過她嗎?
自己真的愛她嗎?
還是從頭到尾,她都只是愛著一種「這世界有人和我一樣」的希望?
因為有人和她一樣,所以她必不是錯的,她必不是假的,她的自我,必然是存在的。
多方便啊,她不需要透過自己厚厚的胸膛和堅硬的肌肉纖維去看自己的心和靈魂,她只需要看向小末。
啊,不,是一個不完整的小末,假的小末,她捏造的小末。
她就能看見自己。
照片從她手中滑落,小草維持著麻木,維持著不痛了的幻覺。
但那些回憶,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但都是小末對她好的回憶,突然如同一團纏繞在一起的毒蛇一樣湧動起來。
她記起在被鎖在黑出租上時,她威脅司機要報警,司機目露凶光,小末擋在她的面前。
她記起兩個人被騷擾,在拉貝特的大街上慌不擇路,一向柔弱的小末突然瘋了一樣跑向她,把她從疾馳的電車前拉開。
她記起自己初見小末的時候,心裡陰暗著想著得有端著狙擊槍的聖母能庇護她。
在旅途中,小草也時刻覺得自己像聖母一樣在保護她,打開小偷的手,把她從推銷的小商販前拉開,在她被不懷好意的打量的時候給她的身上蓋塊絲巾。
但也許事實上,對方是那個端著狙擊槍的聖母。
小末確實引起了麻煩,但總是自己在最後關頭選擇升級矛盾,其實計程車上她們多給錢就能脫身; 其實被騷擾時如果安安靜靜不還嘴就不會被追逐。
但她選擇升級矛盾。
而當她升級了矛盾,小末就端起了狙擊槍。
這些回憶像刀一樣刺穿她,她感覺在心臟和胃之間的位置傳來陣陣劇痛,痛得她的眼淚大串大串從眼眶中流下來。
最痛的不是這些回憶,是她終於明白,她將永遠不知道兩人之間究竟發生過什麼。 她將永遠不知道,那些互相保護是現實,還是她的大腦在近乎刻板地控制著敘事,賦予意義,創造關係。
她不知道,她那一向可靠的大腦是錯的,她賴以為生的理性是盲目的。
她的腦子裡的是一部電影,這部電影主標題叫小草,副標題還叫小草。
它映照了小草的渴望,小草的匱乏和小草的理想。
滿滿當當的。
是根本塞不下第二個人的。
六、
當她知道了,自己所認為的一切都只是常年孤單的大腦,在她的腦袋裡創造出的童話故事,她只感到空蕩。 思維在那個空無一物的地方一圈一圈來回踱步,有時用天馬行空的幻想來裝點它,有時又用無法驅散的疼痛提醒小草。
這裡是空的。
這裏什麼都沒有。
她曾經寄託於幻想、無限膨脹的自我被一根微小的針扎破了,只留下了一個無比虛弱的,僅僅比虛無多一分的存在。
這個自我也許是第一真正被看見。
看見她自己不是通過於小末對比而存在的小草,她原本就有自己的名字,哪怕擁有那個名字的自己,是如此地空洞:
小茉沒有什麼非要說出口的話,那些話語不過是對他人社交行為的低級模仿。
小茉也沒有什麼非要踐行不可的理想,所謂的平權不過是她無法去愛一個人的遮羞布。
小茉不停地走,不停地去嘗試這個,嘗試那個,也只是想在社會認可的框架下有一個最接近自我的存在,好讓她不要在孤獨里發瘋。
但小茉還是在孤獨里發了瘋,她在為自己編織的精美的幻境中發瘋了,因為她其實沒有辦法去相信任何一種非黑即白的論述。
她以前總以為現實是冷的,其實現實只是中性的,是她為自己取暖太久了,已經無法再看見真實的世界了。
看不見真實的世界,這讓她更加孤獨。
她想到,六年前,她之所以去摩洛哥,就是因為她在留學期間陷入持續的,無法干預的低落中,她的醫生建議她出去走走,最好和人打打交道,如果是能説明一下別人,那是最好的。
所以她去當了志願者,這才遇到了小末。
小末真是辛苦啊,當了她六年的解藥。
那現在呢? 自己又要回到低落中去了嗎? 因為顯然她失去了唯一一個最接近同盟的存在。
畢竟連她自己都不是她自己空洞的同盟。
她還有什麼好期待的?
她那無比虛弱的,只比虛無多一點點的自我,還能做到些什麼?
也許她也就這樣了,她會繼續三點一線,專案她也肯定會持續地推進,她也許會取得一些世俗意義上的成就,她反正不回過得很差,但也不會過得很好。
這並沒有什麼問題,又不是所有人的理想都會得以實現的,更何況她根本說不清她是否真的擁有理想。
她於是就這樣活著。
她不再看月亮。
上海的、摩洛哥的月亮,都只是一塊她不再發光,就不會再發光了的石頭罷了。
一天又一天,她覺得自己是一片廢墟。
但詭異的是,這片廢墟卻是會說話的。
它說痛,很痛。
當然很痛,這份痛是在哀悼,哀悼自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東西。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會疼痛,她把自己已經從皮到肉,又從肉到骨地拆解完成了,她已經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哀悼失去的“愛人”,至少不是現實中的。
但她還是很痛很痛。
這份痛是否終有一日會停歇,小茉無法確定,她無法確定這份痛是會停歇,還是反覆不斷的侵襲,亦或是反覆不斷地讓她陷入幻想,飲鴆止渴。
或者,也許這份痛會驅使她不停地看向自己,審視自己虛弱殘缺的自我。
也或許,這份痛會徹底摧毀她,讓她僅僅留下一具軀殼,在廢墟中合著時間的節拍懷著必死的覺悟計算著時間。
但她似乎,總是只能跌落到一個地方,就停住了。
她想要更沉淪,更麻木,但她好像被什麼微弱但非常堅硬的東西攔住了。
在連著哭過幾個晚上後,她總會在某個夜晚沉沉睡去,然後在第二個清晨,起身開始收拾被自己折騰地雜亂無章的屋子。
她好像陷在一個無法脫離的正弦波里,高峰時她的幻想最盛,低谷時她的心最痛,但她從未停止波動,她也無法停止波動,正如她無法真正落入虛無,也無法真正地停下。 她不知道這些力氣來源於哪裡,只知道它微弱,好像一口殘氣,下一秒就會散盡。 但它同時又綿長,它虛弱又堅強地撐住她一步一步往前波動,度過波谷的疼痛,也度過高峰的幻滅。
這不合理。
但在這樣的,一波又一波的重複里,她不得不得出另一種結論。
自我可以被無限條自洽的邏輯保護地密不透風,但自我卻始終不是邏輯,也不是理性。
那些她用來層層武裝自己的論證和哲思,是可悲的防禦。 她以為用精密結構築起一座堡壘,就能保護住內核,可是現在她發現——自我根本不是堡壘內部的君主,它甚至不是堡壘的一部分。
它是什麼? 她現在還不知道。
她只知道,從那個依舊抽象的角落,傳出的深淵一樣的疼痛,是對幻滅的哀悼,也是對自我的殘存渴望。 這個她不曾瞭解也不曾看見的部分,在哀悼著,也在渴望著。
無論她怎麼努力,也無法徹底忽視它、放棄它。 她也許只能選擇看到它。
原諒它。
甚至,也許有朝一日,她可以像對幻想中的小末一樣,完成對它從蔑視到深愛的轉變。
而這份真愛會是真實的。
然後,也許她會做些什麼。
做什麼呢? 她現在沒有答案,但嚴格來說她一直在做些什麼。
是的,她可以做些什麼。
對於外界,她沒什麼好期待的,但她可以期待一下她自己,期待自己行動,期待自己完整,期待自己終有一日,可以看見一位他者,然後愛他真實的樣子。
只是這一次,無論再發生什麼,她要做她自己堅定的同盟者。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