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趟文學愛爾蘭之旅
我是一直愛聽 Van Morrison、U2;也讀過《尤利西斯》、《都柏林人》,看過電影《貝爾法斯特》、《伊尼舍林的女妖》。曾藉由這些作品去片斷拼湊愛爾蘭的模樣,卻在攻略老范這段期間深感不足,他的歌裡有濃郁的靈性追尋,也許並非全然宗教式,但歌詞意境深邃、人文精神豐沛,屢屢提及葉慈、喬伊斯與眾美國垮派詩人之名,不愧是文學愛好者。那些與他生命產生連繫的地名、風景、神話以及悠遠漂泊的情懷,纏繞在我思緒許久,索性找書來看,趁著興頭上一次解決。記得從前好像曾在二手書店看過類似「航向愛爾蘭」之類的書名,便上圖書館搜尋之後發現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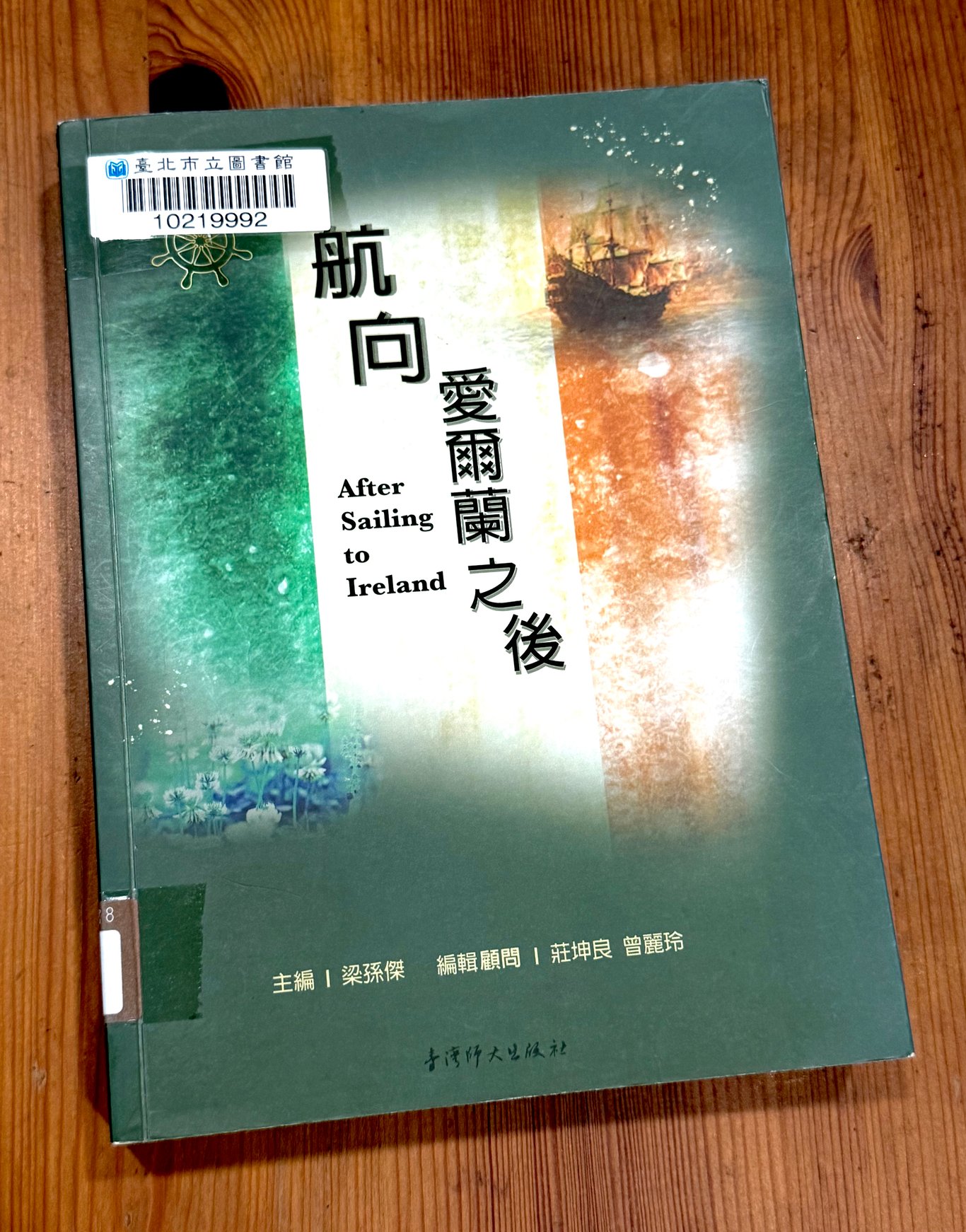
編者梁孫傑教授我知道是今年初方纔上市的喬伊斯巨作《芬尼根守靈》的譯者,來日定當完食它。此書乃論文集子,收錄 11 篇論文,秉持薪火相傳的精神,以多元的視角,從重點研究擴展到更為全面性的愛爾蘭文學研究。梁教授在導讀中說本書書名傳承自吳潛誠(桂冠世界文學經典叢書的企劃)於 1999 年出版《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我才猛然想起對啦這就是我之前在二手書店看到沒買的書,只好馬上再向圖書館預約,同時又加了幾本文中提及的相關著作。
《航向愛爾蘭之後》(2020)
書一開始就提到愛爾蘭長期遭到英國殖民致使人民有種「自我鄙視、缺乏信心、崇尚本源、宗主為尊等文化政治因素混雜交融後所產生的某種輕微語言失能徵候群,從屬階層要充滿自信正確無誤高言發聲,實屬相當艱困之舉。」
若將這段話挪移來當今臺灣,其實和愛爾蘭非常相似:語言從來都是殖民者最想消滅的東西。對照臺語的邊緣化,甚至「支語」氾濫於年輕人間的現象,豈能不與編者同嘆:「臺灣的語言和文化在殖民統治下即將消失佚亡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文學作為身份認同的依存命脈,作為保存語言文化的知識寶庫,自然就成為重要的訴求源頭。」
正是如此,本書開宗明義便串連起臺灣讀者對愛爾蘭感同身受的想像。編者還提到,「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學童,在脖子後方衣領間會插上一根小棍子,叫做『計數棒』(tally stick)。若他們觸犯任何規定(包括說愛爾蘭語),老師就會在計數棒上刻一條線,當天放學前,老師就根據刻線的多寡來決定處罰的輕重。」這豈非和臺灣從前國民黨政府禁止學生在校講台語一模一樣?都看過《狗蛋大兵》裡演什麼吧?
這裡稍微簡述一下愛爾蘭近代史。在被殖民七百多年後,現今的愛爾蘭共和國起源於 1922 年立憲並脫離英國而成立的自由邦,然而深受數百年英國影響的北愛爾蘭地區卻選擇退出,反留在聯合王國之內。會造成這個結果最主要原因是宗教,愛爾蘭多數人信仰天主教,英國人民則是英國國教/基督新教,歧視傳統天主教徒,彼此水火不容。大多數北愛人希望留在英國(聯英派),但北愛境內仍有傾向整個愛爾蘭統一的民族主義者,後來他們更成立愛爾蘭共和軍(IRA),內戰和暴力衝突不斷、死傷無數。直到 1998 年宣布停火、2005 年解除武裝,和平才真正到來。這短短幾年間愛爾蘭由外資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在歐洲名列前茅,贏得了「凱爾特之虎」的美譽。隨後因為泡沫經濟與金融海嘯導致經濟狀況嚴重下滑,近年又復甦,並在英國脫歐之後持續留在歐盟內,卻反令北愛地位尷尬。最終北愛也留在歐盟市場內,以避免在愛爾蘭島上真建立硬邊界。此消彼長的政經態勢導致英國本土出現「Bregret」(Brexit + Regret)現象,難免使得「脫英入愛」的聲音逐漸在北愛增長。
試著把時間拉回和平前,揣摩從十九世紀末葉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直到停火的這一百多年之間,愛爾蘭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書中有段如此說:
某位政治人物:「英國雖不再是世界強國,但畢竟還是個名聲響亮的大國家;和英國合在一起的話,國民平均所得較高,社會福利也比較好。」我認為,這位政治人物的說法只考慮政治和經濟因素,而沒有考慮到文化因素。被壓制了七、八百年的民族,為什麼還一直想要追求獨立?民族情感、民族意識是無法單純以政治和經濟因素解釋的。為什麼今天的北愛爾蘭六個郡的天主教教徒不惜採用暴力,要求脫離英國,併入愛爾蘭共和國?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合併在一起,就政治和經濟上來看,恐怕也沒什麼好處;北愛爾蘭人要求脫離英國的想法,只有透過文化才能充份了解。
括號裡那句,臺灣人聽起來有沒有很熟悉?甚至,我們常常聽到的不是「不再是世界強國」,而是越聽越想睡的「就是世界強國」。有些人只會用金錢去衡量一切,用政治和經濟來定義「強」,但這一點都不能說服人,他們不知道文化的力量,沒有文化才是真正讓人想要遠離的原因。我永遠記得尤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感謝詞: 「祖國不是國旗與國歌,也不是那充滿真理以象徵性英雄為主題的演講,而是一把土地、居住在我們記憶中的人,以及被成染成憂悒色彩的一切。」他們就是不懂,他們就是不懂。
《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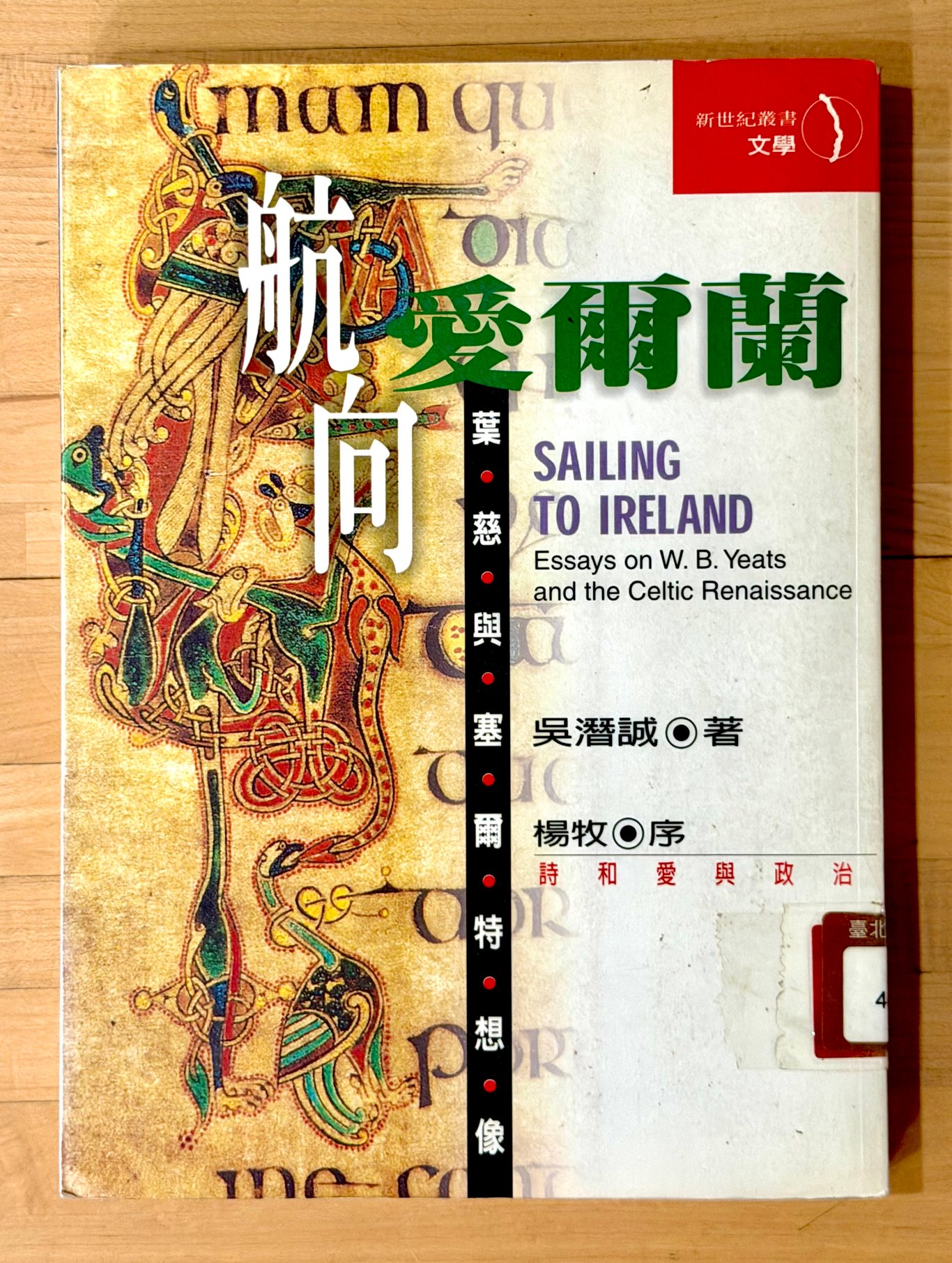
這本好書是吳潛誠教授過世前嘔心瀝血的遺作,他心神嚮往葉慈與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鑽研多年,集結此書。書中從多面向去描繪葉慈,包含文學風格、思想意識、愛情生活、歷史事件,甚至有選譯他的詩作與劇本。此外也論述他民族思想的成因和後果,這忠實反映在其詩風演變上,令他在愛爾蘭文學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承先啟後地位。
談起承先,作者如是說:
愛爾蘭大部分為世人所知的文學,用英語創作,故又有「盎格魯—愛爾蘭文學」(Anglo-Irish literature),「愛爾蘭英語文學」(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等稱呼,但這兩個名稱卻又被認為具有被殖民意識或色彩... 台灣本地的文學不也有相同的問題嗎?「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具有大中國意識,「台語文學」不能概括本島的一切文學創作,「台灣文學」的名稱未能區分出以不同語言(客語、福佬話和普通話)作媒介的文學創作。
他同樣也不禁把臺灣對比愛爾蘭,然後寫到:「冷漠的統派人士對於一切本土的東西都存有偏見,反而對新文學運動構成阻礙。經過質問撻伐之後,葉慈在幾年之內不勝驚訝地發現,統派份子當中也有人對愛爾蘭文學產生興趣了。」這裡的統派當然是指聯英派,但若將其意置換以我們臺灣人眼裡的統派,也是絲毫不違和。土地上的人們生長出本土意識,外人可無置喙餘地。
吳教授還寫到:
愛爾蘭有兩類作家:一種是碰巧出生在愛爾蘭,作品和愛爾蘭並沒有密切的關係,例如王爾德、蕭伯納等作家用英語寫英國的社會或一般性題材,他們只是出身愛爾蘭而已。另一種則是真正的愛爾蘭作家,例如小說家喬伊斯和詩人葉慈及劇作家葛列格里夫人等人便是。葉慈曾在一首詩裡表白,自己誓願歌唱把「愛爾蘭的寃錯化為甜美」,愛爾蘭這個民族有七百多年的苦難,寃錯太多,葉慈要用詩歌加以清滌、淨化,化悲苦為芳甜。
我很喜歡作者的一句話:「葉慈之所以是大詩人,因為他首先是一個愛爾蘭詩人,一個勇於面對愛爾蘭事務的詩人。」更妙的是,他寫到這段時實在難掩激動之情,接下來這段更讀得我拍案叫絕:
相反的,台灣有不少詩人,動輒侃侃而談要超越現實,超越政治;分明是自己對政治欠缺敏銳的感受,却一昧擔心自己的美感經驗中有政治傾向,亟力想撇清任何政治牽連。這一類詩人裝聲作啞成習慣,瞎子或騙子做久了,竟好像真的相信自己已經超越了政治,超越了現實。
葉慈也不乏批評者,主要仍是因為他使用殖民者的語言來寫作。愛爾蘭傳統方言是蓋爾語,但近代會蓋爾語的人越來越少,遑論寫作,葉慈亦然,他曾說:「Gaelic is my national language, but it is not my mother tongue.(蓋爾語是我的國語,但它不是我的母語。)」在後人眼中,譬如愛爾蘭文學評論者兼作家的薛穆斯・丁恩(Seamus Deane)就從民族主義和分離意識出發,認為葉慈是殖民地/盎格魯—愛爾蘭文化的辯護者,不宜稱做現代愛爾蘭詩人。而詩人金瑟拉(Thomas Kinsella)認為葉慈有卓越才能,能夠融會愛爾蘭文化中各股不同的傾向,但可惜卻只選擇「從一個未經清洗的軀幹中特別孤立出一個盎格魯—愛爾蘭文化而已」。吳潛誠歸納寫到:
比較起來,小說家喬伊斯雖然棄絕祖國而去,作品卻與愛爾蘭產生直接而密切的牽連,大量的以新興的中產階級、天主教徒、現代生活為題材,為整體的愛爾蘭提供一面破碎的鏡子。所以,論者常指出,繼起的詩人,大多告別葉慈的孤高姿態,踵繼喬伊斯之後,一脚踩進污穢的現代潮流之中,眼光普及到大多數的愛爾蘭人。
確實,從我讀過的《都柏林人》、《尤利西斯》來看,喬伊斯的書中觸及更多愛爾蘭歷史與當代,走向一個過去沒有同胞前輩走過的路。縱使如此,我覺得葉慈提升愛爾蘭民族精神確實功不可沒,蓋爾語不是唯一能代表愛爾蘭的事物,的確不該任其亡佚,卻也不應是國族主義者的尚方寶劍。
《在黑暗中閱讀》(2017,原著 1996)

從《航向愛爾蘭之後》論文集裡認識這本書及其作者 Seamus Deane,譯者謝志賢將他替本書所寫的導讀文加以增添改寫而成之論文有被收錄於其中。前述認為葉慈不宜被稱做現代愛爾蘭詩人者就是這位 Deane。因為感覺該文中對小說故事的描繪頗有啟發性,既然有中譯本則來讀之,讀完之後頗為喜愛。
這是一則關於背叛的故事,一個被認為出賣了北愛革命同志的叛徒導致其家族後代倫理與人際關係衰敗崩塌。譯者說「丁恩的小說直指從十九世紀以來愛爾蘭抗暴、反英國殖民歷史裡層出不窮、也最令人不安的『背叛』主題。」事實上兩百多年間多次愛爾蘭抗爭運動屢次失敗大多肇因於自己人的背叛,就像喬伊斯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所說「愛爾蘭是一隻吃掉自己幼子的老母豬」。小說裡背叛的對象有戰友、政治信仰、愛人、妻子、孩子等種種型態,甚至即便號稱最為親近的人也無法讓人確認是否曾經真正認識過背叛者,其人洽如「影子」,所有關係人對他的認識都如真似假。纏繞多年的謎團、疏離與不諒解最終只能藉由時間來沖淡與抹逝,令人喟嘆。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2022,原著 1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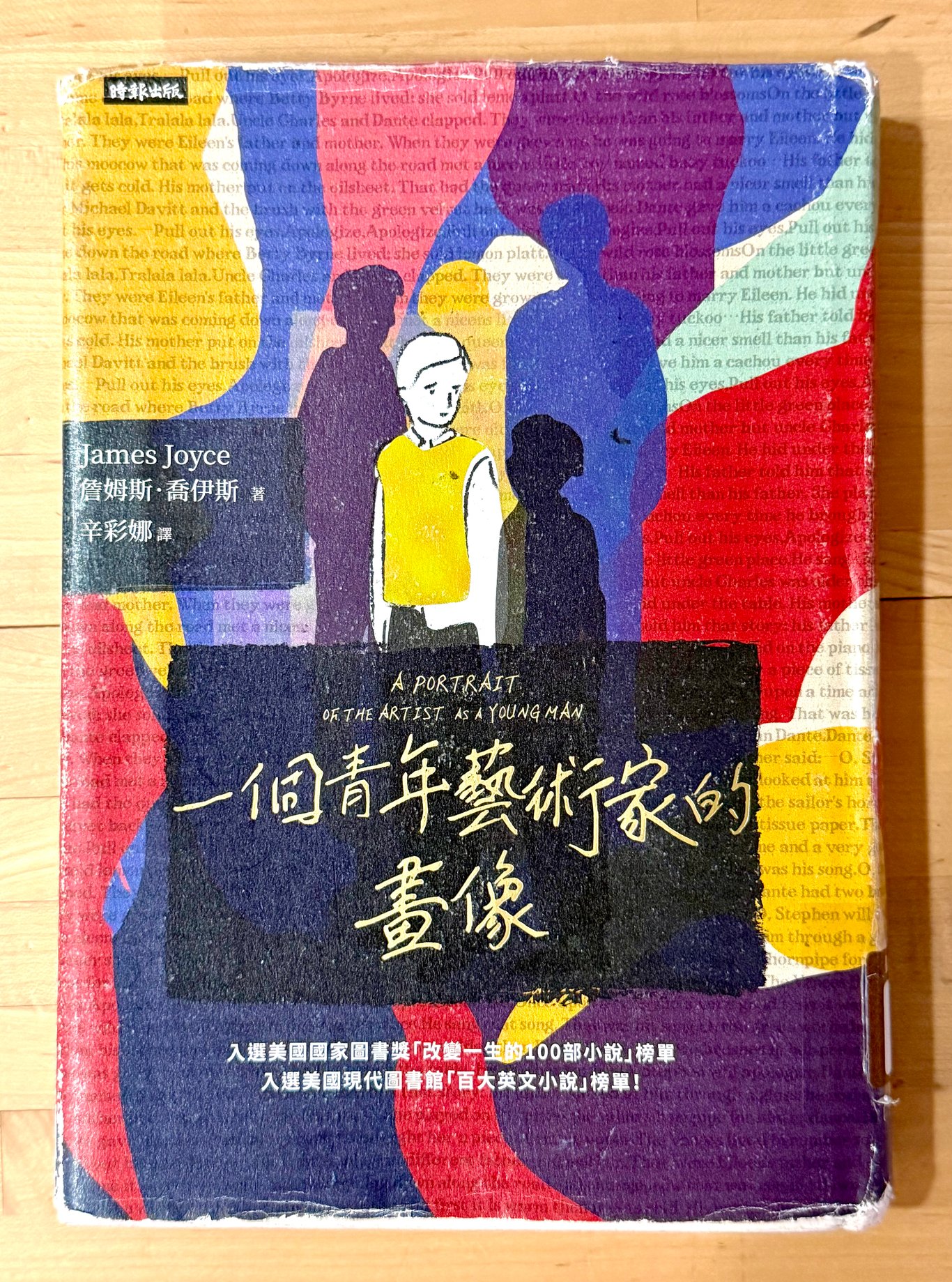
一般來說,北愛或歷史上英國人的觀點是因宗教和政經社會地位而歧視愛爾蘭人,但就連愛爾蘭人自己都覺得他們民族「瀰漫腐爛氣味,因為都關著窗戶,拒絕讓新鮮空氣進來」,譯者在導讀中如是引述。所以前述吳潛誠教授認為從喬伊斯一脚踩進污穢的現代潮流中起,拒絕再用民族意識綁架自己,反而直面污穢不堪,這對於後代愛爾蘭知識分子的良心形塑甚巨。
自以為的自由其實只是虛假的外在自由,內心還是因為各種傳統教條而緊縛滯悶。也許在喬伊斯眼中,葉慈和那些愛爾蘭文藝復興圈中的人士盡皆如此,還是跳脫不了另一種的主流思想。看他如何描寫主角斯蒂芬:
他命中注定要踽踽獨行,尋找自己的智慧之路,或是在遍歷世間陷阱之後,獨自去摸索別人智慧之路的奧祕。
他走過顫巍巍的木橋,又踏回堅實的土地上。就在這時,他似乎感到一股冷氣襲來,側身望去,只見狂風突起,水面黑壓壓一片,浪花飛濺。他心下一沉,喉頭一顫,再次意識到自己對大海那像人一樣的冰冷氣味是何等懼怕;但他並沒有向左拐上沙丘,而是徑直沿海邊那條通向河口的石堤向前走去。
去生活,去犯錯,去墮落,去征服,去從生命中創造生命!他面對的是一個狂野的天使,代表著塵世青春和美的天使,她是來自美麗的生命宮廷的使者,在一陣狂歡之中為他打開了通向一切罪過和榮耀之路的大門。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斯蒂芬從家鄉、學校、宗教中出走,就像喬伊斯 22 歲就遠去歐陸展開流亡生涯,並在 30 歲最後一次離開愛爾蘭後終其一生未再踏上故土。斯蒂芬和朋友的爭執時脫口而出的心境,就是喬伊斯本人的宣言:
當一個人的靈魂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時候,立刻就會有很多大網把它罩住,不讓它飛走。你跟我談什麼民族、語言、宗教,但我就是要衝破這些大網遠走高飛!
幾年前看《尤利西斯》,在不熟愛爾蘭歷史的狀態下看得懵懵懂懂。現在看《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前已經打了不少底,才能清晰感受到喬伊斯的特立獨行。「我們兩個人談話使用的語言先是他的語言,後來才變成我的語言。……對我來說,他的語言既熟悉又陌生,永遠是一門後天學來的語言。這些詞不是我創造的,我也沒有接受。我的聲音拒絕說這些詞。」英語和蓋爾語,到底該如何選擇?這是他身為愛爾蘭人對語言被同化的深沉無奈。喬伊斯不想選邊站,最終他選擇大行己道、玩弄語言,開創另類立場。
譯者的一段話我認為可以為這部小說做總結:
主角斯蒂芬在身體的流亡之前,便早已開始了精神的流亡。雖然身困都柏林,但在精神上斯蒂芬總是與主流保持著理性的距離,對於當時的愛爾蘭來說,文化主流就是癱瘓的中心,桎梏著愛爾蘭人的身體和靈魂。斯蒂芬的自我塑造是建立在對都柏林盛行價值觀的否定和批判之上的。
其實雖然身在流亡,精神卻被都柏林牢牢綁住的喬伊斯,藉由他小說主角斯蒂芬之口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在自己心靈的打鐵店治煉尚未被創造出來的我的民族的良心。」不像葉慈那種「盎格魯—愛爾蘭人」在擁抱民族主義時有著曖昧的身份標籤,喬伊斯直接超脫於標籤之外,終成一方大家。
聆聽 Van Morrison 之旅抵達終點,卻開啟另一段文學上的愛爾蘭想像旅程。那些字裡行間的萬千煙雲,從歌詞幻換成文學,於是我的十一月,很愛爾蘭。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