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幽灵在游荡
我先前写的文章中一直很小心避免使用“主义”类大词[1],因为很多人(尤其是从事人文社科学术的)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都默认别人知道含义,言谈举止间洋洋洒洒地使用了一溜不加解释的学术名词,自己是说爽了,听者可遭殃了。当然他们也会辩称这些话是给同行/同好听的,如果什么都要解释,那就成搞科普了。不管怎样,这件事见仁见智,而我属于尽量对路人小白友好的行列。
之所以唐突说这些,是因为本文将要围绕着“后现代保守主义”(Post-modern Conservatism)一词展开——看到这个词,没学过理论的人会感到迷茫,学过理论的人可能会感到混乱。不要急,首先这个词可以拆成两部分,“后现代”和“保守主义”,接下来就对这两部分一一解释。
说到后现代,也就是“现代之后”,那就必须同时解释“现代”这个概念,这里偷懒直接从以前的文章中复制过来:
所谓现代是在与古代(或者说前现代)的对比中才有独特的意义,现代的特性称为现代性,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称为现代化。现代由多个部分组成,经济上,是追求效率和增长的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形态(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对比前现代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形态(或者说小农经济);政治上,是平等的个人之间建立契约而形成的国家,对比前现代君权神授、遵照传统(也就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将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的王朝;思想上,是个人的、理性的、进步的价值成为核心,对比前现代人身依附、敬畏上天(也就是“封建迷信”)、因循守旧的思想。
正如现代是对前现代的超越,后现代也是对现代的超越。经济上,是从工业化时代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力至上、“基建狂魔”)转向后工业化时代以消费为中心(追捧网红爆款商品);政治上,是从意识形态斗争(主要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转向微观权力斗争(比如批判日常用语中的“辱女词”)。思想上,是从对启蒙理性、线性进步观(认为历史必然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个目标进步)、普遍真理(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任何一个声称能解释世界的理论)的推崇转向怀疑理性、多元视角、解构宏大叙事。
当然,以上这些是我理解的“后现代”,在其他人那里会有不同版本的解释[2]。如果看完后,对后现代还是感觉摸不着头脑,那我将尝试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明:
前现代:上帝创造世界
现代:上帝死了
后现代:原神,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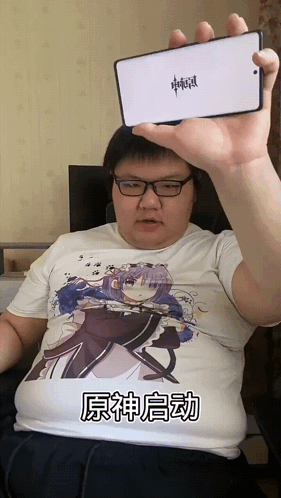
说完后现代,再来说保守主义。日常使用的“保守”一词,当作为形容词时,其含义范围可以从小心谨慎到固步自封再到迂腐落后,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代表着一整套政治理想(正如其同类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其核心理念是抵制变革、维护传统,具体表现可以参看那些自我标榜为保守派的政客,其观点总是离不开上帝、教会、传统、家庭、秩序之类[3]。
到这里如果都理解了,那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按照上面说的,“保守主义”应该会极力反对“后现代”(毕竟连现代也一起反对了),那“后现代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如何成立的?这是因为保守主义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哪里有对进步/变革/加速的逆反,哪里就有保守主义的土壤,正如最初的保守主义诞生于对法国大革命的逆反,如果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那也不会有保守主义。
这种经典的保守主义(为方便论述,称其为“传统保守主义”)追求的是前现代统一在共同的神圣信仰(不管是西方的一神教还是中国的儒家伦理秩序)下的一个各安其位尊卑有序的社会,主张的是守成,只要守住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好。很不幸的是,在当下,传统保守主义往往体现为一种“文化保守”或“个人情怀”,因为现代化已经彻底改造了社会,没人相信这个社会真能回到前现代的“黄金时代”(即使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势力也做不到)。
传统保守主义的衰落并不代表保守主义的消亡,因为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保守主义的更新换代(为方便论述,称其为“新保守主义”[4])。新保守主义是在现代化已是既成事实,外有苏联阵营威胁,内有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情况下诞生的,它务实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反文化运动带来的冲击和失控踩刹车。于是,新保守主义在拥抱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部分),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来捍卫自己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和宗教价值观,这就和传统保守主义显著区别开来,典型代表是里根、撒切尔、布什等领导人。
新保守主义风光了几十年,熬死了苏联,但还是迎来了自己的衰落:全球化掏空了普通人的社区,工厂搬走了,工作也没了,而“建制派”精英们依然稳坐钓鱼台,贫富前所未有地两极分化,这让普通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随着全球化遭遇危机,这套说辞也破产了。然而,这依然不是保守主义的消亡,因为新的保守主义从它的废墟上又诞生了,以川普的异军突起为代表。实际上,关于川普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有很多名词,有说是“另类右翼”(Alt-right),有说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有说是“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还有专门造了个“川普主义”(Trumpism)的。本文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名词上面再叠一个上去,也就是“后现代保守主义”。

上文已经说过,哪里有对进步/变革/加速的逆反,哪里就有保守主义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现代保守主义就是乘着反全球化和反建制派的浪潮,对“全球主义者”展开激烈斗争。然而,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眼看着要破产,但它的影响已经挥之不去,也就是上文论述的“后现代”这一状况。后现代解构宏大叙事的特性使得过去的保守主义(即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那点神圣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导致后现代保守主义者虽然也热衷于标榜那些符号,但实际上并不真心相信这些(至少没有过去的保守主义者那么虔诚)。
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福音派,这个群体被称为川普的铁票仓,然而现在热衷于自我标榜为“福音派”的人,并不是从神学上将自己认定为福音派,而是反对堕胎、反对 LGBTQ、反对“觉醒”(woke)、支持拥枪、开大排量皮卡、反对公立学校、反对疫苗、反对深层政府(Deep State)等观点立场的集合体,只要你支持这些,那你就可以是福音派。反之,一个虽然在神学上符合福音派,但不支持这些观点的人,就会被开除出福音派行列。

行文至此,包含“后现代保守主义”在内的三种保守主义就解释完了。当然我不是专业研究保守主义的,这个划分说到底是外行在盲人摸象,肯定会遭到保守主义者的反驳,但无所谓,因为我研究保守主义其实是为了思考另一件事,就是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基于共同的特定身份(如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开展的政治活动,目的是维护自身群体的利益,争取社会承认和相应权利。它的出发点是传统的阶级(将人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国家(将人视为均质的公民)等宏大的视角只能关注到普遍性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特殊身份群体的独特困境。例如,一个在工作时受到上司欺压的社畜工人回到家里打老婆出气,这件事就没法用阶级来解释。
“身份政治”这个词表面上看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但它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批判父权制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LGBTQ 反抗警察歧视的石墙暴动。身份政治往往被视为左派/进步派的社会运动,因为它在过去几十年间让少数族裔、女性、LGBTQ 等边缘弱势群体能够发声争取权利、反抗歧视和压迫,揭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不公,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然而,身份政治在当下正面临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过度强调群体差异,这导向了对身份的无限细分,身份从分析问题的视角变成用来给自己“叠 buff”的标签,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为了竞争谁更“受压迫”,谁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而滑向“比惨竞赛”,结果导致曾经团结起来共同争取权益的身份现在却陷入了分裂。
比如 LGBTQ(后面还能续很多字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团结的群体,共同对抗恐同恐跨的异性恋霸权社会。然而,随着运动取得初步成功(非罪化、婚姻平权、反歧视立法),LGBTQ 群体进入社会主流视线,内部的张力和分歧开始浮出水面:LGB(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是在性别二元和顺性别(即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根据生理特征被指派的性别一致)下才能成立的性取向概念,而 TQ(跨性别、酷儿)是对这个框架的根本冲击,跨性别挑战了性别认同(gender)必然和指派性别(sex)一致的观念,酷儿则是解构了性别二元,将性别变成了流动光谱。不仅是在世界观上出现了分歧,还有“富裕白人男同性恋”和“贫困有色人种跨性别女性”这种在阶级、种族和性别等身份上都有巨大差异,利益诉求也相差甚远的情况,这就导致原本的彩虹联盟变得越发松动,发展至今出现了仇男的女同、仇女的男同、恐双的同、仇男的跨、仇女的跨、排跨的 LGB、二元跨和支持保守派的“三好 LGBT”等更小的群体——这并不是在玩排列组合,现实就是如此。

说到这,如果你还记得前文的内容,是否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我们忽略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内容,只看它的底层逻辑和行为模式,就会得出一个破天荒的结论:身份政治和后现代保守主义,看似位于政治光谱上对立的两端,实际上却是惊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思想上,两者都是宏大叙事、共识政治崩塌后的产物:后现代保守主义不再相信保守主义前辈们信仰的那些神圣传统,身份政治同样不再相信老左派信仰的“人类解放”“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大团结”。曾经“阶级”是能团结大众的最大公约数,然而,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下,阶级被解构了,它被认为过于简化,无法解释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压迫,于是每个人在发言时都得先“Check your privilege”(检视你的特权)。这种解构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看到曾经被阶级等宏大视角掩盖的困境和不公,但它却导致任何试图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都能被找到各种刁钻的角度加以指责,最终剩下的只有无限细分的身份 buff。
组织上,两者都以“共同的敌人”为凝聚力: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全球主义者”“精英白左”,身份政治的共同敌人是“顺直白男”,一个聚集了主流特权(顺性别、异性恋、白人、男性)的万恶身份。然而,随着身份的细分,敌人从外部走向内部——上面那段排列组合我就不复读了。总之,这种“大清洗”“抓内鬼”的盛行,使得维持身份内部团结的主要方式是不断找到新的共同敌人,这导致不同身份间越来越无法对话,只剩下相互仇恨。
行为上,两者的政治实践都充满了“抽象”(此处为简中网络用语的那个含义)的表演:后现代保守主义者热衷于开皮卡、戴 MAGA 红帽、挂邦联旗和加兹登旗;身份政治倡导者则是使用时髦的进步术语,审查流行文化并“取消”那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这些行为很多时候和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公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种身份的表演,并获取道德上的优越感。

最终,两者共同走向了小圈子小团体式的存在方式,对内需要“表忠心”,随时准备进行“纯洁性测试”,对外要向敌对小团体“开战”,不能有一丝心软。于是,政治不再是全体国民之事,社会共识只能依靠选举来维系(但谁能保证选举就能一直进行下去?),这种情况倒是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叫“部落主义”(Tribalism),意味着社会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部落式群体,每个部落的成员都对部落有强烈的忠诚感,同时排斥其他部落的成员,这有一种返祖的美。
至此本文的主体就论述完了,但还没有完结,因为我说了这么多,说到底都是在讲欧美(主要是美国)的事,即使再怎么讲出花来,体感上依然只是隔岸观火看热闹,于是此时必须要有一声灵魂发问:难道中国真就没有这种情况吗?
总有人抱怨现在社会戾气重,上个网再怎么小心翼翼也很难避免发生摩擦争吵;曾经只属于局部摩擦的地域问题,到了网上让全体网民都同频共振起来,各种地域黑推陈出新大行其道;到了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交圈(如二次元)也并不安全,因为网友处处都是雷点,如果不仔细看各种“避雷提示”,一场口水战就会在所难免,如果进入的是饭圈,那更是会血雨腥风;更不用说性别对立已经成为简中互联网上长盛不衰的头号流量话题[5],无论男女都不乏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的发言,批斗“龟男”和“婚驴”更是这个领域喜闻乐见的节目;即使是在中国受到官方打压,因而更倾向于抱团取暖的 LGBTQ 群体——尤其是其中与主流传统文化更不相容的跨性别——也在不断内部分化为更小的、专注于肃反的小团体(如清蒸协会)……谁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后现代保守主义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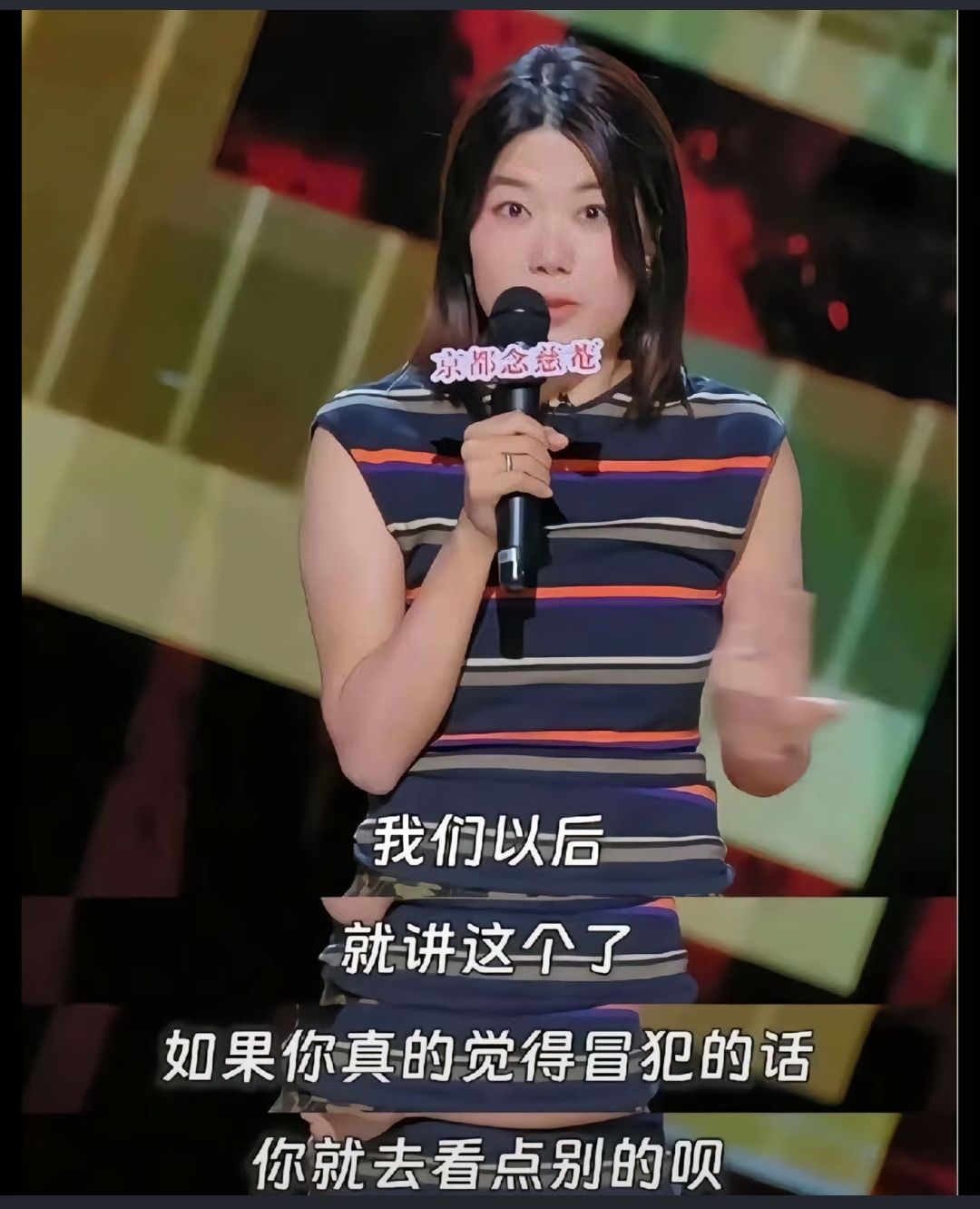
这就是本文最想说的东西。至于社会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后记:写完本文后,突发奇想尝试搜索“Post-modern Conservatism”,结果发现有人已经提出过了,但一点进他的文章,大量的哲学术语就扑面而来,最终决定不用来做参考。
注:
[1] 题外话,现在中文里“主义”这个词被滥用于翻译各种“-ism”后缀的英语词汇。
[2] 如果想深入探究后现代这个概念,可参考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一书。
[3] 这里隐藏了一个问题:保守主义究竟是一个仅适用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概念(这是现在说到保守主义的第一印象,或谓之“英美保守主义”“欧陆保守主义”),还是说它的定义具有普适性,只是各国要保守的传统不一样(于是“中国保守主义”也是可以存在的,比如表现为尊孔复古、国学汉服)?
[4]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多用来指美国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我找不到更好的概括词了。
[5] 性别对立之所以能成为头号流量话题,并不全是因为中国的两性矛盾本身很严重,还有官方有意将其打造为互联网情绪泄压阀的因素在,此处按下不表。
作者:ConsLibSoc
本文得到了 Gemini 的协助,封面图由 ChatGPT 生成。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