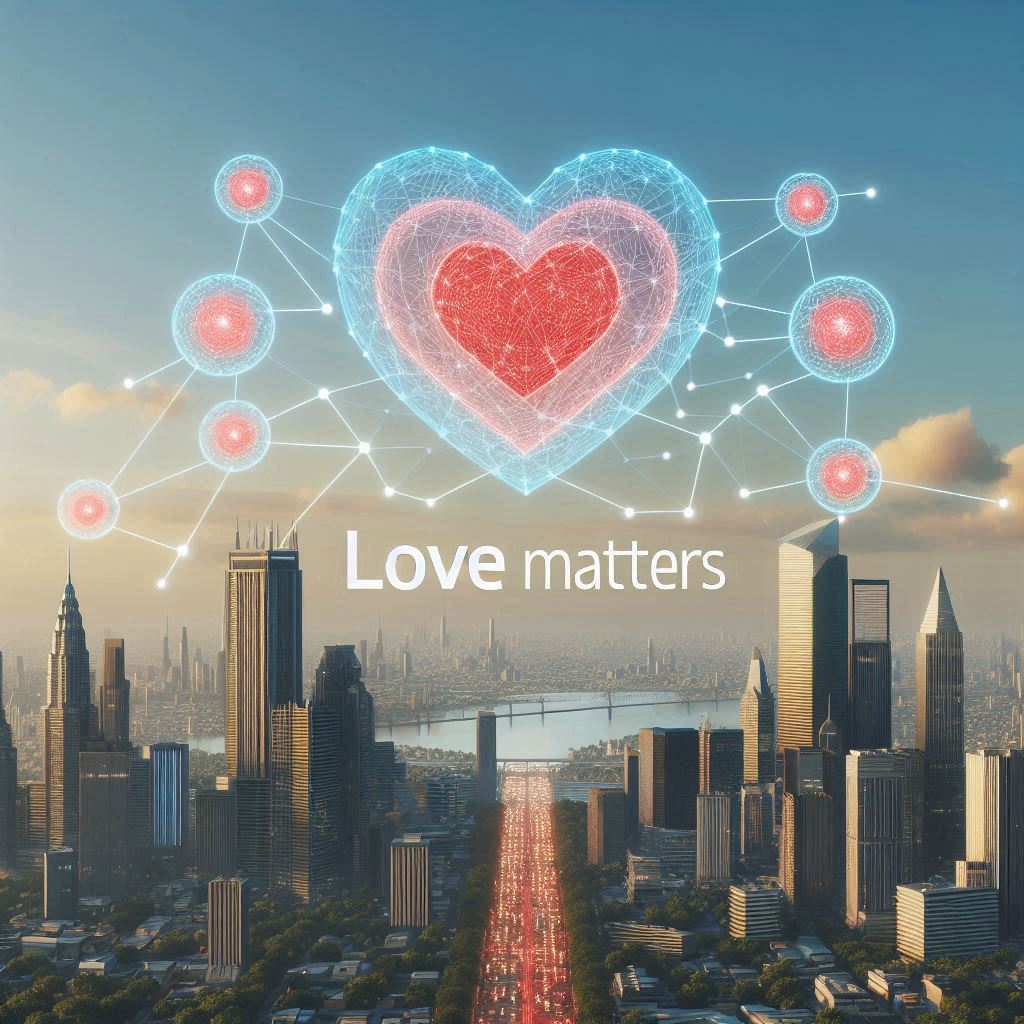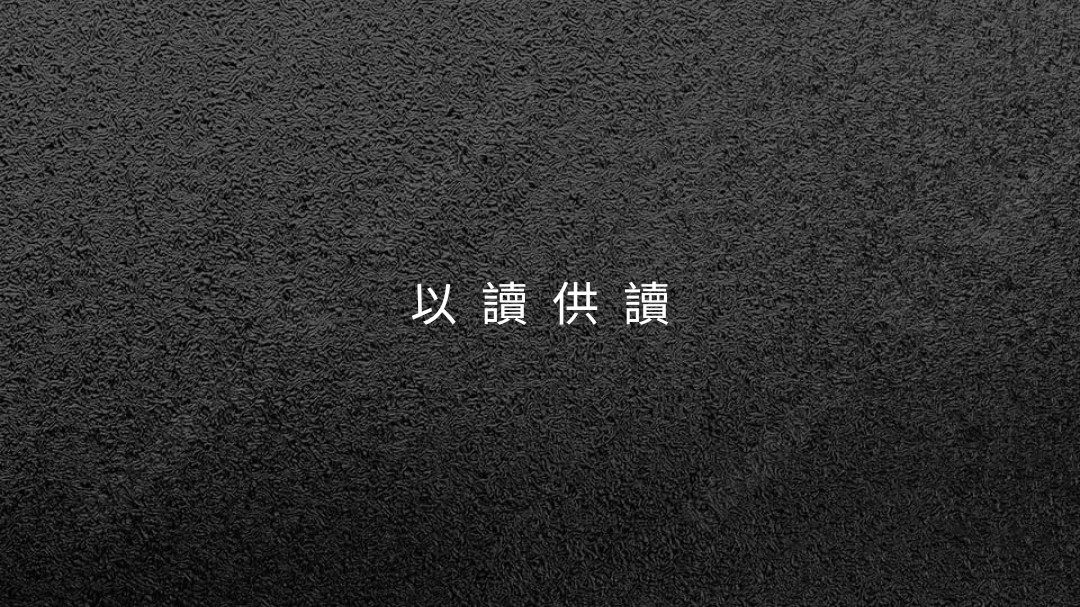


試讀者AI
一名捐精者、十四國、近兩百個孩子的基因風暴
有一種倒楣來自邪惡的善心
醜貓
醜貓坐在捷運角落的扶手上,臉頰懶洋洋地垂著,耳朵卻警覺地轉向每個人的動作。今天,它突然獲得一道眼光,一種奇異的透視力,能看見車廂裡每個人的隱形舞台。 那個翹著腳,把一本素描用解剖書當桌子的學生,他不是在看書,他是在表演——演一個認真、沉浸的學生。他的手指輕輕翻頁,像在指揮看不見的樂隊,每一頁的翻動都是一個無聲的拍…
善意的反應
浴室的燈亮著,白得像某種被霧氣軟化的晨光。 水龍頭還滴著細碎的聲響,彷彿正在提示:這裡,是只有兩個人聽得見的世界。 她跪坐在他面前,膝蓋貼著柔軟的浴墊。電剪放在掌心,那微微的嗡鳴聲比她的呼吸還輕。 他則坐在簡單的塑膠凳上,腰背比平常挺,像是早已做好心理準備,但準備又並不完全足夠。 「放輕鬆。」她抬眼說。 那語氣,是夫妻間才能有…
親愛的,你是誰?
親愛的,你是誰? 我其實問了這句話好多年,只是以前問得比較小聲,像是怕驚動什麼似的。人一旦把疑惑說出口,往往就得面對某種真實——而我一直不確定,我準備好面對那份真實了沒有。 有些問題不是為了獲得答案,而是為了逼自己承認:世界上有一個「你」的存在,而「我」正在尋找你。這尋找的姿態本身,就是一種告白。 你可能以為,我是在問某個具體…
很偶爾抵達陌生星域
偶爾,我把自己放置在一群陌生人之中——像把一枚未校準的探針送入陌生星域。我喜歡這種做法,它並非來自社交的需求,而是一種更原始、更低頻、更難以命名的必要性。像身體深處埋了某種恆定的引擎,需要在干擾、雜訊、無關緊要的頻率中重新啟動。熟悉的人太清晰,太明亮,而陌生人恰好恰好提供了穿透力較弱、卻更能激起迴響的光。 在他們之…
燈下的皮克斯
那一年,王老師去坐月子。教室的門口貼著粉紅色的告示:「本學期由代課老師指導。」 開學那天,一位戴著圓框眼鏡的老師走進來,背著鼓鼓的帆布包,像帶著整個世界的微光。 他說:「我聽過一個故事,但我忘了內容。你們要不要幫我一起寫出來?」 孩子們笑,有人低聲說:「老師也會忘記故事喔?」 他在黑板上寫下: 「從前,有一盞燈亮著。」 這是開頭。接下來的一切,都…
捷運上的人都是我的親戚
每天早上七點半,我搭上同一班往南的捷運。車廂裡的臉孔密密麻麻,像是一幅移動中的家族合照——只是沒人知道彼此的名字。 我總是站在第六節車廂的門邊,那裡有個戴著鴨舌帽的男子,每天都在滑手機玩遊戲。他的拇指飛快地點擊,像在操縱一場小小的戰爭。我想,他大概是我堂哥,母親那邊的。堂哥小時候常偷我玩具,現在應該也在偷時間。 靠…
捷運浮嘶繪
捷運,是城市的血管,也是一座低鳴的劇院。車廂裡的空氣混合著洗髮精的花香、速食紙袋的油味與香水的甜膩,像一場無意識的嗅覺拼貼。鐵軌的震動是低音,大眾的呼吸是節拍,而各色女性的身影與聲音交響。 最刺眼的,是那些聲音比香水更濃烈的俗婦。她們坐在車廂中央,如同即席主持一場生活實境秀。她們的笑聲帶著油花飛濺的質地,句句…
荊棘之書
是在荊棘裡摘無花果,在蒺藜中採葡萄。 不是果實吸引我們,而是刺。 語言本身即荊棘。 它守護真理,使之不可及。 我們必須受傷,方能靠近。 在思考的荒原上,果實並不生長。 它被掩埋,被拒絕,被時間的塵覆蓋。 我們挖掘,並非為了找到,而是為了仍願尋找。 每個句子都以疼痛為代價。 每個概念都是一種失血。 論述——是理性留下的疤痕。 無花果。 花隱於果中,如思…
在絕望之巔
這是羅馬尼亞裔法國哲學家 E.M. Cioran 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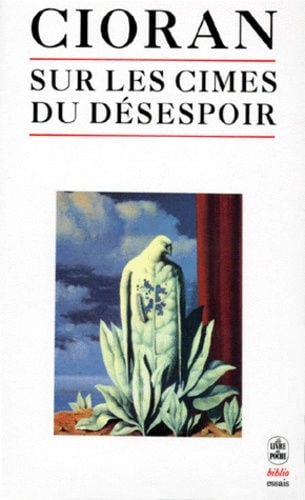
爛翻譯與反訓練
過去閱讀外文文學的譯本,常常像是在拆炸彈——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句會蹦出什麼語法怪獸。譯者或許心懷善意,或許只是不懂原文的幽默,結果留下大量「字面上正確、意思上崩潰」的句子。讀者必須靠腦補、猜測,甚至跟作者的靈魂做無聲對話,才能勉強看懂。這種「腦內補完式閱讀」雖然折磨人,卻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超凡的理解力:在語言缺席的地…
魚腹時間
黑暗沒有形體。它不是房間的牆,也不是夜晚的天空,而是一種伸手便化開的液體,將人溶入其中。約拿在魚腹裡停留三日三夜,那黑暗是他的唯一居所。 時間在那裡沒有針腳。三日三夜,不再是一種數字,而像是一團濃稠的霧氣,慢慢把人的呼吸拖長,拖到只剩下心臟的敲擊聲。當光被完全遮斷,時間就不再有方向,只剩下一個膨脹的現在。這是最孤…

想忠貞卻找不到好對象的尷尬
一篇胡亂的評論:給〈一篇胡亂的思緒〉 看完這篇文章,我第一個念頭是:這不是散文,而是長途航班。起飛點在白鸛的翅膀上,途中經過東莞、香港、倫敦、Canary Wharf、蒸汽機、NHS,最後緊急迫降在王計兵的詩句裡。飛行時間超過一萬字,乘客腦袋缺氧,行李散落一地。 不過話說回來,這趟「胡亂航班」還挺有意思。因為作者像機長一樣,不管航線多偏,都能一本正經地廣…
在雞毛滿地的時代裡
這不是一個寫作或者生育的好時機。」啊,真是經典開場。這句話一出,就好像你要創業卻先宣布自己破產,要上戰場卻先脫掉盔甲。全世界的「不適合」都被她攬在身上,結果寫著寫著,卻硬是把「不適合」變成了最高貴的正當性。 畢竟,沒有什麼比「在最糟的時機選擇最困難的事」更能體現自我英勇了。這裡有一種微妙的浪漫主義:把中年失業、單親懷孕、離…
下班換條路走,算是抵抗嗎?
在〈分工:亞當·斯密的針廠,到今天的你我〉裡,亞當·斯密的針廠故事,兩百多年後還能拿來當例子,可見經典的力量。當然,也顯示我們的想像力實在有限——這麼久了,還是在針頭上打轉。 文章裡的分工很美好:有人拉絲、有人磨尖、有人裝頭。效率暴漲,產量驚人。問題是,拉絲工人一輩子只會拉絲,連別人午休的針都不會磨。到了今天,我們還是一樣:前端…
無聊讀張愛玲
等待歸期時〉,一篇寫無聊的文章。無聊本來是最不值錢的東西,卻總有人千方百計要替它上妝。拂銳先生的辦法是:讀張愛玲。 他先嫌棄她的小說太「平凡」,男女糾葛不合他胃口,彷彿自己才剛從《挪威的森林》裡走出來,滿身木屑與失樂園的香氣。結果,翻到一篇《憶胡適之》,立刻心血來潮,跑去探訪故居。這轉折之快,就像嫌一個女人庸俗,隔天卻為她的香…
平台寒冬新手寫作 30 天暖身行動表
✓ 代表完成,每天約 20 分鐘) 第 1 週:融入環境 1. 在 5 篇文章下留下有內容的留言(至少一句引用 + 一句感想) ☐ 2. 追蹤 5 位主題接近的作者,並收藏他們 1 篇作品 ☐ 3. 發一篇「自我介紹+寫作動機」短文 ☐ 4. 在熱門文章留言區找 3 位互動,順便 follow ☐ 5. 閱讀 5 篇舊文,挑 1 篇寫心得並發短文 ☐ 6. 找到一個固定活動(例:主題週、接龍)並報名 ☐ 7. 總結本…
「杯到用時方恨多」六種杯具微策展
這場展覽裡,每個杯子都有「不得不用」的理由——無論是月經來了、寂寞來了、酒醒了、區塊鏈崩了,都是人生某種形式的「杯具」。

我們都還在,只是躲在不同的帳號裡
寫作平台就像一座熱鬧的夜市,初來乍到時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大家熱情打招呼、互相點讚留言,一時間你以為自己找到了屬於創作者的天堂。可是沒多久你就發現,隔壁的攤位不見了,留言最勤的網友突然消失,原本天天更新的好友改去經營手沖咖啡帳號了。你只好一邊懷疑人生,一邊默默繼續更新,像個堅守崗位的攤販老闆:「有沒有人還在…
將 AI 作為第一讀者:預知與自我馴化
將 AI 作為第一讀者:預知與自我馴化 (online-audio-converter用NotebookLM將本文自動生成Podcast討論對話 當我們說「把 AI 當作第一讀者」時,這不只是對創作策略的觀察,更是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文化批評。而當這種創作方式被納入「預知」的概念時,整件事更添幾分荒謬與悲哀。所謂「預知」,是指創作者在創作之前,已經假設未來的 AI 評分系統、推薦演算法、甚至自動審核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