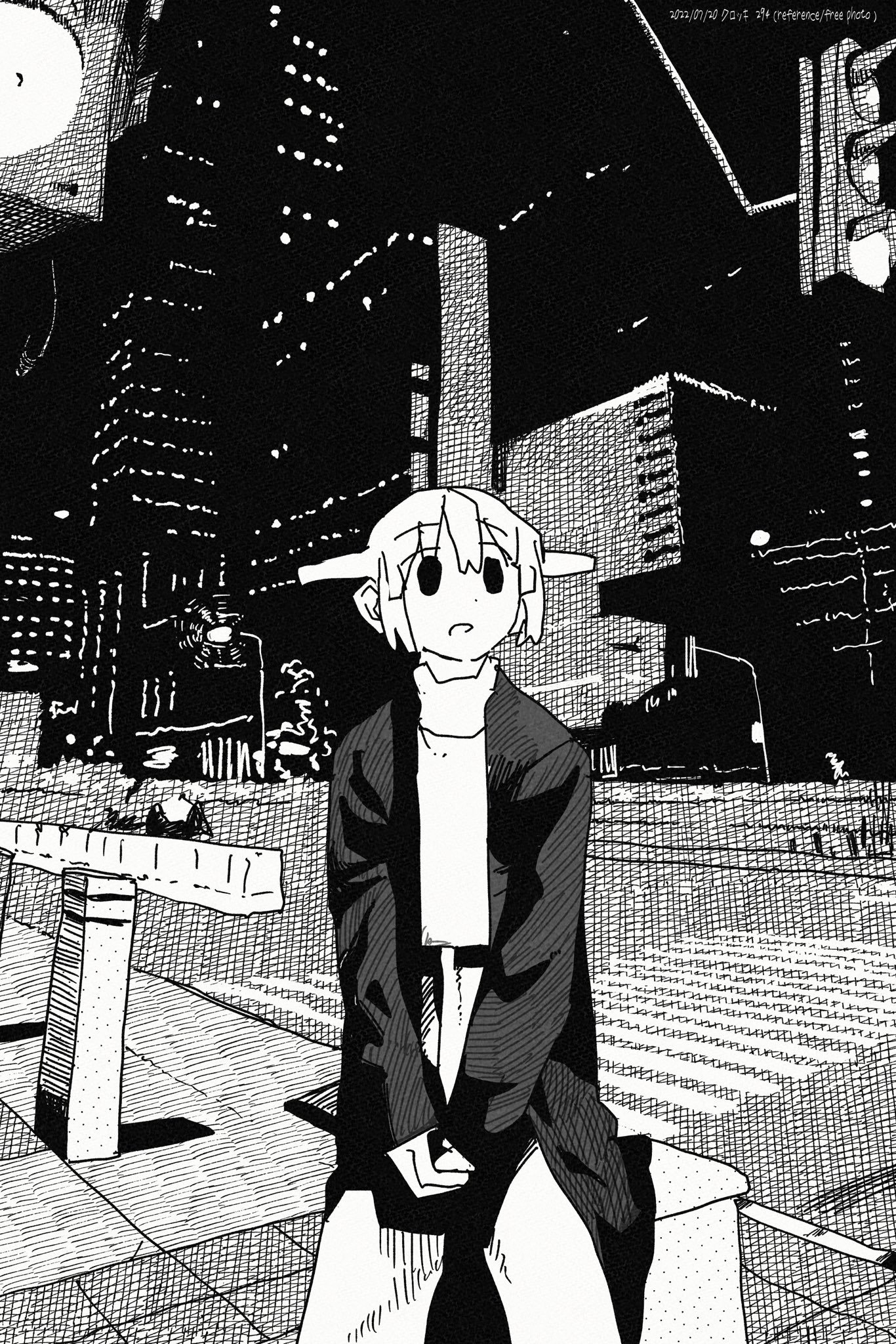柄谷行人《梦的世界——岛尾敏雄与庄野润三》第一节节选
怀有迫害妄想的病者,比如听到要伤害他的他者的声音。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听”他者的声音。如果是现实的声音的话,那是在我们的外侧。换言之,我们对此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对应,可以默杀它,也可以反驳它。或者也可以闭上耳朵。然而,在病者那里,却无法对那个声音保持“距离”。那个声音是压倒性的实在,他只能生活在过于真实的世界之中。指称那样过于真实的世界,我们称之为狂气,狂气的“世界”并不是所谓创造性的空想世界,反过来,应当说是比现实更加显著地现实的世界。
关于未开的“世界”,大概也能说同样的事情。人类学者能够住进去并观察,但不能在那里生活。即使能够生活,那时他就不是人类学者了。我对人类学本身怀有兴趣,但对于把它换成文明史、文化史的术语的比喻性的发想没有任何兴趣。 那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比如只把注意转向狂气思考的“独创性”,而无视那个“世界”的无法摆脱的痛苦。或许反而应该这样换句话说。我们憧憬梦、狂气、未开的思考,并不是因为那些世界是自由放纵的,而是因为那些世界过于苛酷而明晰的真实,不是吗。超现实主义的运动,在现实成为叫做世界大战的严峻时代时,失去了意义。因为现实的世界在那时反而靠近了“梦的世界”。这样想一想,我们对于梦、狂气、未开的思考的关心,也未必不能说是我们只能拥有暧昧而模糊的“现实”的表现。
总之,我们通常称作梦的,全部都是“事后的观察”。在梦的世界里,我们确实是字面意义上在梦中生活着,而且是在生活着与注视它之间没有任何乖离地生活着。在那里,“只是一些本来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们却毫无怀疑地接受着它。“真正的现实性并不总是现实主义的”,卡夫卡所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关于梦的各种理论,几乎都排除了这样的问题。那是如同从外侧眺望生命一般,从外侧眺望梦的世界,并试图解开它的“意义”。然而,如果附上某些保留条件的话,“梦的世界”和“白昼的世界”之间会有什么差别呢。只是差别在于,是否能够隔着距离去看,如果距离被夺去的话,我们只能“像梦一样”地感觉。
我们依稀记得梦的氛围。梦的世界可以说是苛酷得过于明晰,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读卡夫卡的小说而感觉“像梦一样”,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小说中,那些被暧昧、朦胧地涂抹掉的场面,或者那些奇怪的幻想性的场面,一点也不给人梦的氛围,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梦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凭经验知道那是与所谓的梦或幻想异质的某种东西。
无先入为主的阅读使我们确信的,如果要说的话,那就是卡夫卡所描绘的事物的绝对的现实性。他小说中的可见的世界,确实对他来说是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于其背后的东西(即使有什么存在),与物体、动作、会话等等的明证性相比,似乎毫无价值。幻觉性的效果,正是由于它们的轮廓异常的明晰所由来,而并不是由于浮动或模糊所由来。归根结底,没有比精确性更奇幻的东西了。贯穿全部作品,人间与世界的关系,非但没有象征性的性质,反而不断地是端的并且直接的。
正如罗布-格里耶所说,赋予卡夫卡小说以梦的氛围的,正是事物的细致描写和明晰的现前性。卡夫卡写的并不是梦。只是写下了“距离”被夺走的现实而已。
比如在梦之中,假如我们好像正在看树木,事实上却不是那样。树木并不是作为可被观看的对象而存在的,而是只是压倒性地在那里存在。树木为什么在那里并不是问题,而且也无法不看它就算了的那样,绝对地现前着。我们既不能抗拒它,也不能把它对象化。卡夫卡小说中的事物的现前性正是这样的。正如海明威所说,这绝不是模仿梦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已无法隔着距离把生(世界)对象化的时候所产生的东西。卡夫卡并不是把奇怪的梦奇怪地写出,而只是把“只是一些本来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的现实真实地写下而已。
卡夫卡的作品里没有任何寓意,也没有象征性。反而正是通过切断那样的“意义”,把读者卷入过于真实的世界之中。我们称它为“像梦一样”。然而,那时我们原型地感受的,是通常被“意义”所污染的现实世界。
我所称的“距离”,当然并不是实际的距离,而是对世界的内在的关系。我们例如把世界作为客观,或者作为客体来看,但那样的透视法在近代以前的人类是不存在的。比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自己或许正在做梦,然而即使那样,“我思,故我在”这一点却毫无疑问。也就是说,笛卡尔从“我思”导出“主体—客体”这个世界时,前提就是:那本身或许是包裹在一个“梦”之中的东西。至少对笛卡尔本人来说是那样的,即使那样也无妨。对他来说,所谓客观的世界,并不是眼前的世界,而是那样被构成的世界。而我们实际上生活着的“世界”,并不是那样的东西。我们处在那样一种“世界”之中,在其中我们不能对世界保持客观的、所谓中性的距离。
十九世纪确立的现实主义,把在笛卡尔那里不过是抽象的“主观—客观”世界,当作好像实在存在的。那是基于这样的确信:能够对世界采取客观的、中性的“距离”──而且不被任何东西威胁的──然而,那只是一种假构而已,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决不是那样的东西。比如,我们可以客观地考察资本制社会。但是,即使我们怀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身处资本制社会这个“梦”之中,不由分说地在那里被驱动。《资本论》的作者所拥有的,正是这样的洞察,他并不是提出了看世界的看法。他拒绝那样的“意义”赋予,只是想要把握真实的世界而已。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唯物论,他想要看到的,只是这样的生存的结构:无论人类拥有怎样的意识或意志,无论他们如何赋予意义,都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卷入、强制着的结构。换句话说,所谓“现实的世界”,也就是种种意义赋予和自由选择看起来可能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在所谓“梦的世界”之中看到的。
话说回来,我说过梦本身与梦的记忆是不同的。那意味着梦的记忆是我们醒来时构成出来的东西。在梦中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们并不试图去理解什么──也就是说,并不试图把它对象化,而只是单纯地在领会而已。有每一瞬间的领会,但却并不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比如,我本该在家里,突然却在乘电车。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可疑。因为在当下我在领会,所以在那里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
然而,在作为记忆的梦中,每一件事都显得难以理解,而且仿佛是愚蠢的东西。那是因为,当回想梦时,把那些“经验”归结到前后关系、因果关系之中了。也就是说,梦是我们醒来时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故事,而并非“梦的世界”本身。梦之所以显得不可解,是因为我们试图把它整序到“为什么”“如何”“何时”这样的句法之中。
但是,这样的故事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重要的是,不只是梦中的经验,现实的经验也同样是在这样的句法之中被整序的。现实已经是记忆。姑且试着回想一下自己今天一天做了什么就可以了。“我在家里”“我乘了电车”,诸如此类的事情会浮现出来,但其中的过程一点也想不起来。也就是说,所谓实际的经验,也不过就是一个构成而已,我们编织出“一天”“一年”“一生”这样的故事。我们不断地编织关于自身的故事,而仅仅把它称作“自己”。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