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血书写:《Fear of Flying》与女性写作的政治
《Fear of Flying》的问世,无疑是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出版于1973年,与“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同年,共同定义了一个骚动与变革的时代。
然而这部小说远非简单的性解放宣言,而是同时向两个强大的父权话语权威发起了挑战:试图将其欲望病理化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以及用男性经验来定义女性存在的文学正典。
女主角Isadora的旅程始于那架满载精神分析学家的飞机,她要逃离的不只是丈夫或婚姻,而是整个以阳具为中心(phallocentric)的知识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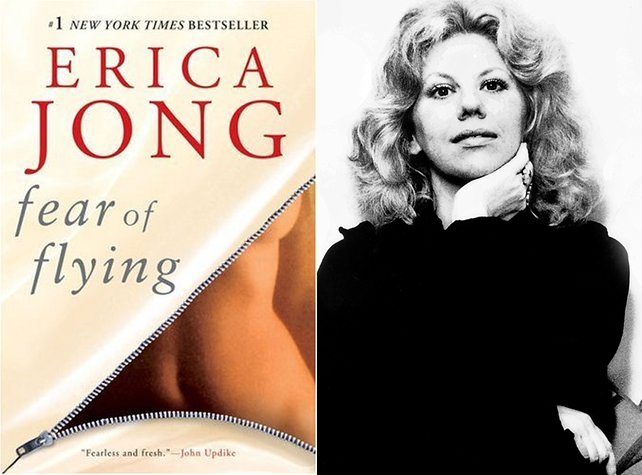
拆解弗洛伊德的躺椅:作为父权规训的精神分析
这部小说对精神分析的嘲讽是连贯而精准的。
书中反复出现那些无能或厌女的精神分析师形象,尤其是那位告诫Isadora要“ackzept being a vohman(接受你是个女人(德语口音))”的医生 ,直接揭露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维护父权制社会规训工具的真相。
小说揭示了精神分析的“谈话治疗(talk therapy)”如何异化为一种压迫机制:它将女性正当的反抗与不满病理化为“神经症(neurotic problem)”,从而将结构性困境扭曲为个体心理问题,彻底消解其反抗的正当性。
Isadora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戳破了这门学科的意识形态核心:
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有人曾这么评价弗洛伊德。他以为太阳绕着阴茎转。女儿也一样。
Phallocentric, someone once said of Freud. He thought the sun revolved around the penis. And the daughter, too.
这句俏皮话既是智识上的反叛,也是语言上的夺权——她以该学科的术语反击其创立者。
这场批判在Isadora与她的精神分析师的决裂中达到高潮。当她质问:
我为什么要听你怎么定义做女人?你是女人吗?
Why should I listen to you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man? Are you a woman?
她实际上是在宣告一种认识论上的独立。
Isadora的“恐惧”因此不再是病症,而是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父权社会的理性回应。
弗洛伊德将恐惧(阉割焦虑)分配给男性,而将嫉妒(阴茎嫉妒)分配给女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性别偏见。Jong的小说则颠覆性地为女性夺回了“恐惧”这一核心体验,但它不再是关于“缺少”什么的恐惧,而是关于“拥有”——拥有自由、欲望与智识——的恐惧。

阳具之笔与经血之墨:女性写作的革命
如果说精神分析的躺椅是禁锢Isadora心灵的第一个场域,那么由“已故白人男性(dead white men)”所构建的文学正典,则是围剿她智识的第二个战场。作为一名诗人,她的核心挣扎,是一场关于女性艺术家如何在由男性话语构建的世界中,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战斗。
Isadora的创作焦虑,与男性作家的“俄狄浦斯式”斗争截然不同。她没有文学“父亲”需要超越,而是根本没有母系谱系可以继承。她的困境和焦虑源于在一个将笔定义为“阳具(phallic pen)”、将女性定义为缪斯或客体的传统中,她对自己是否有权进行创作这一基本资格的深层怀疑。
当她向文学先辈寻求指引时,D.H.劳伦斯这样的巨匠反而成了她的障碍:
二十一岁之前,我一直用查泰莱夫人的高潮来衡量自己的,并琢磨着自己到底哪里不对劲。我可曾想过,查泰莱夫人其实是个男人?她其实是D.H.劳伦斯?
Until I was twenty-one, I measured my orgasms against Lady Chatterley’s and wondered what was wrong with me. Did it ever occur to me that Lady Chatterley was really a man? That she was really D. H. Lawrence?
这段独白直接揭示了问题的核心:被奉为圭臬的、关于女性经验的文学范本,实际上是男性欲望与想象的投射。这种由男性建构的“女性气质”不仅无法为她提供指引,反而成为一种异化的标准,让她怀疑自身的真实感受。
与此同时,当她转向自己的母系血缘寻求榜样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关于创造力之死的警示故事。她的母亲,一位在巴黎学过艺术、颇具才华却最终放弃事业的女性,直白地告诫她:
女人不可能两者兼得……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艺术家,要么生孩子。
Women cannot possibly do both... you’ve got to choose. Either be an artist or have children.
这为Isadora提供了一个毁灭性的反面教材。它传递的信息是:女性的艺术生命力,最终必将被家庭责任所吞噬。这种母系传承的断裂,使她在寻求文学榜样时陷入真空。一方面是男性文学正典提供的异化模板,另一方面是女性前辈提供的失败案例。
正是这种双重困境,催生了她的文学反抗:
直到女人开始写书,故事才有了另一面。在全部历史中,书都是用精子,而非月经写就的。
Until women started writing books there was only one side of the story. Throughout all of history, books were written with sperm, not menstrual blood.
在文学史中找不到榜样,她就成为了自己的榜样。写作由此成为一种政治行动。那支笔不再是阳具的象征,而是一种重新定义创造力的工具。它流出的不是精子,而是经血。

一则由批评家完成的预言
小说出版后所遭遇的抵制与误读,本身就是文本主题的现实延伸。主流(男性)批评界对《Fear of Flying》的反应,几乎以一种讽刺的方式重演了Isadora在小说中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制。
最直接的策略是贬低与丑化。
《纽约时报》评论家Terry Stokes批评Isadora的“whining(抱怨)”拉低了阅读体验。这个词语的选择延续了精神分析式的惯性:将女性的不满病理化,把她们的困惑、愤怒与自省,都归结为情绪失控或心理失衡。女性的异议,被轻易地转化为症状,而非思想。
John Updike在《纽约客》上写道:
这个故事可以理解为一个被宠坏的年轻女人,在经历了一些冒险之后,下定决心要继续宠爱自己。
The story can be viewed as that of a spoiled young woman who after some adventures firmly resolves to go on spoiling herself.
他又讽刺她“在金钱铺就的安全网上轻盈地跳跃(she bounces about on an ubiquitous padding of money)”,并形容整部小说带着“一次心满意足的购物之旅完成后那种沾沾自喜的爽快(the smug snap of a shopping expedition satisfactorily completed)”。
在这些评语中,女性对存在意义与自我定义的探索,被降格为物质享乐与消费欲望;精神与思想被替换为“购物”与“宠坏”。

最极端的攻击来自Paul Theroux,他将Isadora贬为“一个庞大的阴户(a mammoth pudenda)”。这是父权话语的终极还原——将一个有思想的女性作家压缩成一个性征,从而彻底剥夺她的声音与人格。
也正因如此,这样的侮辱反而成了小说主题的最字面化注脚:一个女性若试图发声,立刻会被拉回到身体之中,被迫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更微妙的策略,则是通过看似赞美的比较来进行收编。Updike将《Fear of Flying》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波特诺伊的怨诉》相提并论,称其为女性版的成长小说。Henry Miller则称其为“女性版的《北回归线》”。
这表面上是一种抬举,实际上却是通过男性参照系来赋予其价值。它将一部具有开创性女性视角的激进作品,纳入到一个由男性定义的、早已为人熟知的叛逆叙事传统中。
因此,《Fear of Flying》所遭遇的误读,恰恰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小说揭示的,并非个人命运,而是一种至今仍在运作的文化机制:当女性试图以主体身份发声时,批评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让她重新回到被命名、被定义、被解释的位置。
《Fear of Flying》的激进性,在于它讨论的并非个体的性或情感,而是知识的生产方式。Isadora的困境与反叛都指向一个核心政治命题:话语即权力。精神分析将其病理化,文学正典将其边缘化,批评机制则试图将其收编——所有这些,都是权力规训女性主体性的不同面相。
Isadora的旅程揭示了,女性的解放不仅是社会权利的争取,更是一场针对话语结构的漫长革命。因此,“以经血书写”并非仅仅是一个生物学隐喻,而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姿态——它意味着从被书写的客体,转变为书写的主体,去夺回定义自我与现实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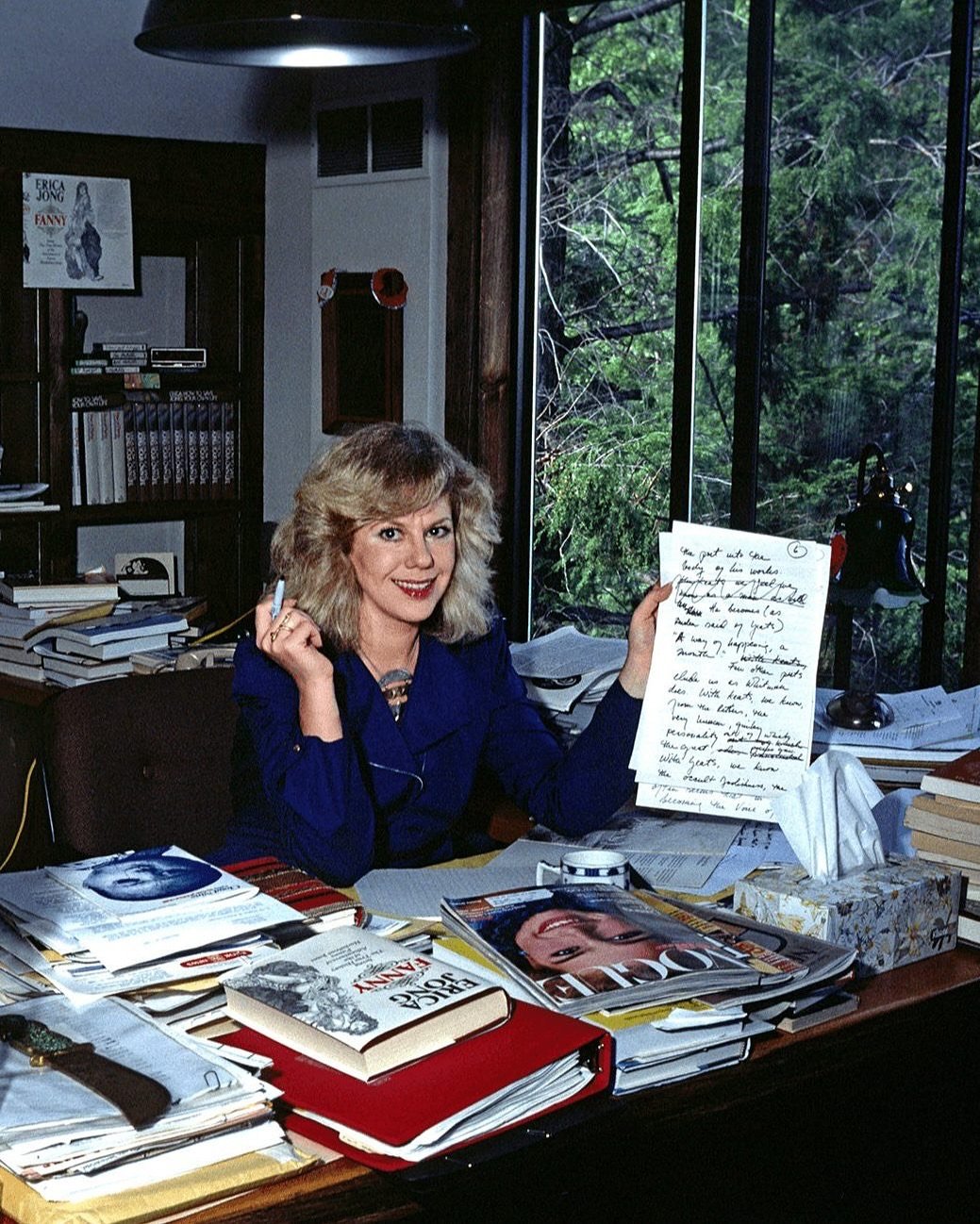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