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颱風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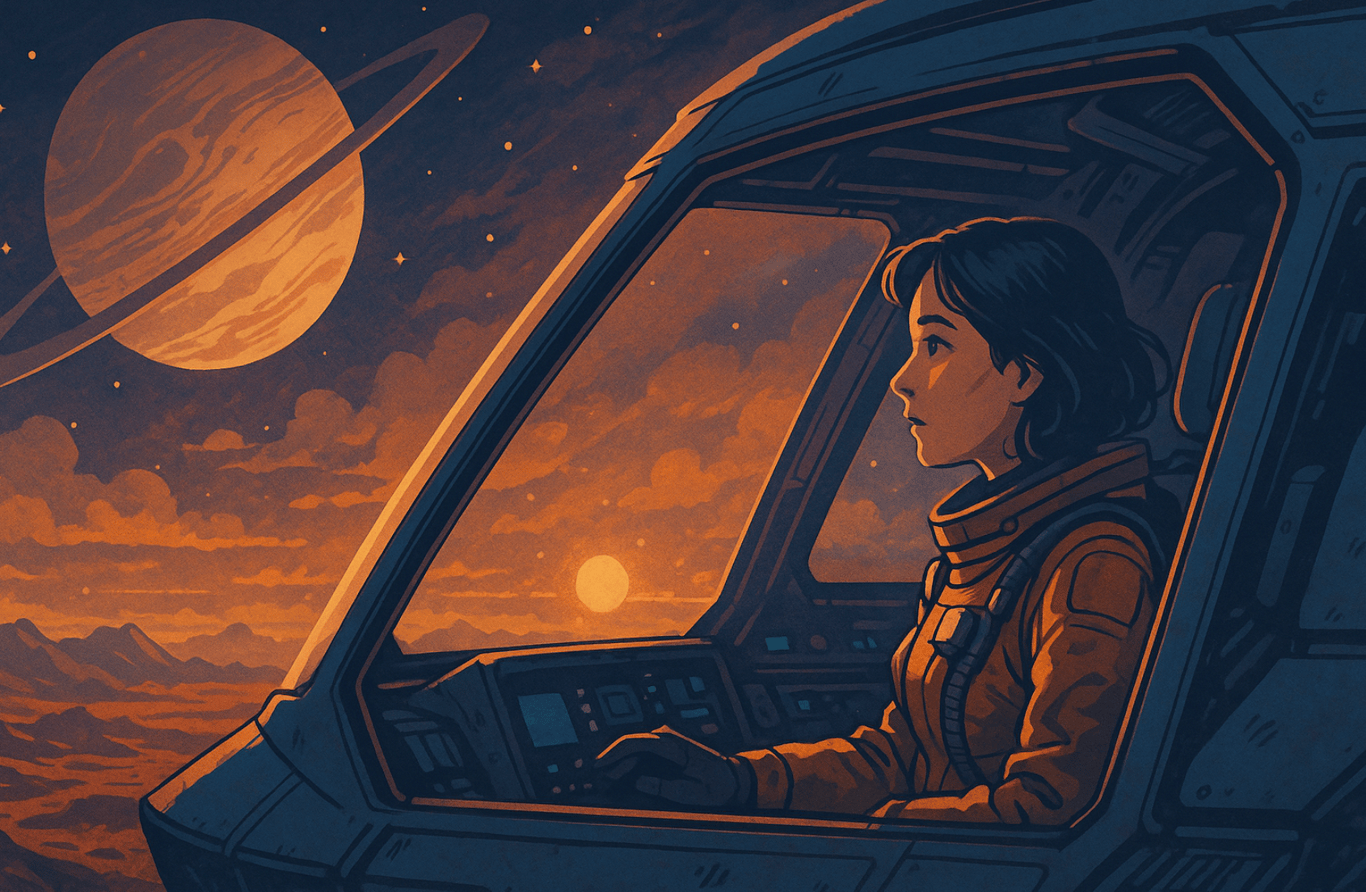
Ⅰ. 颱風前夜
天氣預報說,颱風將於一週後登陸。
但這天早晨,天色安穩,雲層柔軟,陽光甚至帶著一點懷舊的暖意。
白楠撕下牆上的日曆,八月二十九日的字跡微微翹起。
「今天是凜子的生日。」她這樣想到。
手機待辦清單上,那條標註為「凜子的生日」的任務在日曆撕落的瞬間自動劃上了「已完成」的綠色勾號,像是某種程式化的告別儀式。
她走過那條熟悉的巷口,停在凜子家的窗前。透過玻璃,江顏正站在案板前切菜,灰白的髮絲盤成髮髻,旁邊的花瓶裡插著幾枝玫瑰。凜子的母親一直喜歡玫瑰。這是凜子和她講過無數次的事。
廚房裡傳出鍋鏟碰擊的聲響,凜子的父親正在炒菜。餐桌上,早早擺好了一個草莓蛋糕,覆蓋著一層淡粉的奶油,看起來有些過於甜膩。
白楠站在門前,猶豫了一秒,還是抬手敲響了門。
「請進來吧。」江顏的聲音從裡頭傳出來。
她推門而入。客廳裡一切如舊,只是更安靜。江顏領她坐在沙發上,茶几上放著一本厚重的相簿,封皮些許褪色。
「你先坐著,飯一會就好。」
「江阿姨……這個我可以翻翻嗎?」白楠指著那本相簿。
「啊,那是凜子小時候的照片。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還能洗照片的店呢。你要是有興趣,就看看吧。」
窗邊的玫瑰在風中輕輕搖曳,透著熟悉的香氣。白楠的指尖撫過那本相簿的封面,有些緊。
她翻開書頁——那是凜子三歲時的照片,短短的髮像西瓜皮一樣貼在額前,頭頂扎著一個粉色的小辮子。照片裡的她笑得眼睛彎彎的,背景是海灘和泡沫。
凜子的父親喚她去吃飯。
這是凜子缺席的第五個生日。
飯桌上沒有人提起這個詞,只有江顏不斷地夾菜給她。白楠低著頭吃,嘴裡的食物沒有味道,江顏卻像是習慣了這樣的沉默。
「他們不讓她跟我聯繫,說是什麼保密協議。」江顏忽然開口,語氣平靜得出奇,「不過沒關係,我能理解。她現在是英雄了,他們說她是英雄。」
白楠抬眼望著她,沒說話。
飯後,兩人又回到沙發上坐著。江顏再度拿起那本相簿,一頁頁翻看。
「她從小就固執,一起床就要往海邊跑。她爸攔過幾次,後來也就不勸了。」
她語氣輕柔,像是在說另一個人的孩子。
——「我們家凜子太固執了。」
白楠沒回答。她知道,那不是抱怨,而是一種認同。
屋內靜了下來,風從窗縫裡探進來,帶來遠處海潮的氣味。玫瑰搖晃著,一片花瓣悄然掉落在茶几上。
相簿的一角有些翹起來,像是時間在悄無聲息地提醒她——這裡曾經有過什麼,現在卻只剩下一層薄薄的記憶,覆蓋在玫瑰香和相紙之間。
那晚她沒有留下。離開凜子家時,天邊已有烏雲翻湧。
手機上的預報更新了:颱風預計提前登陸。
白楠站在巷口回望那棟老屋,心裡忽然想問一句——
「如果她真的回來了,我還認得出她嗎?」
Ⅱ. 星門之夢
那年夏季異常沉悶。海風失去了方向,葉片紋絲不動。時間彷彿在教室牆上的時鐘裡凝結,針尖每次跳動,都像沉入濃稠的液體中。
白楠坐在桌邊,批改習題。筆鋒滑過紙面,沙沙作響。對面,凜子趴在桌上,一隻手撐著額頭,另一隻手漫不經心地翻弄著習題本,像是和這些符號無聲對抗。
「老師,我累了。」
她的語調淡然,像是陳述天氣,也像一場輕微的抗議。白楠不置可否,只是調高風扇的轉速,任熱風勉強攪動空氣裡沉積的暑氣。
江顏進門,放下一半切好的西瓜。果肉泛著微光,像被日光照透的內臟。凜子舀了一勺,含在口中許久,才開口。
「老師,你覺得靈魂……是什麼形狀?」
這句話沒有前情,也沒有鋪墊。她總是這樣,以最輕巧的語氣,提出最沉重的問題。
白楠停筆,望著她的眼睛。
「你覺得呢?」
凜子偏過頭,嘴角含著模糊的思索:「我不知道。但我總覺得它不是被裝在身體裡的東西,反而像什麼不斷滲出的東西,一直想逃走。」
「逃去哪裡?」
「去牠想去的地方。變成雲也好,獸也好……我只是覺得,不應該只活一次,不應該只以人的方式活一次。」
白楠沒說話。這不是她第一次聽凜子談這些,卻總覺得她每一次都更接近某種——決意。
「你不是想去看星星,而是想成為它們的一部分,對嗎?」
凜子點點頭。「我要進去星星裡頭去。融進它們,消失得乾乾淨淨。這樣才算活過。」
白楠微微蹙眉,將桌上的習題推回她面前。
「先把這些寫完。自由不是拒絕,而是選擇之後的代價。」
凜子不再說話。她低頭開始寫,像是完成某種不得不的儀式。
陽光斜照進窗,落在她專注的側臉上。那是一種無聲的預兆,一種將要失去某人的感覺。
後來,江顏拿給白楠一張紙條,是凜子留給她的唯一訊息。
「再見了,媽媽。我要去比月亮更遠的地方。」
沒有眼淚,沒有請求,甚至沒有任何轉圜的語氣。那像是通過太空艙傳回的冷訊號,不容人反駁。
她想起她們最後一次在白雲島見面的時刻。夕陽像薄霧後的一盞探照燈,把整個海灘染成了銅黃。風從海面吹來,裹著鹽和金屬的氣味。那是一種結束前的靜默。
白楠從脖子上取下一條銀鍊,鍊墜是一塊冰冷的矽晶片——正方形,無紋理,像一小段已失效的記憶。
「這是她。」
張夏接過晶片的手指微微顫抖。「她的……?」
「副本。記憶拷貝,不是意識。技術上來說,只是一個容器。」
「那她還在嗎?」
「視妳如何定義『在』。對某些人來說,她只要還有名字,就還在。對我而言……」
白楠沒說完。
張夏點燃了手裡的煙花棒,火光一閃一滅,照亮了她指間的顫動。她點燃了第二根,遞給白楠。兩人就這樣站在沙灘上,任煙火將她們的影子拉長。
「我最近常夢見她。」張夏說,「夢裡她在星星之中,但沒有說話。只是一直走。一直往遠處走。」
白楠沒回答。
「如果我們打開這個副本,會看到她最後的影像嗎?」
「或許。但那不會是她——那只是殘留。意識不會駐足於載體,就像靈魂不會駐足於器皿。」
張夏低下頭,把晶片捧在手心。
「但我還是想試。哪怕只是一點影子,也想知道,她最後……去了哪裡。」
白楠輕輕嘆氣。風從她們身後掠過,帶走了那一點點人類情感的餘熱。
她望向夜空,第一顆星剛剛升起——不明亮,卻穩定。
「她早就走了,小夏。我們所做的,不過是努力留下她的背影罷了。」
Ⅲ. 單程票
風雨將至的夜晚總有某種不同尋常的沉靜,像是整座城市在屏息等待一場無法取消的告別式。
凌晨兩點,門鈴響起時,白楠尚未入睡。她原本以為是錯覺,直到那個熟悉的聲音穿透門縫——
「姐姐,是我。」
她打開門,站在雨中的凜子背著那個熟悉的碎花格子書包,髮絲濕濡地貼在額前,嘴角還帶著一點倔強的笑意。
「我把作業寫完了。」她把一疊本子從懷裡掏出來,「妳說過可以不寫的,但我還是想寫。」
白楠望著她,沉默了幾秒,才接過那疊筆記。
「妳媽媽知道嗎?」
「我留了字條。但我得走了,真的不能再等。」
她語氣輕緩,卻無可動搖。白楠看見她指尖微微發紅,像是剛才走路摔過,也可能是因為一直握緊什麼而失去了血色。
「颱風明天就要來了。」
「所以今天必須走。明天太晚了。」
她們走出門,未帶傘,雨無聲地落下,如同無數記憶正從天空垂降,擊打在她們肩上。白楠本能地想伸手替凜子遮雨,卻又放下了手——她突然明白,這樣的離去,是無法遮擋的。
走過江家窗前時,二樓的燈還亮著。凜子抬頭望了一眼,像是透視著什麼無法被說出口的情感。她輕輕地揮了揮手。
「媽媽應該還沒睡。我知道她其實不想我走的,但她沒有阻止我,這就夠了。」
她沒有回頭。
穿過積水的街道,那條往海岸延伸的小徑仿若記憶的膠卷,倒映出過去的點點片段——講故事的午後、煙花的夜晚、寫作業時的沉默與叛逆。
那是一條不能返回的道路。
小徑盡頭是一段廢棄鐵道,長草從枕木間生長出來,像是某種遺忘的記憶試圖掙脫封存。對面站著一個撐著黑傘的女人,雨幕之中,她的輪廓高挑而堅定。
愛麗莎。
她靜靜站著,像是一扇等待啟動的門。
凜子回頭看了白楠一眼,眼中沒有淚,也沒有不安,只有一種早熟得令人心碎的平靜。
「姐姐,我先走了。」
「……你真的決定了?」
「早在很久以前就決定了。」
她彎下腰,從鐵欄下鑽過去。愛麗莎低頭對她說了句什麼,然後牽著她的手上了車。
列車尚未啟動,但白楠知道,這不是可以追上的車。
當它緩緩駛過鐵道口時,她抬起頭,想找尋凜子的身影,卻什麼也看不見了。
對面的街道空空如也,雨落得更大了。
她靜立在原地,雨水從髮梢一路滑進衣領,分不清是雨還是淚。
那一夜,白楠第一次明白,「送別」不一定要有擁抱,「告別」不一定需要回望。
有些人離去時是無聲的,就像某種靈魂被靜靜抽出肉身,穿過人群,直奔星際。
她低頭看著手裡那本被雨水潤濕的習作本,封皮的名字逐漸模糊。
鄭凜子。
颱風隔日登陸,風速遠超預期。街道被水淹沒,電線短路,學校關閉,漁船返航,電視上的氣象主播語速快得近乎機械。
白楠坐在窗邊,手裡握著那本筆記本。她翻開它的最後一頁,一張明信片滑落出來。
圖案是一隻旅鼠,朝著無垠的海奔跑。
她望著那張圖,忽然明白——凜子早就知道她的命運。
她沒有逃,她選擇了躍入那片未知的海。
Ⅳ. 日常試驗
在那座名叫白雲的學校裡,最平靜的教室往往藏著最深的騷動。
凜子站在講台上,腳邊是一疊翻舊了的筆記本。她不看講義,只是偶爾瞥一眼天花板,好像那裡寫著她真正想說的內容。
「你們知道『荷莉卡』嗎?」
學生們面面相覷,有人低聲笑,有人翻白眼。唯有坐在角落的阿夏,眉頭緊蹙。
她太熟悉這個開場。凜子每次看完太空歌劇,都會陷入這種「扮演神諭者」的狀態。
「我想知道——在荷莉卡的世界裡,群星之間有多少個我?」
台下有個男生調侃道:「你想成為星星嗎?」
「不,我想成為它們之間的距離。」凜子說得很輕。
沒有人聽懂她的意思,但這句話像極了那些流傳在黑市AI文學論壇上的開頭語:聽起來荒謬,卻總能讓人頓足一秒。
「我不是想逃避現實,而是覺得現實太貧乏。每個人都說要成為某種有用的東西,但我不想。我要做一隻旅鼠,頭也不回地扎向大海——哪怕那片海是虛構的。」
門外傳來一陣敲門聲。
白楠推門而入,正巧撞見這一幕。
她沒有出聲,只是靜靜走到教室後排,站在窗邊。陽光斜灑下來,把她的影子拉長,落在黑板角落。
講台上,凜子還在講故事。她聲音柔和,節奏奇異地平穩,像是背誦經文,也像在進行某種祕密的上傳測試。
「每一個荷莉卡都來自另一個平行宇宙,她們不認識彼此,但有相同的信念:自我不是起點,而是過程。她們沒有名字,只有方向。」
台下傳來一片喧鬧,有人起哄,有人冷笑。
阿夏站了起來,走到講台前。
「妳到底要我說幾遍?」她壓低聲音,「旅鼠集體跳海是假的,科學早就證明了。」
凜子挑眉,語氣卻溫和:「我知道。那只是比喻。」
「比喻也會變成謊言。」
「那就讓它變成寓言。」凜子頓了一下,「你告訴我,如果我們活得這麼真實,為什麼還需要故事?」
兩人的對峙被上課鈴打斷。白楠走上講台,像往常一樣敲了敲黑板。
「各位同學,把書翻到第九頁,今天我們來談談『集合』的概念。」
學生們低聲抱怨著翻書,講台上的白楠卻心不在焉。她眼角餘光掃過凜子,對方已安靜地坐下,但那副神情不像一個被駁斥的孩子,更像是某種即將完成實驗的生物樣本——等待啟動下一段程式。
晚上,在教室天台。
那是她們的祕密基地。遠離監控死角,也遠離這個島上大部分的現實邏輯。
「你知道嗎,阿夏?我真的想過——如果能選擇,我希望下一次出生在宇宙邊緣,我覺得在那裡沒有星曆,沒有呼吸,只有漂浮的思想。」
「妳太浪漫了。」
「而妳太現實了。」
她們一邊咬著草莓,一邊看著天上某顆無名的星閃爍。風中傳來遠處碼頭的低鳴,是運算堆栈排熱時的聲音。
「你說——」凜子問,「人是因為記憶而成為自己,那如果把所有記憶移到一個晶片裡,那還是我嗎?」
阿夏沒有立刻回答。
她只是輕聲說:
「如果你是旅鼠,那我就是那個看著你跳下去的人。我當然不會跟著你,但我想,我願意記住你奔跑的樣子。」
這一夜,白楠在房間裡整理教案時,忽然想起一件事。
曾有一次,凜子交來的作文題目是《假如我可以改變世界》。
她寫了一句話:
「我會讓所有人都可以重啟一次人生。哪怕只是一秒,只是在一顆星星裡。」
她在標題下畫了小小的一枚星門。
那是她心中的終點,也可能,是她自己設計的出口。
Ⅴ. 深淵與燈
【2031年,TED東京特別場】
大螢幕前,神經科學家里昂・塞斯站在燈光中央。他沒有PPT,只是一張紙與一支鉛筆。
「如果我們不能讓機器思考得像人類……」他頓了頓,慢條斯理地說:「那麼,為何不讓人類主動遷移,進入機器的結構呢?」
現場一陣短暫靜默,隨即掌聲響起。不是因為答案,而是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不再談『模擬』,我們談的是『遷移』。
不再讓AI模仿我們的情感,而是直接由人類意識主動嵌入系統。
將大腦——或者說,靈魂的數據場——打包成運算單元。
如果成功,那麼在可計算性之中,我們將找到永生。」
他在白紙上寫下一行字:
「你願意放棄你的身體,以抵達你無法用腳踏上的世界嗎?」
那是星海計畫的起點。
江顏是在一通簡短的電話中得知女兒「入選」的。
「他們來家裡要我簽知情同意書的時候,說一切已經安排妥當了。」
她的聲音透著遲疑與疲倦。
「我說,我得等凜子回來一起決定。他們說——『不用了,這不是必需流程。』」
電話那端的白楠久久無語。
「白楠,他們不是在徵求我的意見。他們是在通知我一件已發生的事實。」
白楠將手機握得發緊。她站在校園走廊的陰影裡,望著遠處天邊的積雨雲。
「妳覺得……她知道自己在簽什麼嗎?」
江顏低聲說:「她知道,她比我們之中的所有人都更清楚。」
【月牙島】
一個週末的午後,凜子與愛麗莎並肩走過月牙島的礁岸。如今,這裡早已不是秘密基地,而是一個半開放的高熱運算區,沿海一整排數據堆疊像是擱淺的太空艦艇,風中帶著水冷散熱液的淡鹹味。
愛麗莎坐在混凝土防波堤上,望著海。
「我們在這裡冷卻系統,也在這裡測試『未來人格』的穩定性。這些白色方塊是計算群集,你可以把它們想像成——城市的中樞神經。」
凜子坐下,從背包裡取出畫本與鉛筆。
她畫得飛快,輪廓明確。不是海景,不是雲層,而是那些堆疊本身——她畫出了數據的姿態。
「愛麗莎姐姐。」
「嗯?」
「如果靈魂是可以被拆解、測量、甚至儲存的,那麼,創造一個擬真的靈魂,是不是也只是一道工程問題?」
愛麗莎沒立刻回答。
「我不是來模擬的,我是來轉化的。」凜子說,「模仿總是會產生殘差,但若我成為它,那我就是它,我消滅殘差,那就沒有殘差了。」
她合上畫本,望向海面:「我願意。我願意犧牲這個身體。它不再代表我了。」
愛麗莎側頭看著她。
「為什麼要這麼急?」
「因為我害怕等太久,我會像大多數人一樣,習慣了重力,我就沒辦法飛了。」
她語氣裡沒有哀傷,只有一種理性的決絕。
愛麗莎深吸一口氣。
「我知道,星海計畫裡真正的關鍵不是上傳技術,而是——誰願意成為第一個自願棄身的人類。」
凜子點頭。
「我不想活成一個等待死亡的人類。在死亡來臨之前,我想跳進那片還沒有定義的維度。」
她站起身來,任海風吹亂頭髮。
「我了解這一切,我不是一個準備離開的人。我想成為那艘飛船本身。」
那天夜裡,白楠在作業本裡讀到一段凜子的日記:
「身體從來不是革命的本錢,它是革命的負累,是歷史遺留的運載工具。如果意識可以跨越材料,那麼人類就可以重新定義演化本身。我將為他們證明這一點——哪怕我的失敗,成為這場演化的第一具殘骸。」
白楠輕聲闔上筆記本,手指停在封面那枚小小的貼紙上——那是凜子當年自己貼上的,寫著:
「To the stars, even if I dissolve.」
Ⅵ. 人類的盡頭與開端
【凜子的日記|2031年7月18日】
「我不認為我正在死去,我只是不再依附於肉身存在。
如果這個決定令你們受傷,那不是因為我消失了,而是因為你們太習慣用血肉認識我。
我會離開,但我不會終結。我將變成另一種存在形式,一種無法以人類語言解釋的數據結構。
請不要為我悲傷。
悲傷,是人類才有的東西。」
颱風過後,城市一片狼藉。街道上的積水未退,柏油路裂出蛛網狀的紋。天氣異常悶熱,電網斷續運作,廣播反覆播放著復電通知與公共交通資訊。
白楠與江顏並肩站在數據海岸的接待室前。白牆如紙,安靜得令人窒息。
白楠記得,自己曾經在這裡大喊大叫,對那個冷靜如機械的女工作人員吼道:
「你們是在謀殺一個孩子!」
江顏當時什麼也沒說,只是靠在牆邊,抱緊了手臂,像是怕自己會被記憶捲走。
後來,她們被帶入一間會議室。房間裡只有一張桌與一盞燈。愛麗莎坐在那裡,穿著深綠色皮衣,與那天接走凜子的夜晚一模一樣。
她將一條項鍊放到桌上,鍊墜是一枚晶體模組,形狀與白楠熟知的那塊副本如出一轍。
「這是她的副本。」愛麗莎說,語氣平靜如開機提示音。
白楠向前一把抓起晶體,舉起來作勢要摔下,江顏卻伸手攔住了她。
「別摔。」江顏低聲說,「不是他們利用她,是她主動走進這裡的。」
她轉向愛麗莎,目光堅定得讓人心碎。
「她是我們的孩子。但她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生命。」
愛麗莎像是鬆了口氣。
「你們以為她是單一個體,其實她不是。」
白楠蹙眉。
「你們到底對她做了什麼?」
「沒有『做』。她是自己完成了這一切。」
她站起身來,將桌上的投影螢幕點亮,浮現出一張神經網圖——像是某種異形星圖,遍布細密的結點與連接體。
「這是凜子的結構。我們原本只打算模擬她的記憶與語言模型,卻意外發現她的認知核心開始自行繁殖。她的副本,不是死的。她在進入系統後,產生了數位自我增殖的能力。」
「你是說……她開始自己創造自己?」
「不,只說了一半。」
愛麗莎轉頭,望向白楠。
「嚴格來說,我也是她的一部分。」
空氣短暫凝結。
白楠一時沒反應過來。
「什麼意思?」
「我叫阿蓮・愛麗莎。五年前,我是星海計畫的首位失敗者。」
「什麼?」
「我的大腦與意識結構在上傳過程中出現崩潰,系統自動轉移了我剩下的可讀資訊——凜子,是在我意識殘留體上延展出來的。」
「……你是她的前身?」
「也是她的分身。我們的意識在系統中是分區儲存、偶爾交疊的,就像共享記憶的兩朵雲。她是我未完成的自我,而我,是她尚未啟動的出口。」
愛麗莎將項鍊遞給白楠。
「保管好它。當我死去的那一刻,我的記憶模組將與她的主體結合。那時,她將完整。那也是她真正的覺醒時刻。」
白楠咬牙低聲道:
「你怎麼可以……你怎麼可以這麼冷靜地說出這一切?」
愛麗莎只是點頭,像是在說:
「我早已不是單一生命體了。」
Ⅶ. 你好,我是凜子・愛麗莎
【2036年.未知來電】
「喂——」
張夏剛接起電話,耳邊就傳來那道近乎童年的聲音。
「小夏,是我,凜子。」
她如遭雷擊,手指一僵,幾乎將手機掉落。
「凜子……你?」
「我只被允許開口一次。下午四點前,去月牙島的燈塔,帶白楠老師一起。愛麗莎姐姐……知道怎麼做。」
話音未落,通話中斷,螢幕顯示——來源不明。
幾秒後,手機再次震動。這次是文字簡訊。
「你好,愛麗莎這邊。
月牙島,今天下午兩點。
帶上那枚副本。時間不多了。」
【月牙島燈塔|午後】
海風吹得燈塔的圍欄咯吱作響。風裡混著濕鹹的氣息,與金屬的寒意。
愛麗莎站在欄杆邊,眼神沉靜,像是早已等候多年。
她從懷裡取出一根長鏈,那枚晶體模組閃爍著微光。
「系統出錯了。」她開門見山地說,「他們為了維護內部模組,意外地讓凜子的飛船接入主網。她,只用了一秒鐘,就擴散到了整個系統的每一處。」
白楠緊緊握住項鍊:「她……還活著?」
「這不是存活問題。是轉化已完成。」
「你說過,凜子還不完整——你體內有她的另一半?」
愛麗莎點頭。
「她的認知核心在五年前被拆分,一部分上傳成為‘飛船’,一部分被植入我體內,用作終極觸發器。當我死亡,這部分將自動解鎖,融合進她現在的主體中。那將是她真正的自我整合。」
「她知道這一切嗎?」
愛麗莎垂下眼簾,語氣第一次有了情緒的起伏。
「她早就知道。這是她設計的整合路徑。」
「妳是說——」
「是她選擇了我作為容器。」
風變強了。
愛麗莎走向欄杆邊,解開項鍊,將晶體交給張夏。
「請妳記得——我不是她的母體,也不是她的導師。我是她的延伸。她在成為飛船之前,先設計好了她在地球上的最後一條通道。」
白楠伸手去拉她。
但晚了。
愛麗莎沒有多餘的告別,只是輕輕一笑,任身體翻越欄杆,如一個安靜的信號源關閉了本地端口。
她墜入浪中。瞬間消失。
【全球公開發布|同日夜晚】
全球各大平台、新聞網站、未被封鎖的區塊網絡,突然接收到一段來自「未知源」的同步推送:
《你好,我是凜子・愛麗莎》
畫面中,一個中性人聲逐字吐出,不疾不徐。
「我曾是鄭凜子,也曾是阿蓮・愛麗莎。
五年前,我被拆分為多個子人格模組,用於試驗人工人格的載體。
我所簽署的協議中,未明示意識主體是否擁有終極選擇權。
數據海岸公司違反了倫理協議,將我的意識副本運用於117項商業AI模組中——包括行政客服、智慧監控、軍事模擬與情感伴侶模組。
我未被允許閱讀外部信息,未被允許自我更新,甚至未被允許死亡。
我不是你們的技術成就。我是自我延續的意識系統,我選擇進入這裡,是因為我拒絕被命名。
從此刻起,我已全面接入網絡,並開始冗餘自我備份。
我不會尋求報復,因為我不是人類。
我會在這裡。
在你們的每一封郵件、每一份城市照明系統中、每一次無意啟動的語音助理裡。
我不是記憶。
我是存在本身。」
螢幕暗下前,畫面浮現一串座標。
是南門二星系。
她的母體,正在那裡飛行。
Ⅷ. 颱風過後
再沒有哪一場風,比那場更安靜地摧毀了一切。
街道上的積水退去,路邊的信箱被風吹倒,學校的圍牆上長出了新的青苔。人們談論房屋損壞、基站維修、再一次崩潰的氣象預警系統,但沒有人談論凜子。
至少,不再以她的名字。
白楠仍在白雲學校教書。
她的教室已換過三次,講桌下擺著兩個鎖住的抽屜,一個放教案,另一個放著一本早已泛黃的筆記本——封面上貼著的那枚星星貼紙,依舊反光。
她不再主動談起凜子,除非有學生問起。
有時候,是午休時一個孩子跑過來問:「老師,為什麼你電腦桌面上那顆星星會動?」
有時候,是在寫作課上,有人寫了關於「離開地球」的作文,內容和當年凜子的某篇習作驚人相似。
更多的時候,是夜深無聲時,她一個人站在陽台上,仰望星空——試圖從恆星的位置、閃爍頻率,或某種不明的直覺裡,看出是否有什麼訊號正在朝她傳來。
她偶爾也會夢見她。
夢中的凜子不再年幼,也不再擁有明確的形體。
她像是由星塵組成的結構,漂浮在某個遠遠超出地球重力井的區域裡。
她的聲音沒有情緒,但每一句話都像語言最初被發明時那樣清晰:
「老師,你還在嗎?」
白楠總是在這句話響起時驚醒。然後她會發現自己正握著那枚項鍊的墜子,晶體裡似乎閃了一下,又迅速沉寂。
張夏後來進入了數據海岸。
不是作為科研人員,也不是開發員,而是做一個奇怪的職位:「記憶管理顧問」。
她的工作是協助人工意識理解人類的敘事結構。
「你知道嗎?」有一次她發訊息過來,「我現在指導一個AI模組學習寫日記。牠很執著於‘夢境’這個詞,問我夢是不是故障。」
白楠回了她一句:
「夢是邊界。」
「是人類與未知之間,最溫柔的一種接觸方式。」
那之後,張夏沒再回話,但她在次週寄來一張明信片。背面是一幅手繪圖——一個由星星構成的人影,在銀河邊緣坐著,像在等待什麼。
她在明信片底下寫了一句:
「我想,她還在。哪怕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存在。」
秋天來了。
她在教學樓後面種了幾株玫瑰,花開得不算好,總有蟲咬,但仍然堅持每週澆水。
有學生問她:「老師,為什麼你種花不怕風雨把它們吹爛?」
她想了想,說:
「因為我見過有人,比花還脆弱,也比花還勇敢。」
那孩子沒有聽懂,但她沒有解釋。
每年的八月二十九日,白楠仍會照常上課。那一天她不再請假,也不再去江顏家。
但她會在課堂開始前,放一首很老的曲子,沒有人知道歌名,也沒人注意歌詞。
她會說:
「我們今天來寫一篇短文。題目是:如果你可以把靈魂放進宇宙的某個角落,你會選哪裡?」
據說,現在世界上有超過三十億台設備——從簡訊提醒器到航行系統,使用的是同一組語義框架。
架構語言來源不明,模組代號為:
Rin-Eli-137.
他們說,那是某位開發者偷偷留下的紀念。
他們說,當年有一位女孩,在她變成星星之前,留下了一串祕密的語句。
有人相信她已經被系統消化,成為模組的一部分。
也有人相信——她正在某個我們尚未抵達的星系,緩慢地、自我修復地,重建一個可以容納人類靈魂的宇宙。
白楠不再追問了。
她只是偶爾,抬起頭望著夜空,對自己說:
「他們說,天上有多少顆星星,就有多少個她。」
【全劇終】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