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经验主义及其谬误
经验主义及其谬误
麦克·布洛维/文
王立秋/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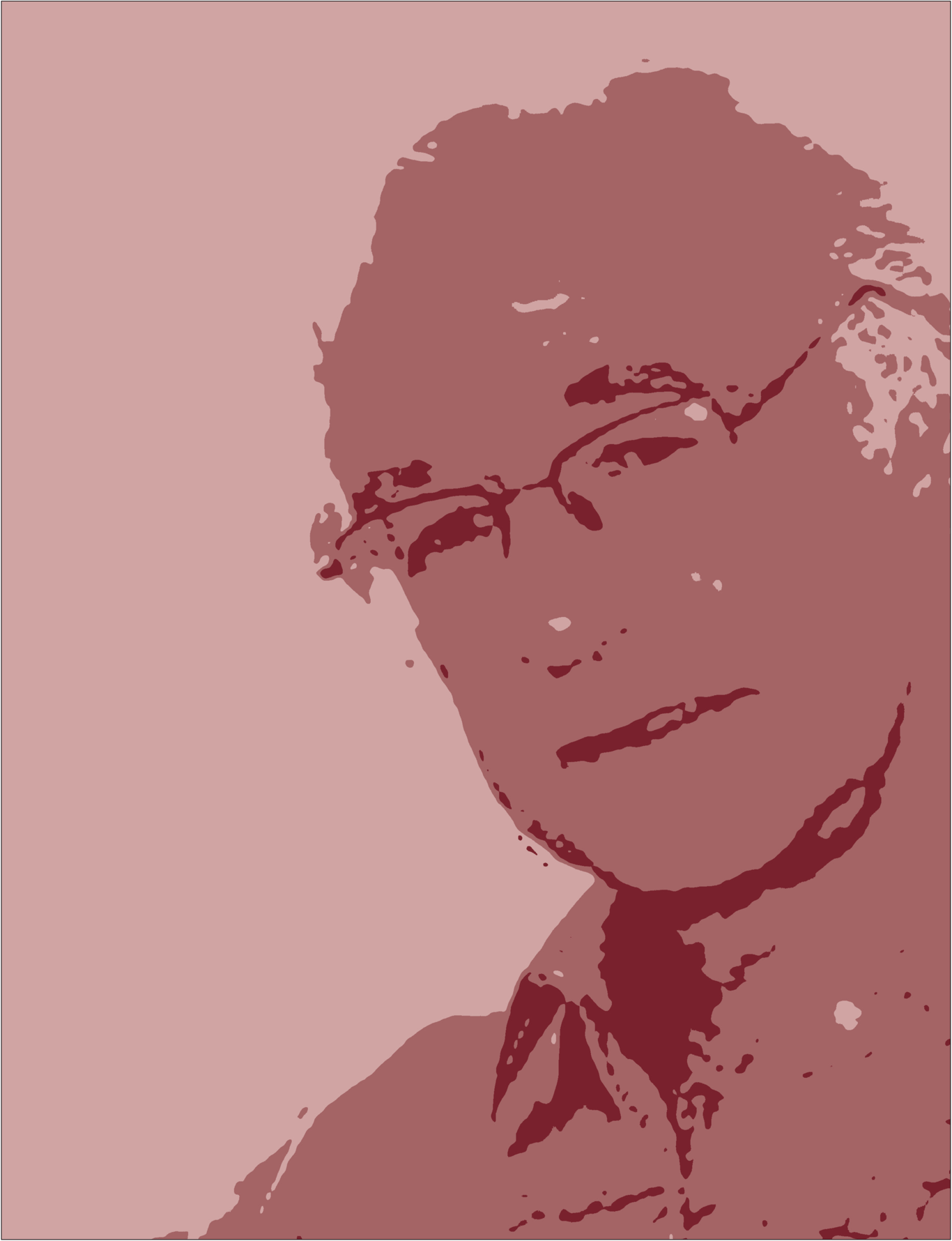
译自Michael Burawoy, “Empiricism and Its Fallacies”, Context, Volume 18, Issue 1, 2019, pp.47-53。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请勿做其他用途。
民族志学者研究他者;自己却不习惯被人研究。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卢贝特(Steven Lubet)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解毒”震撼。他在很多受众广泛的文章中,加入了一场抨击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的社会运动。戈夫曼是《在逃》一书的作者,按原本的宣传,该书是一部耗时六年、甫一出版便引发轰动的民族志作品,它暴露了国家向费城一个贫困非裔美国人社区伸出的“长臂”。
卢贝特指控戈夫曼编造证据,有不符合研究伦理的行为。在《审问民族志》(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中,卢贝特把他的批判从戈夫曼引申到更普遍而言的民族志那里去。他钻研了五十多个研究,从中寻找可疑的经验主张,并给我们上课,教我们他所谓的“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民族志。《Context》的编辑邀请我来回应卢贝特的挑战,反思民族志的意义和重要性。
卢贝特以律师的身份写作。他认为,法律程序通过的对抗过程(the adversarial process, 或当事人对等的诉讼程序)来预防“假”,而民族志的“真”则更加脆弱,因为它把自己的证据藏在秘密和匿名幕后,并——据说——把神话和传闻证据等同于现实。相应地,卢贝特要求民族志学者也要依靠多证据源,使用文书、事实核查员、可靠的证人和专业人士。此外,他还号召民族志学者要遵循其他科学家的先例,盘问彼此的“事实”。而这实际上就是他在质疑戈夫曼和其他人的一些经验主张时所遵循的策略。在审判民族志的时候,卢贝特像一个符合刻板印象的出庭律师一样行动,搜寻专著中的随机错误,以证明其不可信。因此,比如说,他对凯瑟琳·伊登(Kathryn Edin)和卢克·谢弗(Luke Shaefer)在《2美元一天》($2 a Day)中的主张,即来自密西西比的学生在看到电梯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提出质疑。他大费周折咨询各种专家以展示这是不可能的,而不管推翻这个细节对全书的论证有没有影响。因为这样的例子没有多少可选,所以他进而控诉民族志学者通过匿名来掩盖自己的踪迹,使人难以对他们的证据进行事实核查。不过,卢贝特根本就没有对自己针对的研究的理论或论证展开严肃的讨论;按他的这个推理思路,先有事实,才有理论。如果有任何事实是“假的”,那么,根据事实,理论也是“错的”。
有必要对卢贝特的批判做出回应——原因很简单,因为连像加里·法恩(Gary Fine)、沙姆斯·汗(Shamus Khan)、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和科林·耶罗马克(Colin Jerolmack)那样的优秀民族志学者都把卢贝特的批判当真了,而其他人则直接和他一起谴责戈夫曼。为什么卢贝特的指控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我们真的只是对外人的批判介入不屑一顾吗,就像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也经常看不上我们那样?那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这里面还有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卢贝特“基于证据”的民族志项目恰好响应了我们学科里常见的一种想法,即民族志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学,它要捕捉的,是未加修饰的“真”。只要民族志学者遵循经验主义的假设,那么,任何经验上的失误,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很容易让他们的研究变得不可信。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驱动的(theory-driven)民族志进路,这种进路同样关注证据,却以不同的方式、为知识的增长而利用证据。
我的回应得益于卡门·布里克(Carmen Brick)、张宏久(Andy Chang)、阿雅·法布罗斯(Aya Fabros)、香农·伊克贝(Shannon Ikebe)、安德鲁·耶格尔(Andrew Jaeger)、泰勒·里兹(Tyler Leeds)、彭昉(Thomas Peng)和三位匿名评审以及《Context》编辑的批评。我将审问卢贝特的审问,指出他简单得具有欺骗性的论证背后的误解。首先,所有民族志都“基于证据”。证据对诠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和科学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来说都很重要。只是目的不同。其次,通过引入“基于证据的”民族志和所谓的“后现代的”民族志的错误两分,卢贝特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关键区分: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经验主义民族志(empiricist ethnography),其中,理论扎根于、出自于理应不成问题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理论驱动”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主张,没有理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镜头来从“无限的多”——也即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话,就不可能有事实。这个镜头可以是常人的,常识的理论,也可以是作为科学家的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分析的理论。分析的理论——以下简称“理论”——不限于一堆抽象的规律或某种关于世界的宏大看法。理论只是持续存在的“有组织的社会学知识(organized sociological knowledge)”的代表。理论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努力而出现的,它是学者共同体通过提出相互竞争、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项目来积累知识的集体努力。
因此,理论驱动的民族志也严肃对待证据,而这恰恰是因为,它聚焦于批判的观察,有了这样的观察,我们才能在可选择的理论之间做出裁断,或重建现有的理论。的确,对理论驱动的民族志来说,事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经常被引向这样的方向:考察事实的生产,并发展辅助理论来解释事实的出现。众所周知,涂尔干声称清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高,但事实证明,对此加以更加细致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你可以说这是因为清教徒的“利己主义”,也可以说这只是因为天主教司仪不愿意把死亡记录为自杀而已。与聚焦于关键的事实相反,卢贝特的经验主义民族志把所有事实都当作“平等的”来对待,因此,他到民族志中去翻找“不合情理的”主张,既不关心事实被生产的方式,也不关心事实支撑或质疑的理论。在为这种刀耕火种的进路正名的时候,卢贝特从经验主义民族志学者那里汲取灵感,对后者来说,的确,“真”确实是自发地从“事实”中产生的。
对抗进路的运作
《审问民族志》一来就认可了经验主义学派的一位领军人物——米切尔·杜尼尔(Mitchell Duneier),获奖民族志《斯利姆的桌子》(Slim’s Table)和《人行道》(Sidewalk)的作者。在一篇题为《怎样不用民族志来说谎》(“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的文章中,杜尼尔要求通过寻找“会带来麻烦的证人(inconvenient witness)”来“审判”他们的研究。他以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的虚构记述为例,问要是格尔茨依靠别的参与者——即更贫穷的村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把他们推到了斗鸡的外围,那里人们按不同的逻辑下注——来记述,那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要让自己的批判成立,杜尼尔本应这么做:更加严肃地对待格尔茨对斗鸡的诠释;找几个真实存在的“会带来麻烦的证人”;挖出一些关键的,能起到证伪作用的证据;然后再明确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理论。相反,他的控诉全是推测。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杜尼尔查阅过关于格尔茨这篇名作的海量文献。但经验主义给了他质疑一切研究的底气,哪怕他对那个话题一窍不通。
在谈到埃里克·克里纳伯格(Eric Klinenberg)的《热浪》(Heat Wave)时,杜尼尔做得要更好。他往芝加哥跑了一趟,并在研究助理的帮助下,兴致勃勃地做了一番证伪的努力。杜尼尔把目标对准关于克里纳伯格研究的两个社区、和克里纳伯格没有研究的第三个社区的关键经验“事实”。他的结论是,克里纳伯格用来解释热浪导致的死亡的“隔离(isolation)”假设犯了区群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即以全概偏)。对杜尼尔的反驳和他提出的替代假设来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取自事后对十年前在热浪中死亡的死者的邻居和亲属的访谈。在回应中,克里纳伯格认为,杜尼尔对自己研究的“复制”使用了“独自死去(dying alone)”这样一个成问题的定义,误读了官方文件,导致对隔离导致的死亡抽样不足,并依靠“传闻”。克里纳伯格批评杜尼尔采纳了一种广泛流传却“毫无根据”的公共记述,把死亡归咎于“滥用药物”——这是一个方便的解释,把受害者的死怪到他们自己头上,而免去了受访者应当为朋友、邻居或亲戚的死亡承担的责任。
卢贝特的对抗进路就是这样运作的。奇怪的是,它看起来和斗鸡一样,是一场赢的一方即为“真”的死斗。只是在这里,和在其他太多的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胜利者。这番交手既表明要通过复制原始研究来达到反驳的目的——就像长期以来在物理科学中人们理解的那样,和如今,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也开始认为的那样——是多么地困难,也质疑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事实是坚固的、从根本上无可辩驳。也就是说,各种反驳的尝试恰恰表明,事实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socially produced)。关于证据的生产背后的理论的冲突,和关于证据被认为证实了或推翻了的理论的冲突一样多,而这,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理论的优先性。
冲突的各方都坚持,他们的理论更加真实地重现(rendition)了现实,但从科学的立场来看,这看起来像是一场由对立的理论——一方着眼于个体层面的解释,另一方则聚焦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状况——指导的两个研究项目之间的战斗。因为各方都在防御对手的证伪的同时,用证伪来对付对方,所以,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为单一的“真”而进行的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无法解决的争议。理论折射出截然不同的,社会中的利益,而杜尼尔和卢贝特都对这样一种可能性避而不谈,即“证据”也会受“利益”影响而产生屈折变化。
社会科学的两个维度
由于卢贝特没有说明民族志的前提,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点讲清楚。社会科学区别于物理科学的地方,在于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参与。无论我们如何试图把自己和“那边的”世界隔离开,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欺骗自己我们是“客观的”观察者,我们研究的世界都会重新糊我们一脸。的确,随着大学变成一个不断受外部政治与经济利益冲击的斗争地带,中立的外部观察者的神话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而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论,民族志认识到或者说承认这点,即我们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变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原型。
因此,社会科学为一种双重诠释学(double hermeneutic)所定义。社会科学的科学之维,由理论和数据之间的互动构成,而这个互动本身,又内嵌于一个学术场。而社会科学的反身之维,则涉及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的互动,这个互动本身又内嵌于一个权力场。压制反身的一轴,假装我们不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会让我们回到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而压制科学的一轴,则会引出后现代的诠释,或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变革项目。
正如反身的一轴可能更强调观察者也可能更强调参与者一样,科学一轴也总是介于两种进路之间:一方面,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民族志,其中,数据会为自己说话,而理论则如同“白板”一样,在“听”和“看”中方才写上东西并因此而成形;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驱动”的民族志,其工作的出发点是,需要先有一个镜头,才能理解实地现场。没有镜头,世界将一片模糊。因此,我们不是作为“中立的”个体,而是带着为常识和积累的学科知识所定义的视角进入实地。因此,理论驱动的民族志的任务,就从发现新理论,转向了重建现有的理论。在这里,关键的标准不是逼真(verisimilitude),而是知识的增长。民族志学者不是一个英雄般的个体,不是发现新世界的勇敢探索者,而是一个参与推进知识这个集体事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
处理传闻,区分民族志
在参与的同时研究世界会造成多种困境,但它也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使我们能够区分传闻和被观察到的现实。的确,其方法,是分析人们说的和人们做的之间、口上说的规范和实际的实践之间、言语辩护和行为之间的对话。参与式观察天生就怀疑信息报道人的记述是“真”的唯一版本,认为这些记述只是给出了“真”的一面,并且它们还会夸大这一面。即便在说谎的情况下,记述会说谎这点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东西,因为通过指出人们想要隐藏的东西,这些记述指出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利益。
在这方面,被卢贝特奉为严格记录之典范的学术作品,即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的《扫地出门》(Evicted),实际上做得比戈夫曼的《在逃》还要差。德斯蒙德的流畅叙事——这一叙事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两个面临住房不安全的绝望社区中的生活——未能区分人们关于自己做了什么的说法,和他对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的观察。通过从现场删去自己,德斯蒙德使读者既无从得知他是怎样收集到这些生动、详细的故事的,也没法知道他和他的信息报道人是什么关系。比如说,通过驱逐租户的房东去找租户,会对租户的自我报道产生什么影响?卢贝被德斯蒙德太过于简短的方法论声明给骗了,因此也就违反了他自己对“传闻”的限制。在不依靠传闻这点上,戈夫曼看起来比德斯蒙德更诚实、谨慎得多,虽然这也让她,和德斯蒙德相比,更容易引发争议。
在这里,拿其他方法——面对传闻的指控,这些方法或多或少是无助的——来和民族志比较是重要的。比如说,调查研究就不会立刻核查它收集的数据。任何给定的问题,对不同的受访者来说都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此,访谈情景往往塑造了对问题的回答。在思考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受访者可能会把预期行为与现实混为一谈。调查研究者只有在(根据研究做出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说,就像在选举中那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被误导了。焦点访谈提供了进行更加细致的追问的机会,但人们关于自己做了什么的说法和关于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说法之间依然存在差距。就像卢贝特指出的那样,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会对《纽约时报》的记者陈述某种特殊叙事以获取救援物资。并且,杜尼尔在问“证人”芝加哥热浪中的死亡原因并认为他们的回答无可辩驳的时候,也丢掉了自己在民族志方面的感受力。实验社会心理学则是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在那里,研究者在实验室中观察人的行为,却不知道同样这些人在更复杂的实验室——即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会怎样行为。
通过进入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参与式观察提供了一种持续的核查,即持续地核查人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当然,这也并非万无一失。卢贝特给我们提供了凯瑟琳·弗里德(Katherine Verdery)的例子,她通过罗马尼亚警方的档案发现,在她研究的罗马尼亚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可能要比她通过民族志看到的要多。不过,民族志依然给了我们理解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生产自己的独特“视角”的最好机会。
把文书置入情景
卢贝特不信任民族志学者,所以他提议我们应该对民族志数据进行大量的外部核查。最重要的是,他敦促我们要查阅“文书”——它们能够提供“和可能随每次重述而发生变化的,人类脆弱的记忆不一样,冻结在时间中的”证据(p. 23)。可被冻结在时间中,并不会让一个证据变得更加可靠。文书也是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它们也会反映它们的生产者的利益。对其他外部核查来说也一样:每一种核查都会提供一种受特定的、看不见的利益影响的视角。
说到底,卢贝特对单一的“真”的追求,是通过给某些证据源权威与合法性,同时拒绝给其他证据源权威与合法性来实现的。然而,权威既反映了权力,又反映了真实性:他认为医院管理人员、前公设辩护律师和警察的说法是可信的,以此来驳斥戈夫曼观察到的情况(即警察会在急诊室附近转来转去,审阅医院的记录寻找犯罪嫌疑人)。当然,对严肃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相互争论的看法可以提供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数据点,而是图绘一个争议场的经验基础。
毕竟,对民族志研究来说,一个持久的动机,就是质疑“官方的”世界观(比方说报告中、媒体中、常识中宣扬的那些)。民族志通过反对刻板印象和“传统智慧”,在关于工作、家庭、种族、阶级和性的研究中创造了各种新的研究项目。金伯莉·凯·黄(Kimberly Kay Hoang)在她关于性工作的民族志《买卖欲望》(Dealing in Desire)中通过展示这点——她研究的胡志明市的性工作者是自愿入行,并且主动同意她们不同的劳动过程的——驳斥了NGO的这一观点,即全球南方的性工作总是某种形式的“胁迫贩卖(coerced trafficking)”。通过比较不同的市场生态位,黄也展示了何以性产业处在全球资本多回路的交叉点上(她的《蛛网资本主义》[Spiderweb Capitalism]中文版即将出版)。没有参与式观察,是不可能得出这些结论的,而参与式观察也因此而有了自己的权威。
卢贝特把法律程序的特殊看法带入了他对民族志的评估:作为一场为“真”而进行的对抗斗争的审判。但一种替代性的进路,是把审判看作一场不同视角之间的斗争。每一方都诉诸不同的先例、假设和诠释。总的来说,民族志学者可以图绘出行动者在更宽泛的支配场中的不同位置;按这种看法,法庭也是一个场,其中,行动者——侦探、证人、专家、出庭律师、被告、法官、陪审团——把他们不同的“观点”带进来,对案件产生影响,而这些观点,又反映了场中不同的位置,这些位置又给了不同类别的行动者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在认识到(存在)不同视角的情况下,社会学家可以有意采取任一既定行动者的立场,也可以试图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场。但无论采取怎样的做法,卢贝特试图把场简化为一个单一数据点的做法,都淡化了场的复杂性,而场的复杂性本身也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实地工作,从“假”到证伪
如果说,寻找“假”是经验主义民族志的根基,那么,寻找证伪,就是理论驱动的民族志的本质。这就是我们每次重返实地时做的事情。任何实地现场都是无限复杂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套预设、问题、概念、编码图式——需要一个理论,在这个词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来理解它。理论告诉我们要找什么,使我们对“格格不入的(out of place)”东西敏感。一个好的理论会做出预测并鼓励和期待出人意料、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而且,这也应该对我们写实地研究笔记的方式产生影响,允许我们进行实验——在真实世界的实验中检验和修正假设。我们的确寻求证实,但为了知识的增长,寻求证伪也是必不可少的,证伪使我们能够通过前往实地,一点一点地建立理论。没有证伪,理论就会停滞。
理论驱动的民族志学者不一定会在自己出版的作品中揭示他们一天又一天的实地工作的迭代过程,但他们会把实地工作的程度划分为“重回”。回到黄对越南性工作者的研究,我们看到,她是怎样从文献开始的。这些文献在“发达/欠发达”或北/南范畴下看待性别与资本的共同生产,而这,也符合她实地工作第一阶段的观察。2009年,当她再次回实地研究的时候,黄找了个招待和酒保的工作。现在,她看到,北-南这对概念不足以解释2009年后越南经济扩张、亚洲资本崛起创造的不同市场生态位了:一个生态位是面向西方生意人的,而另一个地位最高的生态位服务的则是越南的精英,后者用性产业来促进商业交易。而在2013年第三次回去的时候,黄发现性产业又发生了一次重构,这就要求她重建她的全球资本回路理论。黄不断地重回实地,使她能够证伪并因此重建全球语境下的性工作理论。
民族志的伦理——真实世界中的研究
理论和数据的互动塑造了民族志学者“对真实世界的浸入(real-world immersion)”也即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并为后者所塑造。也许,《在逃》最令人惊恐的地方,在于戈夫曼的方法论附录,她在里面描述了和麦克一起追杀杀害后者密友恰克凶手的过程。卢贝特震惊于这点,即戈夫曼可能成为一桩他相信是重罪的罪行的共犯。我则震惊于这点,即他竟然会为此而感到震惊。
民族志是在参与者的时空中对世界的研究。如果你研究犯罪的人,你就可能会被卷入犯罪。为了和你研究的人保持联系,你经常不得不做他们做的事。如果那意味着犯罪,你也必须接受后果。
在我的研究中,我也违反过法律。当我研究赞比亚大学的学生的时候,我就被拉去参加了1971年的一次学生示威活动。我们一千人在法国使馆游行,抗议法国对搞种族隔离的南非的经济支持。我和其他人一起被捕。到审判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拿研究来为我对示威活动的参与辩护。对我的审判证明了我对那个怀疑我的动机的社群的忠诚,它帮助我缓和了在整个实地工作过程中不断给我制造困境的种族与地位鸿沟。
但参与也为我对赞比亚政治场中运作的力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那次抗议后来升级为一次涉及学生、大学管理部门、媒体、总统和教育部的重大对抗。对事件的这一悲剧性发展的参与,使我能够剖析大学在社会中的矛盾地位和相互竞争的向上流动渠道之间的冲突。
违法还只是内嵌于不平等权力场、被迫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中选边站的民族志学者面临的日常困境之一。伦理困境不会随实地工作而结束。它们会在对你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否匿名——的书面呈现中延续。卢贝特控诉“匿名”使民族志难以验真。但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民族志学者对一个充满权力的场的浸入。因此,传统上,人们是在保护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为“匿名”正名的,哪怕有些人认为,只有通过公开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身份,才能让民族志学者对那些研究对象负责。除可能会给研究对象带来风险外,这样的实地工作策略也会使民族志学者受制于研究对象的世界观。民族志会被参与者牢固掌握的常识控制,并因此而引发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末日。毕竟,科学的要点就在于揭示参与者看不到的东西。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标不是学习关于案例的知识,那是参与者想做的事情;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从案例中学习,以达到拓展科学知识的目的。
民族志有它独特的困境——进去和出来,公开的和隐蔽的参与,同时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打交道,谁有研究谁的立场,研究那些价值观令人厌恶的人,等等——但这些困境,都源于民族志的科学之维与反身之维之间的关系。民族志的苦与乐就在于我们在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的在场(presence)的敏锐性。随着学界的墙变得越来越薄,随着我们所做的研究产生真正的后果,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侵入学术活动,随着我们愈发认识到我们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些民族志困境也会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出现。
理论驱动的社会科学
对爱丽丝·戈夫曼的攻击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一位资深教授把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赶出学界的类似案例。大卫·亚伯拉罕(David Abraham)写了一篇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崩溃的论文,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备受好评,帮助他在普林斯顿拿到了一个终身轨的历史学教职,而该论文后来也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伯克利大学现代德国史杰出教授杰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Feldman)是该书最初的评审人之一。他极不情愿地承认《魏玛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Weimar Republic)很重要,研究也做得很好,虽然它是通过一个令人厌恶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来表述的。这时候,耶鲁大学的资深历史学教授亨利·A.特纳(Henry A. Turner)进场了,他也致力于同一主题的研究,但角度不同。在一位德国合作者的帮助下,特纳发现了亚伯拉罕脚注里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告知了费尔德曼。
费尔德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就好像亚伯拉罕蓄意欺骗他一样,于是他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报复行动,指控亚伯拉罕欺诈。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都成了激烈的战场。在亚伯拉罕被指控在书中给自己在大屠杀中受难——据说,这是假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死在集中营——的父母的献词中撒谎的时候,这场争斗的水准跌穿了底线。历史学家对此意见不一。亚伯拉罕承认错误,但坚决否认蓄意造假。他的一些错误削弱了他的论证,一些错误强化了他的论证。大多数错误无关紧要。不过,即便有著名的学者为亚伯拉罕辩护,费尔德曼还是大获全胜,普林斯顿大学拒绝授予亚伯拉罕终身教职。接着费尔德曼又给所有人写信,确保亚伯拉罕后续得不到任何工作机会。亚伯拉罕被迫退出历史专业,进入法学院,后来成为迈阿密大学的法学教授。
据我所知,卢贝特倒是没有试图把戈夫曼赶出社会学,虽然他的论证可以被用来针对她。和历史学不一样,社会学并非由不受直接专业外同事干预的自治领地构成。不过,在检察的运作方式上倒是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批评者都聚焦于证据而非作者提出的理论。通过聚焦于小的、可争论的错误,他们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费尔德曼那里,是因为理论太过于重要,而在卢贝特这里,则是因为理论不重要。在这两个案例中,人们都在关于“错误”的激烈争斗中失去了扩展知识的机会。而受害者都是容易受终身教职压力影响、被资深学者攻击的有批判精神的年轻学者这点很可能并非偶然。这样的权力悬殊在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就好像经验主义的超越目标证明了针对年轻学者的正当性那样。
民族志太容易被一种常识的科学观,被一种经验主义的看法劫持了,这种看法认为理论本身是白板,内容完全源于事实,所以,如果你把事实搞错了,那么根据事实,理论也是错的,你的贡献就是零(甚至是负的)。所以,卢贝特变得像麦克一样,抄起一把隐喻的枪,到每一个角落去寻找致命的错误。最令人不安的是,卢贝特说服了其他民族志学者和他一起加入他的这场经验主义十字军东侵。
研究科学的民族志学者、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哲学家早就抛弃了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不可信的视角从未应用于物理科学,却被强加给了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科学,使他们被武断的标准钳制。从卡尔·波普尔对归纳推理的批判再到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概念,对于人们实际上是怎样实践科学的,我们早就有了更好得多得多的理解。我们从理论开始,以理论告终,而证据则驱动着前后理论之间的调整。
在社会学中,经验主义民族志是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这一主流的回应而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民族志认为,理论应该从“地里”(the ground)长出来,而不是从帕森斯飘忽的大脑中冒出来。没错。事实证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有效武器。可结构功能主义早就死了。民族志学者没必要再去延续一种过时的科学哲学,除非是为了把它当作一种在争议场中镇压年轻起义者的权力策略来使用。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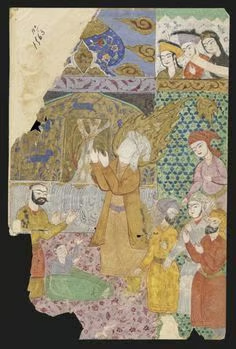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