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權結構的本末倒置
在人類早期社會中,當生存與延續高度依賴生育本身時,女性因為掌握不可替代的孕育能力,在親屬結構、血緣認定與社會組織中,長期佔據核心位置。
隨著農耕社會的出現,土地成為可佔有、可繼承的生產資料,社會開始關注「誰擁有資源、由誰繼承」。在這一過程中,男性在體力、武力與對資源的控制上逐漸佔據優勢,配合私有制與一夫一妻制的確立,男權結構開始成形,並被制度化、合法化。
自農耕社會以來,無論是奴隸制、封建制還是工業化體系,男權結構始終作為一種底層邏輯存在:由男性主導生產與資源分配,女性則更多被納入家庭與生育體系之中。在這過程中,女性甚至變成了附屬品,戰利品。
在沒有戰爭、饑荒或大規模災難的情況下,人類卻開始大規模選擇不婚、不育、不戀。這種現象並非源於自然條件的惡化,而更像是一種結構性回饋——當未來本身不再值得被期待,繁衍就失去了其內在動力。
男權社會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延續那麽久,並不僅僅因為暴力、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強制,而是因為它在很長一段歷史中,具備一個穩定且自洽的運作前提。
一切的前提在於:生產行為本身,能夠回饋到生命延續。
在這一結構中,生產、家庭、生育與消費形成了一條相互支撐的循環。
男性進入狩獵、耕作或工廠體系,透過勞動換取資源與收入;女性進入家庭與生育結構,將資源轉化為下一代的成長與延續。
這並非一種單向的壓迫關係,而是一套在歷史條件下能夠自我複製的社會分工模式。
關鍵是,與性別的本身或者角色無關,
關鍵在於:這套結構對大多數身處其中的人而言,仍然值得被投入、被相信、被延續。
因為在這個結構裡:生產出來的東西,有人需要;付出的勞動,能兌換成穩定生活;建立家庭,意味著確定的未來;生育下一代,代表希望而非負擔。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願意將個人的時間、身體與情感,投入到家庭與繁衍之中,而這種投入本身就是對這種結構的認同。
男權結構的「有效性」,並非來自於它的正義性,
而是來自於它在現實層面仍然能完成承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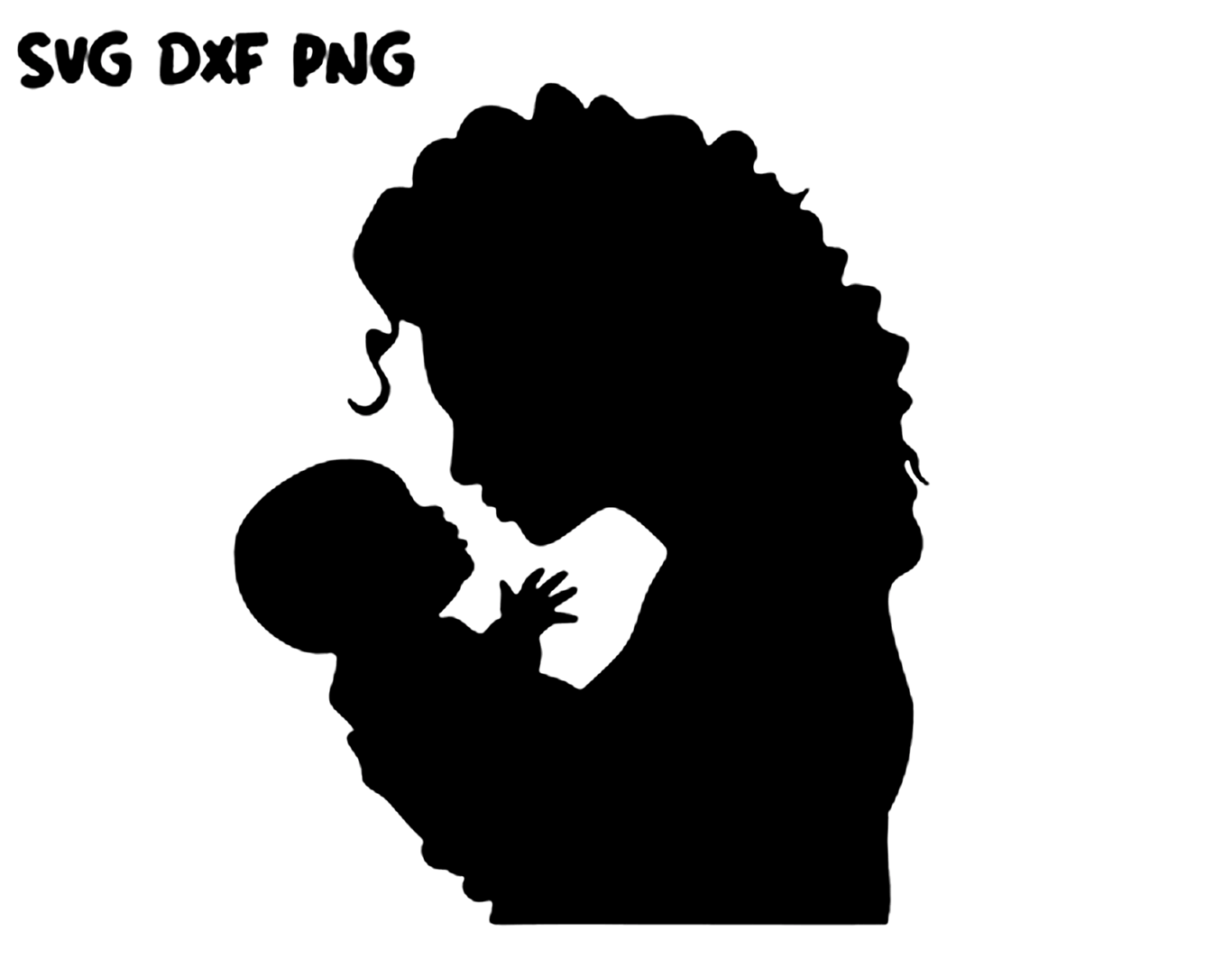
一個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事實是
歷史上的多數人,並不是在追求抽象的權力結構,而是在衡量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
活下去,是否值得?
把生命交給下一代,是否值得?
即便是那些看似迷戀權力的人,在心理層面同樣圍繞著這個問題運轉,只是他們選擇以更大的權力與資源控制,來確保這一答案維持在肯定的一側。
在這種心理下,只要答案仍然偏向肯定,社會就會繼續繁衍,即便結構本身充滿不平等。
也正因如此,男權社會在漫長的歷史中,即便伴隨戰爭、剝削與暴力,卻依然沒有出現大規模、持續性的「自願斷代」。
也就是說,在崩壞之前,我們從這種男權結構裏面獲得的好處是可以令我們容忍男權結構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
而那些看上去迷戀權力的人,實則在心理同樣也想著這個問題:活下去,是否值得;
把生命交給下一代,是否值得。
只是他們是通過獲取更大的權力來實現這一目的而已
也正因為這個前提曾經長期成立,當它開始崩塌時,後果才會如此劇烈、如此反常。
當生產行為無法再兌現為穩定生活,
當家庭成為高風險投資,
當未來本身失去可預期性,
當忍辱負重變得不再有收益,
繁衍便不再是一種自然選擇,
而成了一種理性上難以承擔的賭注。
現在整個結構,甚至連「勉強接受」這一層心理平衡都已經失效。
當生產無法回饋到個體本身,它自然也無法再回饋到下一代。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繁衍從來不是一種需要被反覆說服的選擇。只要環境尚可承受,只要未來仍可想像,生命便會自然地走向延續。
通常來説,戰爭、饑荒、瘟疫、天災,才是歷史上真正壓制生育的力量。
然而,當代社會卻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異象:在沒有大規模戰爭、沒有普遍饑荒、沒有整體性疾病蔓延的情況下,人類開始主動選擇不婚、不育、不戀。
同時,這不是局部地區的偶發現象,而是在高度現代化、物質條件相對穩定的社會中,同步出現的趨勢。這種現象之所以反常,正是因為它違背了生物在安全環境中的基本行為邏輯。
當一個物種在生存壓力明顯下降的情況下,卻系統性地放棄繁衍,往往意味著一個更深層的訊號——環境本身,已經不再對「延續生命」具有吸引力。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選擇並非源於對生命的厭惡,也並非源於單純的個人享樂主義。而是源於,權衡利弊后,這件事情不值得。
換句話說,人們已經覺得,繁衍這件事情已經逐漸失去它的價值,感覺不值得投入。
不值得投入的出現,通常只有兩種情況,第一,有其他更好的投入選擇。第二,整個環境的變化已經令人失去信心。
所以,它更像是一種集體層面的理性回饋。
在這個時代,
不婚,往往意味著對高風險關係結構的迴避;
不育,意味著拒絕將下一代投放進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未來;
不戀,則是對情感投入回報失衡的直接反應。
這三者並非彼此獨立,都同時指向同一個核心判斷:
投入與回饋之間,已經失去了可接受的比例,男權結構走到今天,已經失去平衡。
當建立家庭不再對應穩定生活,當生育被等同於長期負債,
當情感關係成為消耗而非支持,當結構失衡,回饋減少,
退出,便不再是逃避,而是成了一種對結構失效的默認判決。
因此,不婚,不育,不戀,與其説是一種觀念的轉變,還不如說,這是一種對現有結構的一個集體性的回應,同時這種回應是人們理性地平衡好各方得失后的結果。
通俗來説就是,當初人們可以容忍男權結構下的不公,壓迫,暴力,那是因爲,回饋回來的資源能夠平衡人們的怨氣。
而現在,人們就反過來,容忍反抗和不合作的代價,也不想把更多的資源浪費在這個注定會壓迫,暴力,不公的男權結構裏。
現在已經是文明終結前,人們共同發出的警告,
當社會無法回答「為何而生」,無法找出新的平衡點時,
生命的延續,只會有越來越多的自發性暫停。
這正是當下男權結構正在面對的真正危機。
一個失去回饋能力、卻仍要求無限投入的結構,
已經走到了必須被重新定義的邊緣。

在男權結構的原始設計中,是為了支撐家庭、承接生命、延續族群,
保護後代,使個體的勞動能夠轉化為可被繼承和延續的未來。
然而,現代社會正在發生的,卻是一種徹底的倒轉,
隨著生產資料被高度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人被系統性地剝離了對資源、土地與未來的實質控制權。
僅剩下「被雇傭的生產能力」。
在這種結構中,即便個體生產的再多,再努力,再堅持,也只不過是可以被隨時替換掉的耗材,這就是努力無用論會出現的原因。
生命不再被視為需要被承接的核心,而是被視為一種需要被延後、被壓縮、被計算的成本。
在這種生產行為模式下,生產逐漸脫離了生命延續的目的,轉而成為一種只服務於結構本身的空轉。於是,一個本應支撐生命的結構,開始反過來消耗生命。
男權結構仍然繼續要求人們服從、忍耐、投入,卻無法再為這些投入提供對等的回饋。
它繼續要求生產,卻拒絕承接由生產所應當導向的生命延續。
這正是本末倒置發生的時刻。
沒有生命,
就沒有消費;
沒有消費,
就沒有可持續的生產;
沒有未來,
任何生產都只剩下自我損耗。
當一個結構以「生產」為最高價值導向,卻將「生命」不斷邊緣化、工具化、延後化,它就已經喪失了作為文明結構的正當性基礎。
當一個社會走到這一步,要考慮已經不是怎麽去調整,而是要重新考慮,男權結構直到如今,是否真的還適用於當下和未來,去做一個社會和國家的底層運轉基礎。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男權結構也被迫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
第一,繼續當下男權結構的模式,讓人類文明就此終結,或者被取代
第二,對當下男權結構進行革命,對當下分配模式進行徹底洗牌。
在這兩種走向之間,
不存在任何可以局部倖免的中間狀態。
要麽徹底革命,要麽彼此終結
沒有第三條路。
在長期的歷史運作中,男權結構始終被視為一種「穩定器」。它透過生產、佔有與分配,
維持社會秩序,並以家庭與生育作為再生機制,將自身不斷複製到下一代。
然而,當這一結構進入高度集中與極端效率化的階段,反噬便不再來自外部,而是直接發生在它自身的核心機制之中。
當生產資料被牢牢鎖定在極少數人手裡,男權結構便開始失去一個關鍵能力——將生產轉化為再生。在這樣的條件下,生產仍在被要求,服從仍在被強化,競爭仍在被鼓勵,但這一切已經不再導向家庭、後代與未來,而是導向回到男權結構的本身。
簡單來説就是,我們的努力,堅持,忍讓,帶來的好處,以前是導向家庭,而現在所帶來的好處,卻導向回到男權結構,這樣子,除了結構的本身越來越牢固,强大,而且男權結構帶來的壓迫,不公,暴力等一系列的問題也隨之在不斷加大。
它透過壓縮成本來維持生產,卻同步壓縮了家庭形成的可能;它透過提高門檻來篩選「有價值的人」,卻同時排除了大多數人進入生育與延續的資格。
在這個過程中,男性被轉化為可替換的勞動單位,女性被轉化為高風險的生育承擔者,
而下一代,則被推遲為一個「條件允許時才考慮的選項」。
當延續被不斷推遲,它最終就會被取消。
這不是外來的毀滅,也不是被顛覆的結果,
而是一個結構在完成自身邏輯後,必然到達的終點。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在現代資本結構中選擇極端壟斷生產資料的行為,本來就自動等同於要承擔結構性反噬的後果。
在一個以再生為前提的文明中,在一個以互相依賴的系統中——
無人可以只收割、不承擔後果。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