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确答案”之外:《The Easter Parade》对选择女权主义的解构
在许多女性主义小说里,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设定:两个女人,通常是姐妹或者好朋友,一个选择了传统家庭,一个投身独立事业。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后者在历经风雨后,活成了闪闪发光的大女主,而前者则在琐碎生活中黯然失色。
Richard Yates在1976年出版的《The Easter Parade》里,却讲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拒绝落入“传统等于失败、独立等于胜利”的二元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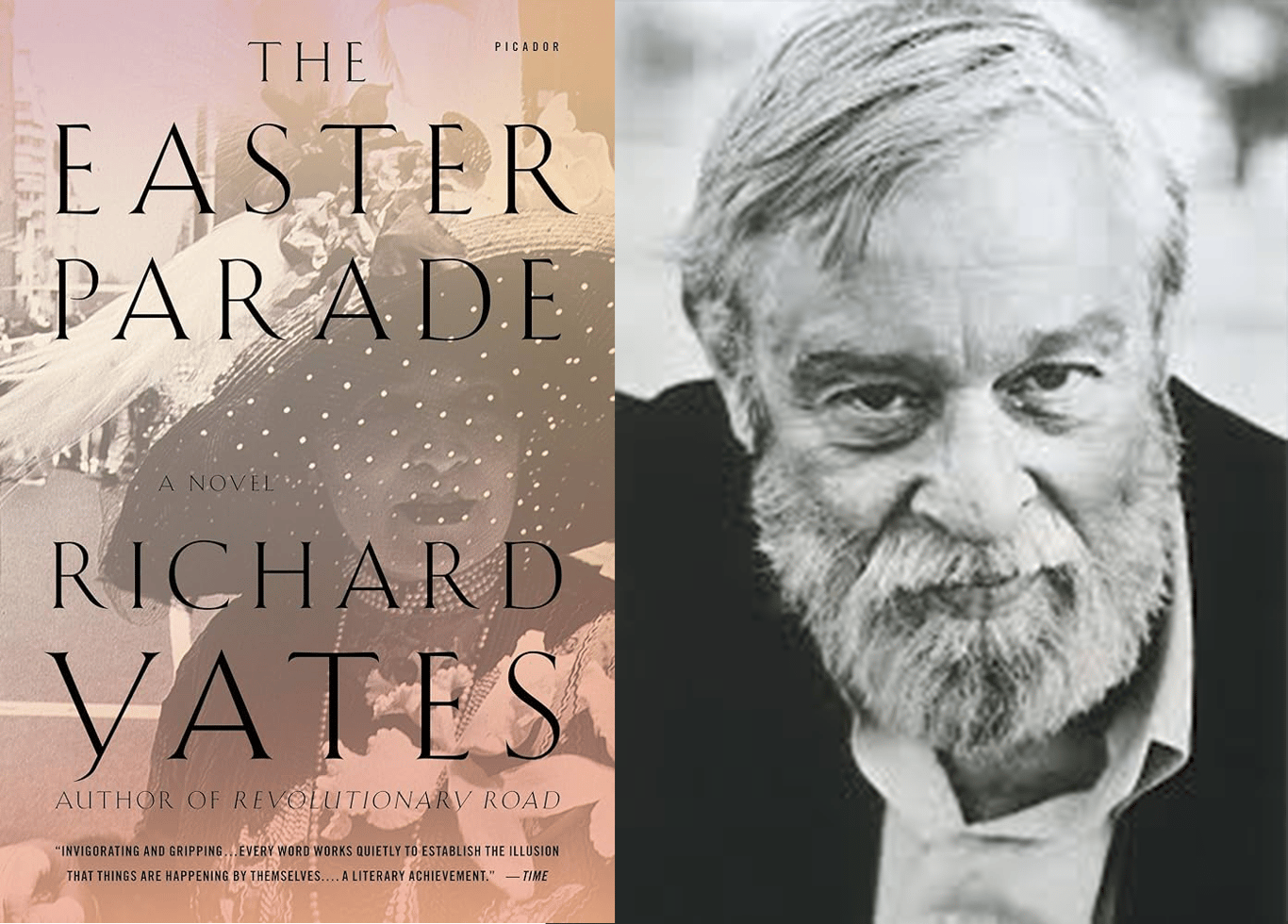
通过对姐妹二人——Sarah与Emily——迥异人生的平行展现,Yates揭示出更残酷的现实:在父权制和社会结构的重压下,女性并非真的拥有自由的选择,而是始终被困在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Yates以平行叙事悄然解构了两个主流神话:一是依托个人奋斗就能实现的“美国梦”,二是“事业就能拯救女性”的现代寓言。Yates的写作没有提供慰藉,而是迫使读者直面一个事实:无论选择传统婚姻还是独立人生,等待她们的,可能都是幻灭与孤独。
殊途同归:两个姐妹与一个困境
在《The Easter Parade》里,姐姐Sarah看似走上了战后美国社会最推崇的道路:一位体面的丈夫、一栋郊区别墅和三个孩子。她努力扮演着“完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把婚姻当作人生问题的答案。然而,这种表面的安稳背后却是长年的家庭暴力。Sarah在沉默中承受着丈夫的殴打,用酒精麻痹痛苦,最终甚至可能死于家暴。
相比之下,妹妹Emily选择了另一条被视为“解放”的道路。她是那个年代的先锋女性,是“最初的解放者”。她拒绝母亲的庸俗价值观,凭借奖学金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追求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进入新闻和广告行业,强调事业与自我实现,在感情中也坚持自主,不愿为没有灵魂的婚姻牺牲自由。Emily的选择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诉求高度一致:女性不应局限于家庭,而应探索更广阔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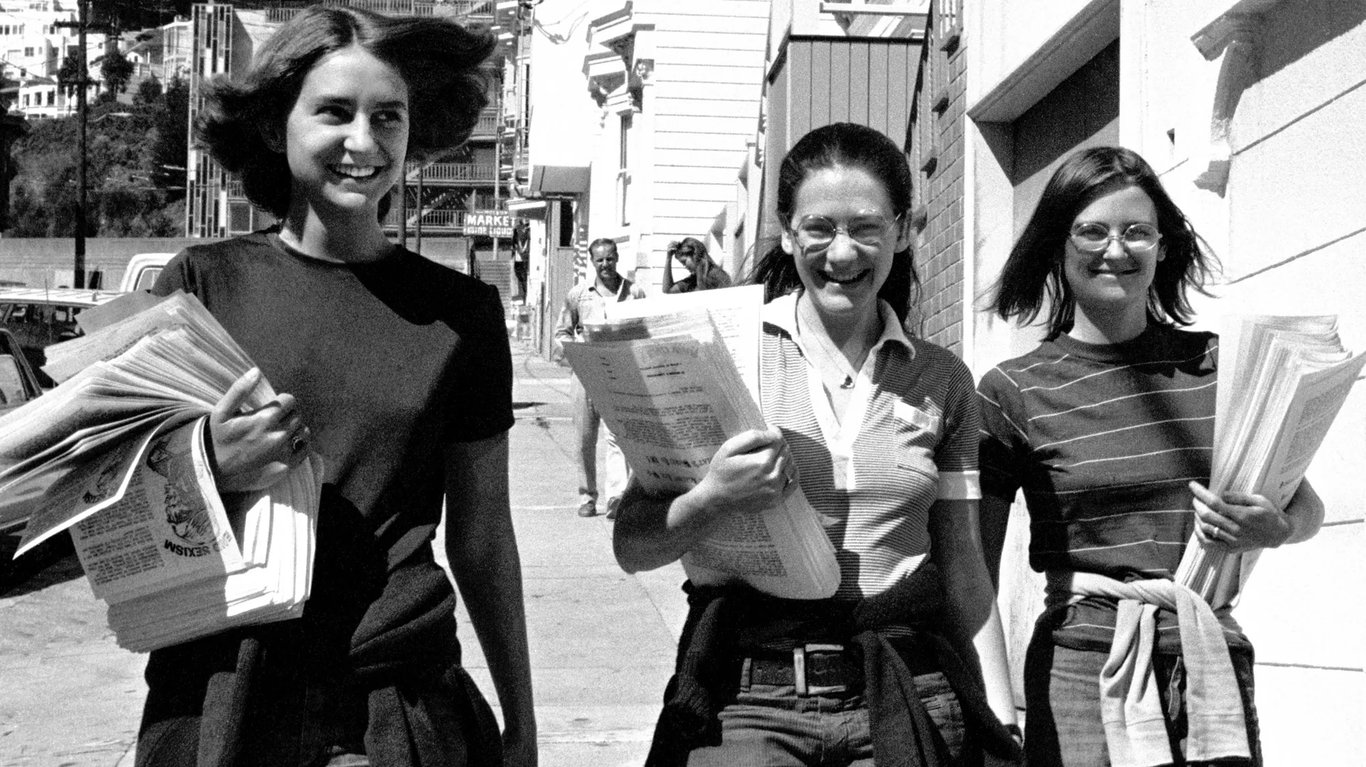
但Yates没有让任何一人成为赢家。
独立并未给Emily带来真正的满足。她在职场屡遭挫折,情感关系也常常以失望告终,最终不得不依赖社会救济度日。年近五十的她孤身一人,陷入彻底的困惑与迷惘。Emily的结局粉碎了“事业可以拯救女性”的神话,也凸显了两条看似对立的人生道路,其实都通向悲剧。
Yates对“选择即自由”的祛魅
Richard Yates在《The Easter Parade》中提出了一种与后来流行的“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完全不同的叙事路径。
选择女性主义常常把女性解放简化为一连串个人抉择,仿佛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拼事业、保持独立、拒绝传统——就能获得自由与圆满。而Yates却借由格里姆斯姐妹的命运告诉我们,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他写出的不仅仅是两个女性的个人悲剧,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现实:在父权社会的结构性桎梏下,所谓“选择”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它往往只是另一种无力的幻觉。
“拥有一切”的理想与“一无所有”的现实
这种将解放简化为“正确选择”的逻辑,在Yates写下这本书的数十年后,反而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并最终被浓缩成一个光鲜亮丽的现代神话——“拥有一切(having it all)”。
以《欲望都市》为代表的“爽文”故事常为现代女性勾画一幅“拥有一切”的理想图景:在大城市中,女性可以通过事业成功、自由的性关系和强大的消费能力,实现个人价值的圆满。这种叙事将像Emily Grimes这样的角色塑造成偶像,许诺给她一个幸福结局。

然而,Yates笔下的Emily直接粉碎了这一神话。她几乎是《欲望都市》中角色的原型: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追求事业的“解放女性”,经济独立,性观念开放,拒绝用婚姻定义自己。
在“爽文”的逻辑中,她理应成为赢家。然而,Yates以冷酷的现实主义揭示了Emily的结局:她的感情注定失败,事业也未能成功,最终陷入孤独和贫困。她的独立没有带来期待中的自由,而是更加深刻的孤立与空虚。
Yates通过Emily的悲剧对“事业能拯救女性”和“独立即是胜利”的观念提出了深刻质疑。Emily的人生正是对《欲望都市》式理想结局的提前否定,揭示了表面光鲜的个人主义背后可能藏着的空虚和失败。
消费主义与赋权的错觉
这种“拥有一切”的许诺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现代变体——它不仅告诉你可以通过正确选择获得幸福,甚至还为这份幸福标上了价码。当“赋权”本身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时,女性主义叙事便陷入了最深的悖论。
在《欲望都市》中,女性通过购买奢侈品、享受高消费生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仿佛“赋权”是一种可以用信用卡购买的商品。

然而,《The Easter Parade》深刻揭示了这种消费主义逻辑的空洞。Grimes姐妹的痛苦源自内心深处,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填补她们的空虚。
Sarah拥有理想的郊区别墅,这座象征着中产阶级成功的房子,却对她来说是一座监狱,而非幸福的家园。Emily生活在消费中心纽约,尽管拥有繁华的城市生活,但她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依然未得到解救。
Yates通过她们的故事表明,真正的幸福和自我价值无法通过消费获得,这也使得那些将“赋权”与消费能力划等号的“爽文”叙事,在现实面前显得浅薄而虚假。
拒绝廉价希望:Yates的女性主义现实主义
读《The Easter Parade》不是一次轻松的体验。它不负责治愈,也不提供慰藉,它拒绝了基于个人“选择”的乐观叙事和廉价的希望。Yates揭示了“选择”的虚幻性,和那些在背后限制所有选择的、无形的“笼子”。
相比之下,后来的“女权爽文”提供的正是Yates早已识破并摒弃的“美国梦”变体,这些故事承诺,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无论是事业、伴侣还是消费),个人就能实现圆满。而《The Easter Parade》通过冷静而残酷的叙述,提前揭示了这种个人主义解决方案的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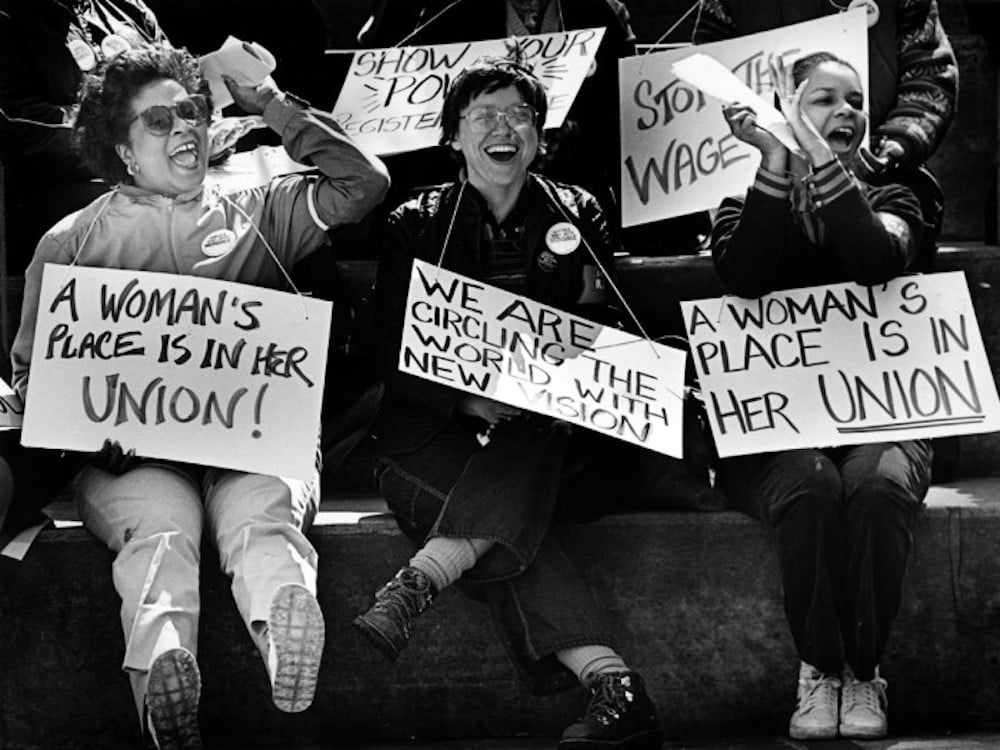
Yates的悲剧现实主义向我们展示了“感觉良好(feel-good)”的赋权故事背后所隐藏的谎言:真正的解放,无法通过个人在有缺陷的系统内做出的“选择”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需要的是对这个“笼子”本身的深刻质疑和解构。
女性主义的真正任务,不是学会在这个系统中做得更好,而是要有勇气重新想象系统本身。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