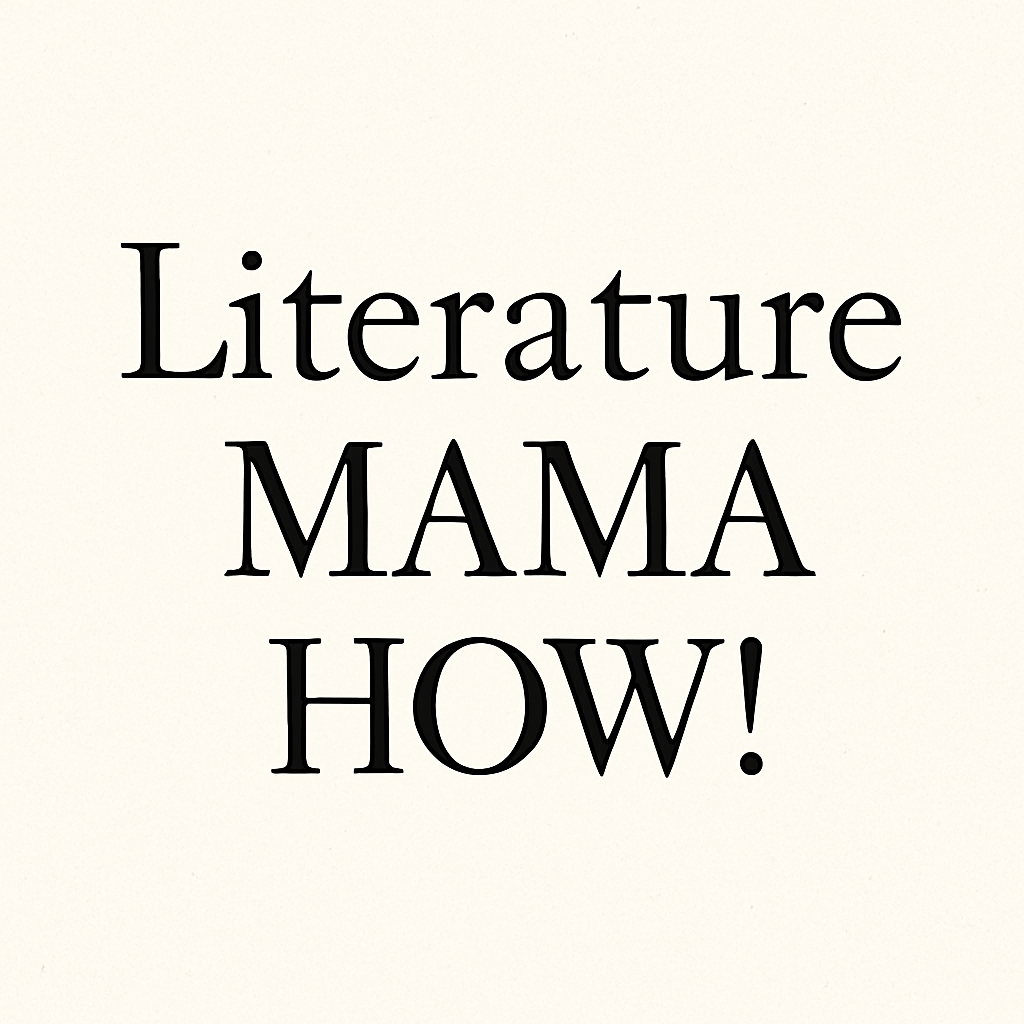重量與觀測:電影《情感的價值》漫談
家屋的重量
德閔:
也許是身陷碩論太久,電影才播映沒幾分鐘,在畫外音娓娓陳述著有關「家屋」種種的同時,我便不自覺地聯想起了巴舍拉的《空間詩學》。
不過我想,早於立論之前寫下這封信,畢竟是出於某種對話的可能性,而非一味地追求對文本的特定詮釋;更何況,面對這樣一部對我來說意義非凡的電影,我根本無意使用理論去框架它。雖然,我也必須承認,倘若將貫串著整部電影的重要隱喻——「家屋」——懸置、避而不談,那麼關於那個於我而言的意義,究竟非凡於何處?我其實說不上來。
我非常喜歡電影中的後設視角,雖然後設之於當代,並非什麼稀有物種(甚至已成濫俗),但那個敘事者的位置,那種沉穩、內斂,彷彿看淡了世間一切的敘事聲腔,卻罕見地以一種「非人」的姿態展開:六年級時,諾拉被要求寫一篇作文,把自己想像成無生命的物。她立刻意識到,她會把自己比喻成她們的房子⋯⋯
如此微妙的切換,將人置換成物/居所,從而以物/居所的視角思考,由此開展而出的某種詩意,我想,也許才是使我瞬即聯想至巴舍拉的真正原因吧(什麼碩論,去死吧)。
於家屋底下,母親逝世、父親回歸,並將一本他即將開啟的劇本,帶至了女兒諾拉的面前。在這之中,存在於角色、演員、導演乃至觀眾身份之間的多重指涉不言而喻。
我想,使我深受吸引的,並非那些機關如何被「設置」,而是機關的「位置」何以如此幽微卻精準?時而讓渡於劇情,時而又沒過情節本身;前進復後退,遊走於鋼索之上,只要不慎踏錯步伐,便立刻陷於墜落的風險。
至於意義,我想你不用猜便知,無非總是那個從外界看來,最最俗氣的親情。
從某個程度上來說,電影其實沒有呈現超出於可預想範圍之外的親情詮釋:絕情的父、無話可說的女兒,與夾在中間,看似處處維護著父親,卻只是不敢憤怒的妹妹⋯⋯然真正引發我思考的,反倒是奶奶的角色。她的自殺,向上牽引出一段不忍卒睹的國族傷痛,向下則隱隱指涉著此種傷痛的遺緒——父親與女兒的雙雙憂鬱——那樣的傷痛如同遺傳性疾病,若置之不理,便會一代接續一代,不停地擴散。從家屋到國族,最後反噬回來:父親酗酒爛醉導致宿疾發作,進了醫院;姊妹倆在病房門外聽見甦醒的父親一如既往的風流調情,不禁笑了出來,好似回到六年級的諾拉自己,在作文中,她未曾將父母的不睦描述為「爭吵」,而是代之以父母製造的「聲響」。
畫外音說道:比起「聲響」,更令家屋感到害怕的,其實是「安靜無聲」。隨著父親的離開,家屋顯得輕盈了許多,往日父母製造的「聲響」亦驟然遠去。然而家屋其實很懷念那些由他(父親)所製造出的聲音⋯⋯
出院以後,父親親自拆除了家屋內部的老舊裝潢,換上風格更為現代的佈置與陳設;作為某種告別,即使他一直很想對女兒訴說的種種關懷與愧疚並沒有真的說開,卻在他遞予女兒的劇本之中,於母親(諾拉奶奶)的角色身上,透過混雜難辨的記憶,將一切重建。
在看到劇本裡的那段臺詞:「我又獨自一人留於家屋,躺在床上哭泣。我知道所有人都會躺在床上哭,但⋯⋯曾有人說,禱告並非真的在與上帝對話,而是承認自己的絕望,置自身於死地,因為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事⋯⋯」之後,諾拉似乎明白了什麼,並出演了父親的電影。
直至電影終於順利開拍時,鏡頭拉遠,我們才赫然發現,拍攝的地點已非原定的家屋,而是改由棚內搭建而成。我想那似乎指涉著某種對於理想居所的投射,好似其實父女的和解終究只存於幻想之中,然而由鏡頭呈現出的眼神投遞,卻又是那樣的真情流露、層次分明。我不確定導演如此安排,是否有意回扣後設敘事,藉以揭穿真實背後的虛構性質?又或者僅作為一種開放式的結尾,把空間留予觀眾,讓存於故事外邊的我們,也得以一同構築自身對於家屋的想像?
不知道。我想答案正如同片名《情感的價值》一般,我們既無法確切衡量,便也更加難以釐清。
德閔,你知道嗎,寫下此封信件的同時,我竟驀然憶起了C師曾告訴過我的話:「親人終究是冤家。」其中價值無論多或少,一旦衡量起來,無非就是一種困陷。若欲與之保持距離,真正要做的,並非離開本身,而是想像。就像諾拉依憑想像,將自身比擬為家屋,即使面臨父親的離去,讓家屋瞬時輕盈了起來,但她終究仍時刻思念著那些負重時的激烈聲響,那些踩踏與爭執,穿過房間、越過樓梯;在家屋的庇蔭底下,沒有什麼是能夠永久分離的。
柏勳
2026.01.09

距離的觀測
柏勳:
這一部幾乎可預測劇情的電影,卻給了我難以預料的觸動。我相信你也是。
老實說,當家屋的構築歷史、畫外音絲毫不帶感情地陳述著一家人的故事,在電影的一開始便被如此冷靜地呈現予觀眾,在黑暗裡,我幾乎就想逃了。因為那口吻,是在我停滯已久且難以重拾的創作中,每每涉及家屋,便尋常選擇的敘事距離,而我總自我說服,我站的位置即是我的發聲策略,彷彿唯有如此,我才能書寫我那難以言明的情感,欲抵達的路徑之遙。
「我們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們之內。我們詩意地建構家屋,家屋也靈性地建構我們。」已是幾年前讀的巴舍拉。而在《情感的價值》裡,在童年時期便將自己比喻成房子的姐姐諾拉,無法阻止由父母製造的各種聲響,直到父親出走,追求電影事業的遠大理想,才擁有些許平靜;成年之後重返舊址,欲著手處理惱人的祖厝,一面得時時和父親拉鋸,一面得及時接住具情感價值的易碎品。有聲的聲響,無聲的聲響,實際的聲響與想像的聲響,不只是在諾拉的心裡,這些聲響也在我心裡共鳴與迴盪。
也因此這是一部既簡單又艱難的電影,因它展示了情感的普世價值裡最最深奧的現象之一。家庭的私密性,具吸引力的神秘感,為尋求出路的窺淫,再加上尋常出現的換幕剪接⋯⋯幕每暗一次,聲音又再起,我只不斷在熟悉的情緒裡低迴,沮喪地換氣。
其實何止是人物/居所之間的巧妙切換、傷痛與憂鬱的代際承繼,讓我看得最入迷的,還有各個角色如何在對方的劇本裡,演出或不演出各自的角色。家庭角色、性別角色、社會角色、電影的分工角色,意即——電影導演父親理想中的戲劇演員女兒,能否用藝術家的方式了解他所揀擇的拍攝;而戲劇演員女兒理想中的電影導演父親,能否以稱職的為人父者不在她的成長中缺席,給予她所需要的愛與陪伴。
姐姐諾拉拒絕出演父親古斯塔夫的電影,甚至連看都不看為她量身打造的劇本。為了能繼續拍攝,導演古斯塔夫說服自己,另一位美國女演員瑞秋能行。因此我們看到了這一幕:在一次排演中,瑞秋的髮型、模樣甚至口音,在不知不覺間,竟有了諾拉的輪廓,和一點勉強的神態。古斯塔夫因見著對方為迎合自身的理想,而露出一副又驚又恍的表情。我想他其實早在那一刻,心裡就已全部瞭然,他的拍攝不能再沿襲舊有的手法和思考,他必須有所改變。
「難道只有我覺得不對勁嗎?」這一位難以飾演的角色,終究被瑞秋誠實地推辭。
成年後選擇成為歷史學家的妹妹艾格妮絲,在童年時曾照著父親的意願,出演父親電影的重要角色。許多年後,面臨父親的要求——要她年幼的兒子也出演新片時,她想起過往的經驗,遵照著復返的情感,幾乎是說出了我最真實的想法,彷彿代我拒絕了突然的親密,以及往後必然的失落。
整部電影最讓我在意的便是這個了。面臨三位女性的拒絕,古斯塔夫的選擇是什麼?沒想到劇情卻在這裡加速,極為輕盈地,以老男人的風流向年輕的護士調笑,就這麼切換到下一幕。而我有些無奈地接受了,因為那正是我父親曾做過的事。
因此這也是一部需要不斷磨合、尋找妥協的劇中劇,就像你所說的,是角色、演員、導演乃至觀眾身份之間的多重指涉。我們的投射路徑,即是電影裡的電影中,演員與導演在作品之外,互相理解、遷就、讓步與協調後的拍攝法。《情感的價值》所使用的後設手法並不在炫技,也非刻意的另闢蹊徑,而是將電影裡的角色和電影外的我們成功地合而為一,一同去經歷虛構的劇本,也一同獲得真實的感情。
電影的最後一幕,是古斯塔夫的電影終於拍成。那雖然是同樣的動線,不切換的一鏡到底,卻已不是原定的手持鏡頭,也不是關起門來留予我們想像的一記聲響。鏡頭切換,是原本不在劇本裡的一幕,我們看見了諾拉自己的詮釋;鏡頭拉遠,發現那也已非原有的家屋,而是另外搭建起的、還保有一些舊理想的新攝影棚;鏡頭再拉至棚外,已超越了戲劇舞台和電影鏡頭之間的差異,是父女彼此打破「框架」的對望,卻也同時完整了《情感的價值》的電影框架。
柏勳,直到看見這樣的對視,我才真正軟弱下來,不再豎起抵禦的刺。並且我知道了,電影一開始便使我的焦灼如此躍動的原因:不論在電影之外的真實生活,在同樣的家屋的考驗之下,我能不能夠處理我心靈的難題,去拆解抑或重建?可能、我可能,還仍保有一顆溫熱的心,期待去拉扯出一次平穩安和的眼波的距離,將我纏繞的所思所想與複雜的情感,但其實簡單的夙願,成功投遞出框架之外,而不再只是絕望地向神傾訴。儘管那距離無法確切衡量,難以釐清。而我相信你也是。
德閔
2026.01.13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