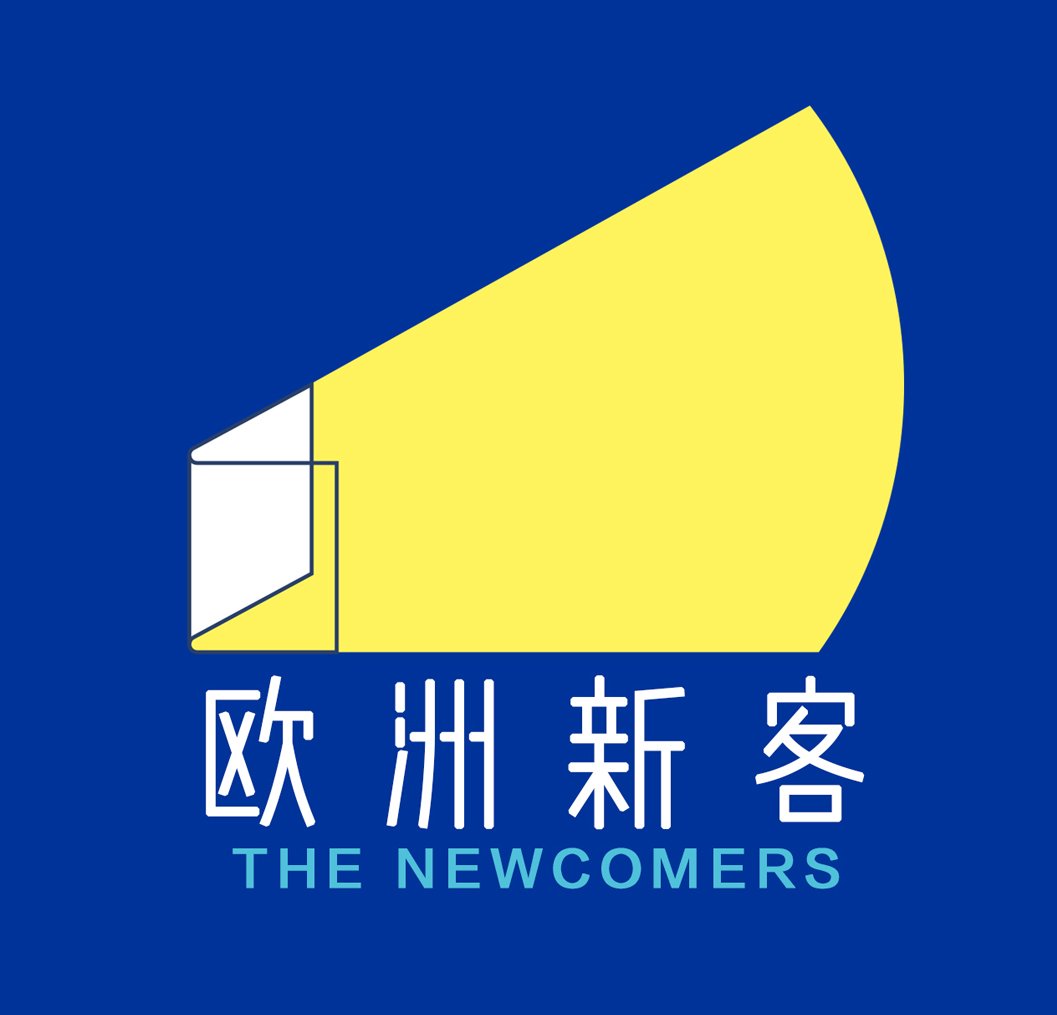我在西班牙打黑工
初来乍到
2024 年 2 月底的马德里还很冷,我在一个海外华人常用的手机 app 上滑动着招工信息。餐馆、美甲店、物流公司——几乎都标着"需自备居留签证"。我拿的是语言学校的学生签证,不允许工作,只能考虑给中国人打黑工。
西班牙是中国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打黑工的人自然也多。在搜索到的马德里招工信息中,大部分都是餐馆、美甲店和物流公司文员,我避开那些标明"需自备居留签证"的工作,询问了几家招半天工或者周末工的餐馆和超市,得到的回复寥寥。
但后来我才知道,"自备居留签证"的意思是只要有居留就行,包括不允许工作的居留类型。毕竟对于老板来说,招黑工不需要办理社保、不需要遵循法定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显然是更划算的。几乎所有规模不大的中国人公司里都有黑工。
"旅游纪念品店招半天工,时间灵活。"这是唯一回复我的招聘信息。
我忐忑不安地去店里面试。下午五点我推开店门,里面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整理货架。告诉她我的来意后,她告诉我自己是负责上午的半天工。“我叫 Elena。老板不在,我先跟你说说要干什么吧。”
这就是我的"面试"——Elena 花了十分钟大致讲了一下店里最常售卖的东西的价格,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开始了这份工作。
与其说这是一家旅游纪念品店,卖纪念品的杂货店可能更恰当。它的位置在一条繁华主路旁的斜街上,光是这条小斜街就有三家这样的商店,老板分别是中国人、墨西哥人和摩洛哥人。
那天我在店里待了将近一小时后,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才悠悠然牵着一只巨大的狗走了进来。
"你就是新来的?"她是 Ines,招工时联系我的老板之一,另一个老板则是她的母亲——这些是在她来之前 Elena 告诉我的。Ines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总是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情,“Elena 都给你讲过要做什么了吧,刚好她要下班了,你就接着干吧。”
Elena 收拾东西时压低声音对我说:"和老板娘相处可能比较累。"
"为什么?"
她欲言又止地笑了笑:"之后你就知道了。"
店里几乎没有标价,因为大部分东西的价格都是不固定的——如果客人说英语或者背名牌包,价格就会更高。
Ines 指着一个货架:"记住这些价格,二十分钟后我考你。"
见到 Ines 的母亲 Maria 时,我正手足无措地站在货架前努力记价格。她端着一碗饭从我背后走过来,"好好记哦!"她的上海口音很重,"要是说错了价格,看我不打死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打死你"这句话。后来我发现,这是这对母女的口头禅。要是我哪件事没做利索,她们就会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怎么回事打死你哦,你是不是想被打死,我看你真是该打死。
工作第一天的内容,除了记价格,还有陪 Maria 遛狗。她们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德牧,每天都带来店里,有时会需要帮忙带去遛,所以跟狗搞好关系也算我的工作之一。不得不说,这是这份工作里我唯一喜欢的部分。
我的上海老板
和 Maria 一起遛狗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体验。
几乎每路过一个咖啡店她就进去熟练地要一杯咖啡几片火腿和芝士,我跟着她白吃白喝了一条街。一边吃她还一边对我说,我在这条街混了十几年啦,你跟我出来都不用花钱的,这时旁边一个服务员过来插话问我是不是她女儿,Maria 立刻抢答是,我尴尬地笑笑,服务员也笑着说了句,撒谎。
接着她又扭头用中文跟我说,你看这些服务员都是拉美人,我跟你讲,这种都是爱打坏心思的穷鬼,没一个好东西!但我的人他们不敢动,我说去你妈的,我们中国女孩不找老外!
我拖着大狗局促地跟在她身后,几乎每家店都有人探出头喊 Hola Maria。盘下这家纪念品商店之前,母女俩在附近的另一条斜街开了六年小卖部。Maria 在西班牙待了二十多年了,和大部分这一代华人移民一样,最开始也是黑在这边给中国人打工,拿到合法身份后慢慢攒钱,把家人也带出来一起开店。
Ines 则是十年前来的,虽然刚来时上了一段时间语言学校,但因为除了在店里时几乎不和当地人相处,她现在的西班牙语也只是基础的日常交流水平。
有天 Maria 跟我聊起这条街上的其他店主:"你看那家墨西哥人开的店,还有那家摩洛哥人的,生意都没我们好。"
"为什么?"
"我跟周围这些服务员早就混熟了,他们都喜欢我又怕我。你知道为什么吗?"Maria 得意地笑,"我就总是笑嘻嘻的,不像那些青田人,整天垮着脸也不跟人打招呼。反正老外也听不懂,你只要脸上笑嘻嘻的,骂他傻逼他都开心。"
在马德里,绝大部分小卖部都是中国人开的,更准确地说是青田人,这个浙江丽水的小县城贡献了西班牙一半以上的中国移民。说起青田人时,Maria 的语气总是带着不屑的。我也逐渐发现,西班牙华人商贩里存在某种微妙的地域鄙视链:数量最多的浙江人瞧不起福建人,福建人和浙江人都不愿意跟上海人来往,而上海人——似乎瞧不起所有人。
"你知道我们上海人和他们不一样,"Ines 有次这样跟我说,"我妈在这条街混了十几年,人缘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跟人相处。"
这或许也是所有海外移民的生活里都会存在的现象——从青田人到上海人,从打工者到老板,从一代移民到二代移民——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种族歧视,大部分人都试图在小小的华人圈子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建立自己的优越感。
“融入”仿佛是不存在的选项,母女俩的社交圈都只有华人,而我“交老外朋友”这件事在 Ines 看来甚至令人困惑。
她觉得跟老外是完全没话聊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平时看的剧和综艺也不一样,怎么聊啊”。我说,就聊聊一些电影啊书啊,社会文化啥的。她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就你这西语水平还能聊社会文化?说完她好像又反应过来,哦你还会说英语。
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每周休息一天——这种叫"半天工"。"全天工"则是十小时起步,同样只在周中有一天休息。对于黑工来说,双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全天工"的工资也不太可能达到两千欧的平均工资水平。我每周的工作时间比法定八小时工作制少四小时,工资是七百欧,比马德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却低四百多欧。
但事实上,这个工资在黑工里已经不算低了。母女俩开店以来一直用黑工,她们都觉得老外很懒,还可能会偷东西。
Elena 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十一点到下午五点,她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始在母女俩这儿工作,互相已经算是比较熟悉。我们几乎没有交集,仅仅换班碰上时偶尔有交流,Ines 倒是常常在闲聊中和我说起她的事情。
她之前在西班牙读本科,毕业后回国上了几年班后觉得"国内工资低还特别卷,实在受不了",又找中介买了一份工作合同来办工签回到西班牙,等待工作居留的办理的几个月里就找了个黑工。
第一天 Elena 对我说的那句"和老板娘相处可能比较累",后来我才知道是特指 Maria。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跟 Maria 怎么相处,她就回国度假了,前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 Ines 两个人待在店里。我的课是在上午,中午一点半下课后回家吃个饭就要赶去上班,晚上回到家已经将近十二点,总是累得倒头就睡。想到找工不容易,又有点舍不得放弃,毕竟比起餐馆、美甲店之类,这里的工作虽然时间长,但内容的确相对轻松很多。
店里卖得最多的纪念品是冰箱贴,客人选完冰箱贴之后要去仓库换新的出来,也就是说需要记住满满两面墙冰箱贴在仓库里对应的位置和不同的价格。这是一开始的主要工作内容。遇到一口气拿十几个的客人,我就免不了开始手忙脚乱,也发生过几次把三欧的冰箱贴记错成两欧的事情,Ines 常常嘲讽我,“幸好我妈不在,不然你就要被骂死了!”
不过 Ines 也并不是就完全不骂人。有天我在仓库找货时慢了点,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慢啊!"
那种语气——似乎没有什么过分的话语,但令人清楚地感到被责备、被嫌弃——瞬间唤醒了我童年被母亲责骂的记忆。
"你急什么呀。"我脱口而出。
Ines 愣了一下,随即没再说话。
从那以后,Ines 再没有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过话。后来 Elena 告诉我,Ines 跟她讲起我时说,这个女孩竟然刚来就会顶嘴。
两个世界的生活
打工的几个月里,我过着完全割裂的生活。
上午在语言学校,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讨论气候变化、移民政策、性别平等。教室里充满了那种典型的欧洲左翼氛围——大家为土著居民的权利忧心,为碳排放的增长焦虑。
下午五点,我来到距离学校仅仅两站地铁的纪念品店,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宇宙。
"你看这些老外,"Ines 指着刚走出门的几个游客,"问了半天价格什么都不买,穷鬼!"
"老外都是傻逼,"Maria 从后面补充道,"又懒又没脑子。"
我站在中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在 Maria 走了后,店里安静了许多,而 Ines 总的来说还是不算难相处,只是她总喜欢拉着人聊天,而我又实在不擅长和不熟悉的人交流,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讲我在听。
Ines 的主业其实是占星师,她对一切东西方玄学都充满了热情且深信不疑,连外卖吃什么都要抽塔罗牌决定。因此,她讲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各种玄学以及身边各种人的八卦——讲八卦讲到最后也会绕回玄学。
"你这辈子怎么样都是已经定好的,"她一边给客人结账一边对我说,"比如你去看那些私立学校的小孩,他们的耳朵都长得特别好。"
"耳朵?"类似突然开始的话题都会让我懵一下。
"面相啊,耳朵代表财运。公立学校的小孩就不一样了。"
Ines 有个同样搞玄学的北京朋友,经常来店里"讨论案例"——我的星盘也被她拿去当案例分析过。这位朋友四十出头,讲话时带着许多北京女孩特有的那种不屑,她通过投资移民来到西班牙,刚买了房正在搞装修。
两人的对话同样大部分时候都是 Ines 在说,聊起玄学相关时,她的语气总是十分不容置疑。
有趣的是,她们讨论玄学时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两性关系。在 Ines 看来,两性关系的核心在于"对方能不能给你提供资源"——也可以说,这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核心。
她认为我现在"虽然也交老外朋友",但都只局限于平时聊天,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这时我插话,他们能陪我练口语,她说这不算)。但如果我换一个更吉利的电话号码,就能遇到老外给我资源和人脉上的帮助。
"太世俗的人不适合搞玄学,"Ines 经常把这种话挂在嘴边,"我们这种能搞玄学的人都得带点精神上的追求。"至于精神上的追求是怎么来的,据她说也是"命里带的"。
没什么客人的时候,Ines 通常都在看剧或刷小红书,也时不时兴奋地把手机递给我分享她看到的视频。"你看这些留子吐槽老外的视频,太搞笑了!真的,不出国都不知道老外都这么离谱,我现在都觉得确实是出国了才会更爱国。"
我第一次在现实中听见有人讲这样的话。虽然母女俩都常把“老外都是傻逼”挂在嘴边,但 Ines 也会骂中国人,中国人素质低、不懂教育、对狗狗不友好,不过这些也不影响她抵制辱华品牌,劝国内的朋友不要轻易出国。
“国内的人是不是都觉得国外赚钱很容易啊?”她放下手机对我说,“我好多朋友都以为来欧洲跟捡钱一样,其实完全不是啊,国外工作也很辛苦,也不是真的都下班早假期多。”
"但至少人家遵守劳动法吧。"类似的话听多了,我就忍不住反驳两句,
"仓库区那些文职都一样从早上八九点干到晚上七八点啊。"
"仓库区几乎全是中国人的物流公司。”我本还想说,在中国人的公司这不奇怪,但还是把后半句咽回去了。
"老外也一样啊!你看那些店的服务员都是连轴转,而且他们干满八小时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她坚持道。
我突然意识到,她对国内的服务业现状可能没什么概念,但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压榨员工的技巧。比如会把店里刚过期的食物"送"给我们,营造小恩小惠的“中国式人情”;比如我每次在厕所待五分钟以上就会开始催——不过后来我发现 Maria 催得更厉害。
即便如此,Ines 也已经计划要在马德里买第二套房子,给未来小孩取的名字也是西班牙语名。当时她有一个同岁的男友,也是上海人,偶尔会在她有事出门时来帮忙看店。到了五月份我准备离职时,两人刚好也分手了。
分手是她计划之中的事。Ines 似乎有很强的恨嫁倾向,又觉得当时的男友不算很好的结婚对象,因此早在分手前几个月,她就开始使用一个实名制交友 app —— 当然,里面全是中国人,她只考虑在西班牙的中国人。
"其实现在我也很看重门当户对这件事,你经历多了就会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她讲话有时让我觉得有点爹里爹气。"我现在找人结婚,那一定不能找给别人打工的,你至少得有自己的店。就算是打工,那也必须是写字楼里的高级工,不然我干嘛要找一个每个月只能挣两千多欧的人?"——马德里的平均月薪也不过两千多欧,这已经是整个西班牙平均收入最高的地区。
类似的对话经常让我感慨,是她太符合上海人刻板印象了,还是上海人真的都这样?另一天,她突然特别惊讶地对我说,Elena 居然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你能想象吗?97 年哎!居然还存在接生婆这种东西!"
她惊讶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尴尬,只能应付地答道,可能小地方是这样的。Ines 表示还是很难想象。过了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道:"可能因为我出生在上海,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吗,"她继续扭过头对我说,"之前一个算命先生跟我讲说,你出生在上海就已经赢了一半人。我一开始完全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在别人讲之前我都没思考过自己的出身,刚听这老先生讲的时候还觉得什么意思啊,后来仔细一想确实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这种时候我除了哈哈哈呵呵呵就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与这对母女相处对我来说确实是种很奇妙的体验——我在小镇长大,来到大城市读社科专业、在豆瓣和读书会上认识朋友,完全没有和这样的典型的中国小市民长期相处过。
同温层的泡泡太过舒适,以至于有时会让人忘记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我不能说她们是坏人,但她们生活在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里——一个有着复杂地域认同、等级观念、生存智慧却也充满偏见的世界。
风暴前的宁静与爆发
四月初,Maria 带着一大堆中国零食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从她回来前三天,Ines 就开始摆出如临大敌的阵势拉着我把所有货架都擦洗整理一遍并清空冰箱里残留的所有食物。“要是我妈回来了你还这样不利索是会被骂死的!”这样的警告声还在我耳边回响,不过出乎意料,因为自己出去玩了一趟忘记了店里很多东西的价格,Maria 头两天不仅没有骂人,还显得格外和蔼可亲。
但好景不长,我又开始被她肌肉记忆般的“老外都是傻逼穷鬼”立体声环绕——Ines 趁着母亲回来开始频繁外出见朋友,我和 Maria 单独相处的时间便多了很多。
头两天的喜庆劲儿过了之后,Maria 立即展现出比 Ines 更夸张的急躁脾气。除了动不动"打死你",还总是用近乎尖叫的方式讲话。这种情况经常被客人撞见,有些人会迷惑地问我她怎么了,我也只能尴尬地笑笑。有意思的是,我那次"顶嘴"之后,Ines 再没有像那样跟我讲过话,而在 Maria 面前"顶嘴",只会让她提高尖叫的音量。
第四天,一个意大利游客试图跟 Maria 争辩冰淇淋的价格。
"太贵了!"那个男人用英语抗议。这是事实,店里的饮料零食都比住宅区的小卖部贵一倍。
Maria 勃然大怒,开始用她那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西班牙语尖叫:"他,脑子,不好!该打!该打!"
她从来不用介词和冠词,讲话就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往外蹦字。配上丰富的肢体动作,让其他同行的游客都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女孩甚至举起手机开始拍 TikTok。
"穷鬼买不起还问什么问,傻逼!"等客人走后,Maria 狠狠骂道。
我想这或许也可以解释 Maria 的好人缘。如果一个这样脾气的老太太不是我的老板,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她有趣甚至可爱吗?我不敢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可能我只是难以想象自己不以员工的身份和这母女俩相处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街区,不仅是服务员们,连警察和地铁站工作人员都和 Maria 相熟,她自己也很引以为傲,经常给我讲她当年开小卖部时的故事——至于其中有没有夸大的成分,我当然不敢肯定。
"那会儿我时不时就跟小流氓打架,眉毛都打破啦,鼻子也流血。“她讲起这些时带着自豪的笑容,“警察都拿我没办法,都跟我说 Maria por favor(求求了),你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多大了又怎么样,我才不怕这些小流氓!"
和母亲一样,Ines 在当地华人圈子里人缘也很好,加上她还做海外物流,跟很多留学生都关系不错。那段时间母女俩多了个新访客,是个和我的母亲年纪差不多大的中年女人,但保养得很好,显然家境优渥,来的时候往往也会带着自己十六岁的女儿。她们和 Ines 是在遛狗时认识的——小女孩来逗 Ines 的狗,两个大人就顺势聊了起来。
Ines 听说对方是来买房的,立刻就来了兴趣,她自认为对马德里的房产情况很有研究,便热心地招呼对方来店里玩。
这对母女都是英国国籍。中年女人的现任丈夫是英籍香港人,全家因为工作来西班牙,现在在一个旅游业为主的小岛开餐馆。她的女儿是标准的海外华裔形象,短发、均匀的小麦肤色、穿宽大的卫衣搭配短裙,看上去和母亲也关系很好。女人最初去英国是因为前夫,一个她在国内认识的英国老头——吊诡的是,她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都不太好,丈夫却几乎不会讲中文。这些事是 Ines 跟我讲的:"你不是也想结婚来拿身份吗,可以问她帮你介绍人认识认识。"
Ines 身边似乎有很多"嫁老外"的朋友,并且在她的讲述里,这些朋友都"嫁得很好"。
有次一个台湾女孩来店里找她,对方走之后 Ines 跟我感叹她找了个好老公,比她大十几岁对她特别好,没让她上过一天班,"这么顾家的西班牙男人真的很少见"。这时 Maria 在旁边说:"这个女的台独哎!以后少跟她来往!"
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Maria 和 Ines 一样喜欢刷短视频,只不过从小红书换成了抖音。有段时间她经常看一些关于大 S 和汪小菲的婚姻故事解析,博主是一个听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姐,总是从大 S 的种种新闻的细节推断她现在的生活如何不如意,分析汪小菲是如何被大 S 坑害了。
Ines 常看的一个博主和她妈的喜好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姐,教大家怎么利用精神分析来拿捏男人,其中里面穿插一些神棍词汇,比如潜意识、防御机制、力比多。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女权概念,比如一个男的对你怎样其实就是在物化你,在打压你的主体性。站在她急于找到结婚对象的角度,似乎算是有点实用。
Ines 对两性八卦的热衷,时常让我产生被顺直霸凌的感觉——她甚至会因为"不想让儿子当太监"而不给狗狗绝育,还觉得女的一般都养公狗而男的一般都养母狗。有次聊起移民,她说西班牙女人特别怕东欧女人。
“怕是什么意思?”这个论断听得我云里雾里。
"现在这边的东欧移民很多,尤其是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东欧女人又好看又勤快,只要有心就没有撬不掉的男人,她们一来,西班牙女人都如临大敌。这还是西班牙人跟我讲的!"
我听得有点不适,"这么讲的话,越战期间美国女人也对东南亚女人如临大敌。"
我不确定 Ines 有没有理解我的逻辑,她只是又补了一句,但东欧女人确实长得好看。
不过生活在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她也对性少数司空见惯,还会去市政府官方的骄傲游行"看热闹"(Ines 不知道 517 和骄傲月,她管游行的日子叫"同性恋节")。她对 gay 印象特别好,觉得比起直男,gay 都又温柔又有钱又会打扮又高素质。我突然好奇,“那你能分辨出女同吗?”
“女的扮演男的那种很明显,女的扮演女的就不一定能看出来。”她的回答并不意外,但我还是忍不住解释道,现实的女同不一定都分得这么明确。
"但这边大部分都是这种的。"她的语气变得有点不高兴。一般来说我提出不同意见时,她都会变成这种语气。我猜她说的"这边"指的是在西班牙的中国人。
店里也卖彩虹旗和彩虹伞,Ines 说这些都是同性恋买的(我想告诉她这里不会有多少人买彩虹旗的,现在大家都挂多元性别旗,但想到还要解释多元性别这个概念我就放弃了)。她说"同性恋"这个词的口气总让我很不舒服,就像她和Maria都管非裔叫老黑,管原住民血统比较明显的拉丁裔叫黑皮——因为她觉得这些人跟老黑那种黑不一样,老黑都黑得发亮,他们是"看起来洗不干净那种黑",管日本人叫小日本(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但当她们说"老外",那通常都是指白人。
然而在这个街区,他们相熟的服务员几乎都是"黑皮"。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的服务业从业者也以移民为主。一个在附近餐馆工作的委内瑞拉大哥经常把母女俩的店当酒馆,坐在店里喝完再回去工作,因为是熟客,他买酒比标价便宜一大半。Ines 告诉我,他三四岁就和家里人一起来了西班牙,至今没有回去过,因为一张机票钱差不多就是他的一个月工资。
"他就是个烂人,酒鬼。"Ines 的父亲跟我说,"都有两个女儿了,管都不管,就知道喝酒,你千万不要理他。"
Ines 的父亲是在 Maria 之后几年来西班牙的,现在不和母女俩一起住,而是待在女朋友的房子里。这一家人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一直没太搞明白。夫妻俩似乎早已分居多年,但一直没有离婚,老头子还会经常找母女俩要钱。自然,Ines 提到他时总是带着怨气,当面讲话也从来没有好脸色。据她说,老头子虽然是个废物但命好,来西班牙之后没打过几年工,女朋友倒是没断过,还都愿意给他花钱。现在拿着退休工资,没事赌赌马、玩玩 bingo,看上去日子过得确实比每天看店到深夜的母女俩滋润许多。
似乎大部分中国女孩,不管有什么样的性格与观念,背后都有一个不负责任甚至非常糟糕的父亲,想到这一点,我对 Ines 的情感就复杂了许多。
离别
五月的马德里阳光灿烂,而我已经因为三个月的连轴转瘦了十斤,加上需要开始准备语言考试,我决定提前离职。
直到离职前几天,我才终于和另一个打工的女孩 Elena 加了微信,此前我们的联系仅限于换班时的寒暄。有天我趁没人在问起她打算什么时候走——我知道她是要走的,因为她已经拿到了工作居留签证,可以找合法工作了。也同样是五月,Elena 开始找工作,有时会因为要去面试而请假,Ines 叫我提前上班的次数增加了许多,还经常在我面前表达对 Elena 的不满。
毫不意外,Elena 告诉我 Ines 同样会在她面前抱怨我工作不认真。加微信之后,她立刻向我大倒苦水,说这段时间Ines老是挤兑她,给她算命说她年纪不小了又没有能力,和现在的男友在一起不会有未来。我有点惊讶,虽然我跟 Ines 关系也不算太好,但不至于讲话这么难听。
"那是因为你一开始就会顶嘴呀。"Elena 说。
当我告诉 Ines 要离职时,她脸色很难看:"你们怎么都要走?Elena 也要走,那我店怎么办?"
"我需要专心准备考试。"
"你不是想拿身份吗?不工作怎么拿身份?"
"我想先把语言考好,再接着读书找合法工作。"
Ines 冷笑:"合法工作?你以为那么容易找?"
Maria 倒是出乎意料地没说什么,只是瘪了瘪嘴:"你们怎么都想读书,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最后一天来上班时,正好 Elena 也结束她的最后一天工作。我们站在店门口,看着这条我们工作了几个月的小街。
我突然理解了 Elena 第一天说的话,"和老板娘相处可能比较累"。比起工作本身,价值观的不断碰撞才是更加令人疲惫的,在我看来会造成伤害的语言暴力,在她们的世界里可能是早已习惯的日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
小狗走过来钻到我们中间,扬起毛绒绒的大脑袋。“还是有点舍不得他呀。”我捏着小狗软软的耳朵感叹到。
"也就只有小狗让人舍不得。"Elena 笑了笑,“以后我都不想再来这条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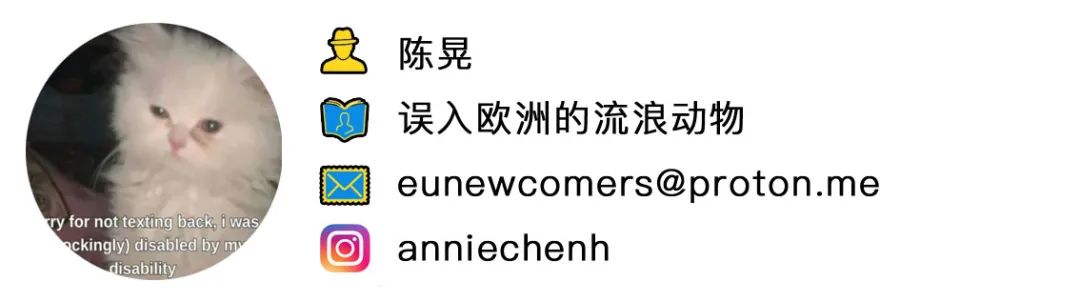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