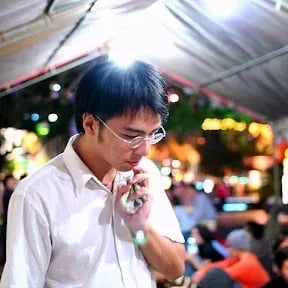失敗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信念從未彰顯
廖建華導演的新片「狂飆一夢」即將上映,本片以深入參與八零年代改革運動、目前已走入遲暮之年的曾心儀與康惟壤為主角,透過鏡頭,重探主角在年少時毫無保留地參與運動的心路歷程。只是眼前卻被社會主流價值觀認定自己是「人生的失敗者」,曾、康如何面對自己因為追求理念,而與常人不同的人生?廖建華導演有個短註,「原來社會進步了,也不保證個人的幸福」。
筆者日前也已閱讀本片的電影書「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透過兩位編著者廖建華導演與何孟樺女士,對八零年代基層組織工作者的研究與採訪,除了讓我對本片兩位主角曾心儀、康惟壤前輩的生命,能有更深入地認識之外 ,也提醒了我,認為「政治菁英」與「群眾」的關係,就是「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或可比擬為「魔笛手」與「孩童」的關係,似乎政治菁英出聲 ,群眾就會附和跟隨,這種視角大有問題。畢竟,異議不會無故突破極權政府的種種圍堵,自然地傳到社會每一個角落。
在廖建華的鏡頭前,「政治菁英」與「群眾」之間的鏈結浮現了,何孟樺的記述更呈現了鏈結的實相:一群以實踐信念作為畢生志業的組織工作者們。在諸多評論中,相較於備受大眾注目、承擔運動光環的政治菁英,通常都會認為組織工作者是「失敗者」,既沒有政治菁英在後半生享有的榮華富貴,或不這麼庸俗地來看,也沒有政治菁英得以實踐信念的聲望與地位,或許能與政治菁英相提並論的僅有疏離的親情,但就是全盤皆墨,一無所獲。
「失敗者」的論斷,是一個讓大眾能夠同情草根組織工作者人生際遇的嘗試,告訴我們草根組織工作者過往的種種抉擇,都是為了實踐信念而有意識地「犧牲」。此種「犧牲說」,比擬「唐吉訶德」般地英雄主義,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或是「愚公移山」,為了後代子孫的利益,不畏艱難持續做工。以上兩種意涵,皆將草根組織工作者的際遇浪漫化了,反而讓後人無法正視他們所真正留下的可貴遺產。
草根組織工作者們留下的可貴遺產,主要有三:其一是意志,當獨裁者用政治手段去圍堵反抗意識,且社會身份形塑的人際藩籬,共構出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組織者不時面對自己「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懼,與遭遇「人生脫離正軌」的質疑,堅定的意志支撐組織者持續地在不同社群間穿梭。第二是信心,長期遭受壓迫的人民,早已適應現狀,十分絕望,但組織者卻對人民抱持幾近信仰般的期待,以各種方式鼓舞人民,並與人民一同改變自己的處境。第三是身段,平等謙和的態度不僅得以親近群眾,更是不使自己「與眾不同」,以身作則地讓群眾能夠期許自己能如組織工作者般,懷抱著意志與信心,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本書中,廖建華摘錄了詹益樺的一段話,足以體現草根組織工作者留下的可貴遺產:
「我現拿鋤頭時,挑擔時,常思考這些問題,台灣社會上弱者在那裡,他們被變成弱者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人造成,是什麼事演變,現我不敢有什麼結論,我自訂一個方面,跌倒成為弱者的人,我站立那個地方扶啟他。」
因此,將這群草根組織工作者們視作「為了實踐信念而犧牲」的「失敗者」,我想並無法忠實地呈現他們在狂飆年代裡的容貌:相對於形容政治菁英「引領時代的風潮」,這群草根組織工作者們則是積極主動地與群眾一起「成為時代的風潮」。但我也不否定將他們視為「失敗者」,只是我想對於草根組織工作者的來說,真正的失敗並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遲暮之年時回首,卻發現後生已無與己相同的熱情,願與群眾一起成為時代的風潮。
最後仍期待友志們,進場看戲或買書閱讀,記憶這起無畏、浪漫與樸實的時代精神。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