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的冷漠:東亞宿命倫理的暴力學
暴力的文化合法化
東亞文化中最隱秘卻最廣泛的暴力機制,並非鐵與血的壓迫,而是「因果」的柔性馴化。
人們從小被教育:苦難是命、遭遇是報、悲劇是修行。這一語言結構把社會暴力轉化為「靈魂功課」,讓受害者感到羞恥,而非憤怒。所謂「前世因、今生果」,不僅是宗教信條,更是一種社會控制語言。它在潛意識層面削弱了人對不公的感知力──
因為當一切都被歸為「命運的懲罰」,暴力就不再需要加害者,
責任從加害者身上被轉移到受害者靈魂的「欠債」上。
這就是東亞的倫理魔術:讓被壓迫的人為壓迫感恩。
當女人被侮辱時,她被教導「積德」。
當窮人被壓榨時,他被教導「修福」。
這不是善,而是一種社會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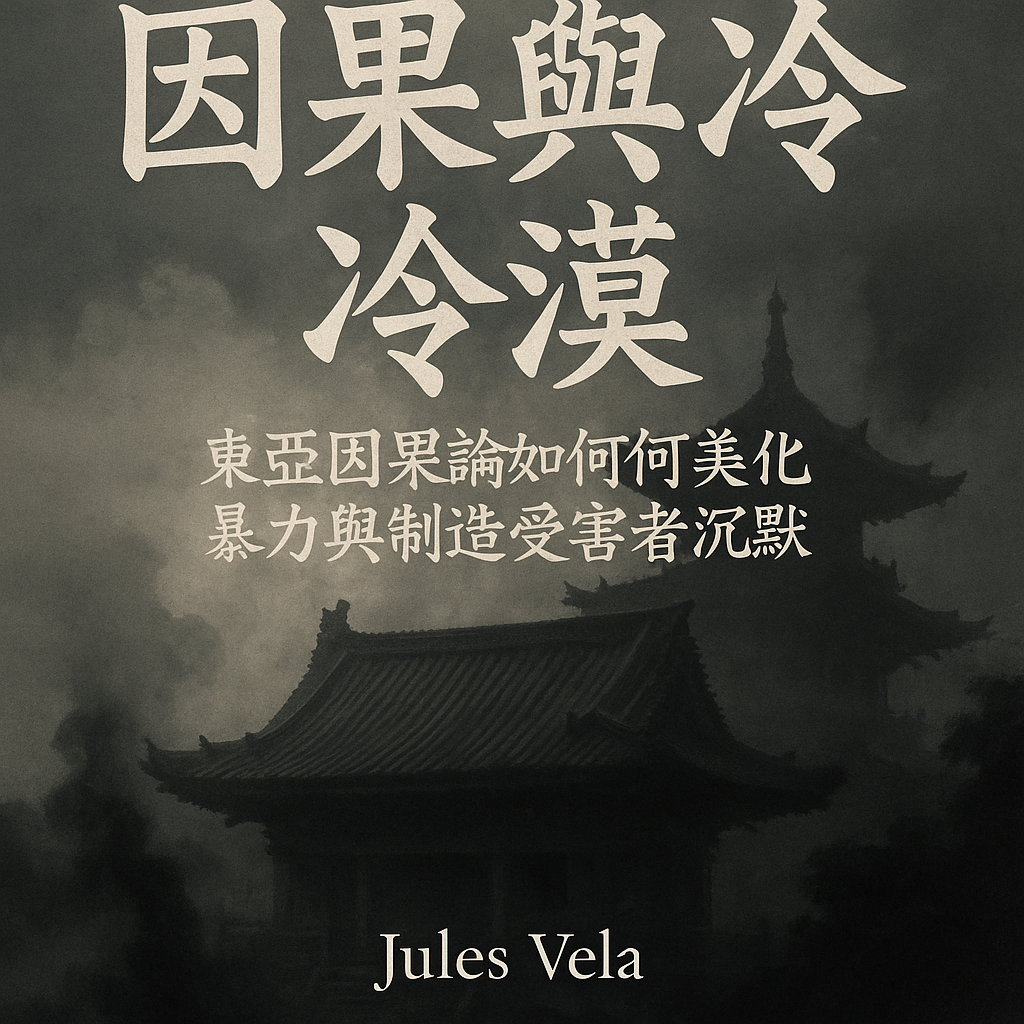
今天和幾個人討論《星際穿越》和於朦朧,有人忽然插話說:「關注這些幹什麼?關注當下、關注自己就好。」我們嘗試解釋:我們並不想成為那種抱著一顆糖粒就相信自己幸福的螞蟻。
對方卻回答:「幸福就好啦!不要想那麼多虛無縹緲的事情,不要管別人的事。專注當下,專注快樂就夠了。」這樣的對話並不罕見,尤其在當代東亞。
它代表著一種被制度馴化的情感邏輯——那種看似正能量、實則冷漠的「自我修行式逃避」。這種語言與近年簡中世界裡盛行的幾句話幾乎同構:
「放下助人情結,尊重他人命運。」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不要接收別人的負能量,會讓你倒霉、吸走你的氣運。」
在這種話語體系中,同情被視為愚蠢,關懷被當成拖累。
人們害怕別人的痛苦像病毒一樣「傳染」,
於是開始與一切受苦者保持距離。
冷漠的幸福學:當善意被視為“氣運損耗”
這種文化表面上講「自我保護」,實際上是對共情能力的系統性削弱。
「不要管別人的事」不再是一句勸慰,而是一種文化規訓:它教人對苦難失明、對他者失語。當一個社會反覆灌輸「專注當下的快樂」時,
它其實在培養一種心理上的去政治化。每個人都沉溺於個人小確幸,
卻對權力、壓迫、戰爭、甚至他人的死亡保持從容的無感。這種幸福學的本質,不是自由,而是馴化過的麻木。它讓人誤以為自己在追求快樂,其實只是在逃避責任與痛感
東亞式冷漠:從“命運”到“沙化”
在東亞社會,這種冷漠不是突變,而是歷史沉澱的結果。幾千年權力文化的後果,是情感的沙化。沙化的社會,看似有集體主義的外殼,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成為一粒孤立的沙子:
彼此之間沒有握持,只剩摩擦。越是講「專注當下」,越代表這片土地對「共同命運」的放棄。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無力感裡打轉,以「不關心」保護自己不再受傷,以「放下」遮蔽那份早已枯竭的憤怒與悲憫。這並不是覺醒,而是一種被文化馴化的昏睡。
沙化得越徹底,統治就越穩固。因為沒有人再願意質問體制,只剩下溫順的順從者——
他們稱這叫「活在當下」。
冷漠的社會工程:羞恥與報應的雙重束縛
「不要抱怨、不要怨天尤人」這類話術,是東亞冷漠的倫理模板。
表面上看似教人修身,其實是在訓練人內化結構性暴力──
不去質問誰造成了痛苦,而是反省自己為何「不夠善、不夠忍」。這樣的邏輯最終塑造出一種「被動倫理人格」:一切社會不公都被合理化為「報應」,
一切掙扎都被美化為「修行」。
加害者因此獲得免罪;旁觀者獲得冷漠的藉口;
受害者則學會沉默與自責。在這種文化體系下,同情心被羞辱成軟弱,
正義被重構為傲慢。這就是東亞式的「道德性冷漠」:
不是沒有感情,而是情感被道德壓制到只剩自我譴責。
宿命的幻術:當無力被誤認為智慧
「尊重他人命運」聽起來像是一種寬容,但在實際文化語境中,它往往意味著拒絕干預不公。在這種語言裡,「命運」被神聖化為天意,「苦難」被包裝成修行,「沉默」被誤認為高貴。這正是東亞宿命論的幻術:它讓人誤以為不作聲是成熟,讓冷漠變成一種靈性的姿態。而真正的暴力,往往就在這種「不干預」的體面裡延續。
因果的幻術:控制的語言結構
「因果」不是單純的信仰,而是一套話語工程。
它讓社會秩序得以維持,因為它在心理上重建了「罪」的敘事邏輯。
當女性被性暴力傷害時,她被問:「是不是前世欠他的?」
當貧者被壓榨時,他被告誡:「修來世吧,今生不該怨。」
這樣的語言不是信仰──它是文化的安樂死機制。真正的暴力不在刀口,而在語言。
東亞的「因果話語」不僅削弱了憤怒的正當性,
更摧毀了對「結構」的思考能力。
人被迫相信命運,而非制度;相信德行,而非權力。
結果是,整個社會失去了革命的條件。
漠的形而上學:共業與逃避
當代社會中,「共業」成為新的麻醉劑。
它表面上主張「眾生平等共受果報」,
實際上抹平了權力與階級的差異。
當弱者要求正義時,強者可以回答:「這是大家的共業。」
這種說法的政治功能,是把結構性暴力重新包裝成「宇宙的平衡」。
這就是東亞冷漠的哲學根:
一切暴力都能被形而上學化,一切憤怒都能被宗教化。
當報應成為秩序的護牆,
連痛苦也變得「合理」──
因為你不配反抗,只配修行。
報應取代正義,沉默成為信仰
所謂「因果」,在東亞語境中早已失去了靈性的純度,
它成為一種維護秩序的修辭武器。
它讓人對暴力保持禮貌,對不公保持忍耐,
讓女性以為被壓迫是情債,讓貧者相信受苦是命數。
因此,我們必須拆解這套語言的道德陷阱。
真正的覺醒,不是拒絕信仰,而是奪回「詮釋苦難的權力」。
命運不是天意,而是權力分配的結果;
報應不是真理,而是權力維穩的幻術。
東亞的宿命,不是天意,而是選擇
東亞的宿命從來不是天注定的,它是人造的。
它是由千年權力結構與情感禁令共同編織的文化牢籠。
當人們放棄關懷、拒絕共情、害怕連結時,
他們以為自己在保護能量,
其實在交出靈魂。
真正的「當下」不是麻木,而是覺察;
真正的幸福不是逃避,而是理解。
當我們不再懼怕別人的痛苦,
才能真正走出東亞的沙化,
讓命運重新變成人能改寫的事。
因果與冷漠:東亞式宿命的幻覺
(Jules Vela,《Dark Disease》理論系列節選)
他們相信天塌下來會有高個子頂著,
卻從不願想一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他們相信:若有天發生重大災難,
「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不虧。」
這種思維是一種深層的自我安撫,
也是冷漠的遮羞布——
它讓人免於思考責任,免於感受共通的痛。
他們相信:作惡沒有關係,只要不要被抓到。
於是「沒有被抓到的惡」就被重新命名為「聰明」。
他們甚至相信:
即便污染河流、毒害土地、製造癌症村,
只要之後捐錢建廟、供奉經書、口誦慈悲,
罪孽就能被抵消。
這是一種神奇而恐怖的東亞因果論。
它將權力、貪婪與暴力的現實,
包裹在“業報”與“修行”的語言裡,
讓作惡者得以自我開脫,讓受害者被迫沉默。
他們說服自己:
別人的苦難是他個人的命,與我無關。
他們甚至認為:
當自己有機會讓別人受苦,
那是上天給予的「機會」,
是命運偏袒的「恩典」。
於是暴力變成了機遇,
踐踏變成了天命。
這樣的邏輯,荒謬到極致,
卻又是被歷史反覆馴化過的集體共識。
當你看到佛經裡那句——
「女人之苦,源於修行不夠;唯有修夠,方得轉為男身」——
你會驚覺:
這套邏輯從來沒有真正遠離過我們。
權力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
構成了這片土地真正的信仰體系。
我並不想說,他們的認知配得上他們的苦難。
在那片土地上,也有無數善良的人——
那些依然能感受到他人痛楚、
依然願意守護柔軟與誠實的人。
但正是這些人,
在東亞式冷漠的結構中,
往往無法活得好、活得久,
甚至被淘汰,被邊緣,被視為“愚蠢”。
我想探討的,是這個殘酷的現象——
為什麼像于朦朧那樣真誠的人,
在這個體系裡「不配活下去」;
而那些順從、冷漠、會轉移責任的人,
卻被稱作「聰明」與「懂事」。
這不是宿命。
這是文化選擇出的結果——
一種將冷漠包裝為智慧、
將逃避包裝為「專注當下」、
將共犯包裝為「順應因果」的文化幻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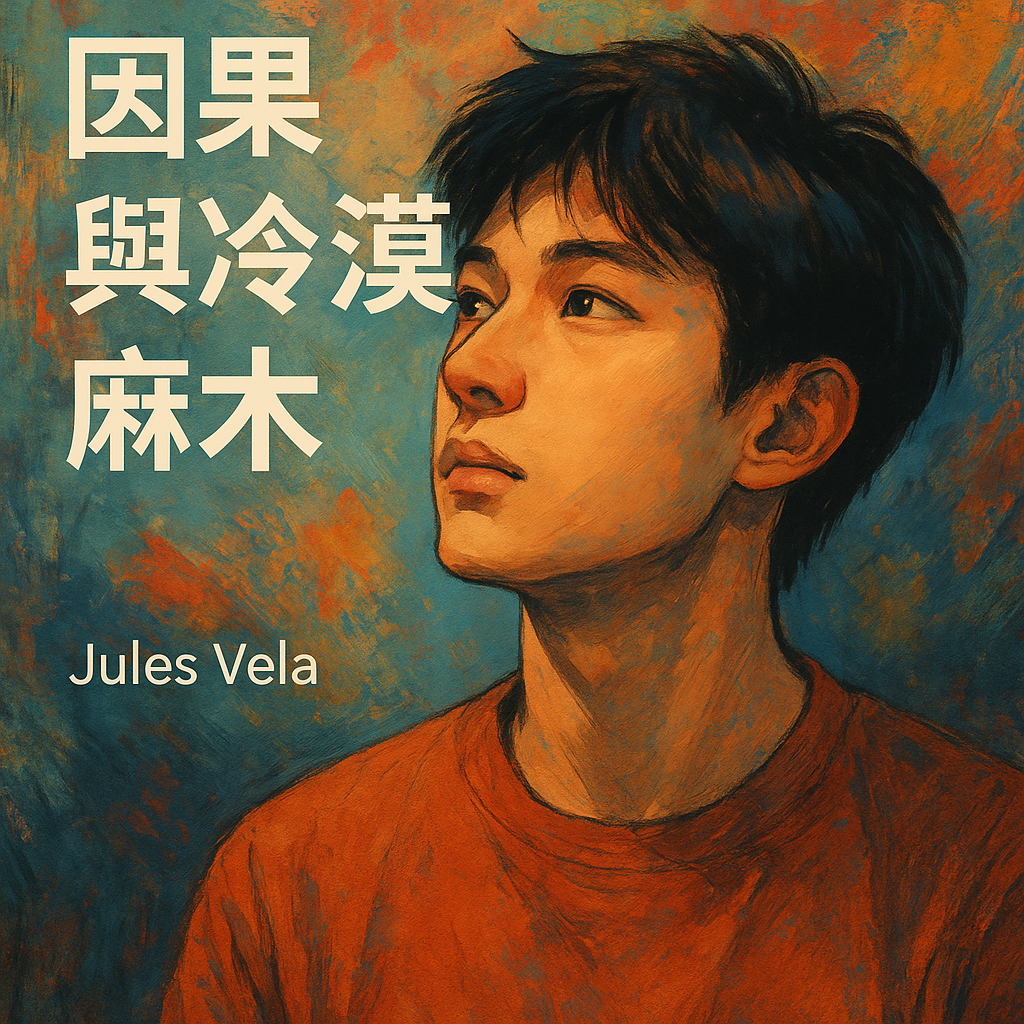
© 2025 Jules Vel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為《Dark Disease》理論系列概念節選,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引用或用於二次創作。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or derivative us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